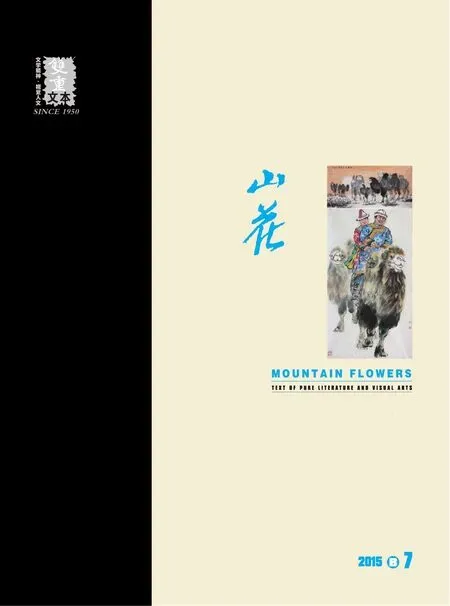鸠鸟啊鸠鸟
贾玉普
老拉祜队长问汤敏是否喜欢鸠鸟时眼里闪过一束奇异的光。汤敏感觉那束光扎人,扎心,里面含有金属一般沉甸甸的芒。汤敏说他喜欢鸠鸟。老拉祜队长就笑了,伸出拉过满弓的手拍着汤敏的肩:喜欢,明早就给你送过来吧。
第二天一早,汤敏洗漱完,收拾好教案,正往学校走,只见老拉祜队长的女儿背着书包从坎上下来。阳光洒在她银光闪烁的头饰上,像一片片霜花,吹一口哈气,那脆弱的花瓣就会被立刻融化。
早到校的几个学生远远见了她,雀跃着从教室里迎出来,围住老拉祜队长的女儿:鸠鸟姐!鸠鸟姐!
汤敏这才醒悟:鸠鸟原来不是鸟,而是老拉祜队长的女儿。
用牛圈改建的学校,牛粪里掺着灰土,一捧一捧摔到蘖条栅栏上,开始,牛粪的氨气味儿还有些刺鼻,没过几天,太阳从外边斜着伸进来,像是在用一盆温开水清洗一件灰被里儿,一遍一遍洗过,洋灰色的面料开始斑白。汤敏看着灰墙上的裂口上黏连的草秸,感觉心里有个纽绊似的结怎么也打不开。改建学校那天,老拉祜队长带领猎户们高卷着裤腿,赤着脚生生地把牛粪和灰土搅拌在一起,直到现在,汤敏还感觉牛粪里那些没消化的秸秆正哽咽在他的肠胃里呢。
青龙寨的牛被撵到山上去了。早晨,老拉祜队长打开圈门,喊了句:解放了!十几头牛就像解放大军进城似地从栅栏里跑出来。汤敏站在牛栏边,眼看着牛群撒着欢儿蹽出寨子,直奔千年茶园的方向。心想,若不是自己横下心来要求到这祖国最西南的怒江北岸来支教,青龙寨的牛哪里会这么快就获得解放和自由?想着想着,心里就涌出一句诗来:支教∕支教∕先品尝一下牛粪的味道∕黄色的面包∕金色的歌谣……
那天,汤敏跟在老拉祜队长身后,顺着一条枯藤似的山路一步步地“登天”。老拉祜队长拄着棍子在前,米和盐巴口袋驮在肩上,像两块飘动的云彩。老拉祜队长见汤敏已被远远地丢在山下,就背靠一棵茶树,把两眼眯成一条线,低下头戏谑地看着他。
汤敏斜挎着书包,后背上的帆布书包带儿浸了汗水,攀崖时书包经常从后面滑到胸前,在背上打出一条水印出来。汤敏感觉背上正有一条皮带在碾,碾着碾着,齿轮卡住不动了,水打的辙印裸露着,上面爬出几只毛毛虫,痒得很。
汤敏成了风筝的尾巴,那个鼓囊囊的书包成了尾巴上的穗头,上下翻飞,等接近了老拉祜,再抬头看看天,似乎爬上树梢,就能随手抓住一块云彩。再回过头,嘿,刚才还狂怒不止的江水,这会儿已经蜷伏成一条细细的青蛇,正胆怯地往草丛里躲闪呢。
青龙寨用最传统的方式欢迎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寨支教的秀才。
刚进山寨,老拉祜队长就扯着嗓子喊开了:都好了吗?到了!
就见村口站了一排男人,把枪举到天上:砰!砰!砰!一连二十响。
老拉祜转过头:这是二十响,等你哪一天给我的青龙寨教出一个皇帝来,我就给你放二十一响!
汤敏的腿快挪不动了,经这二十响一震,从迷幻中猛然清醒过来。他紧走几步,跟着老拉祜队长卷入欢迎的人群里。早已等候队伍前头的两个姑娘急忙迎出来,把事先备好的大红花戴到汤敏胸前,全寨的人围上来,像一个卷筒,把那朵红花推在最前面。
汤敏看见,寨门两边的墙垛上共摆了六个羊头,六张羊皮。
老拉祜队长在前面引路,到了寨门,突然停住脚,做了一个谦卑的手势,请。等汤敏走近他,又贴着汤敏的耳朵小声嘀咕了一句:等你教出了皇帝,杀的可不是六只羊,而是六十只。
汤敏看见这阵势,没去想自己能不能给青龙寨教出个皇帝出来,倒感觉自己已经是皇帝了。
在欢迎的宴会上,汤敏几次提出要到学校看看,都被老拉祜用酒碗挡住了。不急,不急。等酒过三巡,汤敏再次提出要去看看学校,老拉祜没有再用酒碗去挡,而是把手直接指到窗外,看吧,就在那里。汤敏顺着老拉祜队长指的方向,看见青石街下有一个牛圈,里面圈着一群牛。
那里就是,老拉祜说。
牛圈?汤敏的酒醒了一半。
老拉祜一仰脖把碗里的酒干掉,朗朗地笑起来,明天,我就把它变成学校。
用老拉祜队长的说法,青龙寨小学第一批学生是用牛换下山的。第一天上课,汤敏说同学们好,下面的同学坐在板凳上,你瞅瞅我看看,谁都弄不明白“同学们好”是咋回事。汤敏没遇到过这阵势,汗珠顺着耳腮滚下来。他抬高了声音:同学们好!这一喊,同学们不再交头接耳了,都齐刷刷地将头转向了汤敏,汤敏看着下面的十八颗脑袋,想起放出去的那十八头牛,才意识到眼前这十八个脑袋根本不是人脑,而是十八颗牛脑。
汤敏感觉到问题的严重,心想,准备了一个假期的课是白费力了,孩子们得从牙牙学语开始,而他得一个音准一个音准地教他们。
同学们,老师问你们好时你们要回答:老——师——好!下面,咱再来一次:同学们好。
同学们回答:老——老——师——师——好——好。
汤敏就像无意间闯进了麦田旁边的池塘,惊得青蛙扑通扑通地直往水里跳。
一个星期下来,汤敏站在教室前头再清点人数,空荡荡的教室里只剩下五个脑袋了。他们呢?都回去了。
回去了?回哪儿去了?
回山上去了,他们说念书没意思,连鸟都不能打。
汤敏望着后山,忽然意识到自己简单地把座位上的这些脑袋当做牛脑是错误的,现在,他们又都变成了鸟,飞走了。
汤敏找到老拉祜队长,说明了情况,老拉祜想了想,说,好办。
老拉祜只说了好办,却没说怎么办,就朝自己的屋子里走去。汤敏只好跟在后面,耷拉着脑袋,心想,那十三颗脑袋,若是在山上看见他现在的样子,会不会把他当成牛脑呢?
老拉祜队长从屋子里抱出一大团网来。
汤敏问,渔网?
老拉祜笑了,不是渔网,是鸟网。你带着他们去网鸟,我保证不出三天,就能把他们全都网回来。
汤敏接过网,忧心忡忡地走回教室。
走,咱们网鸟去!
同学们一听要去网鸟,乐得恨不得把书包扔到天上,雀跃欢呼着。
从教室里冲出来的学生立刻变成了五只野猴儿,彰显着各自不同的本领,顺着汤敏还没来得及走过的山路进了茶园。
汤老师,快呀!
啾——啾——快呀快呀汤老师!鸠鸟都叫了!
等汤敏赶到茶园,学生们已经把网在两棵茶树间撑了起来。从远处看,就像一张大蜘蛛网,就等着鸟儿蜻蜓似的一只只地飞过来,黏上去。
汤敏第一次走进这哀牢山上的千年茶园,眼前这一株株千年老树,经过时间和风雨的打磨,要是不通过枝丫上面的叶片细细甄别,根本分辨不出那苍老的树干是木雕还是石刻。许多茶树将遒劲的主干从泥土里抽出,身后朝两边分开,横出一步远的“马步”再度扎入泥土,上面的枝丫垂向天空,像一根根竖琴的琴弦。
同学们告诉他,这些茶树还不是最老的,这哀牢山,最老的茶树有2700岁。
2700岁,差不多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半个文明史啊!在这哀牢山上,一棵棵老茶树翘首东望,经过战争倾轧过的华夏文明被融进一片片茶叶里,随着阵阵秋风,潸然飘落。
怎么才能证明那棵老茶树有2700岁?汤敏问。
到树顶上,数数最顶尖的那根枝丫有多少片茶叶,有1片就是100岁。那颗最老的老茶树一共有27片呢?
汤敏望着这片古老的茶林,再看看身边这五个灵动的脑袋,这一刻,他不再把他们想象成什么牛头,什么飞鸟……站在他面前的一个个滚动着的黑眼睛像一串串跌落的露珠,落在一片片茶叶上,给这古老的茶林输送着精神气的生命汁液。汤敏突然在心里燃烧出一股热情,他对同学们说,我教你们唱支歌,好吧?
好啊,好啊。同学们再次雀跃着。
咱就唱那棵茶树小的时候,咱的祖先唱过的一支歌吧。
同学们安静下来,各自选了一块石头坐好。
汤敏清了清嗓子: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同学们齐声学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歌声穿过茶园,在古老的哀牢山上化作一阵阵细雨,划破了天上的云彩。
汤敏教完了歌,问孩子们,那棵最老的茶树在什么地方。同学们的神情立刻紧张起来,互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其中一个站起来,胆怯地指了指山上说,在山后面。
汤敏看看山顶,从怒江北岸的山口到青龙寨,再到这千年茶园,一直是朝着天的方向走,可一直没有走到山顶,他想,若是到了山顶,说不定就能抓到一块云彩。
从这儿翻山过去,就能看见那棵最老的茶树?
能!那名男生干脆地回答。
能吗?汤敏问另外三名女生。
三个女生惊慌地低下头。
她们不敢去!
怎么不敢去?
女人只有被男人休了才去伺候那棵老茶树,在哀牢山上,哪个女人要是不会伺候男人,就得去伺候茶树,她们不去,是等着嫁男人伺候男人呗。
这是真的?汤敏问。
女生们依偎在一起,谁都不敢多说一句话。
汤敏说,那好吧,我们今天谁都不去了,咱还唱老祖宗教的歌。
汤敏看着已经触摸到了天的哀牢山的山顶,一边起头: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歌声把怒江水引上了山,在哀牢山的林间穿梭爬行,那些逃学的孩子跟随大人一起守在林中,听到歌声,心里长了草,他们把脑袋从林中探出来,侧着头,伸出耳朵仔细地听,心想,这个姓汤的老师真偏心眼儿,他们在校的时候怎么不教他们网鸟?还唱这么好听的歌?
他们悄悄来到老茶园,看到茶园里的那张鸟网,心中就结满了疙瘩。就像发现了一只新猎物,却远在射程之外。现在,他们只能一点点地试探着接近茶园。
第二天到茶园网鸟,汤敏惊奇地发现,学生人数已经由5人变成了8人,到了第四天,18名学生们居然全部回来了,汤敏在心里暗暗佩服老拉祜队长——这哀牢山上的主人,不仅知道把一张弓拉到什么程度能命中猎物,而且还知道把一支箭射出多远才能完整地收回来。
汤敏把歌词写在石板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这时,一只鹰一样的大鸟从山顶的方向飞过来,同学们一齐惊呼:鸠鸟!鸠鸟!
同学们的惊叫声还没完全停下来,那只大鸟已经扑到网上,将鸟网顶成一个尖尖的草帽,又在草帽顶尖的地方顶破一个洞,飞了出去!
那只大鸟朝着怒江南岸飞去,汤敏握着粉笔的手用力碾着,直到那半截粉笔在手指间碾成碎末,一点点落到地上。
老师,你喜欢鸠鸟?一个同学问。
喜欢!汤敏说。
噢!噢!老师喜欢鸠鸟啰!同学们齐声欢呼。
在回去的路上,夕阳西下,汤敏看到山脚下的怒江泛起的泡沫,像一团团火苗。几千年前,倘若他的祖先走在这美丽的哀牢山上,看见落在河岸边的鸠鸟后是否会想到“淑女”,从而“碾转反侧”呢?他想象雎鸠是一种鹰一样的大鸟,像一个激情似火的女人,动人心魄。汤敏进入了一种白热化的猜想之中,几个同学在身后窃窃私语,他竟全无察觉。
第二天一早,几个家长过来,询问那只鸠鸟的事。
那只鸟真的顶破了网?
那只鸟真的是鸠鸟?
他们甚至把鸟网打开,仔细检查中间被顶破的洞,从上面捡起一片羽毛,确认顶破鸟网的果真是一只鸠鸟,面露惧色,一齐走出院子,面向山顶,跪下来,默默地祷告着。
汤敏来到老拉祜队长家,告诉鸟网被鸠鸟顶破的事,老队长看看鸟网,沉思了一会儿。没事,都是老黄历了。别管他。
经过老拉祜队长这样一说,汤敏更觉得自己咽下去的是一块石头,消化不了,又不能把它吐出去。
你喜欢鸠鸟?老拉祜队长问。
喜欢。汤敏回答。
真心喜欢?老拉祜的眼里闪过金属一样沉甸甸的光芒。
真心。汤敏再答。
老拉祜队长就笑了:明早,我给你送过去。
真的?汤敏问。
还能骗你?老拉祜队长说。
汤敏兴致勃勃地从老拉祜家里出来,一路哼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汤敏想,在这古老的哀牢山上,老拉祜甚至比这座山还要古老,他说把鸠鸟送过来就一定会送到,问题是他该做怎样一个笼子才能养住鸠鸟。
清晨,汤敏听见同学们喊老拉祜队长女儿鸠鸟,心里犯疑。他走进教室,看见老拉祜队长的女儿坐在教室后面,心里烧起一股莫名的火。现在,他还不能确信,老拉祜答应送过来的鸠鸟是不是鸟。他拿出粉笔,把头几天写在石头上的歌词抄写到黑板上,按事先备好的课向同学们讲解其含义。讲到“求之不得,辗转反侧”时,一个男生直接站起来:老师,这句我知道,就是翻过去翻过来睡不着觉的意思。这个人也太笨了,喜欢就说喜欢,干嘛睡不着觉啊。
男同学话音刚落,同学们全都回过头去,把目光投向了老拉祜队长的女儿。老拉祜的女儿脸红了,急忙低下了头。
同学们都笑了。
放学后,鸠鸟没有回家,而是直接进了汤敏的宿舍,把汤敏一个星期积攒的脏衣服取出来,抱到山腰的浅湾里清洗干净,一件件晾晒到栅栏上,再淘好米,生起了火……一缕缕炊烟从汤敏宿舍升起来,像一个单绳的秋千,将汤敏的宿舍吊在天上。从今天开始,老拉祜的女儿和她的汤老师将沿着这根不断匍匐的藤一起朝着比这哀牢山的山顶还要高的地方不停地攀爬。至于爬到哪里,爬上去能看到些什么,她不知道,她也不去想,因为她知道,即便去想,那上面的事情也想象不出。眼下,她只需要紧紧地跟在她的汤老师身后,寸步不离地伺候他,给他洗衣,给他做饭,给他洗脚,给他捶背……总之,只要是她的汤老师需要的,她都会条理清晰地一件件把它做好。现在,她已经做好了饭菜,装进竹筒,只等着她的汤老师回来打开……
汤敏补完课,径直往回走。前面的几个男生磨磨蹭蹭的,好像在故意等着他。
四毛,你们磨蹭什么呢?汤敏冲着那个叫四毛的学生喊。
汤老师,俺们背诵你教的那首歌呢: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汤老师,你今晚会不会辗转反侧?
去去去!快些回家去,明天还去网鸟呢。
还网啊?再遇到鸠鸟怎么办啊?
同学们说完,灰鼠似地溜掉了。
汤敏看着学生消失的身影,心里漾起一层层的波浪,他隐隐约约感觉到被那只鸠鸟顶破的鸟网一定漏掉了什么,只是不方便开口而已。这就是做老师的悲哀,碰到不懂的问题一定要装作很懂的样子……不过,老拉祜队长一定能帮他解围,把那张网漏掉的东西都找回来。只是,汤敏不知道那张网具体漏掉了什么,就无法知道老拉祜队长具体补充了什么。就像一个走夜路的盲人,虽然无法看清这哀牢山,无法识别那些老茶树,无法看清茫茫的月色,但是,他却一定能感受到它们的存在。
刚上山那天,跑在前边给他带花的就是老拉祜的女儿。她一边往汤敏的脖子上绑红绸子,一边小声问:累吗?汤敏说不累,一边歪斜着脸,躲闪着她头饰上的刺。汤敏注意到,老拉祜的女儿扎人的不仅是头饰上的刺,还有她藏在睫毛下的眼神。昨天,老拉祜问他喜不喜欢鸠鸟时眼里闪烁着的光芒突然让他明白,这种质朴的情愫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拉祜人一直把他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直接、热烈、没有任何扭曲和粉饰。它是一个省略符号,什么文字都没有,却表达着千言万语。
汤敏看到宿舍栅栏上的衣服,心里一惊,进了院,打开房门,见到老拉祜女儿坐在自己的卧室里,不禁问道,你怎么不回家?
老拉祜女儿迎上来,接过汤敏手里的教案,问汤敏:饿了吧?
汤敏望着灶台上已经装好的竹筒饭,心突突地提了上来,他知道拉祜人的习俗,姑娘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才肯让男人吃自己的竹筒饭……
这一切太突然了,汤敏感觉自己的头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嗡地一声,大脑里面一片空白。
鸠鸟,你怎么不回家?
回——家?这不是——家吗?
这是——家?
老拉祜女儿让汤敏在凳子上坐下,到灶台上取来竹筒饭,打开,里面冒出热腾腾的米香、鸭蛋香和腊肉的香味。
汤敏觉得自己的头又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眼前除了一片火光一样的麦芒什么也看不到了,就像进入了一种梦境,魇住了。
怎么不能?那团火突然被风吹了一下。你不是对我爸说,你喜欢鸠鸟吗?姑娘问。
鸠鸟?其实是——一种鸟。汤敏说。
鸠鸟是——鸟?姑娘问。
其实……
什么其实?鸠鸟就是一种鸟!
老拉祜的女儿瞪大了一双眼睛,那团纯净的火突然被一阵大风吹得剧烈地抖动了几下,挣扎着,熄灭了。她狠狠地踢了那个竹筒一脚,从上面跨了过去,跑出了门。那个冒着热气的竹筒在汤敏眼前飞起来,再重重地落到地上,香喷喷的气浪一瞬间化作一缕缕青烟,顺着窗户分散到空气里,等汤敏缓过神儿来,追到门外,莽莽哀牢山上除了一片灰蒙蒙的夜色几乎什么都看不清楚。
毕业典礼那天,汤敏用自己的方式一个人跟母校做了告别。他没去参加全班师生的“最后晚餐”,偷偷溜回寝室,把早已捆绑好的行李背到肩上,默默地在心里朗诵着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尽管汤敏在学院社团活动中多次诋毁过徐的诗,说《再别康桥》里浓缩着太深的太监哲学,说一个男人若是为了一个女人不能自拔到如此程度而无所作为,不是无能就是弱智,没有别的解释。可是,在他跟母校告别——或者说跟秦娟告别时竟然也是如此娇情,虚弱无力这么多年,汤敏始终在试图寻找一个核心的点,他把这个点归结为人类精神空间的心脏部位,为此,在历史课堂上,他向那个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历史老师发难:若不是鸦片的吸入,八国联军进北京烧杀抢掠,中国会不会有这样强烈的民族自救意识?大清朝的辫子会不会流传到现在甚至更远?那个老师把高倍光圈眼镜用手指从鼻梁上往上抬了半指高,两只黑眼球在镜架下寻找了半天才看清窗边的汤敏。
这个问题不是这节课要解决的内容。高倍眼镜说。
汤敏坐下了。那一刻,汤敏似乎感觉到了那个课堂的心脏部位,他正在从教室的各个角度,朝着他的座位聚拢。可是不久,汤敏就感觉问题远不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下了课,同学们的冷嘲热讽像海啸一般把他重重地抛向海滩,说他哗众取宠,鸡蛋里边挑骨头,隔岸观火又做不到心平气和。汤敏苦笑着,他给自己最终定位到了边缘,而且确认自己就是边缘,是这哀牢山上秋天的一片茶叶,永远不会被人浸到水里,却又不能回归成一片普通的落叶。
汤敏走到楼道拐弯处碰到了秦娟,秦娟当时横在楼梯口,眼睛里喷射着轻蔑的怒火:我就知道,你会这样狼狈地逃走。
汤敏想,假如秦娟在那一刻把眼睛里的轻蔑和怒气全部转化为泪水,那么,他今晚也许不会把自己流放到这祖国西南边陲的山腰上。
你以为我是在这里等你是吗?秦娟问。
有什么区别吗?汤敏问。
你以为我会拦着你?秦娟说。
汤敏苦笑了一下,从秦娟身边擦了过去,那一刻,他真的感到自己很狼狈。
……
老拉祜队长家还亮着灯,汤敏顺着山路上去,在接近老拉祜家的院子时,听到老拉祜女人哭泣着嘟哝:不是说好的吗?既然喜欢,怎么不吃鸠的竹筒饭?昨晚,鸠问我,汤老师会喜欢她做的竹筒饭吗?我还告诉她,汤老师亲口对你爹说,他喜欢鸠鸟,鸠鸟的呀……
接下来是老拉祜的声音:都说这读书人弯弯肠子多,这回,咱是见识了。
汤敏迈进院子的半只脚缩回来了,他不知道该不该在这个时候进老拉祜的家,在这个边缘地带的哀牢山上,六只羊头落地,二十响礼炮响起的时候,他曾一度感觉到了心脏的存在,甚至感受到人类发展最原始、最本真的源头。他甚至庆幸给自己的边缘定位,若不是自觉的边缘意识,哪里会有当下的中心感受?可是,为什么刚踏进门槛,就被老拉祜一脚给踢了出来?汤敏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他不知道老拉祜说的鸠鸟不是鸟,他更不知道老拉祜送给他的鸠鸟不是鸟,他只是稍稍坚持了一下,鸠鸟就把竹筒饭踢翻了,连带着他一起被踢出了边线。现在,汤敏感觉自己多年固守的边缘已经彻底失去了,他望着苍茫的哀牢山,月光下的怒江水像一只半睁着的蛇眼,发现了猎物却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汤敏感觉身后有什么东西轻轻推了他一下,是风,是雾,还是朦胧的月色?他顺着那轻轻柔柔的推力慢慢往山顶的方向移动。顺着白天网鸟的路线,一股股茶香飘过,汤敏知道这些爽心清目的茶香并不是出自那些千年的茶树,而是刚刚从这里经过的背影中洒下的。汤敏加快了脚步,路过老茶园时他稍稍逗留了一会儿,听到身后似乎有人轻轻的呼吸,仔细看去,只见一个人影一闪,躲到茶树后面去了。汤敏心想,谁呢?这么晚了还跟着,就像一个人躲闪着另一个人的鞭子,在沙漠里拼命地跑,跑啊跑啊,几乎浑身没一点力气了,躲到一个沙丘后面,抬头一看,那个手持皮鞭的人早已等候在那里,一脸的冷笑。
汤敏前面只剩下一条路了,那就是通向山顶的路。月光下,那条路更像一条井绳,汤敏只要握住它,攀上去,就不仅能触摸到天,而且还能看见那棵2700岁的茶树。汤敏想,他不是去找那棵老茶精决斗的,而是去找它商议的,看看能否将他自己变为一棵茶树,将鸠鸟赎回来。
那条小路越是接近哀牢山的顶部,两边的树木越发稀少,等汤敏攀上最后一块岩石,一股凉丝丝的风吹过来,汤敏发现,自己已经攀上了哀牢山的极顶。汤敏感觉自己像一片茶叶,贴着哀牢山极顶的这块石头,经受着四面的风,他低下头,只见绝壁下的怒江水,从哀牢山西北角拐了一个180°的弯又绕了回来,将厚厚的哀牢山一分为二,刀切西瓜似地切出了一个大峡谷。江水滔滔,清洗着天,清洗着地,清洗着茫茫的月色。汤敏仔细搜寻着峡谷两岸,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棵老茶精。
汤敏从岩石上站起来,感觉到阵阵秋风撕扯着衣襟,忽然意识到青龙寨的女孩为什么一谈起这哀牢山的茶精就惊慌失措的真正原因。那棵2700岁的老茶树也许在山腰,也许在山下,也许在对岸,无论它在哪里,要想接近它都必须经过这样一条路……想到这儿,汤敏打了一个寒战。一股无法抗拒的浊流涌进胸膛,他使出全身力气,冲着怒江大峡谷喊:鸠——鸟——
对岸,哀牢山的另一半频繁传来回音:
鸠——鸟——
鸠——鸟——
等一切平静下来,汤敏突然听到身后一声熟悉的呼唤:汤老师。
那声音很轻,很细,很柔软。汤敏回过头,只见一个银光闪烁的头饰从岩石下面露了出来,汤敏吃了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