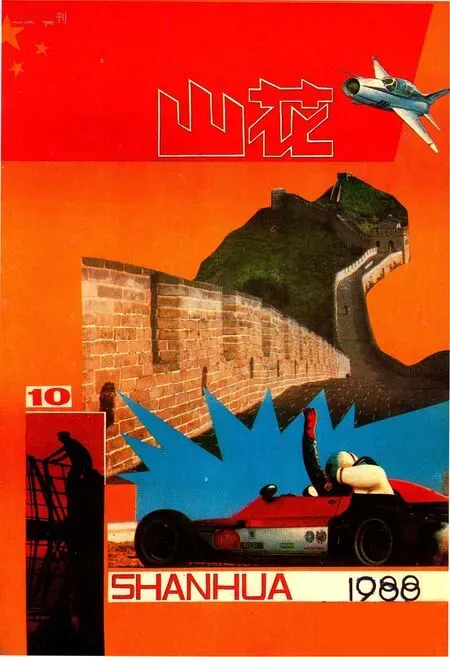阳台
苏兰朵
阳台
苏兰朵
沈鱼经常问自己,到底需不需要一个伴侣?
当然在性方面是需要的,但是其他时候呢?他总是禁不住要在内心里进行比较,现在的生活和以前的。那时候性的要求比现在强烈,他愿意为此交换一部分自由,甚至大部分。
他有过两任同居女友,但是她们最后都以不同的理由离开了他,他知道那些理由是不足信的,因为他心里很清楚,自己并不渴望她们憧憬的那种家庭生活。他也完全知道,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和魅力留住她们,但还是装作一副可怜的样子把她们送走了。在最后的时刻,她们都流露出了并不真想走的期待眼神,但是他假装没看懂,并且在这关键的时刻,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留恋:如果她们愿意回来睡觉,他随时欢迎。于是,她们一跺脚,彻底消失了。
此后,他小心翼翼地过上了另一种生活。每当清晨送走一个女孩,他的满足感常常维持不过两天,甚至在当天晚上,就觉得要活不下去了。他克制着自己,不给她们打电话,甚至为此根本不问她们的电话。一个夜晚,他深知这是自己能够付出的,他宁可对自己残忍一些,也不愿因为软弱而放弃自由,是的,有一个更美好的说法叫责任。他觉得那很崇高。
沈鱼住在一座高层公寓里。公寓的外墙是那种素淡的米色,所有的窗口都一样。有一个阳台,小小的,大约一平方米的样子。只能晒几件衣服,或者,让受气的丈夫在这里吸根烟。沈鱼喜欢站在这里吸烟,面对一座城市吸烟。是的,面对一座城市和面对一个盆景吸烟,感觉是不一样的。
有两三年,准确地说,是两年零八个月,他是舒服的。那段日子,他拥有一个固定的情人,一个大自己七岁的有夫之妇,老公在国外的留守女士。你知道对于一个27岁的单身小伙子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幸福?沈鱼至今都在心里无限感激那个女人,不仅仅因为她给了自己高质量的性爱。他相信,不是每个男人在这个年龄都会有这种幸运的。如果她没有在他们上床之后两年零八个月出国,沈鱼知道这是必然的,他们可能还会在一起,并且可能会一直在一起。那时候,沈鱼觉得自己需要的就是那种生活:一个让自己没有负担的女人;年轻,懒散;被女孩子们的目光追随;还有飞来飞去的演出造成的与现实世界的疏离感。他觉得自己就像一篇小说中的人物,凭空出现,是这个庸俗世界的旁观者,拥有别人无法打扰的生活。
但是一切都在遇到苏非之后改变了。
他遇到过很多女人,他小心地绕开女孩。但是,他竟然没有绕开苏非,直到今天,他也不知道这是幸还是不幸。当他觉得摆脱这个女孩有点困难的同时,意识到自己对她可能也很重要,顺着这条路想下去让他觉得有点温暖,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受,虽然这种感受让他觉得很危险。
那天,当他百无聊赖地站在候机厅的吸烟室吸烟的时候,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里的声音似曾相识,当她报出苏非的名字时,他稍微有点尴尬,旋即显得兴致勃勃,他还没有那么健忘。网络上的精神恋爱是美妙的,下线之后的唯一一次性爱也是完美的。在海边的那个奇妙的夜晚,令他回味。他觉得她的语气有点犹疑,就尽量满不在乎地问,你是不是要结婚了?请我参加婚礼吗?或者做个伴郎什么的,哈……不是!他刚露出的笑被迅速打断了,接着,他听到一种很陌生的确定的语气,我不结婚了,我喜欢你!接下来,他什么也听不到了,自然他也什么都不必说。
现在他想,如果那天告诉她自己正在去外地的途中,要很久才回来,也许一切就都不同了吧!起码她不会一个人决绝地跑到这个城市来找他,烈女私奔一般。当然,他还有第二次机会,拒绝她进自己的家,没有手机遥控她找到他的单元门,并且告诉她钥匙藏匿的地方。他并非不清楚她一旦进来了,就意味着一种转折,因为她的进入和别人不同,别人的进入是为了迅速离开。他不关心这个转折点对于她的意义,女人随时随地都会为生活总结出一个意义,他关心他自己的,他独立的世界可能不复存在。但也许……他想,或许我现在可以再尝试一下两个人的生活来验证我是否真的需要一个伴侣?
事实证明,他过于乐观。
苏非离开的时间是进入这个房间的第七天。那个早晨,她站在门廊与沈鱼互相亲了无数次对方的面颊、嘴、舌头、额头并把背着乐器箱的沈鱼送走以后,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吸烟,忽然间觉得这一切很荒唐。
她与这个房间格格不入,它依然是沈鱼的巢,没有自己丝毫的痕迹。沈鱼不喜欢她打扫房间,他认为那是无意义的劳动,他觉得他们,面对面干坐着也比打扫房间有意义。他的厨房煤气管道没有接灶具,要一次一次叫外卖,如果太晚了,就只能吃方便面,这让苏非没有归宿感。最重要的,她看不出沈鱼的态度。
这个公寓有多少层?三十二?四十八?她不知道,也不关心。她只摁了一下写着二十五的小圆按扭,电梯就把她带到了她要来的地方。二十五层,这已经足够高了。她有点恐高,极少从窗口往外看,更从未到过那个没有封闭的小小阳台。窗户外面,是迷茫的市景。近处是玩具一般的人和车,远处是毫无生机的楼房。
他们都不关心外面的世界。他们关心的是身体。身体的贪婪、兴奋和满足是他们无法抑制也不想抑制的,她能感觉到沈鱼是喜欢自己的。他们都避开了一个敏感的话题,就是苏非来这里的来龙和去脉。沈鱼的回避是不动声色的,当然他有足够的理由回避,因为苏非是不速之客,他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同时,他也没有流露出对苏非有丝毫的反感,他很享受与苏非在一起的时刻,经常静静地看着苏非吸烟,面露微笑。苏非觉得他们不像第二次见面,而像在一起交往了很长时间的恋人,这感觉让苏非舒服也不舒服。舒服的是,他对自己一见如故的接纳,说明他理解自己的行为,没有为此大惊小怪;不舒服的是,他没有为自己的突然出现有丝毫特别的表示,他甚至没有想到为自己去买一支牙刷,这几天,苏非用的都是自己带来的一次性的牙刷,刷毛已经严重卷曲。
他依然困了就睡,要睡得足够才睁开眼睛,全然不考虑苏非的感受,这说明他也并不感激自己的行为,那完全是苏非自己的事。苏非不知道该拿自己当主人还是当客人。也许当主人自己会舒服一点,但是沈鱼什么承诺也没有,这是沈鱼的家,自己怎么好自做主张呢?除了电话里说过“我不结婚了,我喜欢你!”之外,苏非再没对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吐露过任何设想。在网络上恩爱那会儿,自然也只是享受当时,从不言将来。来到沈鱼的家,她才意识到自尊的问题。这七天,这个问题虽然被身体掩盖了,但还是存在的。此刻,当沈鱼离开这个房间,它必然浮现出来。苏非不是个矫情的女人,她也不认为自己的举动是轻率的,但是现在的感觉是,她身处这个房间,却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与这里的一切都扯不上关系。站在洗手间里,她端详着镜中的这个女人,眼睛有点浮肿,皮肤苍白,表情有些呆滞。不知为什么,她联想到一些社会新闻中报道的被男人囚禁在地道多年的女人,这个联想让她很吃惊。她觉得应该尽快离开这个房间。
事实上,在她踏进这个房间的一瞬间,就开始怀疑自己了。
她没有想到这个长头发、白衬衫和牛仔裤都纤尘不染,甚至没有脚臭的男人的家是这个样子。暗,灯有的坏掉了,有的不明亮。厅里的灯勉强可以照明。到处是衣服、影碟、书(主要包括两类:小说和漫画)、琴谱、烟灰、大大小小薄厚不一的塑料袋子,有的来自超市,有的来自服装专卖店,有的来路不明。窗帘是咖啡色的,遮住了不大的窗口和阳光,床单和被子也是咖啡色的,看不出来清洁程度,地板明显是脏了,让她产生强烈的清洗欲望。
她感觉有点复杂,以这种方式进入他的家出乎她的预料。她想象着,他会去火车站接她,站在出站口,穿着浅色的衬衫,随意的牛仔裤,迎着风,很帅地吸烟。看到她的一刹那,露出天使般的笑容,那打动她心的美好笑容……幸好他不在,苏非想,这样也好,有机会坐下来慢慢捋一捋思绪。
首先,她有点失望,这和她的想象有差距,尤其是在作了一个重大决定之后。这个昏暗的房间,就是她的新生活吗?和海边的那个房间比起来……当然,这两个房间代表了两个不同的男人,如果单纯从房间的舒适度来考虑,似乎从这里奔向那里更有说服力,虽然他们是从那里开头的,在那张即将使用的婚床上。她完全可以不到这里来,婚前的艳遇未尝不是一个美妙的秘密,而且是神不知鬼不觉的网恋。她也不是一个冲动的人,当然更不是没见过男人。那个准备结婚的男人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丈夫,喜欢拖地板,也喜欢烹饪,有待遇优厚的稳定工作。他们的恋爱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她觉得自己很幸运,嫁给一个该嫁的人。她知道以后还会遇到喜欢的男人,她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有情人,但是她觉得应该把面前的这个男人抓住。女友们都赞成她的想法。
苏非点燃了一支烟,坐在沙发上,眼前忽然浮现了沈鱼的博客。浅灰的色调,模版的图案是一支燃着的烟,图文雅致、干净。一年前,她鬼使神差地一头撞进去,便被深深吸引。之后是留言,然后移兵到QQ……那感觉与这里形同天壤。她想,现在离开这里或许还来得及,毕竟主人还没回来,房间尚未被自己弄出痕迹,只要站起来,用手把沙发抚平,把洒落的烟灰混在他的烟灰里,然后像影碟机回放一样从这个房间里退出去,一切都可以当作没发生过,包括婚床上的一切,QQ上的一切。这世界上,拥有这种不愿展开的秘密的人太多了,我为什么要例外呢?是啊,为什么?
苏非不愿意承认是身体的意志。面对男人,她觉得可以摆脱身体的控制,因为她曾经成功地离开了一个富有的丧偶的男人,那男人给她的性体验至今令她难忘。她承认,作为一个年近30岁的女人,无法摆脱身体的诱惑。但是单纯的身体,往往控制不了她太久。她想不明白的一件事是,面对沈鱼,那个身体之外的东西究竟是产生于身体之前还是身体之后,或许前后都有吧!而前后又不同。好了,想到这里,苏非明白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她将烟掐灭,站起身来,决定拖地板。
房间里有女人的气息,虽然在打扫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现明显的证据。一根足够长的发丝说明不了问题,因为沈鱼是个长发男人。但是,苏非知道这些女人是存在的,而且长久以来一直存在。自己和沈鱼的开始也能说明这一点。苏非的动作缓慢下来。但是他是个优柔的男人,这优柔当中包含着软弱,苏非相信自己的这个判断,从做爱时他的温柔程度就可以感觉出来。她从来没有遇到过在床上这么温柔细心的男人,你的每个动作,他不光能领会动作本身,而且能够感应到背后的情绪,然后恰到好处地回应,包括在做爱之后长久的爱抚,看不出一点敷衍的痕迹。他的引领是很含蓄的,他让她觉得是她在引领,充分地奔向她想奔向的各个方向,而他就像一个芭蕾舞演员,大部分时间在托举。她第一次体验到,性爱可以很远,不只是身体的远。她不想把这都归于经验,他身上有一种固有的东西,那种东西无法伪装,也无法程式化,但是可以感应得到。苏非相信自己作为女人的直觉,这种东西在男人身上是不常见的,因为它过于敏感、细腻而内容丰富,它也不随意展现,需要遇到对手。它是一个男人的秘密品质,外化出来常常是优柔和软弱,苏非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她知道,这种品质可以让一个女人享用一生,只要她有足够的耐心。他接受了自己进入这个房间,虽然有点迟疑,可已经初步验证了这一点。但是,这种品质也可能使他被各种各样的女人纠缠而不懂得摆脱,受益于自己也同样受益于别人。反正自己已经进来了,苏非环视了一下这个房间,从现在开始,她将是这里唯一的女主人。
事实证明,苏非也过于乐观。
沈鱼是在两天之后回来的。当苏非为他打开门,系着围裙在门口迎接他,他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不是回家,而是到别人家做客。这是一种不祥的预感。进屋之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房间被彻底打扫过,焕然一新,原来触手可及的很多东西突然间都消失了,仿佛从打开的窗口不翼而飞。沈鱼站在地当中,放下乐器箱,给苏非一个莫明其妙的笑容,“我说,这是我的家吗?”苏非判断不出他对这个变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但是她准确地判断出自己喜欢这个男人,从他高大懒散的身躯挤过自己站立的狭小门廊,一丝淡淡的熟悉的烟味从面前飘过,到步入房间,站立和放下乐器箱的姿态,牛仔裤的长度与运动鞋搭配的效果,包括他说这话时的语气和表情。她明白了,自己就是为了这些来的。这瞬间的感受一定支撑了一种表情,这表情像光波一样扩散出去,使她显得很生动。沈鱼成功地被感染了,她看到他的眼睛柔和下来,向前迈了一步,像亲吻孩子一样亲了一下自己的额头,然后他们迅速地抱在一起,越来越有力量。
当沈鱼凭着直觉判断苏非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满足,眼睛里流出如水的柔情之后,他示意这个美妙的女人去客厅帮他把烟拿过来,并且用手爱抚了一下她的小屁股。他一起点燃了两根,递给她一根。他们就安静地吸烟,偶尔有手触摸对方的身体。沈鱼很享受这个时刻,不亚于做爱的进行过程。自从这个女人来之后,他再也没到阳台吸过烟。他觉得这个女人很不一样,她不问一些愚蠢的问题,比如关于打扫房间。在做爱的过程中也没有杂念,不矜持,也不讨好,这份自然让沈鱼觉得舒服。很多年以来,女人是让沈鱼觉得麻烦的事情,如果不是怕得病和担心经济承受力,他宁愿一直叫“鸡”。也许因为知道这次做完了苏非不会马上离开,他有一种莫名的延续感,这种感觉让他心里有一丝暖意,有种在荒山野岭遇到人烟的感觉。这种感觉他在同居的时候常常有,虽然片刻就被对方破坏,却仍然是让他留恋的。只有在那一刻,他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女人完成家的概念。此刻,苏非一直不说话,只是用手交流,沈鱼甚至有点感动,他希望这一刻永远都不被破坏。他没有告诉苏非他的感受,他一直觉得很多话都是不必说出来的,人的表达是一种冒险,有些问题明明没有,是因为话语才产生的。其实人与人的交流有很多种方式,比如,此刻,身体和烟都是一种交流,它的美好效果是语言达不到的;再比如,演出的时候,音乐也是一种交流,在他和人群之间,在他的手指和人们的心灵之间。
他喜欢苏非的沉默。有时候她光着身子,背对着窗口,在逆光中神情若有所思。沈鱼觉得自己不必去触破这些谜团,也许那些都是她自己愿意享用的。事实确实如此,(事实确实如此吗?)当她从自己的世界里回过神来,依然是快乐的。她不像别的女人,作出这副样子的目的是逗引他去询问,然后就势撒起娇来,弄不好还会生气,或者哭,让他无所适从。而如果他不去询问,她们就会觉得无限委屈,也会生气,或者哭。沈鱼不明白,这些女人是被爸爸惯出来的,还是天生就如此?他没兴趣研究这些,这些让他很不快乐。五天,沈鱼觉得过得很快,仿佛只是一天一夜,他和苏非几乎足不出户赖在床上,世界仿佛缩成了一个房间,压迫着他不停地进入她的身体,他没想到自己的身体原来这么棒,简直不知疲倦。如果不是已经签了合约,第五天早上,他真不愿意穿上衣服走出门去。
他站在门口,不舍得离开这个女人,他用不停地亲吻告诉她,希望她待在这里等着,他很快就会回来。
但是苏非没有听到这些。男人有些声音,即使近在咫尺,女人也永远听不到。
外面阳光晴好。苏非调整了一下自己松懈了七天的表情,将门轻轻关上,钥匙放回应该被藏匿的地方。为什么要放在这里?沈鱼的解释是,他的母亲有时会过来送点东西,顺便收拾一下房间。这个答案显然不能说服苏非。她猜想,也许他不在的时候,还会有别人来。而刚来的时候,她却兴奋地认为,这把钥匙,长久以来待在这儿只是为了等她。她那时还觉得,与沈鱼相遇之后,处处都是命中注定的缘分。毅然退了婚约,离开家,来到这里,也是命运安排好的。无法阻挡。
她并不后悔。走出公寓,她回头仰望。伸出指头,一、二、三、四……她想数出第二十五层的那个窗口。她发现这是徒劳的。即便目不转睛地数出了楼层——眼泪都要下来了,她也无法确认横向的那个窗口。巨大体量的公寓,无数个相同的房间,大概只有那个小小的阳台能够区分彼此。有的阳台摆了两盆花,有的阳台晒着衣服,有的阳台放着一把沙滩椅……她从来没有进入那个阳台,因而无法辨认哪一扇窗户后面是她生活了七天的房间。
她真想把那个阳台找出来,仿佛不找出来,就确定不了这七天中的自己。她现在有点后悔,为什么不走进阳台一次?哪怕是站在那里看看外面的日落也好。
现在,她又恢复成一个社会人了,她又听到了令人烦躁的汽车驶过的声音,人们说话的声音,高一声,低一声,似乎在告诉她该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