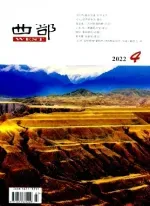愤怒的羔羊
——绝望表妹怒杀丈夫
文/吴垠康
愤怒的羔羊
——绝望表妹怒杀丈夫
文/吴垠康
那时候,我喜欢捎些野果野菌之类往姨妈家跑。表妹来接东西,我们的手在篮子的掩护下,弹簧般碰过,她的脸蛋就红了,然后一甩辫子跑进闺房,留下一地醉人体香。表妹是村里公认的村花,媒婆三番五次来提亲,姨妈好几回都动心了,可表妹就是不点头,直气得姨妈骂人。姨妈老昏头了,表妹心里装着谁怎么就不知道呢。
后来,王村长常往姨妈家跑。村长是村里的土霸王,上面的政策都攥在他手里,松一点,紧一点,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就是两重天。王村长突然屁颠颠地跑姨妈家,打的不是姨妈的主意,而是表妹。当然,这主意也不是替自己打,而是替他的侄子黑毛。
黑毛身材矮,梭子头,老鼠眼,塌鼻梁,他的丑好比表妹的美,都是村中极品。有一次,外乡来的评书先生正手舞足蹈地再现着《水浒传》,被突然挤进里层的黑毛吓了一跳,以为是武大郎没找到西门庆没找到施耐庵,就找评书先生寻仇来了。这么一个丑八怪,别说表妹,姨妈先挡了道。不久,村里把多病的姨夫的低保待遇取消了,表哥生二胎的指标也一直批不了。王村长再从门口过时,姨妈陪着笑脸主动喊他进屋坐坐,说自己没意见,女儿那边再劝劝。
那一夜,姨妈在表妹的闺房里又是鼻涕又是眼泪,表妹噘着嘴,嚷嚷着老死在娘家也不嫁那个黑毛。姨妈又哀求说:“不看僧面看佛面,他叔叔王村长出面了,人家有权有势,我们一个穷苦人家哪里得罪得起啊?”母女俩僵持到公鸡打鸣时,隔壁传来了姨夫一连串痛苦的咳嗽。姨妈说:“你爹的药前几天就断了,村里又催你嫂子去引产,你就答应娘这一回吧,就算养你十八年的心血扯平行不?”表妹不再争辩,喘着粗气伏在床上哭。
就这样,表妹没有成为我的新娘,而是踏上了黑毛的花轿。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村里女人们又多了一个茶余饭后的话题,讨论时还顺带捎上了我。那段时间,我在村子里度日如年,好在城里一次招工机会让我摆脱了这种尴尬。
城里的姑娘多,几场电影下来,我的同事、现在的老婆就架不住了。同时,新婚的甜蜜和家庭的琐碎也让表妹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我的梦乡。闹“非典”那年,姨妈颤巍巍地来城里找我,说乡下孩子都把板蓝根当糖吃,价格涨了好几倍,表妹托我帮她批发点。
再见表妹,她已是两个女儿的母亲。岁月和生活像催熟剂一般,三下五除二就把一个亭亭少女变成了黄脸村妇。最可气的是,黑毛学会了使性子,不再像新婚时那样,又是给她弄好吃的又是抢着倒洗脚水。每次赌博输钱回家,表妹就是他的出气筒。而婆婆盼抱孙子快疯了,进进出出拉着一张马脸,成天指桑骂槐,像谁欠她八辈子债。老娘儿俩你这边一顿打,她那边一通骂,搞得表妹三天两头哭哭啼啼拖着女儿往娘家跑,偏偏表哥也是个脓包,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认命吧。
一开始,表妹当然不想认命,毕竟黑毛是癞蛤蟆吃了天鹅肉。她尝试过武力反抗,而以卵击石的后果是变本加厉的皮肉之痛。也动过离婚念头,但黑毛的叔叔是村长,她担心法官板子乱拍。再说,即使离了,自己逃避掉了,那孩子呢?娘家人呢?她甚至想过以潘金莲的方式报复黑毛,又觉得那样活在世上跟猪狗没什么区别。最后,表妹像一只断了翅膀的天鹅,不得不听命于现实,让自己成了癞蛤蟆的下酒菜。
表妹第一次上我城里的家是在一个黄昏。我拉开门,发现她鼓着个大肚子,一脸的惊恐。表妹求我和妻子容她躲几天,说这是王村长的主意,乡里正在搞计划生育突击检查,风口浪尖的,必须避一避。计划生育是国策,我和妻子都劝她别生了,将来负担不起。表妹开始抽泣,说不生个儿子,这辈子腰板就硬不起来。表妹撩起衣袖,一块伤疤蜘蛛一样爬在上面,那是黑毛用茶杯砸的。表妹还要解胸扣,妻子一把按住了她的手。看着表妹哀求的眼神,我一拳擂在茶几上,把茶杯盖震掉在地。妻子的心也软了,不但答应表妹的请求,还给她壮胆,说黑毛再敢欺负人,就去告他!
表妹言而有信,乡下计划生育浪头刚过,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她包车回乡下去了。随后传来这样的消息,表妹生产时没敢进医院,婆婆在山芋窖内铺好一床破被子,算是产床。由于怀孕期间不敢出来活动,胎位不正,加上营养跟不上,表妹险些丢了小命。可惜送子观音这次还是没有垂怜她,她成了三个千金的母亲。
俗话说屋漏偏遇连阴雨,那位一直关照着表妹家的王村长在换届时落选了。倒了乘凉的大树,在又一轮计划生育突击月里,死活赖在地上的表妹被“请”去做了绝育手术。
在黑毛和婆婆眼里,表妹成了不能下蛋的母鸡。
那天,表妹打来电话,还没说几句,就哽咽起来。不用猜,这又是黑毛打人了。只见握着话筒的妻子气息渐渐变粗,一副义愤填膺的架势,机关枪般骂了一通,并让表妹快去找村干部评理,不相信主持公道的人都死了。
以前,表妹受了再大的委屈,还真没找过村干,这不仅因为家丑不可外扬,还因为黑毛叔叔是村长,找他评理能评出什么天地良心。现在不同了,村里换届,保不准新上任的张村长就是包青天。
张村长坐在老板椅上,点上一支烟,喝了两口茶,不紧不慢地说:“牙齿还咬舌头哩,夫妻好比过家家,灶头翻脸床头和,忍一忍就过去了。”
张村长这样搪塞几回后,表妹就不再去麻烦他了。
江南春来早。柳条已经发泡飞絮,公鸭忙活传宗接代,乡下的正月越来越短暂,没外出打工的开始犁田靶地,整墒浇粪。适逢周末,我和妻子回老家看父母,远远望见一个女人在犁田,妻子同情地说:“估计她家男人是出门打工了,她便就地取材教育女儿要努力读书,要不然大了也要犁田。”说话间,喘着粗气的牯牛被叱到了田这头,女人仰头紧系了一下头巾,我和妻子几乎同时张大了嘴巴,她居然是表妹,表妹居然学会了犁田!
“黑毛干什么去了?”我问。
“唉,别提他了,就知道没日没夜打麻将。”表妹叹了口气。
我和妻子临时决定去教训一下黑毛。
初春的山村,河水淙淙、鸡犬相闻,鳞次栉比的小楼宽敞而考究。在打工经济和惠民政策支撑下,农家的小日子的确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表妹家例外,住的是两间红坯两层楼,大概是无钱装修,已成了烂尾楼。我抬起头,山墙砖缝里几根衰败的茅草在微风中摇曳,摆着小手,仿佛不欢迎我们这些不速之客。
表妹家的大丫上山拾柴火去了,二丫在同几个小朋友过家家,沾着泥巴的小手冻得虾子般通红,怯怯地接过妻子给的巧克力,好奇地把玩着,却不知道怎么吃。
“二丫,去茶馆喊你爸爸回家,说县里伯舅来了。”表妹说。
过了一会,二丫一个人回来了。
“你爸爸呢?”表妹问。
“爸爸不回来,他还要打几圈。”二丫说。
表妹愣在那,像尊木偶,再使劲揉了揉眼眶,才缓过神来,浅笑着招呼我们进屋喝茶。
我问一圈多少钱,表妹说100块。我正要骂黑毛怎么参加那么大的赌博时,突然传来婴儿的哭闹,表妹三脚并作两步冲进房,连声哄着:“三丫别哭三丫别哭……”
三丫就是在我家躲过一段时间的小宝宝,粉嘟嘟的,长得煞是可爱。等表妹把三丫的衣服穿好,黑毛垂头丧气地回来了,看样子这几圈被人宰得不轻。黑毛嬉皮笑脸地解释说:“闲着没事,去茶馆打几圈小牌。”我和妻子也不想闹僵,委婉地说了些责任、担子之类,看他唯唯诺诺的样子,就让许多话烂在了肚子里。我们要起身告辞时,表妹的婆婆怀里抱着东西来了,说:“你们是贵客,饭都不吃,怕沾穷气啊。”老人家在隔壁起火另过,我们来的时候应该就听到了动静,现在专门送些鸡蛋来,这在乡下是打发走人的意思。
第二天晚上,我们回到城里还没落座,电话响了,是父亲打来的,说黑毛又下毒手打表妹,头发扯下好几把。
“昨天黑毛不是答应改过自新吗?”我说。
“你快别提昨天,就是你们昨天去他们家惹的祸。”父亲还警告我少管别人家的事,担心惹火上身。
原来,我们的不期造访被黑毛误解了,认为是表妹请我们去故意跌他面子的。
妻子咽不下这口气,拨通110替表妹报了案。当地派出所出警后,见是夫妻间的打闹,也许是想起了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古训,批评教育黑毛几句后,就鸣金收兵了。
“割麦插窠,割麦插窠……”当布谷鸟们在田间地头吹响节令的号角时,忙碌的午收季节已经拉开了序幕。割麦、脱粒、晒场、翻地、整墒、插窠,山村的五月交织着汗水和收获、播种和疲惫。前后不到个把月时间,一圈弄下来,再壮实的汉子骨头都要散架。表妹像一只落单的孤雁,起早贪黑同农时赛跑,左手一把汗水,右手一把泪水,发誓下辈子做牛做马也不做女人。
表妹在堂屋里排了几箩筐小麦。她早盘算好了,集镇上有几个收购小麦的摊子,先挑一担去,顺便到童装店给女儿们添几件夏衣,剩下的再晒两天,再装进有内膜的蛇皮袋里,堆在猫窝旁,待逢时过节磨些面粉,免得孩子看人家吃麦粑麦面流口水。
那天中午,表妹疲惫地扛着锄头进门时,发现麦子不见了。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一口气冲到茶馆,也不知是哪来的力气,一下子掀翻了黑毛正打麻将的桌子。然后抓起茶馆公用电话,嘟嘟嘟,拨下三个数字,说家里失窃了。派出所的人赶到后,黑毛说狡辩道:“警察同志,卖自家的东西算偷不?!”派出所的人就批评表妹,让她没事别乱打110,那是要承担法律后果的。
这一次,表妹虽没有承担法律后果,却付出了两颗门牙的代价。黑毛龇牙咧嘴地骂她,还将表妹往死里打,威胁她不要再报警。
今年黑毛赌博手气不错,白天赢了点钱,晚上就去城里发廊妹身上花掉。等表妹察觉到这事儿,黑毛的魂早被发廊妹拴死了,兜里没钱,就手臂一伸,卖血。表妹实在不能容忍了,心想黑毛虽是只癞蛤蟆,毕竟还是孩子的父亲,十多年来,即使没有爱情可言倒也没有背叛婚姻。现在倒好,我不给你戴绿帽子,你倒给我披绿头巾,这不是撅起屁股让人笑话吗?再说,要是惹上了性病,全家人还不死定了。表妹跟黑毛拼过几次命,但俩人力量悬殊太大,她身上这边旧伤未愈,那边又添新痛。
表妹再到我家来,是左手小指肿痛一直不好,不用问,又是黑毛的作品。妻子陪表妹去医院拍了片子,已经骨折。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她摸摸口袋,坚决不同意,忙说家里孩子牲畜还要人照顾呢。在门诊打好石膏,妻子又马不停蹄带她去了县妇联,分管信访的劳主席接待了她们。劳主席仔细地问仔细地记,几次拍案而起要替表妹伸张正义。最后,拿起电话打到乡妇联,要求积极介入,一定要维护好妇女同志的合法权益。
可惜现在的妇联有职责无手段,就像表妹的拳头,比熟透了的柿子还软。这次妇联之行带给表妹的不是解放,而是黑毛的又一通老拳。也不知道表妹是磨砺出了拳击运动员一样的抗击打能力,还是神经麻木了,雨点般的拳头落在她身上,不回击,不讨饶,不避让,不吭声,像打一团棉花。
表妹的确心灰意冷了,几次跟妻子流露过要走绝路的念头,就是放不下三个可怜的女儿。这可把我们急坏了,我开导她说好死不如赖活,有手有脚还怕饿死不成……妻子也很着急,抢过话筒说:“你为他死值得吗,不但不能死,还要坚强地活着,孩子大了就是出头之日。”
表妹挣扎一段时间后,终于提出了离婚要求。别看黑毛平时是个虐待狂,把表妹当作可以随时发泄的工具,当作不取报酬的长工,要离婚却死活不答应,说哪天太阳从西边上山了,就去签字。
表妹只好诉到法院,并请法官看了身上的几处伤疤。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法官只说伤疤并不能说明感情破裂,须先走调解程序,半年后再行诉讼。
表妹与黑毛分居了,准确地说是表妹不要黑毛睡一床,为防不测,枕边还备了一把剪刀。
表妹已分居五个月,再熬一个月就可以开庭,想到非人的日子快要结束,她又摸了摸枕边的剪刀。但黑毛可等不了一个月,他踹开房门,夺过表妹挥舞的剪刀,强奸了她。
那一夜,黑毛睡得很香。那一夜,彻底崩溃的表妹用剪刀让睡梦中的黑毛去了另一个世界。
警车呼啸着赶到表妹家,表妹没有一丝惊慌,木然地向警察伸出瘦如枯柴的双手。当二丫和抱着三丫的大丫哭喊着追过来时,她才止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只听“扑通”一声,表妹跪在了警察面前,哭着说道:“求求你们,让我再看一眼我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