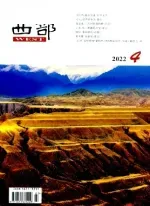敦煌之梦
杨献平
敦煌之梦
杨献平
这好像是第四次。在敦煌饭店,我洗掉一身尘土,使劲把自己扔在床上,看了一会儿天花板,不知不觉睡了。紧接着,开始做梦。——每次来敦煌,只要闭上眼睛,我就会做梦,每次都梦见一些奇怪的事情,其中有从不认识的某些人,还有自己。每一次都有一个故事或一个情节,比历史更幽深,比现实中的那些人情事态更有意味。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只要进入敦煌,我就觉得有点异样,周身似乎有些不明所以的气息缠裹,似乎连周身毛孔也灌满了,还有一种暗示般的牵引,耳边也一直响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谶语。
2007年7月,我第一次到敦煌,想法很简单,就是像那些到此一游的人一样,来敦煌看看,往电脑硬盘里多填几张在敦煌拍的照片。下车,找住处,吃晚饭,黑夜覆压下来。和妻子、山东的朋友鲁青一起,走到市中心,忽然看到环形马路中间矗立的石雕塑像——反弹琵琶。那一瞬间,我惊呼一声,原本人头攒动的街道一下子空旷无比,只剩下我一个人似的。丰腴曼妙的身姿,温情俯视的眼瞳,包含了深刻、简朴的自由与无以伦比的欣悦。在此之前,我看过许多雕塑,但第一时间即给我如此感觉的,只有这一尊反弹琵琶的伎乐天。
那种美是超凡脱俗的,是那种六根清净,了绝人间纷纭是非、万般纠缠之后的大了然、大彻悟、大悲悯、大清净。她曲线玲珑,胸部凸起,腰肢如蛇,脸颊飞媚。妖媚而不淫荡,勾引而无关色欲。灵魂在此如遭点化,如遇前生。在那尊反弹琵琶的伎乐天面前,我想我可以就此臣服,甘受驱使,不管是祥云升空或者坠落地狱,我都会拼命拉着她的裙角,哪怕成为一把枯骨,也要与她须臾不离。
在此之前,我没发现世间还有如此的美,美得彻骨、安妥、欲罢不能。我想,这位女子一定出身唐朝,丰腴的腰身,胸脯尽耸,后背如柔软草坡,眼眸间,闪着一种超凡脱俗的大慈祥。——妻子拉了拉我胳膊,我才如梦方醒。掏出相机,沿着街道转了一圈,连拍照片。到敦煌夜市,见到诗人方健荣,我还说,仅仅一尊反弹琵琶,敦煌就足够荣耀和不朽了。
凌晨时分回宾馆,有些醉意。再次看到那尊反弹琵琶,胸中一阵潮动。恨不得太阳此刻升起,到莫高窟去拜谒反弹琵琶伎乐天真身。洗漱睡下,浑身轻快,很快就睡着了。——我看到一个骑马的人,从西边沙漠带着一缕烟尘,狂奔而来,在一家杨树环绕的小店前停住。他的红色马匹不断咴咴嘶鸣,抛动前蹄。那家小店是黄泥加芦苇和木板建成的,上面飘着一面蓝色旗帜,旗帜下方飘着流苏。骑士下马,小二接过缰绳。小店门前的台阶是木制的,骑士摘下方帽,走到靠窗户的桌椅前,慢吞吞坐下,然后是带血的骆驼肉或牛羊肉,如同蜂蜜般粘稠的水酒。他的旅程很长,或者这就是目的地。他是一个孤独的骑士,也或许是一支队伍的探路者。
我好像也是一个外乡人,也骑着一匹红马,从东边来,不知怎么着,就和他坐在了同一张桌子边。我想吃他盘子里带血的肉,可就是伸不出手。他只是吃自己的,也不招呼我一声。我看着他吃,生闷气,像一个孩子一样,把日光挪到窗外。奇怪的是,我的那匹红马和他的那匹红马竟然变了模样,上身是人,而且还是女人,非常俊俏,就连鬓角飘下的长发,也妩媚至极,让人失魂落魄。
可惜的是,她们的下身还是马,屁股后面扬着茂盛的尾巴。两匹马在说话。开始我没听清,后来听到一个说,我这个人是从赵地邯郸来,要去西域的高昌,那里有我失散多年的弟弟;那匹马说,那个吃肉喝酒的男人是西域楼兰人,到沙州(敦煌)来看望他多年前嫁给这里的一个贵族的妹妹。后来,我的红马说:看起来,这两个都是与这地方有血亲的人。……他们的奔跑是有目的的,而我们则只是被骑乘的!他的那匹红马神色黯然了一下,大大的眼睛里流下一滴泪。那泪在阳光下晶莹剔透,如于阗国的白玉石。下落过程中,还在空中转了一个圈儿,然后像一枚尖利的石子一般砸进马厩外松软的浮土。
我惊异,朝着对面的那位骑士大声喊,让他快看。可一回头,坐在对面的他早已没有了影子。我怔了一下,再朝窗外看,却发现两匹红马也不见了。我急忙跑出来,转过小店墙角,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一个似曾相识的素衣女子,怀抱一支琵琶,看着我,绽开脸颊笑了笑,又优雅地作了一个揖。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转身还是靠近,只觉得浑身燥热,血管就要爆破一样。
这女子我似乎在哪儿见过,感觉像是穿越了几个轮回,在这一片沙漠边缘的绿洲小店再一次相见。她的笑让人心碎,有一种被母亲抱在怀里的感觉,还有一种可以交付此生的安妥感。我扭捏了一下,低头,深吸气,紧走几步,张开双臂就要抱她的时候,她却倏然一闪,不见了踪影。我大喊,转着身子四处巡望,到处都是杨树,叶子金黄金黄,似乎置身于黄金宫殿。我想喊她的名字,使劲喊,要把喉咙撕开一样喊,后来大哭。……醒来后,大汗淋漓,妻子在身边睡着。我看着即将被黎明点燃的白色天花板,回想起这个梦境。——玄奇的梦境,远方来的骑士,和我一般的目的,我们的红马不约而同,由马而成人,无意间闪电一现的女子,那么熟稔。这其中,肯定蕴含了某种心理期望。是想另外一个女子么?还是一种隐藏许久的心理暗影?或者两者都不是,只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梦境,与现实之间任何人事甚至念想都没关系?
整整一个早上,这个梦境真实清晰,如在眼前。其中的情景与人,还有发出的嘶喊与哭叫,都像是刚刚发生过。去卫生间时,我特意照了照镜子,发现自己的眼睛确实有点红肿,像真的哭过。乘车向莫高窟的路上,心里却隐隐觉得,川流不息的敦煌马路上,也有一种让人倍觉迷离的旧朝或者异域气息,就连路边的田地,劳作的农人,都似乎与自己隔了几个世纪。我对妻子说,敦煌这地方是有些神奇之处的,它使人似乎置身于一种飘渺而又确乎其在的梦境或者仙境,让我觉得了一种被拥裹和围绕的轻盈感,还有一种被托举的澄明感与被接受的宽容感。
或许,敦煌从来都是包容的,也是流变的,是一只彼时、此时都在扩张、内蓄的文明文化的巨大容器,当然,它也是纷乱的,是一座有着血腥和铁腥味的边地城市与冷兵器年代的关隘垛口。在史前,大月氏、党项、匈奴、乌孙、西羌是主要聚居者,最开始是大月氏进入,迫使西羌和党项民族向更高的地带迁徙。再后来,是“为人强力,宽大信人”的张骞及其随从堂邑父等人,用节杖和长弓,打开了从长安到中亚诸国的绵长道路。他的探险使得中央王朝第一次张开了世界性的远眺之眼,也第一次看到了广袤大地上诸多的人类及其文明文化,为西汉对匈奴作战并取得最终胜利,拓开了一条可以无限扩展且清晰如画的战略路线。
再后来,是匈奴的冒顿,派遣其子稽粥(老上单于)于公元前177或176年第一次进击大月氏,将大月氏从今张掖一带驱赶到敦煌附近。两年后,稽粥再次出击,不仅将大月氏的汗王头颅做成了镶金酒壶,而且将他们驱逐到了今伊犁河流域及天山谷地,从而,引发了发端于匈奴的中亚乃至欧洲大陆板块上的民族大迁徙。
另一个是我至今不喜欢的河北人李广利。他第一次远征大宛,损兵折将,最终撤回玉门关,而汉武帝却派人持剑将之拒于关外,曰:“敢有越玉门关者,斩!”这个裙带将军最终被匈奴俘获,被砍下头颅。其实,将军的功业从来就不是自己的,而是一种家天下的政治资本。既为资本,便有了被剥夺而易主的特性。与李广利同时期的李陵,在做酒泉骑射都尉时,也一定来过敦煌。我甚至想象,这一位千古悲绝的将军的坟茔也应当在敦煌或玉门关附近。他和其祖李广、其父李敢三代人之英雄作为、悲剧命运乃至人格魅力,真如钱穆先生所言:“令千载下读史者想慕不已!”
正在胡思乱想时,莫高窟到了,站在对面的售票处,我看到了莫高窟如此低矮,或者说,它的简陋甚至偏僻确实不会吸引目光。相比敦煌市中心翻版石刻的反弹琵琶,简直有霄壤之别。过王圆之道士塔的时候,我想到,莫高窟是佛家之地,一个道士,何以在此安身?或许是我浅薄,但佛道是有区别的。至于他发现藏经洞并拿给斯坦因、伯格曼、科兹洛夫等人换成银两之事,我觉得应当原谅,而不能一味地跟着某种观点大加挞伐。一个苦心维持莫高窟的道士,一个在动乱年代无甚文墨且不懂得文物及其价值的俗人,是艰难的生存让他有了变卖文物聊以度日的念头,其身、其心无恶,何以说恶?
走过只剩下一团绿藻的宕泉河,迎面的杨树枯枝甚多,但绿色占据多数。走到莫高窟前,看到陈旧的墙壁,似乎空洞之口的洞窟,胸中忽感悲凉。我想,那个叫做乐的晋朝和尚,在此忽见佛光,进而落身成庙,这其实是最富有理想主义和宗教意味的。一个人走路累了,或者说,一个人向着佛祖靠近感觉无望了,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为佛做一些发扬光大的事情,这种作为实际上是最大的虔诚。因为,信仰是一个人的,而将信仰传之万众,便是一群人的。一群人的力量,总是比一个人强大和持久。
进洞,我没看是第几窟,——关于这个编号,似乎是张大千所为。我想,张大千之所以成为大师,一定与这些洞窟壁画有着非常深刻的渊源。他起初说要几个月就可,最终住了三年,回去之后,画风大变。虽然对这段历史或者传说不甚其详,但我隐约觉得,莫高窟之于张大千乃至所有在此获得灵感的艺术创造者,无言的壁画一定为他们带来了某种天神的昭示。
敦煌似乎是艺术的大汇集、大隐藏和大展示。
在那些日渐残缺的画像前,我看,再看。导游在讲解,我听了一点儿,就转身走了出来,不是不爱听,而是觉得不能呆久了,人越多,口气越大,这些壁画已经损坏和剥落至此了,我作为一个热爱莫高窟并被之慑服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少看一眼,少在里面停留一会儿,让那些壁画及神灵们多在墙壁上停留一些时间。在一座洞窟里,我看到飞翔的伎乐天,她们的飞是纯粹的,优雅的,开放的和自由的,那种气度,是现在任何影像之中所找不到的。我忽然想到,莫高窟壁画之伟大,其实是民间艺术对每一个目击者内心及灵魂的征服,是前世之美和朴素创造在后世雷电一般的展现与惊醒。
洞内一片阴凉,全身犹如凉水冲洗过。我觉得,那些壁画、那些人物甚至佛陀座下的莲花、手持的兵刃,还有飘飘衣袂,都已经具备了不可阻遏的灵性,都已经在幽暗之中修炼得道,他们的世界是另外的,耽于尘世实在高天,形式老旧而内心清澈。我垂手而观,身心肃穆。我知道,这或许不是神灵,而是先人胸中的景象,这也不是壁画,而是先民的灵魂图腾。
在第323窟,我看到了张骞一行出使西域图,众佛环绕,官要揖拜,张骞骑马,佛俗紧随,衣饰华丽,远近适宜,正中佛庙,石碑围竖,一派西域景象。我不知道是谁将之绘上墙壁(自北魏至元代,敦煌画师来历纷纭,不仅当地,且中西皆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张骞及其勇气和实际作为,是每个人所景仰的。将之描绘于洞窟壁上,也一定有怀念其对西域的开拓之功的用意在内,若非张骞,敦煌乃至离中原更远的西域城郭诸国,一定会再云遮雾绕若干年后,才会被中央王朝撩开面纱,丝绸之路也会再迟一些进入人类文明之版图。
看过可以看的洞窟,坐在莫高窟下的树荫当中,仰头,断层之上,流云飞渡,天空幽蓝,有着苍天的深邃与开阔,也有着人间之干净底色。我想,莫高窟盛名,是以其旷世绝伦的艺术创造与流传构建起来,当然,这不朽的艺术是数以百计,没有留下姓名的民间画师,攀高凌空绘就的。还有一些官家、士族及渴望画像成佛的商贾、乡绅及略有钱财的普通百姓,如唐时归义军张议潮、曹议金家族,当地名望人家翟氏、阴氏,以及隋代的沙州或敦煌节度使,乃至元代和明初的地方行政长官、乡绅士族等等。特别是隋代人,他们至今的形姿放肆不羁,渴望就此成佛,《维摩诘经》应当是他们的修行纲领。
可是,肉身是易灭的,灵魂永生不仅是一种渴望,而且是一种普遍的信仰乃至精神支柱。唐代的壁画非常自由、雍容,充满活力,那个时代是大度的,向外的,就连普通歌姬也都大气昭然,有着强大的信心,也有着与世界交流,与全人类联姻,同在这颗星球上行走的勇气与自信。单从反弹琵琶的伎乐天神态,就可以看出一个大国的风度与魅力。倒是宋代一些官要的画像,表情黯然,似无生机。元代的画像乖张一些,放肆一些,其中还有明显的暴力崇拜色彩。
在一所宅院门口,看到陈寅恪的一字句“: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或许,这句话似乎是对王圆道士发出的第一声谴责,当然,陈寅恪先生所谴责和痛心的,绝不是王圆这么一个人及其行径,而是对彼时中国学术连遭浩劫而发出的忧愤之声。可以说,彼时的王圆其实就是当时整个中国情景的微缩,有怎样的国家就有怎样的国民,尽管王圆等偏居一隅,但其身上甚至灵魂里,都暗藏着一些败坏和麻木的东西。至于余秋雨后来的文章,将这种其实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谴责或者忧愤推向极致,我觉得也是不应当的,起码要区分具体情况。
告别莫高窟时候,我特别想买一本在莫高窟外货摊上兜售的涉及色情的书籍,好像也出自藏经洞,但售价太贵了,只好作罢。向外走了一段,再回头看,莫高窟真是一个美轮美奂的盛放与隐藏之地,它的存在似乎是一种暗喻和昭示。暗喻的是,信仰可以使人纯净,心思笃定,金银可以使信仰幻化成真,并被更多的人接纳和尊重。其实,在王圆身上,就有两种境界:笃诚和世俗。这是每个人的两种境界,因为,肉体的存在必须由物质来维持,而唯有肉体,才能够包藏甚至保护好灵魂与信仰。
晚上,又是喝酒。在街道上转了一圈,回去睡觉,洗澡,才觉得了累。躺在床上和妻子说了看莫高窟的感受,睡去。又做了一个梦:从西边的盐碱地,缓慢行来一支驼队。骆驼中有的是来自阿拉善的双峰驼,有的是中亚地区的独峰驼和白驼。它们脖子上的铃铛响声真的像风吹沙子,碎石敲钟,像薄的兵刃切骨,像党河初冬的冰渣子在正午碎裂。那些骑马的人都包着头巾,腰上有刀。马鞭在空中划出弧线,吆喝声刺疼红狐与黄羊的耳膜,紧接着是惊慌张望与逃窜。驼队之后是黄色和白色的烟尘,用散乱的形式,在浩瀚之地犁开一道消失与呈现的道路。
这可能是波斯人,或者粟特人,条支人,他们运载香料,也运载文明,运载铁器,也运载宗教。——在敦煌,各种宗教从西方而来,除了有名的佛教,还有琐罗亚斯德教(祆教)、基督教(景教)、摩尼教、禅宗等等。在此之前,亚历山大大帝派遣麾下向东进击,在中亚一带遭到伊朗军队毁灭性打击,其十字军一部失去踪迹,后被匈奴郅支单于收留,其“夹鳞鱼门阵”曾为匈奴挫败过陈汤、甘延寿所带西汉军与西域附属国联军,但郅支单于人少难支,陈汤火攻,郅支单于被一汉军砍下脑袋,其麾下十字军最终落足于今甘肃永登县河滩村。
这些大都源自史实,除非历史也在杜撰。在梦中,我似乎是一个熟知经史和掌故的人,站在山冈上,看着这一支自盐泽流沙之地逶迤而来的商队。再后来,我看到一队穿着铁制盔甲的战士,护送着一辆四面包裹严实的马车,从长安或者洛阳,一路向西。这一定是和亲的使团,一定是汉室家天下皇帝某个宗室的女儿,她向西,是一种政治,她去而不归,也是一种政治。
再后来,还是我,背着一柄锈迹斑斑的长剑,干粮斜挂在肩上,水壶在腰间。我总觉得那马车里坐着的人好像是离散多年的妻子,这一生最爱的女人。我千里奔行,就是要把她从全副武装的军人手中抢回来。可我总在惧怕,那么多带刀的战士,而我仅有一柄长剑。我不想早早死去,不想救不出妻子而葬身黄沙,不想让爱我的人就此断了念想。我犹豫、害怕、焦急,内心嘶哑,血液逆流,骨骼作响。
我的追踪似乎是从凉州开始的,进入山丹,我就觉得了这条道路的漫长,有时候奇怪地想,这条路究竟有没有尽头?向西的最终,是不是就可以到达传说中的王母山?一侧的祁连山好像出自匈奴语,根部是黝黑的,头顶洁白,尤其是金乌下落之时,白雪之上就是天堂。另一侧是连绵的山丘,寸草不生。山后是金黄色的沙子。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像是次第相连、密密匝匝的乳房,那么光洁,富有无尽的弹性和诱惑力。
一路上,我总是想,救出妻子后,两个人就隐匿在这无边无际之地,一片无人的绿洲,一条清澈的河流,再有一些芨芨草和马兰花,我可以用长剑伐木建屋,翻沙铲土,在越来越苍茫的西域,养一群孩子,在独自的沙漠绿洲之间,终老一生。
这也许仅仅是一个梦想,事实上,天下任何地方都是人的,人会拿刀,会因为生存而斗争,而杀戮。可以说,这个梦想从一开始就是绝望的。我想,一个人不能没有了这种梦想,尽管奢侈,不可能,但梦想或许就是信仰。
早上,太阳把窗帘烤热。出门吃饭,去鸣沙山。敦煌市区到处都是外地旅游者,各式肤色,各式表情。这时候的敦煌有些繁闹了。人太多,仅仅在看。会不会有人和我一样,白天震撼沉思,晚上做梦呢?去阳关的路上,戈壁张开,天空幽深。在张骞的石像前扭捏作姿照相,再仿效古人出关,看到只剩下一座破烽燧的阳关,还有王维的塑像。
“西出阳关无故人”。一句诗可以不朽,这大概就是文化的力量了。一句诗可以打败汹涌激荡的时间,这就是人之高贵所在。而西出阳关其实故人多多,王维的这句诗还是狭隘悲观了些。晋高僧法显、唐玄奘,乃至后来的左宗棠、林则徐、彭加木等人,他们的故人何尝不在阳关之外,中国之内?
站在连废墟都称不上的阳关旧址,向西张望,苍茫长天,横无边际,其实没有一条道路。在隋唐时代,从敦煌,分别有三条道路可以延伸而去。北道从伊吾(今哈密)而越天山,沿草原之路西行,过铁勒、突厥等游牧地区,一直到达东罗马。中道从高昌(今吐鲁番)西行,经龟兹、疏勒,翻过葱岭,进入粟特地区,再到波斯,最终到达地中海沿岸地区。南道从鄯善到于阗、朱俱波(叶城)、盘陀(塔什库尔干),过葱岭后,再经瓦罕山谷、吐火罗地区(阿富汗),进入印度。
这是一条满载丝绸、马蹄、梦想、海市蜃楼、英雄主义、传教士乃至诗歌、刀兵与绝望的道路。细君和解忧公主,班氏家族的英雄们,还有郭子仪等将领,这些人在西域开拓的是中央王朝的疆土与文明,在民族交流史上,用切身胆略之为,传播韧强雄健精神。而处在丝绸之路咽喉位置的敦煌,则是东西文化和人类文明的集散与流变地,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能在莫高窟和榆林窟找到最初和最后的影像,几乎每一种文化,都在敦煌刻下至今不灭的痕迹。
从阳关下来,正值中午,山下的村庄生机浓郁,葡萄满架,花开正艳。吃饭时,我觉得此地好像世外,甚至能够感觉到一些西汉的气息。李广利大军在此停驻一年有余,其三万兵士肯定有一些落足此地,繁衍至今。西域之地,自古就是混血的,戎族聚散,兵戈频仍,还有贬官、逐臣、戍卒和囚徒,就像现在,很多外地人在敦煌乃至西北与当地女子联姻,甚至终生驻留于此。
因此,敦煌从来就是兼容并蓄的,积极含纳的,对每一个人乃至每一种思想,它都在接受,并透过自己的胃液进行有效的过滤,将东方传之西方,将西方引进中国。这不仅是一条丝绸之路,更是一条横贯人类历史及其文明的绵长通道,尽管在许多年间被烽烟战火割断,可来自民间及贵族阶层、宗教笃信者对于财富、信仰的渴望与坚守,使得这条道路从没有真正中断过,要不然,莫高窟何以自北魏至元明仍旧兴盛?那么多的绘画和传说被画师描绘,至今流芳于世?
我甚至想到,应当在莫高窟继续建造佛龛,开凿洞窟,也请一些民间画师,按照有兴趣人们的意志,将他们绘上石壁。再若干年后,这肯定是一种接续,一种文化上的传承接力。可惜,人们都在热衷影像,已经没有了那种心向佛陀的虔诚与耐心。如果允许,我想我会这么做的,不是为了坐地成佛,只是为了把自己留在敦煌。
因为这是一块令人心生光芒、肉体澄明、思想沉着的异域美地,在当下,或许只有敦煌让人能够感觉到一种真切的自由与灵魂上的纯粹境界了。
回敦煌市区的路上,我有点发晕,靠在车座上睡着了。我又梦见了那个骑马的人,他其实还在那张桌子,即我的对面,坐着,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那两匹红马依旧是红马,嘴巴探进胡杨木打制的食槽里吃草,还有黑豆和苜蓿草。
我和那人一起喝酒吃肉。他说他并不是来自楼兰,而是若羌,他路过的国家比我见过的城市更多,经历的稀奇事儿比我的胡子还要茂密。然后,他有点醉了,站起来唱歌,好像是维吾尔族民歌,也好像是哈萨克族或者蒙古族的。声音高亢,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我给他唱另外一首民歌,是陕北的,也像是青海花儿。两个人你一声我一声,拍着桌子唱,弹着刀锋唱,唱着唱着,一转眼就都到了外面的杨树林里,我抽出长剑,他紧握弯刀,两个人对峙,一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仇恨模样。
这究竟是怎么了?我在问自己,一遍遍地问,脑子好像转不过弯似的,憋得太阳穴和腮帮子起起落落。
忽然醒来,车子已经停在了鸣沙山下。我仰头,看见大片的沙子,在炽烈日光下,一色焦白或惨白。有一些拉着骆驼供人骑乘的当地人,一个劲儿叫我们来试试。我想还是走路好,——关于骑乘骆驼,我有过几次经验,都在额济纳旗。第一次在胡杨林里,一头高大的双峰驼差点把我从它背上扔到铁丝网上。另一次,在额济纳旗小城边缘的一条只剩下白沙的河沟里,遇到一位刚从山里挖苁蓉回来的汉民和他的骆驼,我想靠近,结果被骆驼喷了一脸鼻涕。
每一种生灵都是有信仰的,也有情感,骆驼也是。我从来没有接近过它们或者与它们有过喂养与爱护的关系,它们拒绝我,甚至对我进行不友好的攻击,是正当的,它们有自己的个性与要求,它们值得尊重。
到水位日渐下降的月牙泉边,腥味扑鼻,我有点不习惯。倒是岸边的芦苇甚好,在初秋,白头变得更白,绿叶边缘正在变黄变脆。我知道,芦苇的叶子卷起来,可以吹出好听的音乐,苇杆掏空可以做笛子。——我南太行的老家也有很多,小时候,父亲经常给我用芦苇做笛子,可惜,我至今一首曲子也没学会。
沿着沙坡向上,赤脚,有种迅速的滚烫感。再向下,则有点凉,感觉两重天。很多人在沙坡上下行走或攀爬,大呼小叫,兴奋不已。我和妻子,还有鲁青、健荣等人一起向上爬去。天近黄昏,沙子变黄,再变红,最后变黑。在沙山顶上,凉风吹来,远处的敦煌又是一片灯火。借着暮色,我发现敦煌的夜空中时常会飞过一些不明物体,轻盈自在而又充满神意。
晚上继续做梦:我跟着那台马车和护送的军士好像行了无数的时光,从植被茂密到大河横流,从高山耸峙到视野开阔,湿土换成黄沙,道路隐没,苍天如幕。有时候我在沙窝里睡觉,被一群红蚂蚁咬醒;有时候则在树巅上,旁边有一个喜鹊窝儿;有时候在一所黄泥宅院里吃饭,或者和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讨论什么。
第二天早上回到久居的酒泉以北毛目小镇后,诸如此类的梦境戛然而止,夜晚就是睡眠,早上醒来,觉得自己忽然实际或者沉重起来,没有了那种轻盈感觉与迷离气息,眼前身边的是什么就是什么,真实得叫人绝望。2008年初,受一家杂志之邀,在西北空阔、尘土风动之际,我从嘉峪关乘车去往敦煌。到瓜州,人迹寂寥,到敦煌,人迹寂寥,街道上全是细土,干枯的树枝上还没有春的味道。
中午和方健荣、曹建川、刘学智诸朋友喝酒,和外地的几个朋友通过电话后,又去了曹建川所在的七里镇。——这名字很有意味,诗意而又刀光,还有一些睿智与雄悍之气。我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来又喝了一杯青稞酒,紧接着是失态的呕吐。凌晨一点多,和方健荣一起回到敦煌市区,随便找了一家私人小旅店睡下。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莫高窟的粗砂崖顶上,心里一直想到该不该跳,跳下去,洞窟里的神灵,特别是那位唐代伎乐天会不会半空将我接住?后又想,她弹着琵琶,没有手可以用来接我了,我肯定会直接坠地,然后没了性命。
可我必须要跳下去,后面好像有几个半人半兽的家伙在追我,他们非要我从莫高窟顶上跳下去,否则,就把我身上每一块肉都撕下来,卖给开黑店的土匪和恶人。我想还是自我结束的好,总比一刀刀地割舒服一些。灵魂离开肉体,肉体才能真正放下自我。可我不想失去肉体,我想到我所爱的人,我要做的事情,那些脸庞、话语,还有动作,电影一样流转,每一幅都让我心疼不已,深深留恋。
我四处看了看,想寻一个较低的、有沙土的地方,那样一来,神仙们如果不出手接住我,我跳下去,摔不伤的话,还可以爬起来再行奔逃。
恐惧纠结一夜。方健荣叫醒我,说,该去吃饭,乘车了。我一骨碌爬起来,在简陋的院子里打水洗漱,可是喝酒多了,还有些晕,舌头跟个木头片一样,毫无味觉。坐在车上和方健荣挥手作别,再次走过通向莫高窟的马路,心里忽然升起一种亲切感。想起在这里多年的季羡林、常书鸿、高尔泰、李承仙、段文杰等人,尤其是想起常书鸿和高尔泰的部分回忆文章,蓦然觉得莫高窟栩栩如生起来,脑子迅速展开一连串的图景:在洞内临摹的人,做饭的人,挖蘑菇的人,影像是黑白色的,极尽沧桑,充满质感。
我想,常书鸿等人于莫高窟、于敦煌都是功业至伟的,于敦煌艺术更是不可或缺的,还有当时为之奔走的胡适之等人,先驱者王国维、刘鹗等大师,都是敦煌及其艺术的功德者。到瓜州,我睡着了,在车上,虽没做梦,但总是觉得自己在告别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一座若有若无的海市蜃楼。它们都在尘世无迹可寻,却在内心隆重异常,它们在众生之间不露端倪,但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时常春光乍泻。
这一次后,我总觉得自己心里似乎多了一些什么,有时候撑得胸脯发胀。凡在书店看到敦煌二字,便一阵欣喜,都要买下来。买了数十张关于敦煌的音乐、宣传片和仿造物,陈列在自己的书房。我觉得,敦煌是适合在内心、在灵魂中盛放的。它之大,大到苍生万众,天上人间;它之盛,盛装古今未来,文明人心。
再一次去敦煌,是2009年夏末,一个人,——我喜欢独行。在河西走廊,不管是乘坐火车还是汽车,感觉都像是置身一只汪洋中的船,即使高速路上,也有一种颠簸和晕眩感。敦煌的人依旧多,在夜市吃喝穿行,在莫高窟摩肩接踵,在鸣沙山大呼小叫,在阳关乃至雅丹地貌、玉门关抚摸仰望。我再去莫高窟,买票,进洞,也还是一个人。我想看看那些逐渐剥落的神灵,他们的时代究竟是怎样一种情景。这些,都可以从他们的神态和眼睛里读到。
我慢慢发现,游人散去之后的莫高窟才是真正的清净所在,尤其是傍晚,落日逐渐在高崖上撤退,莫高窟次第变黑,我发现,这里俨然是一方神秘仙境,众神们来自不同地域,甚至有着这样那样的悖论和逆反,但都会相互尊重和包容,各守寸土,站或者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在幽暗处心向光明,于无声时说出万事奥秘。
一个人坐在莫高窟前的树荫下,叶子被风拍打,四野无声,一切都如此幽静,且又充满内在的骚动。或许,那些壁画上的人根本就没有消失,画代替了肉身,成为一种永久的居留和念诵。他们的手指甚至细长的睫毛,都似乎是一张嘴巴,只要你盯着看,就会得到一些箴言般的心灵辉映和启示。这种辉映完全是出自每个人甚至宗教深处的,它不直接,也不嗔怒,而是一种张开,一种参悟和领受。
再回到敦煌市区,觉得喧闹。没吃饭,洗完澡,就把自己扔在了床上。晚上,又是一个梦:梦见自己趴在敦煌市中心那尊反弹琵琶伎乐天的脚下,开始像个无耻的求婚者,眼泪鼻涕一起哀求。而石雕仍旧是石雕,依旧微笑着,朝着我似看非看。又梦见自己一个人在莫高窟的洞窟里转,还拿了手电,正看得入迷,忽然一声大吼,一个身穿制服的保安拿着警棍站在面前,说要把我扭送公安局,以偷盗文物定罪,我急忙申辩,说我就是想进来看看壁画,绝对不会是一个文物盗贼。那保安就是不听,冲上前来,用警棍猛敲我的头,我大声喊疼。
醒来还不到午夜,想了一会儿刚才的梦境,兀自笑了一声。穿衣出了酒店,走到敦煌夜市,独自一人,吃了十多串羊肉,还要了一条烤鱼,有浓郁的土腥味,吃了一口,就放下了。喝完啤酒,往回走的时候,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叮叮当当地发出清脆的响声。到市中心,又看到那尊反弹琵琶伎乐天石雕,忍不住脸红,自己发笑,搓了一把脸,就回酒店了。
这一次,我很晚才睡,一直在看电视,探索发现频道,到凌晨五点,想睡会儿,闭了半天眼睛,也没睡着。索性起身,一个人在酒店附近走了一圈,除了早起的清洁工人,醉了酒睡在车里的男子,一个人也没有。太阳升起时,人声车声渐起,我提着包,上了火车,靠在座椅上,看着逐渐驶离的敦煌,心里暗暗的,痛痛的。我拿定主意,一定要说服妻子和母亲,在敦煌市区买一套房子,在莫高窟,众神与众生之间,如此这般生活,终老一生。……这或许也还是一个关于敦煌的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