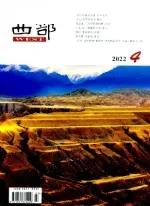秋熟
甫跃辉
八月八,收庄稼。一夜之间,山下一直滚到天头地脚的水稻得了讯息,齐齐俯下穗子,浑身披了金黄。几个月来,悠闲惯了的村子耸了耸肩,一下子忙碌起来,家里施工的人家歇工了,在外打工的男人回来了,小学中学里也放了农忙假。孩子们放假回来,总随父母到田间地头,帮忙抬个肩杆,抱捆草绳,拿把镰刀,拎个水壶。除了打杂,也不闲着,他们有一件重要活儿要做:拾稻穗。对于拾稻穗,男孩子们的积极性是不高的,稻田里多半是女孩子。这些个热闹的,或者寂静的女孩子,为秋收时充满阳刚气的田野平添了一份温柔。秋收轰轰烈烈,刀光剑影,流汗流血,是一组乐曲的最强音,拾稻穗是尾音,她们将这尾音唱得袅袅娜娜,回味悠长。
在女孩子们的世界里,那个一袭黑衣、一双小脚的衰老的身影就格外引人注目了。村里人叫她“老龙太”。她已经死去三十多年的丈夫确实是姓龙的,她的儿子也确实是姓龙的,但她姓什么呢?不得而知了。又或者,村人是喊她“老聋太”?她也确实聋了,你和她说什么,即便很大声,大声得像吵架,她仍什么也听不见,你声音里真掺了不满了,声音大得山崩地裂,她还是笑眯眯的,豁着没牙的嘴巴,一只手笼着耳朵,凑到你的嘴边,说:“阿侄,你说什么?”
老龙太很老了,村里的男人她都喊“阿侄”,女人都喊“阿妹”。有时候,这些阿侄、阿妹会问她:“老龙太,你多大年纪了?”她总算听明白了,笑眯眯的,说:“你猜,你猜得到,我就说给你听。”人们有时来了兴致,说:“你总有九十了吧?怎么说也得八十,总不可能是七十。”老龙太自始至终微笑着,并不答话。老人除了一张窄窄的脸布满皱纹,远看上去,倒还真不显老。她又瘦又高,或许太高了,腰总是弯着,弯着才能看到地上的稻穗。她一面和人说话,一面不断深深地弯下腰去,吃力地捡起一穗穗稻穗,杵着膝盖,直起身子,放进身后的背篓里。她背的背篓与众不同,口子那儿,还绷着一张塑料布。老人聪明呢,她是怕她弯腰时背篓里的稻穗倾出来,用塑料布盖住,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那时候,村里人都为老人抱屈。老人有两儿四女,分家后,老人的老伴和大儿子吃,老人和小儿子吃。小儿子有一个女孩儿,女孩儿两岁那年得了脑炎,医好后,有点儿傻。正想着再生一个,不想小儿子在外面和人口角,打起来,被一砖头拍死了。过了不到半年,那年纪轻轻的媳妇撂下老人和女儿,和一个外方人跑了。一个好好的家,一下子散了。村里几次和老人的大儿子龙光明说,要他负担起老人。谁想龙光明又是哭穷,又是耍横,说她年纪是大了,谁要是真有良心,怎么不把她接自己家里去养起来?去说的人愤愤然,也无话可说,只好不再管。
除了老大给几百斤粮食,老人没什么经济来源,每年就靠拾麦穗稻穗。村里有些人莫名地觉得亏欠了老人,见老人拾稻穗,远远的,就招呼老人到自家田里,割了稻子,顺手散放一些。老人耳朵聋,眼睛却分外尖,见到成束成束的散稻子,总是捡起来,放回主人家的稻子堆里。主人家不乐意了,说:“哎呀呀,老龙太,你老昏了?拾了稻子不放进自己背篓里?”老人满脸的皱纹聚成一个夸张的笑,说:“我昏了,可没你们昏,好好的稻子,随手就乱扔。”也有些人家厌恶老人,见老人朝自家田里走来,就做出驱赶麻雀、驱赶鸡、驱赶猪的手势,说:“走,走!”老人也就转身走了。老人走了,一直跟着老人的傻女孩儿怔怔站在那家人的田边,对那家人翻白眼。直到那家人骂她,朝她走过来,她才转身去追老人。
女孩儿将近十岁了,什么事也不会做。她的衣服鞋袜大多是村里人给的。她经常穿的一件蓝底白碎花的衬衫,听说是老人自己缝的,现在再也见不到那么土气的衣服了。她还喜欢扎两个小辫子,辫梢用红头绳系住,这也是老人给她弄的。老人照着十几年前、几十年前流行的样子,精心打扮着女孩儿。若不是那双眼睛,女孩儿真算得上漂亮了。因为老人从不让女孩儿干活,她的手和脸俱是白白净净的。脸是瓜子脸,下巴稍稍有点儿尖,但并不显得刻薄。五官清爽,很匀称地配合在一起,尤其一双眼睛,静静地望着你,让你不由得心里一动。可正当你打心底里感叹,怎么如此粗鄙的农村,竟有如此洁净水灵的女孩儿,她忽然眼珠子使劲儿往上一翻,露出白瞪瞪的白眼仁,狠狠地剜你一眼,连带眉毛、鼻子、嘴巴,一齐变了形,变得无比丑陋和凶狠。
女孩儿不上学,不和同龄的孩子们玩,也没人和她玩。有时候,路上聚着一群孩子,嘻嘻哈哈玩得欢,她也会站住,眼睛亮闪闪的,似乎含着几分羡慕。那些玩耍的孩子注意到她,也不理会,笑得更欢了,不由得带上一些显摆的成分。笑声一大片一大片,很慷慨地在秋天的土路上播撒着。女孩儿却渐渐皱了眉头,显出几分厌恶的神色。那些玩耍的孩子有点儿不自在,就有人过来撵女孩儿,挥舞着脏兮兮的小手,满脸稚嫩的凶恶。女孩儿往后退着,并不惧怕。远远退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她又往孩子堆里瞥一眼,这一眼,简直是极度的鄙夷了。孩子们的欢乐黯淡了,一个个呆立着,望着她一个人寂寂远去。
老人走到哪儿,女孩儿跟到哪儿。老人出门拾稻穗,她也跟出门。不过她并不帮老人拾稻穗,老人也不让她帮忙。无论什么时候,哪怕是睡觉了,她怀里总抱着一件东西,有时是一个脏兮兮的断了胳膊断了头的布娃娃,有时是半个皮球,有时是一只鞋子。老人拾稻穗的时候,女孩儿怀里是几枝荷花。稻田外面有一大片荷花田,女孩儿手中的荷花是看荷花田的老田给的。老田满脸络腮胡,吓退过好多偷荷花的野孩子,可从没吓过女孩儿。他总是问女孩儿:“要什么颜色的荷花?红的?白的?”女孩儿说都要,他就都给摘了两朵,说:“翠妮,叫我一声阿公,我就把荷花给你。”女孩儿不叫,眼珠子白白地翻上去。老田把头扭到一边,笑着说:“害怕,害怕,你不叫算了,不要吓我。”说着把水淋淋的荷花递到女孩儿手中。女孩儿是叫翠妮,谁都知道这名字,可任谁叫她,她总不答应。叫上两遍,她就拿白眼仁翻你,因此有人怀疑她不但傻,还是个哑巴。
“翠妮!”罗春城媳妇直起腰,嗓子如同破锣,大声责备女孩儿,“这么大个人了,怎么不帮你奶奶拾稻穗?”
翠妮怀抱四枝荷花。四条翠绿的荷花梗,从断裂处扯出紊乱的浓白丝线,盘在翠妮的蓝色衣襟上,散发出苦涩的清香。荷花有两朵白的,两朵红的,两朵半开,两朵全开,花瓣上还挂着清晨的露珠。四朵花聚成一大团,簇拥着翠妮的脸。翠妮的脸明艳无比,时而粉红,时而粉白,她似乎没听到罗春城媳妇的话,眼睛悠悠地望向远方,脸色格外平静。下巴往下压了压,压到嫩黄的莲蓬上,再抬起头,下巴上沾了黄亮的花粉,脸颊上挂了几颗硕大晶莹的露珠。
老龙太慌忙对罗春城媳妇摇摇手,说:“阿妹,让她玩,让她玩,她什么都不懂的。”老人望望翠妮,脸上浮起笑。
翠妮很少笑。翠妮总喜欢望向远方,脸总是那么平静,不喜乐,也不悲伤,犹如一汪很深的水,不起一丝丝涟漪。只在下面这种情况,人们才会听到翠妮笑。
收割结束后,有的人家会将稻草留在田里堆起来烧掉。潮湿的稻草堆里,红红的火苗牛血似地缓缓流淌,冒出一绺一绺纠结着的浓烟。收割后日益荒凉的田野里,这边一堆火,那边一堆火,将黄昏的天空照耀成一条血色的大河。老龙太仍背着个背篓在稻田里游荡,偶尔捡起一穗半穗稻子。翠妮跟着,不时停下,看田埂上的小花。蒲公英、野莴笋、灰灰菜,这时节都举着小小的花朵。老龙太也不时停下来,转回头喊:“翠妮——翠妮——”翠妮仰起脸,望望老人,又无声地跟上来了。她们走到一堆火边,翠妮忽然撕下一瓣碗口大的荷花,在老人眼前一晃,一丢手,扔进火堆,火苗从白色的花瓣周围钻出来。老人慌慌伸出手,把花瓣抓出来,拍拍上面的灰,责备道:“好好的花,你烧它做什么?”翠妮不说话,狡黠地瞅一眼老人,又撕下一瓣红色的花瓣,迅速扔进火堆,老人又一次伸出手,抓出烧软了的花瓣:“你个偷生鬼,你做得好?”老人埋怨着,脸上却开了一朵花。翠妮不答话,“咯咯咯”笑了,又撕了一片花瓣……翠妮跑在前面,等老人追上来了,才把花瓣扔进火里。她们从一个燃烧的草垛跑到另一个燃烧的草垛,翠妮的笑声就从一个燃烧的草垛飞到另一个燃烧的草垛。正在收割的人直起腰,握着镰刀,说:“你听,翠妮笑了,小姑娘会笑呢,不是哑巴。”另一个人也直起腰,静静地听。翠妮的笑像一串冰凉的露珠,咕噜噜灌进她的耳朵,她却对前一个人的说法表示怀疑:“这怎么说得准呢?会笑也不见得不是哑巴。”
村里人都熟悉老龙太和翠妮之间的这个游戏。他们不明白她们为什么每年都玩这个游戏,为什么每次都笑得那么开心。这有什么好玩的呢?一点儿都不好玩。可不管怎么说,他们愿意看到老龙太露出笑容,愿意听到翠妮咯咯咯笑。在这简单的欢乐中,他们内心潜藏的对祖孙俩的歉疚会稍微得到一些安慰。
当老龙太给自己砌了坟,他们内心里的歉疚又减了几分。那是三年前的事。秋收过后一个多月,老龙太找来几个年轻人。村里人不明白这老龙太要做什么,问她,她满脸笑开了花:“给自个儿堆个窝呀。”老人的话让人摸不着头脑。第二天,后山叮叮当当响起小钢钻敲击石头的声音,一星儿一星儿很欢快,村人才明白老龙太是找人来给自己砌坟。一个月后,坟砌好了,石匠们体恤老人,要价很低,拢共才要了五百块钱。可这也不是小数目啊!老人笑呵呵的,说:“是我拾麦穗稻穗攒的,攒了五六年啦。”村人不由得对老人竖起大拇指,心里又都有些泛酸。
“这下我什么顾虑没有了,今后就专门给翠妮攒嫁妆钱了。”老龙太望着翠妮,眼里星光点点。
村人不好说出口,心里都想,那得拾多少麦穗稻穗?又都想,即便攒够了钱,哪个会要翠妮这样的女孩子做媳妇呢?人傻,又什么都不会做,只会抱束花到处跑。漂亮归漂亮,一点儿用也没有。村人在心里直摇头,表面上却还给老人的热乎劲儿添油加柴。老人的一张老脸焕发荣光,满脸的皱纹花一样盛开。
村人一直记得老人那张无比幸福的脸。不过,他们不用为翠妮多操心了。
那天,翠妮和老龙太又玩了那个烧花救花的游戏。她们玩得格外投入,鸭蛋壳青的天空下,她们轻盈无比,像一只蝴蝶追逐另一只蝴蝶,像一段欢快的岁月追逐另一段欢快的岁月,她们的笑声肆无忌惮、铺张浪费。人们一个个直起腰,让镰刀愣在手中,几乎带着嫉妒地说:“你听,她们祖孙那个乐!”
她们真乐啊!村人看到,翠妮手中只捏着四五根翠绿的荷花梗,而红的白的花瓣全到老龙太手中去了。老龙太两手各捏一把花瓣,小脚一翘,两手一扇,真像一只蝴蝶了,真要飞了。村人看她们这么乐,心里也乐,就连沉重的秋收活儿,也一下子轻了。
“翠妮——翠妮——”老龙太嘴角挂着笑,气喘吁吁地说,“坐一会儿,阿奶跑不动了。”
老龙太在田边的一棵椿树下坐了。椿树还小,只有手腕粗,老龙太一靠上去,树身倾斜了,簌簌掉下两片叶子。老龙太抬眼望望稀稀疏疏的枝叶,枝叶切割着明亮的天空,天空格外高,格外轻,也格外静。老人身子挺了挺,不让全部重量压到树上,小树又直了。
翠妮见老人闭了眼,猫着步子,蹭到老人身边,一瓣一瓣抽出老人手中的荷花,又一瓣一瓣盖到老人蜡黄的脸上,老人满脸满身盖了红的白的荷花瓣,恍如盖了一面锦旗。翠妮禁不住“咯咯咯”笑了。往常,老人听到笑,睁开眼见到满身花瓣,总会面带微笑骂翠妮几句,翠妮总是偷眼看她,抿着嘴笑,可这次老人没醒。翠妮静静等着,那束光秃秃的荷花梗举在胸口。她低下头看看,荷花梗上便开出别人看不见的花朵。她又抬起头望着远方,无穷的远方仍是丰收的田野。立着的人,弯腰的人,跑来跑去的人,交织在大片绚烂、哀伤的风景里。翠妮收回目光,又看看老人,老人还不醒,翠妮等不得了,推了推老人。老人脸上滑下几片花瓣,小椿树又簌簌掉下几片黄叶,一片,又一片,覆盖了老人露出来的脸。翠妮再次抬起头,远方带着丰收的喜悦和肃穆,蜂拥着,缩进她的眼睛里。
黑剩一线的月亮如瞎了一半的眼睛,空空洞洞地瞅着山脚的小村子。村人久久不能成眠,他们在被窝里坐起,说:“你听听,龙光明老婆那哭声,比杀猪还难听。”“是啊,是啊,”另一个人附和,“人一死,就数她最孝顺了。”
葬礼进行得很热烈,锣鼓尽情敲,狮子尽情耍,哭丧的尽情哭。连天地的色泽都为葬礼很好地渲染了气氛,天青到不能再青,地黄到不能再黄,成片成片大涂大染的颜色,有一种平静而又浓烈的哀伤在里面。村里好多人搁下手中的活儿来帮忙。龙光明说:“哪个再说我不孝顺,让他睁开狗眼来瞧瞧!”
村人在葬礼上只见到翠妮一次。婶子跪在火盆前,哭了一巴掌鼻涕,一叠一叠黄钱扔进火里,卷曲着烧成灰烬。翠妮蹲在旁边,怀抱几朵娇艳的红荷花,荷花和火光映在她脸上,她的脸便有了几分飘忽、几分不确定。她伸手撕了一片荷花,“扑”扔进火里,火被压住了,哽咽了一下,又“嘭”地旺起来。她的眼睛在火光里晶亮地一闪,又撕了一片荷花。忽然,婶子一巴掌拍过来,把她手里的花瓣拍掉了,又去夺她怀里的荷花。她死命抱住,红艳艳的荷花抓散了,落了满地,她还紧紧攥着荷花梗。荷花梗细密的小刺在她脸上划了长长一条道,又刺了婶子的手。婶子急急抽回手,抚着手背,骂道:“没良心的!老太太天天夸你,疼你,人死了,怎么不见你嚎一声磕个头?”又伸手去推翠妮,要翠妮跪。翠妮扭着身子,不跪,盯着婶子,白眼仁猛地翻上去,一张脸鬼魅似的,丑陋而凶狠。婶子不提防,吓得倒抽一口冷气,一撒手,翠妮跑远了。
好几天不见翠妮,村人暗地里议论,翠妮会不会找她妈去了?她妈在哪儿呢?村里的大人尚且不知道,翠妮如何知道?就算知道,她一个小女孩儿,何况还是个傻子,又如何走得了远路?路上倘若遇到歹人,见她那么干干净净的脸蛋儿,保不准不会起邪念。她哪儿还有路走?村人不敢再想。那么,是找她亲戚去了?可村里人都知道,翠妮除了老龙太,再无一个可靠的亲戚了。议论来议论去,没个结果。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仍不见翠妮,村人的议论就有些不着边际了。有人说,翠妮不会是老龙太接去了吧?老龙太怎么丢得下翠妮呢?说这话的人自然免不了被旁人一顿批。可批斗完了,大家却沉默了,脊梁骨一阵阵冷,从此有心无心的,总多注意一眼村里的沟沟汊汊。几日下来,也并未见尸体浮起。
又过了些日子,村人再提起翠妮,就只剩下叹息了。不止一个人想起她那张脸,不高兴时会翻白眼,平时总那么望着远处。她望什么呢?又附会出种种神秘的解释。话题渐渐远离了翠妮,牵扯到世间万象,人世悲苦,人们心里某个柔软的地方被触动着,在一种平缓的悲伤里,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忙完秋收,翠妮仍未出现,村人渐渐不再提起她,似乎认为这样悄无声息的消失本就是她命定的归宿。只是偶尔抬头,看不见、听不见草垛间老龙太和翠妮追逐,才隐隐觉得少了点儿什么,又说不出那具体是什么。光秃秃的田野里,褐色的稻茬零星冒出一些绿芽儿,远远看上去一派宁静,静里疏疏落落立着红的马、黑的水牛。马和水牛低头揪嫩稻芽儿吃,大白牙齿磨过来,磨过去,忽然莫名其妙停住;尾巴寂寥地扫过来,又扫过去,使稻田里的积水有了细小的波纹,天色都搅乱了。水面映出蓝的天,白的云,水泡泡的如一滴坠落的泪,稳稳搁在土地的心窝里。此时,土地活像一个生产的女人,经过漫长的妊娠和剧烈的疼痛,产出一些东西,譬如粮仓里等待回到土地的谷子;又补充进一些东西,譬如躺在地底下等待轮回的老龙太。土地既干瘪了,又充盈了,额头爬上疲倦的皱纹,眼角眉梢却有了几分喜气,手脚懒懒地搁置着,静静蓄积着力量,好似转眼就可以握住某件东西,好似站起来就可以走到某个很遥远的地方。沉静之中的等待是那么有力、安详、动人心魄。
这一天,罗春城媳妇正清理田垄,一面和旁边田里的女人说闲话,腰弯下后,又直起来,眼睛眯缝起,嘴巴慢慢张开。
“翠妮!翠妮——”罗春城媳妇手搭凉棚,望着远处的那个女孩儿,惊喜得脸红心跳。旁边的女人也直起腰,随她的视线望过去。
翠妮仍穿着那件干干净净的蓝底白碎花衬衫,脚上套了一双崭新的白色运动鞋,怀抱一大束水淋淋的红荷花。荷花异常硕大,笼住了翠妮的半张脸,只看得见她的眼睛、额头,有些乱的头发……
老田把荷花递到翠妮手中,又拍拍翠妮脚上的新鞋,啧啧嘴说:“真好看,翠妮真好看!”翠妮眼睛眨巴着,好似两只扑闪着美丽翅膀的黑花蝴蝶。老田轻轻咳了一声,望望远处已经露出败象的荷花田,又说:“翠妮,你明天别来这儿了,明天这儿的水要淘干,要挖藕了,没有荷花了。”翠妮没翻白眼,睫毛抖了抖,不说话,低下头,把半张脸埋进苦涩、清香的荷花丛中。
翠妮抱着荷花,朝罗春城媳妇这边慢悠悠地走过来。旁边那女人忽然小声说:“听龙光明两口子说了,找回了翠妮,他们就把她送人。”罗春城媳妇吃惊地望着她:“送给谁呢?天底下这么多人家,哪有人家会要这样一个女孩儿?”那女人越发压低了声音:“真送人倒好了,就怕是卖……”罗春城媳妇脸色陡变。两个女人都不说话了,又一齐望着翠妮。
“翠妮——”
翠妮不答应她们,慢悠悠地走,走到一堆缓缓燃烧的草垛边,停下来,撕了一片花瓣,扔进火里。红色的花瓣给红色的火苗裹住了,渐渐卷曲起来,发出一股苦涩的臭味,丰厚的红色花瓣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缺黑黑的硬壳。翠妮怔怔地看了一会儿,又往里扔了一片花瓣。再往前走,到另一个燃烧的草垛边,又撕下几片花瓣,扔进火里。这时候,田野萧疏、寂静,下午的阳光明晃晃亮着,寂静越加广大了。在这一望无际的静里,突然拱出一个翠生生的声音,好似大冬天里,一个嫩嫩的青草芽儿。两个女人面面相觑,以为自己的耳朵出毛病了,很快,那声音又拱出来了,向她们证实,她们的耳朵并未出毛病。她们看到翠妮往火堆里扔进几片荷花,走几步,回头看看,喊一声,很焦急的样子。“翠妮不是哑巴!”罗春城媳妇急切地对旁边的女人说,像要得到她的证实。那女人也很激动,满脸含笑,说:“真不是哑巴。”可她喊的是什么呢?“烧化”“烧化”?“不是,不是。”罗春城媳妇不同意。两个女人竖起耳朵,眼巴巴望着翠妮,她们隐约看到翠妮一脸焦灼,似乎想伸手抓出火里的花瓣,却不敢伸手。可同时,她又不断扯下花瓣,朝火堆里扔进去,嘴里喊着:“烧花嘞——烧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