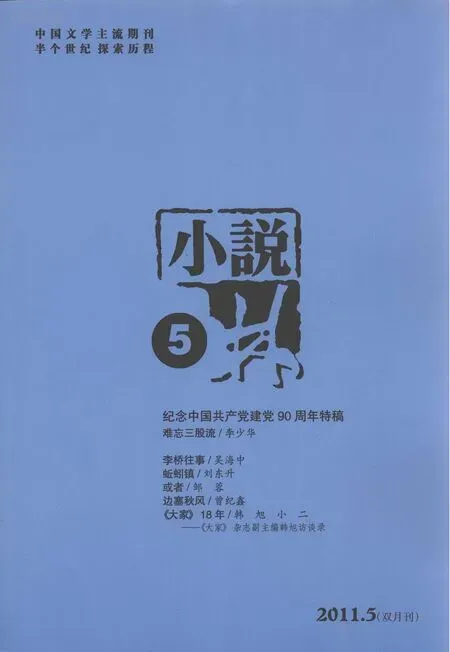蚯蚓镇
■刘东升

来这个镇子,时间不短了,还没取得什么业绩。虽然我——一个药材公司营销员,隐约感觉到了其中的缘由,但出于对公司营销部门的信任和对自己前途的负责,我还不能离开这里。
所以,我一有空就带两大包药材,到亭子下面鼓捣。亭子里,每天都有那么几个人,有的很老了,胡子耷拉在地上。他们是镇子里最早的一批失业者,没事做就来这里,在这破败山河的一隅,发呆、聊天。
这里很阴凉。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才感到舒服,这点习性,跟我院子里的那些个蚯蚓差不多。刚才出门的时候,就有一只蚯蚓在门槛旁翻着肚子,天太热,它又跑出来,暴烈的日光注满了它身上的每一条沟壑。它一定要死了。
“又想你的蚯蚓呢?”阿拉美冷不丁来这么一句。
我吃了一惊,就像脑子深处的一根麻绳被他抽了出来。
“那是我的命啊,蚯蚓能入药,你不知道?”我正在用锤子捣碎那些翘壳的药材,直到捣成末子。
“人都快死绝了,还想什么蚯蚓呢。”这个老瘸子,几天不见,说话鬼里鬼气的。
这时我才想起把另一包药材拿到亭子旁边的大路上晾晒。与其说是路,不如说是大坑。这些深浅不一的土坑里散落着凌乱的脚印和一些腐朽的看起来像是铁锹柄的木棍。我踉踉跄跄地越过一个高坎,在一个破围墙边找到一片平整的地面,支好摊子,让稀薄零碎的阳光洒在由蒲公英、蘑菇、蚯蚓干、花生皮混合而成的药材堆上,看这阵势,大概一个小时翻晒一次就可以了。
回到亭子里,阿拉美已经靠着柱子睡着了。这老头,比上次见到他的时候还要消瘦,胡子都不愿在他脸上生长了,还是原来的那几根。他的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在地上形成了一小片水泊,这片口水拯救了两条正路过这里的又黑又瘦的蚯蚓,我虽然有点恶心,仍然抓住它们扔进了袋子。我清理手上污渍的时候,隐约听到有人有气无力地说,“活不了了,活不了了。”
这一会工夫,阿拉美做了一个梦,这是他醒来后告诉我的。他梦见一个狂风骤雨的夜里,他的儿子阿亦非自杀了。当时不知是几点,阿拉美拖着一条瘸腿起来小便,因为没找到那把破伞,更多的是害怕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劈下来的闪电,他没有跨过院子去厕所,就在堂屋门口战战兢兢地尿了一泡。他路过儿子卧室时打了一个哈欠,透过残破的窗玻璃,他发现一个人的身子悬在房梁上。
阿拉美借助凳子想把儿子从绳套里弄出来,他一瘸一拐的,上去多少次,凳子就歪了多少次。阿拉美对着暴雨击打着的小窗户使劲喊,“干你娘!有人没有?有人没有?干你娘!”鼻涕、眼泪一起唰唰地淌,后来他累了,靠在床板旁呆坐着,面色苍白。他顺手摸到两页纸,阿拉美不识得几个字,根据他的口述来看,这应该是儿子的遗书,上面大概是说:
“爹,我不活了,所以我先死了。去年美凤跟大款跑了,她嫌这个家穷,不想跟着我受苦一辈子。谁知道呢,这也不是我个人造成的。这个镇子也许真的没救了,自打咱的河黑了以后我就不抱什么希望了,也不会有人上访了,谁都知道是哪些工厂排放的污水,有啥法子呢。美凤说咱这旮旯土壤不行了,蚯蚓都养活不了,咋养活人呢。她说的对,蚯蚓是咱镇的命根子,世世代代都靠它,制药的每一个关卡都离不开它,现在的土块太黑了,抹了焦油一样,蚯蚓能不跑出来吗,一出来就碰见太阳,再好的园子也圈不住。爹,咱多少年没吃到自己种的庄稼了,白面馍、玉米棒子、大豆油,爹,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在阴间了,或许这里还有别的食物,可是我可怜的爹,你该怎么活啊。儿愿你每天吃得饱,喝得香,这几年你没少受罪,起早摸黑地找蚯蚓,挖蚯蚓,圈在院子里养蚯蚓,可那该死的玩意儿就不吃咱这土块子。说起来可笑,世代做药的主儿连自己的病都治不了,就因为一直没啥收入,要不你那类风湿的腿也不会瘸啊。哎,活不了了,蚯蚓都快跑完了,也许去往别的镇子,也许死在半道上了。爹,锅里还有几块窝窝头。爹,我不活了,我先死了。”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全神贯注地摆弄药材,偶尔去大路上给那些药引子翻翻壳儿。阿拉美磕磕绊绊地讲述着他的梦境,我时不时瞥他一眼,表情笨拙、木呆、沧桑,这就是阿拉美。
“这不是真的吧。”我调侃他说。
“真的,一个月前的事情了。”阿拉美说。“刚才梦里又经历了一遍。”
往后不久,我就肯定了这件事的真实性,因为我再没能见到阿亦非。这对我虽说算不上一件多么悲伤的事情,但他毕竟是我在这个镇子上认识的第一个人,偶尔想起来,多少还是让我有点失落的感觉。
两年前,我被公司派来这个镇子推销药材。那是一个清晨,不巧碰上了大雾,我顺着那条著名的河流,目标直指蚯蚓镇。雾气像浓牛奶,在河面上静静地流淌,依稀能感到浑浊的河水在暗处的汹涌。同样,雾气也掩盖了五米以外的稀落的林木和荒田,有几次我差点跟对面的行人撞个满怀。在大雾中我迷迷糊糊地摸了一个钟头,总也找不到那个上面标着“蚯蚓镇”的路牌,这真让我恼火,在这个神鬼不至的地方有个三长两短,岂不冤枉。我正暗自抱怨,突然一个年轻人——他就是阿亦非——冒冒失失地从我对面直冲过来,几乎快要撞到我了,我们才下意识地躲开对方。他拎着一把铁锹,大概因为太累了,铁锹几乎是被他拖着过来的,在地上发出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剧烈的声音。他不打算再往前跑了,顺势坐在地上喘粗气。“妈的,跑了跑了。”
出于一个营销人员有必要迅速融入当地工作环境的考虑,也顺便歇歇脚,我跟他挨着坐下来。
“我在追一只蚯蚓……”他说。
“什么蚯蚓?”
“蚯蚓你不知道?你是城里人吧,这玩意儿长长的,活着会跑,死了能做药引子,来钱的。刚才你没看见?从你这个方向跑过去了。”他掂起铁锹把子,往我身后的大雾里瞅。
“你追它做什么?看你的衣服都破了,你的眉毛都歪了。”
“它不吃这土块子,它活不了了,你看你屁股下的土都黑了,其实是那河先黑的,后来庄稼地也黑了,它就想去别的镇子。我的蚯蚓窖子就在那河边,这几天死了几百条,跑了几百条,它跑我就追,有时候它跑着跑着能飞起来,我总是追不上。”他看起来有点生气,用铁锹使劲拍了拍地面,我这才注意到这条小路上的土是浅黑色的,尘土很少,像是什么化学药剂渗入里面凝固了一样。
他愤愤地骂了一句,继续说,“俺们商量好了,去城里上访,不知道这次有啥效果没有,对了,你知道那个青天制药厂吗,哦,你不知道。那厂子在县城的郊区,俺这河就流过那里,俺这河不该从那儿过,过了就黑了,多好的水啊,到俺们镇子就乌黑乌黑的,上面飘了一层子黑油……”
我就是青天制药厂的。我知道这条河怎么回事。可一个小员工,咱管不了,也不敢管。上个月的一天晚上俺老板刚出门就挨了一砖头,差点没死掉。都知道咋回事,可有啥办法,那些老百姓可不是好惹的。只顾挣钱了,发展医药事业了,搞黑了人家的河,吓跑了人家的蚯蚓。下游来的村民几次上访都被俺厂子的人硬生生截住,用大篷车拉走丢到郊区。什么叫民愤啊,惹急了能不砸你吗。话说回来,虽说这两年因为污染问题厂子里有点不太平,下有老百姓,上头还有政府呢,可不知老板在哪儿使劲儿了,硬是把俺这青天制药的大船驶得稳稳当当,效益也是非常可观。
我来蚯蚓镇两年了,每天除了摆弄药材,偶尔联系一下稀稀拉拉的客户,其他也没什么事情可做。有时就在院子里望着那些枯死的树干发呆,土质越来越坏,几棵大榕树也死了,傍晚的时候很多乌鸦停在树干上呱呱地叫,我用铁锹吓唬它们,它们不但不跑,反而叫得更厉害了。我用铁锹有所谓没所谓的挖蚯蚓,挖出来就是外快,挖不出来权当锻炼身体了。院子最里面的角落被我挖了一个大坑,几乎快挖出泉眼了,但没什么效果,蚯蚓很少了,我就坐在坑里胡思乱想,一会儿我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乌鸦还没有散去,我不知道去哪里,外面都没有路了,庄稼地也没有了,都被镇子里的人们挖掉了。无聊、孤独甚至恐慌的感觉在我洞悉了一个微妙而危险的趋势后愈加强烈了。那天清晨,我去街上买盐,磕磕绊绊地跨过那些大坑,路过阿拉美家,他正蹲在小坑里打瞌睡。
“你买盐去吗?”阿拉美双眼微睁,有气无力,一字一顿地说。
“买盐。”
“别去了。”阿拉美说,“没盐了,卖盐的现在不卖盐了,卖米的也不卖米了,不卖了,没有钱了,窝窝头都吃不上了,他们都瘦了,都在家挖坑呢,他们的最后一把铁锹也快磨损了……什么?你不信?你去转转吧,我再睡一会儿……”
我在镇子里转了好几圈儿,也没见到一个卖东西的。搭着灰草棚的店铺就像一个个张着嘴的饥饿的小兽,它们的主人站在柜台旁,望着天花板,有的坐在门槛上,不发出一点声音,甚至懒得扭动脖子望一望远处大路上的情景。大路上丢满了铁锹把儿和装蚯蚓的塑料袋子,我一步一踉跄地走着,一只瘦狗在后面跟了我一路子,它在向我要吃的,几次都没能打走它。兜里的几个硬币发出清脆的响声,我吹起了自编的口哨,我不知道这是幸福还是悲伤。
暮色降临的时候,我已经走出了这个镇子。无边的旷野毫无遮拦地展现在我面前,地上交错着粗细不一的蚯蚓爬过的痕迹,仿佛一面构造复杂的大网,我感到一阵眩晕。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雪,我这才发觉早已进入了冬天,我得赶紧离开这里。积雪越来越深,我在最宽的一条蚯蚓痕里艰难地向前移动,一会儿就开始喘气了,我骂了一句,扔掉了兜里所有的硬币。前方不远,一个佝偻着背的老人向着大雪深处一瘸一拐地挪去。是阿拉美!我想叫住他,他不吭声。雪大块大块地落下来,他走得越来越快,他的背影慢慢变成一个细小的黑点,几乎看不到了。我疯狂地向前奔跑,总也追不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