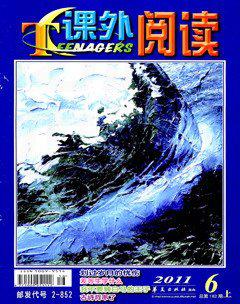大声说话的哲学
荣筱箐
我在报社做实习生时有幸师从一位见多识广的资深记者,老师洞悉世事,经常在谈笑间不经意地泄露天机。那天,他坐在办公桌前,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人的地位越高,讲话声音就会越低。
其实,好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讲话音量与社会地位间这种微妙的反比关系:贩夫走卒平头百姓人微言轻,即使把声音提高八度,也不见得能有听众;而重要人物声音越低,越是有人围在身边拼命地伸着脖子听,也就因此越发显得更加重要。所以,就算是天生的大嗓门,一旦意识到了自己的重要,为了显示身份也得练着压低声音。
照理,能够在简单的音阶之外,听出细微玄妙的层次和不可言传的内涵的中国人,对声音的理解和运用显然远比一根筋的老外技高一筹,但当东方遭遇西方,需要面对面出手过招的时候,我们却常常吃了哑巴亏有苦无处诉。不管是欲擒故纵的捻须沉吟,还是谦和含蓄的君子之风,不是被当做智能不足,就是被看成自愿放弃,在吞吞吐吐或默不作声中自生自灭。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对此心里最清楚。
华裔小学生,因为整个学期没有在课堂上讲过一句话,被老师认为有学习障碍,其实他一言不发,只是因为妈妈告诫他开口前要想好了再说。又有在大公司任职的华裔雇员,每次与客户开会时,只要他的顶头上司在场,他就尽量不说或少说,心里想着把表现的机会留给上司,结果却以沉默寡言、不善和客户沟通为由被辞退。
在美国,从带孩子做饭的主妇到无家可归的游民,甚至正在服刑的在押犯,都常常理直气壮地高谈论阔,指点江山,依仗的其实不只是肺活量和嗓门,而是对自己的声音如纳西斯对他的倒影般的迷恋和对声音的价值如对宗教一般的坚信不疑。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这多半被看做是自以为是,我们虽然常常在镜子跟前自我膨胀,却早就学会在走出家门时夹着尾巴做人;我们常常发些不疼不痒的牢骚,却早知道它在出口的那一刻就会随风散迹无可寻。我们其实不乏有棱有角的真知灼见,但往往还没开口,就被自己发出的一声冷笑弄得无地自容,而忙不迭地闭了嘴。越是这样,我们就越习惯悄无声息。
其实即使在美国,普通人的声音要想改变世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当听证会对所有人开放,立法者就必须对任何人的发言一视同仁地尊重和倾听。连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时,也常把水管工乔伊的话挂在嘴边,人们至少可以相信自己不是在自言自语,这时候,每个人多说一句,就可能发挥一份作用。
大声说话的人多了,声音才可能恢复其原本的功能和形态。人们不用整天绷紧着神经等着“于无声处听惊雷”,不用担心自己的声音吓到别人或是吓到自己,讲话也就有了底气。
想提高音量,最关键的也许不是练嗓门,而是练信心。
(老越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