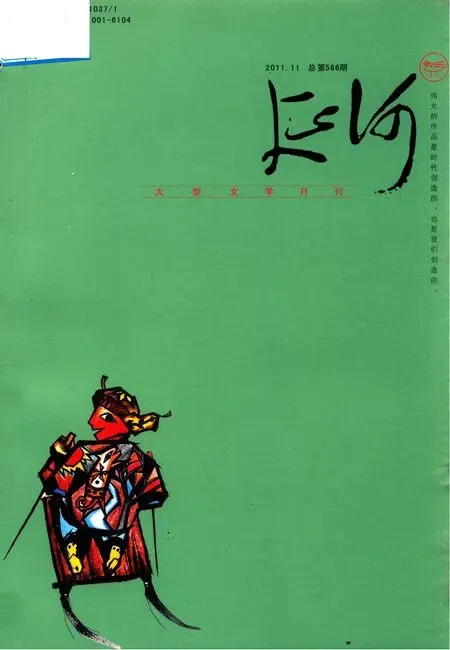藏枪记
常胜国
我是一个王
谣曲之王
在逝去的二十四个节令
我写下过二十四首纯净的谣曲
——李岩·歌民和歌王
一
“打死也不能说。”我又一次听到哥哥的声音,想起那个遥远的傍晚,我哥哥带回一条枪,那条枪装在一只厚厚的帆布袋子里,我哥哥把那只布袋抖开,但他只抖开布袋的一角就急忙又包起来了,他一脸惊慌地问:“你在干什么……人都睡了吗?”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傍晚的时候我趴在炕上画了一张画,临摹一个国际伟人的头像,画得不像样子。在画画的当中我又想加工一只弹弓,做的过程中那把生锈的老虎钳子把我的左手食指拧起一个血泡,就扔下不做了,我再去画画,把伟人的眼睛涂得像煤球一样黑,太不像了,也许没人能画好一个外国人,再说屋顶上吊的那颗灯泡也不够亮。我再去摆弄另一个物件,试着把一截自行车的链条拆开,加工成一件武器,这时我哥哥回来了,我把所有摆弄过的东西都丢在炕头一条牛毛毡上。
“都睡了。”我说。我的眼睛只盯着哥哥手里的布袋,急切地想看到布袋里面的东西。“你怎么知道都睡了?你就知道瞎说!”“我再去看看。”我开门出去,在大院里转了一圈,院子里住着和我们同样的十来户人家,我妈妈的屋子已经黑了灯。“都睡了。”我回屋又说了一遍。哥哥对我一脸的不满:“真不想给你看……”哥哥不情愿地把一支枪从布袋里提出来,我看见它像一个陌生的怪物,挺着僵硬的身体,黑色闪亮的部件非常严密地组合在一起。哥哥拉动枪栓,一颗金灿灿的子弹从枪膛里跳了出来,哥哥推上枪膛,让我试试。哦,这个家伙比我高大,我无法摆弄它。我把枪杵在地上,一只脚踩住枪栓往下用力,“咔嗒”一声踩开了枪膛,子弹又从枪膛里跳了出来。
枪和子弹都是真家伙,是一个女人交给我哥哥的,那个女人满脸麻子,用一个铁环束着头发。她曾和我的父亲一起去攻打一座县城,父亲把一台苏联制的拖拉机改装成装甲车,车上压上机枪。打完县城以后我的父亲死掉了,有人说他是被活埋的。那个冬天,女人把父亲从土里面挖出来,把一套灰色的中山服缝在我父亲僵硬的身体上,并让他手举一本红宝书。父亲被安放在一辆特制的架子车上游街。女人对我们说:你父亲是个英雄,不能就这么死去。游完街父亲的尸体不知去向。女人把一条枪交到我哥哥手里,准备让他去打仗,并准备把我哥哥培养成一个大人物。就在我哥哥准备去打仗的那天下午,那个女人被别人打跑了,同样不知去向。
哥哥再把枪装在帆布袋子里包好,我帮他把枪藏在一只老式的柜子底下。第二天一早,我们照例被母亲派出去“寻生活”。哥哥在一个建筑工地当了小工,而我每天从家里出发,臂弯里挎着一个柳编大筐在城里走一个圆圈或半个圆圈之后又回到家里。我出了大门,向一侧的巷子里走去,这是我家所在的居民区,离东门不远,标志的建筑是有许多高墙大院和一个很大的牌坊,牌坊下面的石狮子被人打烂了脑袋,上面的字迹也被人用斧头刻意敲打过,已经一片模糊了,任谁高兴还可以拿起斧头在牌坊上敲打几下,牌坊的立柱像两条粗壮的腿,但它无法行走,它已经岌岌可危了,但还是憨憨地立在这个叫东门焉的地方。离牌坊不远处就是我们的学校。我本来不该到这里来的,这里没有单位,不光寻不到生活,而且学校附近常常会遇到一些没意思的人呵斥我,因为他们是学校的老师,所以我没法跟他们计较。我今天真是魂不守舍,不知该去哪里寻生活,我一心只惦记着那条枪,如果不是哥哥语气严厉地一再叮嘱我不要动它,我真想拿出来好好玩玩。我沿着一条碎石路向居民区的髙阜走去,这条路的路面统一铺成向下弯的形状,住在上面的人家把这条路当做排水道使用,什么脏水都往下倒,所以这条路总是臭烘烘的,这时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路两边的垃圾地里生长一丛丛齐腰高的臭蒿。我差不多是一路踩着垃圾向高处走,来到东城区最高的地方。我站在一个很大的山包上,这个山包在两千年前就埋了一个很有名气的人,我一时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山包上有一个亭楼,我把筐子放在亭楼里,在亭楼的木挡上坐下来,整个城市就在眼前了,我家也就在山包下面不远的地方,我等于是在我家的脑畔上溜达,心里惦记着那条枪。我想起这个城市里最有意思的几个地方:青石街道两边的铺面,油漆的门板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打开,有时候我手里攥着几角钱等着铺面的门板打开,等得人心烦。有人从铺面里面摘下了门板,我一下子闻到了铺子里面的煤油、烧酒和糖果的混合气味;离南门口不远有一条小街,小街上有一个鸡肉馆,买鸡肉的都是合作社的老头子,做好的烧鸡都放在玻璃罩子里;南门外就是电影院,每一部电影都放映三天,影院守门的管理员都是没意思的人,没有票谁都不准进去。

李樯摄影作品·北方风景系列 陕西榆林 1994年
我突然想起我的筐子还是空空的,我得装点什么回家。
我提上筐子从山包的另一侧取路下山,这里有一个粮站是供应我们那个居民区的,现在还没有上班。我在粮站的院子里转了转,没有发现可取的东西。在下山进城的路上要路过文庙石牌坊,牌坊比东门焉的那个小一点,还有一个小门洞,叫进士圪洞,因为进城赶集的农民找不到厕经常在这里拉屎撒尿,所以又叫尽屎圪洞。
我沿着青石铺就的街道行走,要在某个院子里寻到今天的生活。我钻进一个单位的院子,鼓捣一会儿以后又转到街道上确定下一个要去的地方。我拣煤渣,拣破烂,拾粪便,这些脏东西最后都被转换成另一种物质填进我们的肚子里去。我去的最多的地方是父亲曾经所在的工厂,那个墙院里面到处都在冒蒸气,地上撒满了煤渣;一只黑黑的电磨子在飞快地转动,生产一种叫火药的非常重要的东西。今天我还是去了我父亲曾经所在的工厂,我认识的人和我不认识的人都跟我打一两声招呼,他们对我说:“提走吧,以后再甭来了。”而我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可鼓捣的东西时还是要到那个墙院里来。这一天上午,我寻到的生活是一筐烧过一半的煤球,我提着煤球回家的时候,院子里的人家都在做饭,浓烟笼罩在院子的上空。我的朋友大满兄弟他们家烟囱不上烟,大满呛得鼻涕眼泪,手里拿着一个片子在门口起劲地呼扇着。夜里,哥哥从工地上下班回家,我想跟他提一下枪的事,他一脸愠怒,连半个字都不让我提。其实我只想告诉他,我一整天都没动那个帆布袋子。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也就这样过去了。
哥哥被做裁缝的母亲打了一顿,打得哥哥杀猪似地叫唤,这是暑假最后那几天的事,因为哥哥开始不去工地正经干活了。哥哥不去干活是因为有人开始追查枪支的下落。不知谁在城区的山头上打了一枪,枪子打中了一个在马路上行走的无辜的农村女人的屁股。调查事件的人是公安局的,名叫“王家的三儿”。三儿挨门逐户地查问,问人们有没有看见谁藏了枪弹。眼看三儿就要查到我们这片居民区了,我哥哥每天晚上像耗子搬东西一样,把那条布袋里的东西搬来搬去,白天他察看藏枪的地点,发现那地方很容易暴露,晚上就再转移一次。“打死都不能说出去!”哥哥对我说。我从家里走出来,沿着一条长长的石板坡道开始在城里画圆圈的时候,看见三儿在不远处与人谈话,我很快地走掉了。
我从文庙的石牌坊下面走过,走进一所空旷的学校。红军转战陕北的时候,许多新中国的缔造者曾在这里上学。我想在学校里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帮哥哥把枪藏起来。我从学校礼堂破烂的门缝里钻进去,绕过同样破烂的连背椅,跳上讲台,再扶着一道咯吱作响的楼梯爬上阁楼,那里漆黑一团,我划了一根洋火,看见阁楼连接墙壁的地方有一个蛛网密布的破洞,我从洞里爬进去,我又划了一根洋火,看见里面的图书堆成了山。
我告诉哥哥,我找到了一个藏枪的好地方,哥哥不以为然,他根本不相信我能找到更好的地方。而当我把最初的几本书籍换成砉砉作响的钱币的时候,我再也不想把这个地方告诉任何人。
我和哥哥去上学,我哥哥对学习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放学以后很自觉地在家里读书。母亲说我哥哥懒惰,害怕放下书本去做别的活计,后来我哥哥就在被窝里用功;我和他睡在一个炕上,看见他爬在被窝里,把书和本子放在枕头上写字,数着指头努力地要确定某一个数字;他常常以为我很早就进入梦乡,悄声拿出纸笔,惟恐有人发现他用功读书。有一回他告诉了我一个数学名词叫“有理数”,第二天我坐在教室里等老师讲有理数,等了很久老师都不讲,后来我一想,也许要等好几年老师才能给我讲有理数。等老师背过身去往黑板上写字的时候,我打开教室的窗子很麻利地登上课桌跳到教室外面去,穿过哇哩哇啦的几排教室,很快就溜出了学校,我心里想:去他妈的有理数。
我从文庙牌坊下面走过,走进那所空旷的学校,穿过连背椅,跃上讲台,登上阁楼,像老鼠一样在黑暗中行进;我钻进墙上的破洞,从口袋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洋火和洋蜡,这个厅堂的地板上堆的是书,架子上搁的还是书,这些书已经非常陈旧,并且正在发霉。我在我空空的书包里面装满了这些发霉的图书,又在腰里别了几本图书,整理了一下衣裳,背起沉甸甸的书包向街道进发,我找到那个摆书摊的残障人,换得3元钱。我回头再去厅堂里取书,这一回我拣的是被老鼠糟蹋得不成样子的图书,把它送到废品收购站,得了7角钱。
我花了一分钱在南门小巷的鸡肉馆里买了一根鸡肠子,慢慢地把它吃下去。一只玻璃罩子下面放着一只金黄色的烧鸡,翘着老高的屁股,它的脑袋被放在另一个玻璃罩里面,卖3分钱;我哥哥经常给鸡肉馆的老爷子们挑水,每挑一担水赚5分。我一辈子也不想给鸡肉馆的老爷子们挑水,早晚我会掏钱把玻璃罩下面那只金黄色的烧鸡吃掉。
我妈妈又把我哥狠揍了一顿,打得他杀猪似地叫唤,原因是他以学习为理由拒绝去拣煤渣。那天晚上我在一支并不明亮的灯泡下面看见哥哥躺在被窝里啃他的有理数,一张被泪水弄脏的脸上带着专注的神情,一只苍蝇在他的头上盘旋着俯冲下去,我仔细一看,他的头顶上开了一个小口子,苍蝇叮在红色的血痂上面不肯离去。这肯定是在拣煤渣的时候被别人打的。我有点同情我的哥哥。我决定带他去那个藏宝的地方。第二天下午,我把哥哥领到礼堂阁楼上那个破洞前,首先看到的是成群的老鼠在书山上面动弹,烛光下,它们瞪起黑亮的小眼睛注视着我们。
我哥哥掉头往楼下摸去,他说:“我讨厌老鼠。”
星期天,我从我自己的一只胶鞋里面挖出脏兮兮的一卷小钱,领上大满等几个朋友去游泳池里游泳,给他们每人买了一根冰棒,之后又请他们到电影院里看电影,电影开映后,大满兄弟说后侧座上坐着一个穿新衣裳的女娃娃。我从大满手里接过一只弹弓,装上纸制的子弹,朝女娃一弹弓射过去,然后继续看电影。
我花光了那只鞋子里面所有的钱之后,又回到阁楼上去,我想取些书去换钱,但是我累了,我倒在书里面睡了一觉,醒来以后发现老鼠正在啃我的腿肚子,已经啃得鲜血淋漓。我拿起书本一边还击,一边咒骂。我要买一口袋老鼠药给你们过生日,然后再看看这地方到底是谁的。
秋天的时候,我的母亲给我和哥哥各扎了一套衣裳,是用日本的尿素袋子缝制的,我哥哥不肯穿那套衣服,又被母亲扇了一耳光。我穿起日本的尿素袋子,穿过牌坊,直奔那所学校。走进大门后发现王家的三儿正在向几个玩耍的孩子调查枪击事件,他看了我一眼,我无缘无故地掉头就跑。“站住!站住!”三儿在后面直追过来。“站住!日你妈站住!”我冲过牌坊,一口气冲上了东山山巅,山上有一个亭子,亭子里挂一口明代的大钟,足有一间小房子那么大,我钻进钟肚子里,像壁虎一样攀住铸铁的内壁,三儿喘着粗气追上山,“他妈的!”他说。他咳嗽,唾痰,绕着亭子转了一圈以后搜索下山。我从钟肚子里钻出来,我撒了一泡尿,风把尿水挡回来,淋湿了我身上崭新的尿素袋衣裳。
二
母亲领着我和哥哥去一片乱坟岗给父亲烧纸,我们都不怀疑那一堆土里面埋的就是父亲,正如许多次我莫名其妙地跟着别人伤心哭泣,但我并不知道谁死了而我为什么要哭。
父亲和母亲站在大河的岸上捞河柴,大河里浊水汹涌,使人晕眩。父亲站在岸边没膝的浊水里,母亲挺着大肚子。一条小河和大河在城北的一个地方交汇,一路向东流向黄河,东门楼在大河西侧高高矗立,两边城墙依稀,城墙下的石崖上刻着一个古人的手迹:钟灵毓秀。在更高的地方,人烟稠密,拥着一个山岗和一座祠堂,那是我们家所在的居民区。当年秦太子扶苏曾在那里点兵点将,并在北门外的校场滩里练兵,以后又自杀在城内的某个地方。母亲肚子一阵剧痛,一头栽倒在河滩里,父亲慌了手脚,捞到的河柴又被水流卷走。父亲挑起筛担,一头挑着母亲,一头挑着一块石头,急急入东门,扶遥而上。母亲生了,是个小子,父亲在地上团团转,嘴里咕噜着一个早已成熟的名字:“狗蛋狗蛋。”隔了一年母亲又生了一个,这回母亲想生一个女娃,母亲说:养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铰的。生下来见是小子,母亲改口又说:养小子,要好的,穿蓝衫戴顶子。父亲在前窑里大声问,生了个甚。母亲回答:二蛋。
父亲穿着背带工装裤,戴着一顶深蓝色的鸭嘴帽,前往上海的一个机械厂参观学习,他的一张黑脸带着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神气,操着一口哇哩哇啦的土语,上海人根本听不懂,上海人问父亲:侬是不是柬普寨公民,父亲哈哈大笑,回家以后给狗蛋和二蛋各做了一套工装裤和一顶鸭嘴帽,父子仨以立正姿势,向柬普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致敬。
我和哥哥去上学,老师冲着狗蛋和二蛋的名字犯难,他想以毛泽东的“泽”和“东”分别为兄弟俩重新命名,被犟头犟脑的狗蛋拒绝了。
有一天,我哥放学以后想把自己的鸭嘴帽戴在家里的一尊佛的头上,佛是父亲从上海以柬普寨公民的身份买回来的,对他呵护有加,早晚上香参拜。哥哥把自己的帽子戴在佛的头上,佛突然倒在地上,啪的一声碎作一堆。“老人家!”父亲说,“小孩不懂事,冒犯之处还请见谅。”他把那一堆碎瓷片盛在盘子里,放在桌子上继续上香供奉,那一天,母亲给我们做了一顿鸡蛋和烙饼,之后我有两年多没有再吃到煎鸡蛋,也没有吃到一顿肉。过年的时候,父亲让我们对那一盘碎瓷片顶礼膜拜,父亲因为没有肉供奉那堆瓷片而发出长长的无奈的叹息。又过了一年,父亲清理了盘子里的碎瓷片,并且把家传的几张古老的字画放火烧掉,以后又跳到房顶上把兽头砸了,把雕有各种神怪的盆砖砸了,把花墙砸了。我和哥哥回到家里,那个大大的高雅的庭院被父亲砸得面目全非,母亲在哭泣中清理着一堆又一堆的废砖烂瓦。
父亲下班回来,把一个酒瓶塞在我手里,再给我几角钱,要我到街道上给他打几两散酒,我给他打了几年散酒,有时赚他几分钱,有时一分钱也赚不到他的,我不情愿去,他就踢我一脚,我给他的酒瓶里兑水,他喝了几口之后大怒,叉开手指劈头盖脑打过来,母亲来护我,连母亲也打在一起,打得母亲口鼻出血在地上呻吟。冬天,父亲领着我到一个亲戚家吃喜宴,有酒有肉,父亲吃醉了酒,被人抬到房里睡觉,随后有人要我回家给父亲取棉裤,说他尿湿了裤子,还尿湿了炕上的铺盖。我回家向母亲要裤子,母亲一听便瘫在了地上。
麻脸女人到家里来找我父亲,常常是吃过饭以后来,她坐在一把椅子上抽烟。她以嘲讽的口吻对父亲说:你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而她自己如果打不倒XX人就一辈子不结婚。说话的时候带着一脸坚毅的神情。“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父亲喝着酒,激动得满脸通红,握紧拳头把桌子擂得嗵嗵响。一日,麻脸女人走后,父亲穿起他的背带裤,戴上深蓝色鸭嘴帽,在镜台前照了又照,随后带着酒气走出门去。第二天,他和麻脸女人集合一帮人去抢一个弹药库,没有成功,父亲被麻脸女人指派回厂去制造一门大炮,大炮在河对岸的工厂里制造成功了,他们把它放在河畔上朝东城门的方向试射,父亲没想到炮的威力会那么大,射程那么远,一炮就把城墙石崖上钟灵毓秀四个字炸个稀烂。
多年以后,麻脸女人在一间垃圾成堆的房子里抽着廉价的烟草,用沙哑的嗓音告诉我,你父亲的坟不在乱坟岗,他安葬在革命烈士陵园的旁边。那年冬天,父亲游完街后,一场武斗开始了,他僵硬的尸体被拉回指挥部,在一张桌子后面,在武斗领导人的背后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由麻脸女人亲手埋葬。
我担心藏宝的地方被人发现,就加紧往外搬东西。我找了两条小麻袋,装满书后双手拖着到废品收购站卖掉。我翻动最后一个书架的时候看到一窝小鼠仔在架子的底层动弹,我移动着手里的洋蜡,它们在强光下面闭着眼睛,我捏住一只小老鼠的尾巴把它提在空中,它不情愿地在空中挣扎。鼠妈妈蹲在书架上面望着我,我把小东西放回窝里继续装书,最后一本书我别在裤腰带上,用我身上崭新的尿素袋盖起来。我拖着两个麻袋走下阁楼,走出礼堂,我站在空旷的操场上回望礼堂,一只老鼠蹲在阁楼的窗眼上久久地注视着我。我系紧自己的裤带,抓住麻袋角,拖着它们离开了礼堂和学校。
那天下午,我来到鸡肉馆,指着玻璃罩下那只屁股翘翘的烧鸡说:“我买它。”掌柜的老头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我说:“两块。”我点给他两块钱,接过那只烧鸡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吃起来,一只狗在我周围转悠了很久。我包了一只鸡腿给哥哥吃,他接过鸡腿贪婪地嗅着,好久都没舍得吃。
我装模作样地去上学,趁老师不注意的时候跳窗逃走,继续在街上画圆。我在南门口又碰上了王家的三儿,我想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立在南门洞的墙壁上,看着三儿朝我走过来,他抓住我的衣领问我:“上次你为什么跑?”我说我不知道枪在哪里。“我问过你枪的事吗?”他说,“你小子什么都知道,老老实实地跟我走。”他抓住我的衣领一路提溜往一个地方去。路上许多人尾随着,问三儿是不是又捉了小偷了,三儿说你们都去吧,什么事都没有。三儿把我带到城内文庙的庙堂里,这是派出所办公的地方,三儿坐在原本立着神像的位置上问我叫什么,我说我叫二蛋。他说老老实实把一切都告诉我。我说我不知道枪在哪里,他把桌子一拍,大声问:“你偷过人没有,偷过东西没有?”我说:“我没偷过人,我拣的都是破烂货。”他说:“我再问你,枪在哪里?”
“我不知道枪在哪里。”
“你看见什么人有枪?”
“我没看见。”
“如果你不说,今晚上你就回不了家了。”
我站在墙角继续抵抗。三儿走过来朝我脑袋上打了一巴掌,说小子你是个小流氓,我才发现你是个小流氓,老子专治的就是小流氓。
我突然止不住地掉起眼泪来,我开始浑身哆嗦,我想撒尿,我想回家,我想离开这里。
“不要哭。”三儿继续说,“把你知道的事情都告诉我。”
我想不哭,但是眼泪不住地往下掉。我哽噎着说:“我什么也不知道。”
三儿把我的姓名、年龄、学校、住址、父母姓名都问了个清楚,然后说,明天把你的母亲叫来,你也一起来。
我回到家里什么也没说。第二天我一早就出去,我躲着所有的人,夜深以后我回到家里直接就睡觉了。第三天,我们全家人被校长请到办公室,我一看到三儿也在那里,浑身就哆嗦起来。三儿告诉我母亲:要好好配合政府。他说,我们做过调查,你的丈夫造过枪炮,搞过武斗,他死了我们就不说他了。但是经过调查,有人看见你儿子藏有枪支,这是对人民的犯罪。你们的父亲是个很没脑子的人,你们不要像他那样,不要向他学。“现在请你们告诉我,枪在哪里?”
“我一点也不知道。”母亲看着我和哥哥,“你们告诉人家枪在哪里。”
我哥哥摇了摇头说:“不知道。”
我也摇了摇头说:“不知道。”
母亲征得三儿同意,要把我们领回家进行劝导,校长说,你们回家去,什么时候把问题交代清楚了,什么时候再来上学。
哥哥终于对母亲说了实话,说他藏了一支枪,是麻脸女人给的,现在藏在烂泥滩的炕洞里。
我奇怪我母亲并没有痛打我哥哥。她叹了口气说:“那你把枪送给人家。”
我说:“妈妈,不能把枪交出去,不然我哥哥会坐牢的。”
我母亲没有听我的话,她决定去问一问三儿,事情到底有多严重?三儿说把枪缴出来就没事了,政府的政策是宽大的。越快越好。
那天晚上,母亲告诉我哥哥明天去缴枪。我哥哥把书抱在被窝里写作业,突然流起眼泪来,说不知道学校还让不让他继续念书。我说学校是个球。我去找我的朋友大满兄弟,说我需要帮助。大满说这有什么难的,把枪拿给三儿就是了。大满找了把手电筒,我们一起去烂泥滩的窑洞里挖出那条布袋和布袋里的枪。北门外的烂泥滩曾经有我家一块地,如今只剩了一孔破窑和一个小院。我们找到王家三儿的家,大满去敲门,并且直着嗓子说,王公安,我们给你送枪来哩。三儿在屋里把事情问清楚,但就是不开门,最后说你们回去,明天把枪送派出所里。大满说我们就是要今天送,明天麻烦哩。三儿在屋里骂起来:你妈个X!想弄甚哩?想行凶哩是不是!大满也是个没脑子的家伙,跟着骂道:日你妈!我给你妈X上钉铁环哩!王家的儿,出来爷爷我一枪嘣了你。
三儿说好小子,老子不叫你坐大牢就不姓王。
我们叫不开门,送不了枪,只好回去了。第二天三儿带了几个公安到我家里带走了我和哥哥,后来我放出来了,哥哥却被关了起来。
三
我的母亲来自一个遥远的山村。她的幸福生活从我父亲开始酗酒以后就结束了。父亲有一只用钢珠加工成的不锈钢酒杯,它可以盛酒,也可以对付我母亲。母亲对父亲的荒唐事说半个“不”字,父亲就饮尽不锈钢杯子里的酒,把杯子砸在我母亲的脑袋上,留下一个又一个伤疤。父亲心情不愉快,就逮住一切东西出气,包括我和哥哥。他把我举起来随便往什么地方扔,我母亲这时候就跟他拼命,直到被父亲打得爬不动为止。
我和大满兄弟去乡下收购鸡蛋到城里来贩,我在乡间的一条土路上看见一只母鸡引领着一群毛茸茸的小鸡慢悠悠地从路上经过,一只狗想沿着土路朝前走,但是它碍着小鸡的事儿了,被鸡妈妈好一顿乱啄,狗只好灰溜溜掉头而去。我在小鸡的旁边拍了一巴掌,鸡妈妈张开翅膀从另一头追杀过来,一副冲我拼命的样子。我被鸡妈妈镇着,站着不动,看着小鸡们叽叽欢叫着离开土路,钻进草丛里去,大路朝前各走一边。我突然掉起眼泪来,大满说,你个傻瓜,你冲着鸡哭,鸡就给你下蛋了?
我说,我想起了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在我哥哥被捕后找王家的三儿算账,她理论道:那枪是公家人交到我儿子手里的,还指望他拿枪闹革命哩。他哪里会打枪!那个女人的屁股是我儿子打的吗?你看见了吗?当初你说枪缴上来就没事了,怎么就把我儿子关起来了?三儿呀!你好好拍拍良心,你老子你娘找我扎衣裳,几年我没收过他们一分钱,你怎么就不讲点情份,怎么就知道欺负我们孤儿寡母!
见三儿不领情,母亲就指着三儿的鼻子骂:“三儿,你是个狗娘养的!”三儿说:“你骂,连你抓起来坐牢。”母亲大怒,一拳把三儿家的玻璃砸个稀烂,又一头把三儿撞了个仰面朝天。三儿连滚带爬,说反了你!反了你!
母亲的头发乱成一堆,母狮一般发起威来,把三儿家自鸣钟砸翻在地,冲着三儿咆哮:“把我儿子还给我!”
母亲从三儿家一直闹到公安局,她三天没吃一口饭,我去找她,她说儿子我顾不了你了,你各自活去吧。公安局长问她:“你为什么闹?”她说:“我要我儿子。”局长说:“你儿子犯了法,由公安看管着哩。”母亲问:“我儿子犯了什么法?”
“藏枪的法。”
“枪不是你们给的嘛!”
“谁给的?”
“麻脸女人给的,她和你们一起工作。”
“为什么藏起来不缴?”
“枪不藏起来不是要出天大的乱子嘛!”
“胡搅蛮缠!你说放人就能放人?王法是儿戏吗?出去,轰出去!”
三儿问局长,这些人都是街上的无赖,天不怕地不怕的。他们再来家里闹怎么办。
局长气呼呼地说:“我知道怎么办?”
“那就把那小子放了算了。”
“胡说!”局长再一次说,“王法是儿戏吗?”
母亲被公安局轰出来,她堵在公安局大门口等局长,等了很久都没见局长出来,母亲就对进进出出的人说,我给你们公安局做饭行不行!我不挣你们一分钱,只要让我照看我的儿子。
我在邻居的周济下过了好些日子。我开始在邻居的指导下熬一点稀粥给母亲喝,后来我很快就学会了做饭。吃饭的时候我拿出两副碗具,母亲骂我没脑子,说你哥难道就永远不回来了?给你哥的碗筷拿上来,盛上饭。我睡觉的时候也要把哥哥的被褥铺张开来。否则又要被母亲骂。我常常在夜里被一种响动惊醒,那是哥哥在被窝里翻弄书页的声音。
哥哥被捕以前有人托媒向我母亲求婚,别人说我母亲能干,又是个好裁缝,人也长得漂亮,就是两个十七大八的儿子拖累着她。母亲说谁好心把我两个儿子抚养成人,我就给谁当牛做马,我说到做到。别人说狗蛋他娘你终究是个有福气的人,会有好结果的,又指着我说,二蛋如果是个女娃你就更不愁了。
有人送给我母亲一套新衣裳,也送来好吃的东西。哥哥被捕以后,母亲因为得不到别人的帮助,就把别人送她的新衣裳扔到垃圾筐里倒掉。别人说我的母亲是个好女人,就是太厉害了,这么厉害的女人谁还敢要。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沿着长长的青石坡,经过文庙石牌坊,到街上去画圆,我常常什么也得不到。我不像以前那样放着胆子去拿取身边碰到的有用的东西,这么做一定损害了别人利益。母亲上班以后,我回到家去翻可以变卖的东西,把翻出来的破铜烂铁卖掉。我母亲多年以来一直把锁着一只笨重的老式柜子,不允许我和哥哥去碰它,我不知道那里面到底有什么,时常惦记它。趁母亲不在家,我找来几样父亲留下的工器具,并不费劲就把锁子给弄开了,我打开两扇厚厚的门,里面黑黑的,看上去空无一物。我伸出手臂往里面摸,摸到一根冰凉的管子,捏了捏,有点沉重,用力一拉,拉出一件东西来,一看就知道是我父亲的手工,钢铁的管子已经生锈,它是那样粗笨,那样的不合时宜,却又那样使人怦然心动。
——那是一支枪。
四
哥哥上小学的时候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我想他先是为了一张挂在墙上的奖状而发奋读书,然后才举起拳头,为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他仍然是班级的第一名,许多花朵一样的女学生经常跟在哥哥身后问这问那,哥哥很腼腆,每次都是红着脸作答。我想他那样用功学习,坚持在被窝里弄清楚一道道难题,是为了更好地把花朵一样的女学生留在自已身边而不让她们跟着别的男生。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我们走出学校,都要去上山下乡,然后走进工厂,谁会去想远大的前程。
我哥哥走进看守所的第一句话,是噙着眼泪问看守:“我还能上学吗?”看守回答说:“你当然不能上学了,你要劳动改造。”
哥哥又问:“我能自学吗?”
看守说:“这要看情况,看你表现如何。”
我和妈妈去看哥哥,在离城十几里远的山沟里,我和妈妈被告知站在远远的地方看,我看见哥哥被剃了光头,穿着灰色的单衣,和一群人在一起填一条沟渠。妈妈已经哭倒在地上。冬天的时候我又去看哥哥,他和一群人在一个院子里无目的地行走着。
我已经在一个街道办的搬运社里扛了一年大包,一天晚上,我正和母亲一起吃饭,照样把哥哥的碗筷放在桌子,有人推开门进来,是个公安,他问有没有别人在我家里,母亲说没有,我儿子出什么事了吗?公安说你儿子回来了,他来取学习用具。
我哥哥从门外闪进来,叫了一声“妈”。公安说,别说话,收拾了东西咱们走。妈妈和我立在地上不知做什么好。我看见哥哥紧闭的双唇在颤抖,仿佛就要哭出来了,但哥哥没有哭,他说我来取书和学习用具。我和母亲手忙脚乱地去收拾东西,装满了一书包,公安过来检查了一遍,说该走了。母亲说我能不能给儿子做一顿好饭吃?公安说绝对不行,他回家看你们这已经破例了。我母亲一再请求,说不能做饭就买一点好吃的让儿子吃上一口,公安想了想说,那就快一点。
母亲问哥哥想吃什么,哥哥说什么也不吃。我说,吃鸡肉。我夺门出去,飞快地跑到鸡肉店,买了玻璃罩下那只屁股翘翘的烧鸡,拿回去以后哥哥却没有吃,临走时哥哥又一次颤抖着绷紧的嘴唇说:“妈妈我很好……”
我掰了一只鸡腿在后面撵哥哥,我说:“哥哥你吃上一口。”哥哥回过头说:“好好照看咱妈。”
以后我又去看守所去看哥哥,却总也看不到他,犯人们有时在挖山填沟,有时在担水浇沟里的菜园子。一次,我大胆而小心地凑近一个犯人,问他看到我哥哥没有,他想了想悄声说,你哥哥在所里面学习哩,他现在是我们的文化教员。
我妈妈给公安局长的母亲做饭洗衣裳,一年里从未间断过,从来不收一分钱的报酬,局长多次拒绝都没有成功,随后就由着她去了。局长说,你有一个好儿子,比什么都强。最初,有人向局长汇报说,看守所里有一个孩子,不分白天黑夜地写作业,发给犯人的擦屁股纸,每一张上面都被他写得密密麻麻。局长给看守吩咐说:“这孩子是个奇才,你们听着,让孩子边劳动边学习,学习的时间要大于劳动时间。”局长与我哥哥第一次见面,问我哥为什么那么不要命地学习,哥哥回答说,我从小什么事都做不好,也许以后也做不好,所以我只想做好一件事情。
一年以后,看守所允许哥哥每周两天时间在学校里上课,一辆吉普车准时在哥哥放学以后把他接走。哥哥偶尔也回家里坐一坐,但他从不吃饭,也没有同学来,我再也没有看到花朵一样的女同学跟在他的后面。
有一天下大雨,放学以后那辆吉普车过了很久都没来接我哥哥,哥哥回家要了一件雨披,要走回十几里路外的看守所去。我和妈妈劝他在家里住一晚上,他不同意,说这违反纪律。他动身的时候我找来了大满兄弟,我们推了一辆自行车,但是雨太大,三个人根本无法骑车行进,我们就推了车往看守所走,走到看守所,那里大门紧闭,岗楼里也没有值班的人,哥哥也没有叫门,他让我们回去,他站在看守所大门的照明灯下一动不动。我和大满离开他,在漆黑的雨夜里往回走,回头看见哥哥还站在那里,我叫了一声哥哥,哥哥没有听见,我泪如雨下。
一天,我去街道办的搬运社里上班,看见一群人揪着一个老头在街上游行,那人胸前一块牌子上写着“历史反革命”。我仔细地瞅那人,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竟然是公安局长。他身后跟着王家的三儿,他在振臂高呼:打倒!打倒!
我想起老头在公安局说过的那句话:王法是儿戏吗?王法确实不是儿戏!
那以后,我哥哥再未被允许去学校上课,再也没有回过家。又过了半年,我哥哥出狱了。这一年,全国恢复了高考。哥哥差不多是从监狱里直接走进考场大门的。我哥哥戴上了眼镜,一条镜腿不见了,代之的是一根蓝色的鞋带。哥哥虽然被破例允许参加高考并以全县理科状元的身份考上了首都的一所大学,但是政审未获通过,哥哥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
五
母亲说,大满那孩子没脑子,你跟着他会吃大亏的。
从前我和大满去偷农民的西红柿和黄瓜,都是大满提议的,他说有一个好办法可以让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农民菜地里的东西拿到手。我只同意做危险性较小的事情。大满把我领到大河边,两人做了分工,他往上游走,我往下游走,他在上游钻进农民的菜地里摘瓜摘菜,扔到大河里让它们顺水漂下来,然后他若无其事地打着口哨走出菜地;我在下游从水里捞起漂下来的瓜菜,若无其事地装在筐子里提走,我们到了安全的地方平分。
我父亲和麻脸女人计划去抢一个弹药库,没有成功,后来弹药库被另一些人打开。城里的大事大满总是第一个知道,他站在我家门外用口哨给我送暗号,从口哨里听出大满在呼我父亲的名字。你妈有野汉子哩大满,你又在骂我爸爸,他拉着我往弹药库走,人们把枪支从弹药库里运出去,未及运走的子弹箱垛在地上,上面标着一千发的字样。大满率先打开一个箱子盖,里面是排放整齐的纸包,抖开纸包,一排排金灿灿的子弹真叫人欢喜。大满一把一把往口袋里装,跟着我也揭开了一箱子,与大满比着速度往口袋里装子弹,顺手又拿了一些弹夹。我们离开弹药库,到僻静的地方把子弹一颗一颗插到弹夹上去,我插满6个弹夹,大满插满5个。正在我得意的时候,大满掏出一枚铜质的雷管,说二蛋你有这个吗?说着话,他拉动雷管上的引爆线,把雷管扔到远处,咣的一声炸起一团火光。
共和国缔造者们创办的学校里发生枪战,两股武装势力你攻我守,从头天下午打到第二天下午。枪声响起以后,有人在石坊下面挑着一担水,子弹把他的一只水桶打开一个窟窿。枪战结束后,大满打口哨约我,我们挎上筐子胆战心惊地走进那所学校,有人打手势要我俩过去帮他把地上的自制手榴弹提到操场上面的窑洞上去,提完手榴弹,大满问那人,说我们能不能扔两个手榴弹耍一耍,那人让大满把一筐手榴弹提到硷畔上,往下面一个空院子扔,我捂上耳朵看大满扔了一个,但没有响。那人叫大满捡回扔出去的手榴弹,给大满演示怎样投弹,并把一颗手榴弹投到下面炸响,大满学着他的样子拧开保险盖,拉动引爆线,把手榴弹扔下去,爆炸声响过之后,刺鼻的浓烟从下面冒上来。我和大满把一筐手榴弹扔完,那人夸大满有胆量,说窑洞里还停放着两个死人,问大满敢不敢看,我们走近窑洞,踮起脚从窗洞往里照,果然看见炕上躺着两具血乎乎的尸体。我们把弹壳和弹片装进筐子里到废品收购站卖掉。大满想把一枚雷管加工成烟嘴,他想用钉子和石块把雷管打通,打了几下雷管突然爆炸,把大满炸得满脸是血。
大满比我更懂得怎样生存下去,多年以来,他一直提着一个遮盖严实的篮子,盛着白生生的蒸摸偷偷地到街上去卖。当年卖蒸摸差不多像现在贩卖鸦片一样,是被禁止的。当年直到以后,人们从生存需要出发,权衡了生存和风险的利害关系后,始终在进行着一些黑市勾当。
我母亲告诫我别跟大满瞎混,说大满没脑子。那时候大满要我和他去乡下收购鸡蛋,到外面去进销服装。他叫我和他一起穿紧身的喇叭裤。我担心被人骂,后来经不起他再三劝导就穿起来了,结果我们一走到街上就碰到了王家三儿,三儿冷眼瞅过来,我就像犯了罪一样躲着他的目光,但还是没有用,三儿以所长的名义要我们跟他去派出所,并喝令我们把裤子脱下来,他说:“你们羞先人哩,穿球得怪里怪气,小流氓习性永不改。”我把裤子脱下来,三儿拿过去扔到庙堂外边,我下身只穿一条松垮的短裤。三儿要大满脱,大满不脱,他争执说:“我为什么要脱?我的裤子是自己花钱买的,又不是偷来的。”三儿说你自己花钱还想上天哩。把大满逼到墙角脱了他的裤子,大满里面什么都没穿,瓷实的腿股之间吊着一个灰溜溜的小东西。三儿冷笑着说,看老子管了管不了你!
三儿给大满一条花裤衩让大满穿上,然后把我们一起驱赶到街上去。
“日你妈呀!”大满站在街上高声骂,“日你姓王的亲妈呀!”
回到家,大满越想越气恼,大满说我们已经长大了,还被别人这么欺负,不报此仇枉为男人。他做了一个复仇计划:往三儿家门上扔狗屎,用石块砸他们家玻璃,打闷棍等等。后来又把第一个计划推翻。他想起自己还藏了一颗手榴弹,说他决定用手榴弹给三儿一家伙。
等大满把计划做完了,我说,你什么也别做,几年以后也许我们有权利让三儿赔我们一条裤子,并且给我们道歉。
大满说,谁耐烦那些事情。
大满真是个没脑子的家伙。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和他上街去溜达,又碰上三儿,大满小声骂:“三儿,我穿你妈的花裤衩哩。”三儿哪里肯受,扭住大满就是几个耳光子,打得大满口鼻流血,大满用头抵着三儿:“王家的儿,你打死我。”三儿拳脚一起来,把大满打得满地乱滚,我从近处摸了一块半砖,照准三儿的额头砸下去,三儿捂着额头倒在地上挣扎去了。
母亲把我和大满藏起来,派出所很快就派人来抓我和大满,没有抓到,他们把我母亲带到三儿那里,母亲给三儿二百元医疗费,三儿说你收起来,给你一天时间,明天捉不到你儿子,就抓你去坐牢。和尚跑了,庙跑不了。
母亲回到家里没有过多地责备我和大满,她说你们逃,今晚就逃。她打开那只紧锁的柜子,摸出那支枪,用一件旧衣裳包起来。“等着我,”她说,“我要把这件东西还给人家。”
多年来,母亲一直把家庭的不幸迁怒于满脸麻子的女人,并怀着深深的仇恨。我为这支枪担忧过,但我不曾和母亲交涉,我知道和枪一起锁着的是母亲的沧桑和机密,这是一个绝对的私人的空间,它也许对我母亲的生存十分重要。
母亲带着枪出了门,我和哥哥,还有大满都远远地跟在她身后。她过了东门焉牌坊向东城门走去,出了城门是一片阡陌纵横的菜地,蛙声在菜地间此起彼伏,我母亲走进菜地,走到大河弯曲的地方,那里有一间破烂的小房,亮着微弱的灯光,小房的四周垃圾成堆。
“你是XXX不是?”母亲在破房子里大声问。
“是。”
“我来还你一件东西,认识这支枪吗?恶魔,你害死我丈夫,这还不算,你还害惨了我儿子,害惨了我们全家,你没有资格再活在世上!”
母亲声泪俱下:
“老天开眼,我儿子们都长大了,是两个争气的儿子,有骨气的儿子!恶魔,你去死吧!以一个母亲的名义,我要把你打下地狱!”
母亲抖开旧衣裳,端平了那支粗糙的枪。
很久以来,我一直可笑地认为,以我们的不幸遭遇,有人会给我们一定的补偿,有人会允许我们从生存的需要出发做一点出格的事情,但我们从未被允许。这使我觉得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而那天晚上,我发现我创造了奇迹。许多人仅仅是因为活着就创造了奇迹。妈妈是个奇迹,我也是。我们比别人想象得有价值。
我哥哥比我和大满快一步走进了破房子,他夺过妈妈手里的枪:“妈妈,让她活下去,谁都有资格继续活下去。”
出了破房子,我们和母亲来到大河弯曲的地方,那里有一汪清泉,深不见底。
我哥哥把那支枪在一块青石上一断两截,把残肢扔进水里,水波激荡,水波复如明镜。一轮皓月在水波之间奔涌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