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过悬崖
□田 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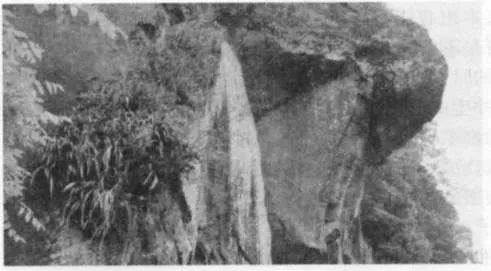
每年春季夜里总有那么三两天,屋外狂风咆哮,树木呼啸,一阵紧过一阵的惨烈让人心惊胆战。如果碰上电闪雷鸣,房顶上的瓦片也发出翻动声响的时候,老人们就会一脸虔诚地祈祷:“风过悬崖,扯水上树;风过悬崖,扯水上树。”对于这种近似于迷信的乡间风俗究竟起源于何时,已经很难考证了。我只知道,祖辈这样说过,父辈也是如此。到了我求知的年龄去问伯父,他要我去找景公,因为这是村里一位见多识广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景公好像一生都在帮别人“赶鬼”。如果哪家的狗学猫头鹰叫了,或者谁被飞鸟从空中拉下的粪便击中头顶了,准要找他算上一卦。每逢这个时候,只见他微微闭上双眼,伸出长长的五个手指头,从食指的第一个关节开始掐算起:“甲子,乙丑,丙寅,丁卯……”,他念得越久越让人着急,但又不便打断他。唯有等他睁开双眼后说一声,“没大事,只不过遇见小鬼而已”,求助者方才松口气,便请他帮忙“赶鬼”,了结心事。
“赶鬼”这事说起来神秘可怕,但其实很简单。用薄纸扎一个小人形状的木偶,选择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无人经过的岔路口摆上一堆香火和供品,风水先生手操一柄桃木剑在空中挥砍,然后狠狠地吼一声,“怼”,随从者随后点火将那木偶一烧了之。这个场景在村里是未满十八岁的人无法看到的,而我却独自例外。这并非我有什么特异功能,而是我比一般人的字要写得好一些。景公年事已高,在夜里书写“赶鬼”文书时需要一个帮手,所以我有机会比同龄人更多或者更早地察觉成人世界的脆弱面,也让我有机会向他讨教诸如“风过悬崖,扯水上树”是什么意思的问题。
刚开始他说什么也不愿讲,但慢慢地经不起我的纠缠,也或许看到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执著劲,趁帮人看风水之机,带上我随他登上高山顶俯视一切。在他的指点下,我发现故乡依山而建,背靠青杠凹,北倚掉主岩,东临大瀛上,南望小岗斗。四座高低不同的山峰把一块坝子围成一个并不完全封闭的小盆地。正因为如此,山雨欲来之时,这里便是风云激荡之处。难怪,乌云有时候会像一只巨大的鸟,扑打着翅膀俯冲过来,顿时让人感到渺小和无助。他说,如果风能从悬崖边上卷过,而没有摧毁人畜、房屋和庄稼,那是一件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至于“扯水上树”,哪怕我当年穷尽所有的办法向他寻找答案,仍然不得要领。即使他也曾经暗示过我:金木水火土缺木。但我那时根本不懂太高深的道理,也就不好意思再追问。
乡村不像城里以每个单元为单位独处,只要你愿意,夏夜乘凉的时候,老人们便常对晚辈讲起:以前的掉主岩原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就连名不经传的马桑树都有一个成年男子的腰那般粗,那时常常听到野狼的嚎叫,看见野猪的出没。后来,为了大炼钢,砍掉了那片森林……对于年长者津津乐道的回忆,我总以为他们在编造传奇。遥远的往事于吾辈仿佛就是一阵轻风吹过,而我们俨然是一群顽固不化的石头,岂能在心灵的湖泊上激起半点涟漪?我想,这事怪不得我们这一代人。生下来就面对着这片山坡上的荒凉和贫瘠,不要说高大的树木没有见过,就连野猪的足迹也没有发现过。常见的只有那矮小的刺梨,和从旁边庄稼地里窜出来的几只野兔,仅此而已。
真正改变我对故乡曾有一片茂盛森林持有怀疑态度的,是田垄间那几棵李子树。与松柏相比,它们显然没有伟岸的身躯和勃勃的英气,既做不了家具,也成不了枕木。要不是春天里能看李子树开出雪白的花朵,夏天能品味到又脆又甜的果实,单凭它们那歪歪扭扭的树干,参差不齐的树枝,竟能避开人类的砍伐,那实属奇迹抑或怪事。
困惑之余,老天爷注定要给迷思者某种启示。在收到高中录取通知书后的第三天,我和景公在李子树下歇脚。他突然问我:“你知不知道这些李子树为什么能够存活下来?”我圧根儿没想到这个平时话语不多的长者会主动问我这个问题,连忙摇头回答不知道。他叹了口气说,“你把它们砍掉后当柴火烧吧,又觉得有些可惜,因为它们每年总会结果实;你把它们当做顶梁柱培养吧,又觉得实在不合适,天生就不是那块料。你说该怎么办?是不是觉得它们有点用,又没有大用?”这让我一下子堕入云山雾海。受知识和阅历所限,我一时转不过弯,但又不甘心无话回应他遭轻视。于是自作聪明地问:“你赶了一辈子的鬼吧,鬼长得是什么模样?”谁知他竟然哈哈大笑说:“给你讲个悄悄话,你可不能跟别人说。我赶了一辈子的鬼,一个鬼也没看见过。”这话打死我也不相信。他也知道我不会相信,所以临走前语重心长地告诉我:“鬼是人心长出来的魔。乡亲们的劳动本来就已繁重,遇上不吉祥的事就会增加一层多余的心理负担,这划不来,所以我要帮他们赶。”
那时虽然听不懂他话里的深意,但隐隐约约觉得他的内心世界肯定比别人丰富得多。再去找伯父求知,他向我道出其中的原委。故乡的山坡上曾经确实有一片森林,当年要砍伐时,读过私塾的景公站出来反对,结果每次运动他都挨批斗,从此变得不爱发表自己的意见了。“没想到他会对你说起这些,看来你应该好好读书了。”伯父如此鞭策我。
带着“风过悬崖、扯水上树”和“有用又无用”的疑问,我踏上了异乡求学的路。渐渐地从家人给我的信中得知,景公在我离开故乡后的第二年已经去世,连那几棵李子树也被砍掉了,据说是故乡的土壤适合种植烟叶,有一条乡村公路要从那里经过。在“要想富先修路”的主张下,没有什么能阻挡人们追求富裕生活的步伐。这本来是好事,但世事难料。后来一场六十年未遇的洪灾袭击故乡,冲走了两条人命和三条黄牛,看到泥沙翻滚的景象,乡亲们才惊恐地发现,这块养育自己的土地需要有一片森林来遮风挡雨、“扯水上树”,于是大伙在灾后自发地聚集在一起,一致同意“封山”,并立下了人和牲口一律不得进入育林区内的乡约。
等我回到阔别十五年之久的故乡,掉主岩上的那片绿色生机跃然于眼前,虽然还不够茂盛,但有了苗子就有了希望。听村里人讲,这回“封山”是来真的:有一次阿福的羊跑到掉主岩上去吃草,当天晚上,阿福家就主动地杀猪宰羊向全村的父老乡亲赔礼道歉……
我祝福我的故乡和善良的人们,但愿将来我能有机会站在那片森林前自豪地对晚辈讲起:“风过悬崖,扯水上树”,在天地万物之间,有一种债——它名叫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