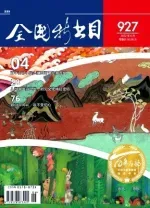青春到处便为乡
⊙
这是一个70后作家用多种方式记录的在路上的青春,散文浓酽、想象纵横开阖;诗歌诡美、曲折,具强烈音乐性;摄影神秘、风格奇异。作者足迹踏遍大陆香港台湾三地以及欧美重要的文化城市,对青年文化深有体会,折射于诗文中,流露出意气风发又特立独行的气质,文字和图像也呼应这种不羁,风格自由流动,内容都关乎现实与内心中的旅程。本书表面虽是游记为主,但实际上写的是青春之激荡与冲突。

《衣锦夜行》
廖伟棠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7
定价:26.00元
“青春到处便为乡”,台湾友人阿钝送给我的诗句,写得真是骄傲、洒脱,有能把路过的地方当成家乡去爱的勇气的人,便是有情人,便是精神青春者。这种青春的勇气不可谓不大,因为你要去爱、去生活,便意味着你要认识和接受它的方方面面:那不止是华丽和享受的一面(这是观光客可以轻易占有的),还包括它的琐碎、复杂、苦涩。但是你要是用心品味的人,你必能在这苦中品出蜜来,而且,这是你自己独特的体味,和任何一本书上描述的都不同。
这句诗,阿钝也用来形容我,在他眼中,“浪游者廖伟棠已经越岛无数,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我却把这句诗献给我在不断迁徙移动中遇到的无数同类。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注定是属于迁徙的一代,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中国对城乡流动的限制放宽、大学逐渐扩招,年轻人借着升学、工作的名义在一个个城市之间流动,而对于其中我等“波希米亚人”来说,根本不需要借口,我们是文化流浪汉,逐精神上的水草而居。最关键的是我们都有把异乡作故乡的精神,有此精神的人便能得到他所“过处”给他的报偿,他和他生命中经过的地方不是马和驿站的关系,而是恋人之间的关系。
人,本天地间之羁旅者,百代中之过客。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称为真正的家乡,尤其当一个人知晓了这命运,他便应该接受并且热爱变动不居的生涯——那他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旅人。对于这一层次的浪游者,旅游是不纯粹的,他要的是生活本身,他要求生命就是一场完全的盛宴;观光是不彻底的,他要的是体验本身,他要求他生命所经历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爱有恨、在他的灵魂深处留下印痕。正如古人所谓“过处便有情”,爱上,便住下——倒过来讲:要住下,怎能不爱上?爱不止是一夜眼神的勾连、繁花之间的擦肩,爱一个人怎么能不完全体验他/她?同样,在世间流变中,一个有情的旅者,若爱上了一个偶遇的地方,又怎舍得不去融入它的生活、成为它的一部分?
对于我(和我的大多数朋友),北京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我去北京居住之前,我已经在四个城市生活过:出生地粤西小城新兴、少年移居珠海、求学地广州、最后举家移居香港,皆不出岭南范围。所以当一九九六年我第一次去北京时我就被镇住了——或者说被她下了蛊。中国原来有这么疯狂洒脱的地方,而且吊诡的是,就在其历史和政治的核心,我新认识的每个人都似乎在过着这样一种生活:我原来只在《巴黎,一场流动的盛宴》、《流放者的归来》、《伊甸园之门》的文字中想象过的生活,诗歌、摇滚、醉酒、爱情与决斗,几乎天天都在发生着。于是我日夜谋划,年年去北京,二零零一年索性从香港搬到(美其名曰自我放逐)北京,一住就是五年。
关于香港,我曾经写过这样的句子:“在香港,一个异乡权充了故乡,最后仍是异乡”,混杂的文化背景一度使我迷醉——他理应成为我血液中的一部分,但是还没有。二十出头的我年少气盛,结果在游戏规则过度完善的香港感到很不爽,这里的艺术家、诗人们也太小心谨慎,许多人只是把艺术视作上班之一种,而我渴望的是生活即艺术、艺术即生活。看来当时只有北京这道烈酒能满足我的胃口。在北京的五年,是我把自己彻底抛给偶然生活的五年,最初我和当时北京残余的“地下”艺术家们一样,凭着激情过活:诗歌、摇滚、醉酒、爱情与决斗……一个新鲜的自我也如青草萌生、疯长。北京成全了漂泊的人,同样漂泊的人也成全了北京如今风尘浮浪的气质,这里的青春大多数是远离故乡寻找机遇的青春,急欲找到停泊之处,又急欲找到自由的出海口,因此北京的散聚来得特别快,因此陈升那首歌只能唱给北京。

更好玩的是,以北京为基地,我可以四处出游,五年里我去西南三次、西北三次、东北七八次、中原与江南更是无数次,然后就去台湾、欧洲与美洲。最难忘的是二零零二年春在台湾的环岛铁路漫游和二零零四年冬在巴黎的浪荡。台湾也是一个仿佛和我血缘相近的地方,每年不去一两次心里就发痒,如果说北京呼应了我性格中疯狂的一面,台北则和我骨子里的寂寞相呼应,在台湾我与一种清丽的寂寞惺惺相惜——不足为外人道也。而巴黎,那曾经在我少年时的阅读中臆想过无数次的波希米亚精神之都,仍然没有在全球化冲击中变得让人失望,主要是冬天的刹那风刹那雨,仿佛把所有曾经在巴黎流浪过的伟大鬼魂都召唤了出来与我同游,结果成就了我最忧郁的一本书《巴黎无题剧照》。然后我又回到最现实、最粗糙的今日波希米亚精神之都北京。
北京的粗糙、混乱其实是她最动人的一面,然而她在奥运之路上渐渐把自己规整(无论是形象还是精神上),敷了许多化妆品,渐渐令我失望。可是“我来了,我看见了,我生活了”,君子行在,从心所欲——北京到底鼓励这种“雪夜访戴”的精神:“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我辈新迁徙者亦如此,想去一个地方,连夜便去,这是自然;爱上一个地方,住它数年甚至一辈子,也是自然;若突然想离去了,便轻身独然去,那更是自然。
先我离去的是诗人马骅,他二零零三年赴云南义教,从此隐身激流中不见。二零零五年,我北京的友人状况大多如此:诗人高晓涛长驻西藏,画家陆毅远走印度,音乐家颜峻在甘南学习喉音,音乐家宋雨喆去了意大利,音乐家李铁桥去了挪威……友人星散,而我说:“时光就是一袭隐身衫。”并且当时的中国正在“热”起来,我写道:“我的这个中国,即将卖做戏剧中那个中国。”当我在北京渐渐找不到北京的时候,我已尽兴,于是我又选择了离去,回到渐渐冷下去的香港。
但是对于经历过北京的我,香港又重新成为一个异乡——如今异乡真正成为故乡的代名词,他再也不是束缚我的地方,反而成为我的一个新的“发射基地”。新迁徙时代早已来临,我和这些“失散”了的北京浪人们,总有将来不确定的某时、在不确定的某地相聚的一刻,生活正因未知而充满可能。“青春到处便为乡”,这既是一个赞许,也是一个要求,要求我们在寻找“生活的别处”的时候时刻保持青春的气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