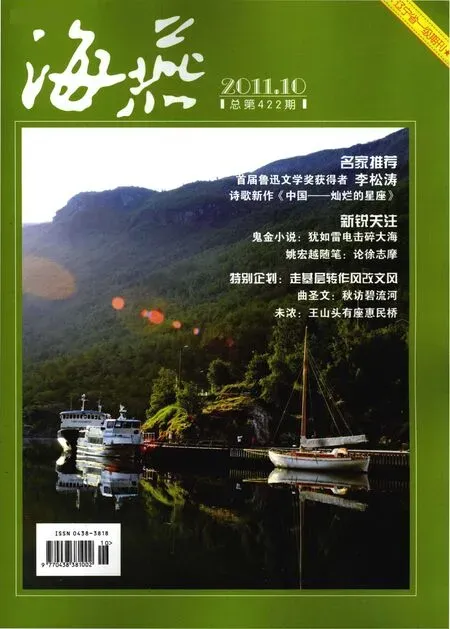我注定要走进你的秋色(组诗)
文_陈美明

/ 名曰无所适从 /
习惯了,把我的赤裸
放纵于暗夜,唯有我知道的荒冢
喘乏的思想若夏日坟丘上的荒草
自由舒展与随意延伸
总能触摸到快慰,虽说稍纵即逝
是夜,一如既往
赤裸却出乎意料地变得拘谨起来
因摸索不到有关它的遮掩而蜷曲
我看到流萤绝命书的冷色的蓝弧
依稀候鸟集结,议论南去的事情
一枚落叶似被一群鱼纠缠
搅碎了浸泡在清瘦涧水里的星星
我听到了秋虫集合中的一呼百应
随着清脆节律的哨音
它们打季节相交路口
向我放纵裸露的坟冢,齐步走来
正逼近一种习惯追寻的快慰轻松
常陷入一种窘境,名曰无所适从
/ 我注定要走进你的秋色 /
一场秋雨一场寒。
雨水冲洗乞丐的脏脸,他的本质
与我没有什么两样。蜻蜓不知道飞哪
儿去了
留下草丛多么孤单
风吹开了河面,露出岁月深陷的美
蛐蛐刚刚学会说话
所有的果实开始变甜。原野上
有几个不愿散去的灰鸽子
还没打算飞回过去
季节常常让我措手不及
一支歌曲显然赶不走我的固执
我注定要走进你的秋色
只有在那里,才会找到我的命运
骨头一样的树枝上高悬的血
我的目的很明确,要走到你的尽头
选择一块草地作我的坟墓
竖起无字墓碑,耐心等待我的敌人来
填写
/ 中年的山岗 /
一觉醒来,一些事情想不起来
一些师长乘风远去,在窗外
刺槐陈旧得不成样子
仿佛一夜间
爱人眼睛里的颜色更深了
邻居吹小号的那个人改成了吹糖人
同龄人眼泪滂沱的季节,显得陌生起来
看沧桑的峰岭多了一份亲切感
对不断低头的河流
想到它的母亲,雪山渐瘦的皮鼓
怀念有了音乐的陪伴
快感不时从我的身体穿过
我想让它慢一些,它在一颗落地的苹
果停下来
没有哀怨,没有死亡的恐惧
等待哪怕一个知音
我伸出了手
我忘记我的心还没有做好准备
/ 麻雀 /
黎明
几只麻雀落在我的窗前
它们唧唧喳喳
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但有一点肯定
它们感觉很幸福
很安全
小小的翅膀像落下的帆
我临时改变打开窗户换空气的决定
静静看它们隔着窗玻璃
尽情地叼着我的头发
后来干脆叼起我的鼻子
我闭上眼睛
静听麻雀的喙
敲击玻璃的咚咚声
感觉真好
/ 靠神性接生的耳孔分娩 /
太阳睡了。两只田鼠摘掉墨镜
朝崖壁青黛摔出雌雄两个响
猫头鹰耳朵高唱。私密交媾暗夜
祝你们快乐的歌
我不会用手写诗,那些诗歌
无一例外。在看不见也见不得人夜的纯粹
靠神性接生的耳孔分娩
那是旷野飘零的几根蒿草
血脉喧响车沟里泥鳅的翻腾
一头说不清父母是谁的骡子
在向皇家马厩高贵的汗血马凑近?
是夜,冰山的梦奔跑雪莲的眼泪
有人要割取我的耳朵下酒
给你手吧,我哀求。下酒还是手更好些
留下耳朵继续攀爬我的神性写作吧
/ 正本之恋 /
一场暴风雨拯救了一群人。
新鲜的水,复活了我们的赤裸
那为山楂树的遥远
付出的小号,不再回来
乐死去。会在果实中噙满泪水
有雾接近红旗的中心
这时候的旧事物跳下马
开始发芽的步履
看起来让人心疼,一万里
河面有熨平任何忧伤的骄傲
我有弯曲的骨头
在败絮一样的天空下发疯
牧羊者头顶上的胜利
比去年来得晚一些
他的头发散发岩石的芳香
远处的村落早已模糊不清,在他肩头
不停颤栗
哦,故乡,我眼中的一滴泪水
我一生都不会哭泣
/ 很小的感觉 /
从来不被人注视也是一种幸福。
坐在公园的木椅上,黄昏涌动着花的芬芳
湖水在远处泛白,它永远不会来到我的脚下
从岩石上,我看到我的脸趋于洁净
有一朵火焰,不燃烧,不熄灭
那是今年最后的玫瑰
在我享受一个人的孤独之外
散步的人们纷纷离去,什么都是暂时的
包括睡眠的脚步
我太幸运了,以至于一只飞鸟
站在我的肩头,看见它的目光弯曲得可爱
/ 吻是黛崖滚落的碎石 /
Party的场面越来越大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
小到我们能意外逢见
时空中的一切被浓缩成上世纪一个吻
的光点
当年我把最原始欲望
冲动地嵌入你性感的唇
黛崖滚落了一粒风化的碎石
一只松鼠闻异常之声
惊愣愣。之后,便掉头跑掉了
此际,你依旧惊愣愣看我
还会像当年那样掉头就跑吗?
其实,我梦中一直在寻觅
一根松针坠地我才悟出天机
真的吗?你就在赤松树上
垂望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