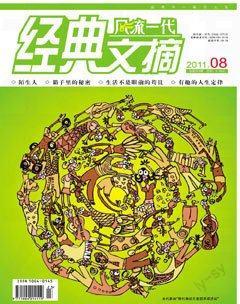被拆开的军令
伊尔泽.艾辛格
很长一段时间司令部没有下达命令了,种种迹象表明,这种状态或许会一直持续到冬天过去。在驻地周围的轮伐区里,灌木丛里最后的一批浆果也落了下来,腐烂在潮湿的苔藓地里。被遗忘的值勤哨兵依旧守在树梢上,木然地守候着夜幕降临。敌人就在河对面,一直没有任何动静。黑夜一天一天变长了,每天清晨洼地里升起的雾气也越来越重。炮兵自卫队里,一些年轻的志愿兵有些沉不住气了,他们受够了这些天来没日没夜的等待,对这样的战争越来越失去了耐心。于是私下里决定,倘若必要,即使上头没有下达命令,他们也要在下雪之前,发起进攻。
所以当他们中的一个,没过几天被分队指挥员派往司令部送一封信时,立刻产生了不祥的预感。谁都知道,如果下面的士兵计划暴动,哪怕只是随口说说,上头都不会当儿戏的。到了司令部,他把信交上去以后,他们问了他一些话。他觉得几乎是在审讯自己,心里惴惴不安起来。
他等了很久,终于接到指示:拂晓之前,将一封军令送回分队。他越发感到意外了。他被安排坐车抄近路走,还拿到一张标了路线的卡片。而且还有一个士兵奉命与他同行,尽管他很不乐意这样。透过打开的车窗,他看到自己要踏上的路。这条路先是横穿一块林中空地,然后蜿蜒在榛树林里。长官再次提醒他路上要小心,他俩便上路了。
正午刚过,云霭刚刚还在吃草的牛羊头顶的天空,刹那间便悄无声息地消失在灌木丛里。道路很糟,有些地方车几乎不能行驶。灌木丛密密实实,司机稍微加速行驶,枝条就抽打着他们的眼睛。这片树林看来急需有人来修整了。还有这条河,看上去神秘莫测,在伐过的林地的几片低洼处,它的魅影时隐时现。正午的阳光下,山坡上伐下的树闪着亮光。自然界里的一切毫无界限意识。
车开得很急,穿过林地之间轮伐区通向山地深处。汽车在树根上颠簸行驶。那个开车的士兵好几次转过身来,瞅瞅怀里揣着军令的炮兵,似乎在确认自己的货物是否还在。他心里感到很不舒服,越发觉得,这是派他送信回去的长官对他不信任的表示。
信里会是什么呢?也许是某个边远的岗哨清晨发现了河对面敌人的什么动静。不过,此类谣言不总是有吗?很可能是指挥部编造出来,好稳定大家情绪。当然,这封信也可能只是一个伎俩,他们对他表示信任,也许只是装模作样。如果他真送去了重大消息,那么,从现在这封回信里一定能看出来。他想。最好是现在,在路上,就知道里面写了什么。要是上头追究此事,就这么为自己辩解。他的手摩挲着那封信,手指触及到上面的封印。想打开军令的渴望,像火焰一般越烧越烈了。
为了赢得时间,他请求和司机换一下位子,由他开车。手握着方向盘时,他的心绪渐渐地平静下来。汽车在树林中已经行驶好几个钟头了。路上有些地方堆满了卵石,这是他们的部队堆的障碍,以便在近敌处射击目标。不过,这反倒使他镇静下来,也许自己就在这里牺牲,也不必开启军令的封印了。他从容地开着车,汽车平稳地行驶着。突然,前方的道路像神经错乱一般塌陷了下去,车一下子陷进泥泞的土地里。幸好,他俩安然无恙。马达熄火了。几声鸟鸣,寂静的树林显得更加寂静。地上全是繁茂的蕨类植物。他俩把汽车从泥坑里弄了出来,开车的小伙子主动提出自己去查看故障,爬到了车下。炮兵还是坐在车上,他毫不迟疑地拆开了手中的军令,本该尽量保持封印原样,匆忙之中什么也顾不上了。他探身窗外,读了起来。军令上赫然写着:处死他!
在小伙子的脑袋从车下伸出来之前,他迅速地把军令塞回到胸前的口袋里。“一切都好!”小伙子高兴地说。接着,他就问自己,是否继续乘车前行。是的,他应该继续前进。可当汽车被发动时,他又暗自思量,也许应该杀死这个同伴,就在现在,或者等会儿在汽车行驶中。毫无疑问,这家伙就是派来押送他回去接受处决的。
路在最低处,宽阔起来,好像后悔它刚才突然下陷似的,又平缓地朝上蜿蜒。自杀者的灵魂,由天使托着,炮兵心想,她们会把自杀者的灵魂托到法庭,曾以为是正义的行动,将会被证明是罪责。没有接到上级命令,合谋擅自采取军事行动。他疑惑不解的是,为了处决他,他们竟然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
天渐渐暗了,他和司机换了回来。看着前面同伴的轮廓,脑壳、肩膀、摆动的双臂——清晰的轮廓,可在他的视线里总是模糊不定。这个轮廓融入了夜色之中。
司机转过身来,对他说:“今晚我们会一切顺利的!”这话听起来简直是讽刺。越是接近目的地,他越显得健谈。没等他回答,司机小伙子接着又说:“我们平安到达就好了!”他从皮带上拿下了手枪。树林里很暗,似乎黑夜就要来临。“我小的时候,”小伙子说,“上学回家必须穿过这个树林,要是天黑了,我就大声唱歌给自己壮胆,那时……”
他们很快到达最后一片开垦地,比预料的要快。他想,等过了这片开垦地再动手,到那几户烧毁的农家——炮兵营所在地之前,后面都是茂密的树林。可是,最后这片开垦地比前面的都要宽阔得多。那条大河也离他们很近,河水泛着光。月光柔柔地洒在直达山脊的轮伐区上。很久以前,这里走过马车。路上车辙清晰可见。月色下,干涸的车辙像假人面具的内壁。他看着河对面的开垦地,突然觉得,这片土地好像戴上了一张陌生人的面具。
他手握着枪,搁在膝盖上。第一声枪响时,他以为自己手里的枪走火了。倘若子弹射中了坐在前头的小伙子,那么就是他的“幽灵”表现出了极大的机智和果断,因为车还是在飞快地行驶着。过了一会儿,他才意识到,原来是自己被击中了。枪从他的手里滑下去,他的胳膊无力地垂着。车驶入树林之前,又有好几枪朝他们射来,幸好都没有命中。
前面的“幽灵”转过身来,高兴地说:“到这儿就安全了,刚才是段危险地带,卡片上标记了的。” “停车!”他喊道。“这里不行,”小伙子回答,“往里头走走再说!”“我被击中了。”他绝望地说。司机朝前又开了一段,突然刹车,顾不得观察周围动静,迅速帮他把伤口包扎起来。血暂时止住了。小伙子只说了一句:“我们就到了!”——这是他知道的唯一能安慰受伤者的话。接下来就是面对死神了,受伤的炮兵悲哀地想。“等等!”他说。“还有什么事?”小伙子有些不耐烦了。“那封军令!”他说着左手伸进胸前上衣口袋。就在绝望之际,他突然想到,对这个军令还可以有别的理解。里面只写着处决送信者,没有具体人的名字。
“我流血太多了,”他说,“代我转交一下军令吧!”如果他拒绝,那么,就在这里解决一切。沉默了一会儿,他感觉到,手中的信被拿走了。“好的!”另一个说。
最后半个钟头在沉寂中熬过,时间和道路像两头厮咬着的恶狼。羊群到达天上牧场,是安全了,可这里却是它们最后的刑场。
炮兵营所在地原有五栋农房,在过去的大小战斗中,三栋房子被烧毁了。院子还算完好,里面透出的光清楚地表明,黄昏的羞涩还没有退去。这地方四周都是树林,草地被践踏过,上面停满了军车和大炮。营地与树林之间架设了铁丝网。
站岗的哨兵查问车里装着什么,司机回答说:“伤员,带着一封军令!”汽车沿着营地操场行驶。他挣扎着,在座位上坐起来。他觉得,这里并不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像归宿地。所有的地方都让人觉得是出发点。听见有人在问“他还清醒着吗”,他闭上了眼睛。要争取时间。
在他们知道真相之前,他恢复了一些气力,要为逃跑做好准备。被抬出汽车时,他虚弱无力地耷拉在他们的胳膊里。
穿过一个院子,里面有口汲水井。他被抬进了一楼的一个房间。两只狗围过来,嗅来嗅去。伤口很痛。他被放到一张长椅上。这里没有灯,窗户都开着。“你们照看一下他!”司机说,“我不能再耽误时间了。”
他等待着,会有人来给他重新包扎伤口的。他微微睁开眼,这里只有自己一个人。也许他们去拿绷带了。一会儿,他又觉得房子里人来人往,急促的脚步声,门不停地被合上又被打开,还有嘈杂的说话声。不过所有这一切却蕴含着沉寂,就像林子里的鸟叫声,反倒使林子更加寂静一样。究竟怎么回事?他想。过了好几分钟,还是没有人来。他盘算着如何逃跑了。过道墙上靠着几支步枪。他就对站岗的哨兵说,指挥员又派他去司令部送一封信。他随身带着身份证明。这么做,不会有人怀疑。
他爬起来,惊诧自己的身体比刚才伪装的要虚弱得多。他慌忙把两只脚伸到地上,想站起来。没有成功。他果断地试了第二次。这下可好,一用力,刚才司机给他包扎的急救绷带一下子被挣开了。伤口像某个隐密的愿望突然爆发似的,猛地裂开了。血浸透了衬衫,他倒在长椅上,那上面也全是血。透过窗户,他看到了石灰墙外的天空,接着听到了马蹄声,马匹被牵进了马厩。屋子里更加聒噪嘈杂。似乎就要发生什么了。他想把身体靠到窗户上,却滑了下去。他喊叫,没有人听得见。他完全被忘记了。
躺在那里,在绝望之中,他反倒觉得一阵轻松,似乎血流就是他,从紧闭的大门逃了出去,从所有的卫兵面前逃了出去。屋子被对面灰亮的墙照亮了一些,就像被雪光照亮一样。说穿了现在就是一种状态。所有状态中最单纯完美的状态难道不是这种孤寂,鲜血的奔涌难道不是一种行动?既然他曾图谋采取行动,不是出于自卫,那么这个在他身上执行的判决,就是正确的。他受够了总是处于生死边界,这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
远处响起了枪声。他睁开眼睛,回想着这一切。把军令交给他人,这么做毫无意义。他们会枪毙那个人,自己却躺在这里流血而死。他们会把那个人拉出去,拉到院子里烧毁的椽木之间。也许这会儿他的眼睛已经给蒙上了,只有嘴巴还吃惊地半张着。他们上好子弹,瞄准目标,射击——
他醒过来时,发现身上的伤口被重新包扎过了。对一个将要流血而死的人,即使天使这么做,也毫无必要。这种善心来得太晚了。看见分队的长官站在床边,他吃了一惊:自己竟然没有死。
“那个军令,”他说,“军令呢?”
“被子弹击中了,损坏了一点儿。”长官说,“不过,内容还看得清。
“应该是我把它交上去——”他说。
“我们还算命大!”司机打断了他,“河对岸的敌人已经发动了进攻!”
“那是最后一条我们必须等到的命令。” 长官转身要走了。走到门边时,他又回过身来,只是为了再说些什么,“幸好你不知道军令的内容。为这次行动,我们采用了特殊的密码。”
(谢亚摘自《译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