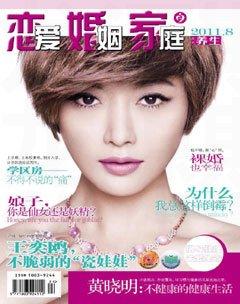美丽“入殓师”
陈彦炜
见多了死的悲伤,才想让自己每天都快乐起来。
尸体不过是工作对象
小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夜。清早,成都北郊的磨盘山上,空气阴湿。
23岁的女孩张庆平醒了,她拿出手机看了下时间——6点半,距离上班时间还有一个钟头。她一骨碌爬起来,推开房门。正对着她宿舍的是一排贴着白色瓷砖的平房,这个时段,每个房间里都已摆放好了一具尸体;花匠们忙前忙后,将一盆盆菊花摆放在棺材周围,黄白相间,还搭配着绿色的芭蕉叶。张庆平早已习惯了这种场景,她走到水龙头边,用清水洗了把脸,然后用肥皂反复搓手,最后搽上护手霜。
按照成都人的风俗,人死后,尸体要放上3天,然后入殓、火化;入殓的时间越早越好,最好不要拖过下午。所以,3点过后,张庆平和她的同事们就可以下班。但殡仪馆毕竟是个顶特殊的地方,尽管民俗如此,还是有些外地人甚至外国人不分昼夜地到此办丧。馆里立下条规矩:上班的人要连上两天一夜,而这一夜就必须住在馆里,随时待命。
吹鼓手的声音远远传来,这是开始上班的信号。没过多久,刚才那个空旷、安静、冷清的殡仪馆就变得拥挤热闹起来。几声哨响后,礼炮开始轰鸣,哀乐轮流在各个告别厅奏响。张庆平穿起一件白大褂,将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然后捂上口罩,戴上粗棉线手套,外面又套了一层塑料的一次性手套,拎起一只红色的软皮箱子,走进了一间阴森的屋子。屋外不起眼的牌子上写着“冷冻室”3个字。
冷冻室,是尸体到达之后第一个停放的地方。张庆平的工作,就是把尸体从冰柜的抽屉里抽出来,推到沐浴室帮他们洗澡、做防腐、整形,再穿好衣服,做修面、化妆,最后送到告别厅。在告别厅里放着的,是已经处理完毕的尸体。他们安然地躺在那里,面庞红润,没有死亡的暗影、离世的痛楚,有的只是如同睡去的恬淡;而他们刚被送来的时候,脸色苍白或者瘀黑,头发凌乱,衣冠不整,惨不忍睹。张庆平说,看到那些跟自己差不多大的女孩子直挺挺地躺在面前,她就一定要想方设法把她们化得漂亮一点,心里才好受。
从早晨到下午,张庆平要处理将近30具尸体,冬季则远远不止。夏天的尸体数量要少一些,不过湿热的天气、频繁的雨水、活跃的蚊蝇,还是让她觉得“透不过气来”。
成都殡仪馆年代久远,条件不好,穿着不透风的工作服闷在屋子里,与具具尸体相伴,张庆平常会感到压抑、困顿。一开始接触尸体的时候,她一点也不恐惧——由于学医的原因,她感到人体很神圣;现在,到殡仪馆工作将近一年的她,“早就麻木了,没得啥子感觉”。她学的是中西医结合临床五官专业,去年从成都中医药大学毕业后,高分考进了殡仪馆。在她眼里,殡仪馆是国家事业单位,稳定、有保障,而且可以留在她热爱的成都。至于尸体,不过是个工作对象而已。
为殉情的女孩化一个新娘妆
张庆平要给死者化两种类型的妆:油彩妆和粉妆。老年人、中年男子,还有一些家属要求不高的死者,张庆平就给他们化油彩妆。一块有些旧的海绵,蘸上点特制的油彩颜料,在死者脸上来回均匀地擦上几下,再涂上少许的胭脂,人就会变得红润起来。如果是年轻人,特别是尚未结婚的少女,她就会格外用心地给她们化上粉妆;有的时候,她还用自己的化妆品,给死去的女孩化新娘妆。
那天,殡仪馆里送来一具女尸,看起来年轻而又时尚。张庆平上去一问,跳楼死的,为情自杀,年龄竟与自己相同。家里人给女孩披上了一袭素洁的婚纱,要把葬礼当作婚礼办。张庆平受不了,流下了眼泪。天天看尸体,她很少流泪,她坚信她所直面的死亡,都是与己无关的;她就是一个看客,把自己隔绝于死亡之外,看别人痛苦哀伤的一幕幕悲剧。
但这一次,张庆平被感动了。灯光下,她细细地为女孩打粉底,从发际、唇部、鼻翼、嘴角到脖子,将一些死后皮肤呈现出的暗斑遮蔽;再以粉饼轻薄地施一层透明蜜粉;用眉笔画出柔和自然的眉型,拿小刷子刷匀称……新娘妆常见的眼影、眼线、鼻影,一个步骤都没有省略,前前后后花了一个多小时。张庆平说,她从来没有如此上心地化过妆。告别仪式开始前,她又提着化妆箱去为女孩补妆,最后一笔口红描过的时候,哀乐响起。
经过了医学院5年的历练,张庆平并不惧怕尸体。在她眼里,正常死亡的人都很安详,有的还挺好看;但是,那些死于非命的(如车祸、凶杀、自然灾害等),往往血肉模糊,惨烈而又狰狞。令她困扰的是,现在在路上看见一个人,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假想他闭上眼睛的模样;每次在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听见协警吹哨子,她就赶紧捂上耳朵——殡仪馆每次为死者鸣放礼炮前,工作人员吹的也是这种哨子。
学医的人多少都有点洁癖,张庆平说自己是“超级洁癖”。每处理完一具尸体,她都要使劲地洗手,来回搓上不知多少遍,手一度被洗脱皮。现在,護手霜是她随身必备的东西,而且她会挑贵点的、牌子好的。她为自己办了一张美容院的年卡,下班了就去做皮肤护理和头部按摩,既是保护自己,又是一种放松。
外人以为,殡仪馆的薪水很高,高到神乎其神。张庆平笑道:我倒想像他们说的那样呢,可我一个月就2000多块钱。
一个爱笑的美丽女孩
悠扬的琴声响起,面庞俊雅的本木雅弘用一块小小的方巾替死者慢慢擦拭身体、穿好衣服,将那双略显僵硬的手紧紧相扣,再绕上一串剔透的佛珠。如同宗教仪式般幽玄空寂的场景,伴着久石让静若止水的配乐,无比庄严……“啪”地一声,张庆平关了影碟机——全长两个多小时的片子刚放了十几分钟,她就看不下去了。
这部《入殓师》是朋友推荐给她的,今年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张庆平无法理解这部片子,作为一名中国的入殓师,每天要处理30多具尸体,“都像电影里那样唯美地操作,殡仪馆门口估计要堵车了”。
在单位里,同事们都称张庆平为“美女”。她长得确实标致:唇红齿白,皮肤也好,笑起来还有个酒窝。23岁的她,是个地道的川妹,性格外向、活泼,只要不是面对尸体,她就笑个不停。殡仪馆里的一切都那么肃穆、冰冷,终年只闻哭泣不见笑靥。张庆平说,自己需要笑,不然受不了。
在殡仪馆工作的年轻人,很多就在附近租房住,但张庆平决不。她宁愿住在距离遥远的市区,上班的早晨5点钟就起床,然后打的到单位的通勤车站点,再坐一个小时的班车去馆里;两天一夜的班上完后,她拎起包就走,从不在单位多停留片刻——她希望一结束工作就不要再和殡仪馆扯上任何关系。每当车子开进三环路,林立的高楼逐渐浮现、红油和辣子的味道满街飘香的时候,她总是长舒一口气。即便吸进鼻子的是汽车尾气,她也很满足,毕竟触摸到了城市的烟火,那么的生机勃勃。
有时候,张庆平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干这一行,因为自己的性格不够“庄重”。她始终对那些阳光的、快乐的、新鲜的事情充满兴趣:上网、逛街、泡吧、寻找美食……殡仪馆的老一辈员工,有许多不成文的规矩:不参加亲友的婚寿喜宴,不递名片、不主动介绍自己的职业,不对访客说“再见”、“一路走好”……张庆平听到这些以后,表现出了惊讶,更加害怕自己的处世方式与职业格格不入。因为她从来没有把自己归到“特殊人群”的范畴,什么事情都会做、什么朋友都会交、什么场合都不避讳。她并不掩饰自己的生活态度:“女娃子嘛,就是上会儿小班、睡会儿小觉、吃点好东西、找个好男人,就可以了。”
见多了死的悲伤,才想让自己每天都快乐起来。张庆平觉得,她的生活逻辑就是这么推导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