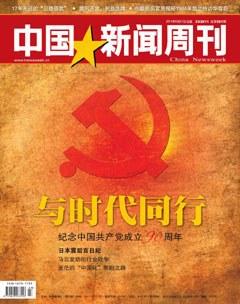“幸福”的另一面
徐贲
一个关注不幸福的社会要比一个对幸福沾沾自喜的社会更成熟也更理智。这就像成熟、睿智的预言,它关注未来的灾祸一定甚于幸事。思考不幸福多于幸福,那才有可能将未来的幸福最大化
对许多人来说,追求幸福不仅是一生的目标,而且也是基本权利。例如,美国的《独立宣言》就说,“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追求幸福被当作一种“不言而喻”的真理。
幸福一般被视为一件当然的、自然而然的好事。对于讴歌幸福的人们来说,“幸福能够给我带来什么”(“幸福为何有益”),与“我因何幸福”是同一个问题,因此也只需要同一种回答。那么,幸福会给你带来什么呢?回答是,幸福可以帮助我达到重大的人生目标,如事业、财富、地位、荣耀、荣誉。幸福可以为我稳固重要的人间关系,如家人的亲情、夫妻的恩爱、志同道合的朋友或同志友情、崇拜者对崇拜对象的绝对崇敬、对民族群体的无条件认同。幸福可以扩展我人生的范围,如智慧和知识、见解和判断、思想的乐趣、艺术兴趣和修养。幸福还可以提升我的福祉和心理健康,如让我快乐和满足、令我愉悦、免除焦虑和烦恼等等。
在这样的理解中,幸福展示的永远是光明、美好的一面。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事物从来都是两面的,有利就会有弊,为什么偏偏幸福就是例外呢?最近,2011年第6期的《心理学研究透视》杂志上刊登了3位研究者讨论幸福的文章,涉及的正是幸福不为人注意的另一面,文章的题目是《幸福的阴暗面?幸福如何、何时、为何并不总是好事》。三位作者都是心理学家,他们是耶鲁大学的June Gruber、丹佛大学的Iris Mauss和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Maya Tamir。
他们在文章中提出的基本问题是,追求幸福和体验幸福是不是也可能带有负面的后果呢?这个问题是从四个方面来提出的。
第一,幸福是否有不适当程度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提出,美德和一切可以称之为“善”的事物,必须要程度适中,有益的东西一旦过犹不及,便会转变为有害的东西,幸福也需要适中,不能提倡无条件、无止境的提升。
第二,幸福是否有不合时宜的问题?我们所熟知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既是一种不适度,也不合时宜的幸福。在许多人还生活在贫困之中的社会里,炫耀和展示财富带来的幸福(宣扬所谓的“豪华”或“顶级”享受),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第三,幸福是否有追求手段不当的问题?
第四,幸福是否有错误的种类和方式问题?
后两个问题其实是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吸毒、淫乱、挥霍(尤其挥霍公共的财物)、奢侈、专制独裁,权势者的飞扬跋扈、盛气凌人、耍威风,老子天下第一,享受特权、损人利己,这些都能给人带来幸福感,但显示的幸福是光明的,还是阴暗的呢?
许多人是在既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也没有认真思考过幸福的情况下感受“幸福”的。这种幸福有它的价值,但并不代表幸福在更高层次上的意义。从古代开始,思想家们更关心的是一种高于个人感受和情绪的幸福,那是一种与普遍的公共生活有关的幸福。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把幸福认识为一种与美德相一致的行动,而不只是一种心理感受的状态。幸福是“好生活”的特征,即人可以用优秀的方式实现人性善(自由、勇敢、节制、审慎)的那种好生活。幸福是“灵魂按照理性而进行的美德行为”,或者说,幸福是美德的行为。这是一种必须在公共生活中来理解和追求的幸福,它以人们共同的好生活为条件,也以这样的好生活为目标。
不思考的幸福是肤浅的,它使人陷入一种病态心理的“欣快症”(Euphoria),让人飘飘然而忘乎所以,因此变得越加可能不合时宜、不合度地,以不当手段和不当方式去追求幸福。一个关注不幸福的社会要比一个对幸福沾沾自喜的社会更成熟也更理智。这就像成熟、睿智的预言,它关注未来的灾祸一定甚于幸事。思考不幸福多于幸福,那才有可能将未来的幸福最大化。
对个人的幸福如此,对群体的幸福也一样。古罗马曾是一个空前强大、富有、成功,而拥有无比幸福的帝国。然而,弗洛鲁斯在他的《罗马简史》中恰恰在这种帝国的幸福中看到了灭亡的开始:“疯狂的内战是极度繁荣引起的⋯⋯(罗马)的堕落首先是从征服叙利亚开始⋯⋯财富和权力摧毁了道德基础,使国家陷入自己造成的罪恶深渊,并淹死在其中。”他问道:“难道不是我们的财富引起政治野心,造成道德日趋严重,因此引起⋯⋯大动荡吗?穷奢极欲的盛大宴会和十分慷慨的赏赐难道不是将巨大的财富挥霍殆尽而变成贫困吗?正是贫困使卡提林策动叛乱。独裁统治的欲望难道不是过多的财富造成的吗?财富以复仇女神的火炬武装恺撒和庞培,让他们去毁灭自己的国家。”这种幸福的阴暗,不是很值得我们警惕吗?★
(作者为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