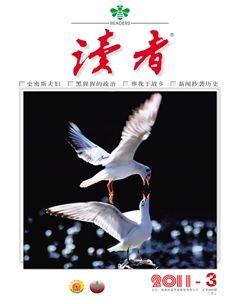史密斯夫妇
赵炎秋

2001年,我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做访问学者。2月一个周六的下午,我正在大学所在地查普希尔市的弗兰克林大街上匆匆赶路。前几天刚下了一场小雪,这天天放晴了,但气温并没升高,嗖嗖的冷风刀子似的刮得脸生疼。我把脸扭向右边,以避开冷风的势头。因此,当一位80多岁的满头白发的老人迎着我走上来时,我并没有注意到。
“嗨,下午好。”老人与我打着招呼。
“您好,先生。”我狐疑但客气地回答道。
“您是新来的吧?”
“是的,来了十几天。”
“中国人吧?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我叫史密斯,查普希尔市市民。我们想送份报纸给您。”
“它是免费的。”另一个女声补充道。
这时,我才注意到史密斯先生的背后,还站着一位优雅的女士,也有80多岁了,怀里抱着一捧鲜花。见我看着她,她向前迈出一步,与史密斯先生并排站着,微笑着说:“我是史密斯夫人。我们想请您花点时间看看我们的报纸。十分感谢。”她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的腔调,使她的话显得格外妩媚。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德语的尾音。
说着,她递给我一枝鲜花。
花很鲜艳,香气扑鼻。
报纸对开八版,报头用花体字写着《查普希尔和平信使报》,下面是“史密斯夫妇编辑”,再下面是一排通栏的黑体字:“同样的世界,一样的人们,无论你是谁,让我们一起祈求和平,不再杀戮。愿上帝保佑我们!”
晚上回到住处,我告诉我的房东老王,今天碰到了一对有趣的老两口,女的送花,男的送报纸。
“史密斯和汉娜!”老王笑道,“查普希尔的老风景了。每个星期六的下午他们都上街送报,除了1998年汉娜生病住院的那段时间,周周如此,雷打不动。”
“他们那么大年纪了,还卖报?”
“哪里,他们有钱着呢。”老王听出了我的意思,“那报纸是他们自己编的,每周一期,每期印3000份,除了寄赠给固定的客户之外,剩下的就拿到弗兰克林街上送人。都是免费的。”
美国人有个性,今天算是见到了一对。可是,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呢?
问老王,老王也不知道。
我不禁对史密斯夫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我的好奇心便得到了满足。
这是一个英军少尉和一个德国姑娘的故事。
英军少尉1942年大学毕业之后应征入伍,参加了诺曼底登陆,在进入德国本土之后的一天,他奉命带一支小分队前去侦察。侦察途中,他们与一队德军巡逻兵相遇,双方发生激战,少尉与他的小分队被打散了,他突围出来,顺着来的方向,摸索着返回自己的驻地。
想着战争即将结束,马上就要和妻子凯瑟琳相聚,少尉心中充满愉悦,脚步也轻快了许多。突然,他似乎听到了隐隐的脚步声。他立刻警觉起来,放慢了脚步,猫一样地溜到一块大石头后面。
周围一点动静也没有,但英军少尉的第六感告诉他,石头的背后有人。由于子弹在刚才的战斗中已经打光,他从腰间拔出匕首,沿着石壁向后面摸去。拐过石角,他吃惊地发现,就在他前面,一个德军军官正背对着他,握着手枪,向着前方张望。听见声音,德军军官飞快地转过身来,举枪就要射击。英军少尉飞起一脚,踢飞了德军军官的手枪,同时匕首迅速地向德军军官刺去。德军军官一闪身,躲过了这致命的一刀。他用左手抓住英军少尉持刀的右手,同时,右手伸向自己腰间,拔出刀来,英军少尉也连忙用自己空着的左手抓住。
两人就这样僵持住了,激烈的搏斗变成了力的较量。谁也不敢松手,谁也不敢乱动,谁也不敢率先打破这个平衡。两人的身子仿佛凝固了,汗从两人的额头滚下来。
英军少尉身高1米85,体格健壮,但德军军官同样体壮如牛,两人势均力敌。然而,英军少尉由于已经出外几天,身体比较疲惫,在角力中德军军官渐渐占了上风。英军少尉感到对方的刀尖慢慢地向自己逼近,他感到自己再也支撑不住,马上就要崩溃了。他眼前飘过妻子凯瑟琳的身影。他们已经半年多没有联系了,上封信中,妻子告诉他她已经怀孕了,现在孩子应该已经出生了吧?可他连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就要永远地离开他们了。他感到一种莫大的悲哀与绝望。然而,正是这悲哀与绝望给了他孤注一掷的勇气,他大吼一声,抬起膝盖,撞在了对方的下胯上。猝不及防的德军军官痛得弯下了腰,英军少尉趁机将匕首刺进了他的胸膛,永远地结束了这场角力。
德军军官躺在草地上,汩汩的鲜血冒着泡沫,顺着几乎没柄的匕首流出来,很快染红了周围的地面。这时,他才注意到,这个德军军官还很年轻,也是个少尉,估计很有可能就是刚才遭遇的那支德国巡逻小分队的指挥官。看来那场遭遇战实在激烈,不仅他们被打散了,德军也被打散了。
英军少尉拾起德军少尉的手枪,准备离开。忽然,他发现德军少尉正恳求地望着他,左手艰难地抬起,指着自己上衣右边的口袋。英军少尉警惕地走过去,小心地打开那个口袋,从里面掏出一封信和一张照片。
信是从德国国内寄出的,娟秀的字体一看就知道出自一位女士之手。
照片上一位娇小美丽的德国女郎正期待而深情地望着他,太阳照得她微微眯起眼睛,显得分外妩媚。
德军少尉的生命之火行将熄灭,眼中的沮丧与恐惧已经消失,流露出的是无限的牵挂与不舍。他用最后的力气,用简短的英语断断续续地说:“这是……我的妻子……她,她已经,怀孕了……请,请一定将这些东西转交给、转交给她,并告诉她……我爱她。”他示意英军少尉在他面前蹲下,“我不怪你……要怪的……是这场该死的战争。”
英军少尉突然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残忍的事,不禁歉意地握住德军少尉的手。德军少尉死后,他花了两个钟头,挖了一个坑将他掩埋了,并按照他衣服上的信息,在放在坟头的一块大石头上写下了他的姓名、职务和去世的时间,并在后面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不久,战争结束了。在举国上下的欢腾声中,英军少尉踏上了返家的路程。车轮“哐当哐当”地敲击着铁轨,仿佛是他心跳的声音。很久没有收到妻子的信了,她和爸妈现在一切都好吗?考文垂终于到了。少尉来到自己的家门前,然而曾经熟悉的一切都面目全非了,以前常走的林间小路被翻了个个儿,二层小楼,他与新婚的妻子在这里度过难忘的日日夜夜的家只剩下一片瓦砾,屋子周围的山毛榉被齐腰斩断,变成了一根根枯干。他好不容易找到幸存的母亲。母亲哭着告诉他,考文垂在1940年11月遭受德国空军的致命轰炸之后,一直比较平静,谁知1944年9月,就在盟军登陆法国成功之后,德国空军再一次飞抵考文垂。由于市中心在上一次空袭中已基本被炸成废墟,所以这一次空袭的重点放在了郊区。两颗炸弹落在他们住的地方,除了那天正好外出的母亲,一家人全被炸死了。
少尉来到父亲和妻子的坟前,默默坐了两天。第三天,他告别母亲,前往德国城市德累斯顿,去完成他对那个被他杀死的德军少尉的承诺。
这个城市也曾遭到盟军的轰炸,到处都是废墟。他按照信上的地址找到德军少尉的家。眼前是他熟悉的场景,仿佛又置身于轰炸过后的家乡。他像在这里生活过似的,下意识地顺着林间小路来到了废墟的背后,一个用烧过的木料搭起的三角形帐篷前,他看到了照片上的那位漂亮女郎。不同的是,她已经憔悴得不成样子,满脸疲惫,肚子明显地鼓了起来。她正在把废墟中有用的东西清理出来,见到英军少尉,她停住手中的活,带着些微的慌乱,看着这个仿佛从天而降的胜利者。
“我是英国人,叫史密斯。”少尉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用不熟练的德文说,“我和您的丈夫有过一面之交。他死了,临死前,他托我将这些东西带给您,并要我告诉您他爱您。”
女郎早有预感似的默默接过那封信与照片,转过头,抽泣起来。
英军少尉看着她瘦削的肩头、孤单的身影和鼓起的肚子,不禁升起一种深深的怜悯与同情,他再一次感到自己做了一件残忍的事。在当时,作为战士,这种感觉还不太明显,然而在战争结束后,作为平民,他深深地自责。他毁掉了一个家庭,毁掉了这位少妇的幸福和希望,使一个还没出生的孩子永远地失去了父亲。强烈的内疚感折磨着他,他不由自主地在她的面前跪了下来。
“原谅我吧,您的丈夫是我……我杀死的。”他艰难地吐出了后面几个字。
女郎转过模糊的泪眼,看着少尉。
“您骂我吧,打我吧,怎么惩罚都行。”少尉低着头说。
女郎止住哭泣,将少尉拉了起来。
“我不怪你。”她说,“这是战争,不是你杀他,就是他杀你。如果是你死了,今天哭的就是你的妻子。”
“我的妻子已经死了。”英军少尉低声地说。
女郎睁大眼睛,吃惊地看着少尉。
“在德军的一次空袭中被炸死的。”
女郎满怀歉意地握住英军少尉的手,同情地挨近少尉的身旁。
少尉揽住女郎的肩头,虽然他们才相识,但他却觉得似乎与她认识很久了,两人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几天之后,他离开了,跟着他一起离开的,还有那位德国女郎。
不用说,他们就是现在的史密斯夫妇。
2002年2月,我访学结束,离开了美国。回国之后,我还和史密斯夫妇保持了三四年的联系,后来就中断了。2008年,房东老王给我发来一条短信,说史密斯夫妇去世了,两人相隔只有30天。两人葬在一起。他们的家人在墓前立了一块大理石墓碑,碑上刻着他俩的故事。故事的下面,是这样一段铭文:
他们本来应该成为仇人,但共同的遭遇和爱使他们结合在一起。从此之后,他们唯一的事业就是让两人曾经的悲剧不再重演。
(叶伟摘自《文学界》2010年11月号上旬刊,本刊有删节,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