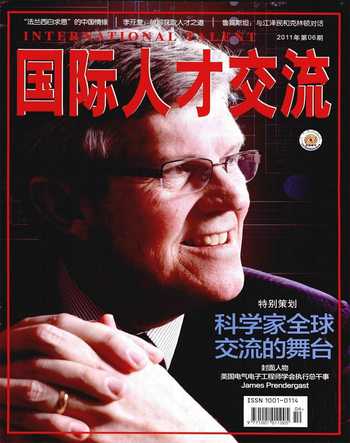姐姐的时间挂在墙上,弟弟的时间悬在海外
郭生祥
1911年的时候皇上被打倒了,1949年之后家长制被作为封建礼教取消了。今天,既有市场,又有习俗,还有权力与计划的影子,农民如何面对这些环境,如何选择自己的标准,的确是困惑着的。
今天拿什么来维护乡村
我是中国农民的儿子。
可能很多人说,我们也都是。对于中国城市里的人,大都不过三代前就是农民。这说明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其实早不过三代前。
但是我说我是中国农民的儿子,更多是从学术视角而言的,也就是我的学术占位是以农民利益为视角的。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一是始终保持感情上倾向这样,当然也还要具有理性,二是还需要具备清醒的学术能力和自觉。我是不是这样做到了。不敢说。
至少我是坚持这样的,努力这样的。
首先从情感上,除了了解农民的优点外,我更知道农民的缺点,农民分散、朴实,其实这是农民在自然环境、政治环境下的一种表现,并不完全就是农民的本质。今天的农民由于受到现代商业气息感染相对较少,一定程度地保留着传统习俗,以及1949~1979年时候、或者是1979~1989~1999年时候的部分习俗,因此,或多或少较之城市里更多一些诚信和质朴,更多一些勤劳与宽容,更多一些合作与友爱,我不知道这个较之城市化商业化落后不止10年的农村,随着自身的商业化起来,会不会改变?
这种担心好在孔子说过,“礼失求诸于野。”这说明不赶时髦的乡野从来都是传统保持的最好容器。
但近来我倒是观察到城郊农村人格分裂的阵痛,这里晚上似乎保留了一点传统的习俗,白天却有着比城市里更严重的纷乱,也许他们认为自己比城市弱势,他们夸张了城市的纷乱,因而自己模仿着的时候,就采取了过头的策略,这也是一种博弈论。
但这不能说明农民的本能、本质。
我要说的是,习俗是根,良善是传统,但是维护这公序良俗最后的保障是什么呢?今天又如何变化的呢?也就是农民之间是如何寻找自己的公平和正义的呢?过去是依靠家庭的父亲来主持正义,家之外就希望清官主持正义,最高是皇恩浩荡,主持最后的正义。
1911年的时候皇上被打倒了1949年之后家长制被作为封建礼教取消了。今天他们既有市场,又有习俗,还有权力与计划的影子,他们如何面对这些环境,如何选择自己的标准,的确是困惑着的。
所有这些混沌能否给今天的农民寻找到良善与可依靠的习惯、风俗、礼教、政治呢?如何能够协助他们建立起基本的公平和正义呢?
姐姐的时间挂在墙上
我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离刑、村的。20多年后,我回到我的家乡,路还是那条泥泞路,小道旁边还是那些旧房子,时间在这里望去似乎是凝固的,但是田野依然是那么生机勃勃,如果3月下田甄鲜花和绿叶,同样鲜活得让你不知道时间。
其实在我脑海里,时间一边是挂在墙上,一边是生长在田野里的,所以我说我姐姐是鲜活在时间静止中的姐姐。
相对于我的姐姐来说,尽管我们是同胞姐弟,童年生长在同一个乡村,但是今天的我似乎赶在时间的前面,我不但在80年代中期就跨越了农门,而且在80年代末期赶上了出国。
我的时间似乎走在姐姐的时间前面。
但是我的情感却还在姐姐与我的童年时代。人是感情的动物,血缘关系的情感今天至少还是没有多少污染,还是具有高度的历史积淀,给人类一丝温暖和指引。
姐姐只读过两年书,出嫁前上小学4、5年级两年。那时候我们那一代的农村女孩子在出嫁前,象征性地给念两年书,然后就准备出嫁。我姐姐就是这样。之前的女孩子是不是有这个福气我不知道。大约是没有的。我记得姐姐上学的时候,年纪显然是大了点,当然村里还有其他类似的女孩,也是姐姐平时种田的伙伴,她们似乎比姐姐高、大些。
在我的记忆里,姐妇一直显得并不大,而且单薄。
姐姐是我上面的一个,她只得带我到学校去,这是农村的习惯,大带小,再承包家里的洗衣煮饭喂猪。当时农村孩子们大都这样,一边上学,一边干家务
我跟着姐姐,先是躲在课桌底下,后来也跟着学习起来。
偶尔我也跟姐姐们跳绳、踢踢皮球,偶尔也不去教室,姐姐们上课了我跟别的小孩在外面玩。
记得最真实的一个场景就是1976年9月9目之后紧接着的一天,记得那时农村已经比较冷了'地上似乎结了一层薄薄的霜,但是我舍不得把姐姐为我新做的鞋子穿上。那时小学教室里有为毛主席布置的灵堂,窗子四周用黑布蒙着,松柏树做的花圈竖立在教室中央,毛主席的标准像安放在花圈中间。似乎点了什么灯?要不然黑咕隆咚怎么看到主席的遗像呢?
全村男女老少都成群结队地排成长队从教室一个门进去,另一个门出来,然后是穿过田间游行,我跟着姐姐,提着鞋子。在我准备进灵堂的时候,记得有大人过来要我穿上鞋子,我进去的时候穿上了,但在田野游行的时候,我又脱下来,提在手上。
还记得不久之后,为庆祝打倒“四人帮”,我写的“铁拳痛打‘四人帮…在全大队开会的时候,上主席台念。这是我记忆中最早的作文。
后来父母笑话我,说我上台也不紧张,叉开两条腿,双手胳膊拐在桌子上,眼睛盯着念,但是却不知道下面是破裆,据说有人笑,但是我当时是不知道的。
这就是我最早的上学记忆。
今天回想起来,我有时候觉得那么复杂的文明,居然在我那个落后偏僻的村子里可以传承,我还可以从那里走出来,上大学,成为今天所谓的跨国人才。我不知道今天叫我回去,去村里代课,能否带出一个大学生来?
从这个角度,从我内心深处,我敬仰我的那个小村,敬仰那里的父老乡亲,一个离文明那么遥远的乡村,居然还有可能培养一个链接世界的学生。
这么跨度的历史,让我在众多的感激之中,当然最感激我的姐姐。
姐姐尽管上了两年学,但是即使在这两年,她还负责家里9口人一年一双的鞋子,纳鞋底、做鞋样,一针一线。姐姐的小手那时经常被针剌破,每当流血的时候,我是最不敢看的,至今都怕看到血,可能这是小时候留下的记忆。
记得我做完作业后,姐姐还在煤油灯下纳鞋底,我确实不知道姐姐什么时候睡下的,但是我知道姐姐辛苦,她第二天还要与我一块儿上学。
记得不久我就比姐姐念的年级高了。
小时候尽管不懂事,但是我也是不敢骄傲的,因为我知道姐姐的辛劳。
每当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我都不敢写下去,眼泪每次都打湿我的面颊,我不知道姐姐知不知道,但是我知道。
人的一生无非是过眼云烟,但是这人世间的姐弟情却是永恒的。
我常常这么想。
记得村子里,很早就说我很乖,很聪明,其实在我内心,并不觉得自己聪明,这都是姐姐纳鞋底纳出来的。
姐姐比我大不了几岁,却完全是另外一个人生。
对比起来我是有愧的。
姐姐很快念完了两年,就又去栽秧割谷、积肥做家务去了。
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冬天冰封雪冻的,姐姐要与上面两个哥哥、父母上水利,开挖沟渠,在软软的沼泽
地里,小小的个子,像大人一样挑担子,踩在软软的泥土上,水与泥一直陷到膝盖,走路都是难的,还要挑担子。小时候我体验过,几乎全身都翻滚在泥里,我想我小小的姐姐,是如何从那里走过来的呢?而且一直在那里走着?
每当我回忆儿时的记忆,总挥不去上面两个形象,一个是主席,一个是我姐姐,这么天差地远的链接,可能在我心深处,我想无论怎么样,要改变命运,其实就是要改变公平和正义。
这是我心中永远的念想。
这是我研究追赶型经济学之所以得出要矫正的办法,首要的机制就是平权、确权、维权,其次才是外生的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排在后面的才是反哺机制和救济机制。
姐姐出嫁的时候,我还在上学,我不知道姐姐的婚礼是如何办的。
因为高考在身,容不得分心参加婚礼。
但在我的记忆里,出嫁后的姐姐塞了我不少次钱,每次都似乎是偷偷的,而且是不容分说的,我知道姐姐的钱得来不易。
但是我从来不敢问。
那时姐夫家在农村公路旁边打铁,是80年代最早的万元户,姐夫家乡比我的家乡离城市近些,那时我以为离城市近一些,就富一些。
但是不久姐姐因为生的不是男孩,就不断地超生,还把一女孩送了人。
后来我自己也做了父亲,我知道姐姐的心里肯定是难受的。
90年代初期,我从国外回国几次,想在家乡兼职做点事,那时其他兄弟姊妹还小,下面3个尽管都已经辍学种田了,我还是把他们从田间拉出来,一个个都上了大学,然而却没有考虑帮姐姐—下,因为姐姐早已嫁人,还有了自己的家,下面小弟小妹前途要紧,于是忍痛没有顾及姐姐。
2000年之后,姐姐到武汉来,她自己在街上擦皮鞋,一次我看到她逃城管的人,提着皮鞋箱到处奔跑,姐姐看到我,也还跑,他可能知道弟弟其实也帮不上忙。
那一刻在我心里特别特别地痛。
我知道自己没有本事,我知道所有像我一样上了大学的朋友,其实在城里早忘记了自己的父母姐妹兄弟,因为今天许多的政策就是他们制定的。
有一次我去印度,我看到五星级酒店外,依然有乞丐,大家都相安无事,我想什么时候,那些由姐姐妹妹父母兄弟供养上了大学的人,再不制定驱赶自己姐姐的政策该是多好呀。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说梦话,但是我是真心地这么想。
对于这些,我实在是无能为力,所以躲在老远老远的国外,辛苦地学习、辛苦地养家糊口,为的是将来如果有出息,能够建议我们的政府在城市里,即使为了市容,也不驱赶他们,比如可以考虑为他们留下一个小小的摊子?
为他们的劳作遮点风、避点雨。就像当初他们用同样小的肩膀为我们遮风避雨一样。
我继续留在国外,为的是不断地用功,看能否做一点学问,比如什么东方经济学,研究如何改变类似我姐姐那样的命运,看能否获得一个什么大奖,让自己的学说出点名,让更多人被感召。
其实除了这个办法,我的确是毫无办法。弟弟的时间悬在海外
2010年的时候,姐姐的大女儿结婚,—对新人在婚礼上,在双方亲朋好友的见证下,非常热闹,幸福得完满。
在一个大酒店里,宴席不无排场,姐姐分外骄傲,女儿女婿都在武汉过起了城市的生活。
讲台上,他们落落大方,讲话得体,坐中姐姐姐夫喜不自禁。
‘
我在为姐姐高兴的时候,却掉下了最多的眼泪,似乎只有我知道姐姐的故事,知道她的喜怒哀乐,我知道姐姐走到今天的城市为自己的女儿结婚,那是多么遥远的路,那是多么的不简单。
但是我看着姐姐对过去似乎毫不牵挂,只感觉着眼前的幸福,于是我也为姐姐深深地感到了幸福。
或许痛苦和幸福,知之者知之,不知者不知之吧?
但愿姐姐永远只感知幸福,而不感知不幸福。
这是小弟的心愿。
显然这是多么的唯心,但是我只能这么唯心。
而我除了继续努力,企图把信用、价值、货币、精算、知识产权、银发经济学等研究到感动上苍,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么个学问,然后齐心协力去改变它以外,别无他法。
我知道自己不能如宗教家们那样给姐姐一颗感知幸福的心,也知道自己不是老板,不能通过外生的投资来改变他们的命运,更不是政治家可以通过解放政策,让农民们拥有内生的谈判能力,以及更加艰苦的努力,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只有希望自己学习、研究,再学习、研究,无论地老天荒,与孤灯为伴。
都说四十不惑,我已经走过了一个四十,接下来还会再走一个四十,甚或更多,也许没有那么多。
我不知道自己的将来,我对自己的将来没有拥有任何胜算的概率,这一点与我姐姐一样,祈祷似乎是唯一的。
外国政府官员来华取经
5月10日,由中国商务部举办,国家外国专家局承办,国家外国专家局培训中心具体负责实施的援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项目——“发展中国家智力引进官员研修班”在北京开班。此次研修班是国家外国专家局为发展中国家举办的第八届智力引进官员研修班。共有来自巴基斯坦、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埃塞俄比亚、哥斯达黎加、莱索托、赞比亚、肯尼亚、乌干达、智利、加纳、委内瑞拉、马拉维和巴勒斯坦等15个国家的25位学员参加研修,他们均任职于所在国的外交部、贸易部、经济部等部门。我国30多年来的对外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家外国专家局希望通过开办“发展中国家智力引进官员研修班”形式,与发展中国家智力引进部门共享引进国外智力经验。(国家外国专家局培训中心供稿)
外国专家看四川
中国外文局组团重访灾区
5月15曰,由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副局长陆彩荣带领的‘冲国外文局汶川地震3周年对外报道采访团”抵达四川成都。采访团一行24人抵达四川成都后马不停蹄地与新华社四川分社、四川卫视及四川新闻网的代表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入的座谈,地方负责人分别就各自汶川地震3周年的新闻报道工作进行了总结,与外国专家分享了各自的采访、报道经验。据了解,中国外文局采访团由来自美、法、西、日、俄等国的5位外国专家及《人民画报》社、《今日中国》社、《人民中国》、《中国与非洲》杂志、《北京周报》社、《中国报道》社、《对外传播》杂志及中国网等相关单位的领导、记者共计24人组成。活动发挥了中国外文局在多语种对外宣工作中的优势,是外文局外宣工作中一次大胆的尝试。(来源: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