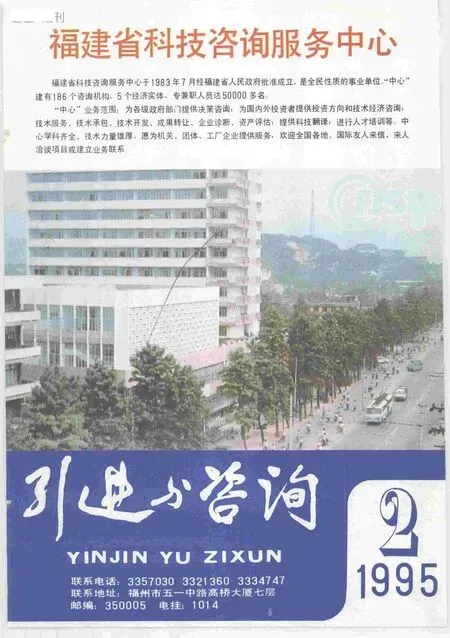媒介文化及媒介环境、媒介人物、媒介事件
张建华
媒介文化及媒介环境、媒介人物、媒介事件
张建华
闽江学院
媒介文化是因大众媒介的社会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它以媒介环境、媒介人物、媒介事件的创造在一定程度上重构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价值规范和社会价值意识的建构。
媒介文化 媒介环境 媒介人物 媒介事件
什么是媒介文化?媒介文化是通过再现媒介环境、媒介事件、媒介人物等一系列媒介元素来分析评论并且创造传播消息的能力。正如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所认为的那样,“电视以及其他媒体文化的形式在构建当代的认同性和塑造思维、行为等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它意味着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媒体文化,说明媒体已经拓殖了文化,表明媒体是文化的发行和散播的基本载体,揭示了大众传播的媒体已经排挤掉了诸如书籍或口语等这样的旧的文化模式,证明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由媒体主宰了休闲和文化的世界里。因而,媒体文化是当代社会中的文化的主导性形式与场所”[1]。也正如著名学者孟繁华所说,“传媒决不仅仅是新闻、消息或言论的集散地,它在有意参与政治的同时,也以渗透的方式渐进地改变了读者或观众的价值观念。”[2]
1 媒介环境
沃尔特·李普曼是20世纪美国最负盛名的新闻学者、社会哲学家与专栏作家,他的《舆论学》(1922年)一书则是在新闻史上最早对舆论传播现象做出系统梳理、总结与探讨的著作。在这本书第一章的标题就是“身外世界和脑海世界”。李普曼认为身外世界(即现实世界)是非常广阔和复杂的,人们很难用亲身直觉去感知它,例如现在的美日韩的海上军事演习、石油价格的涨跌及关税等这些人类面临的问题,我们却不能直接接触它们。对于我们来说,身外世界体积巨大辽阔,内容纷繁复杂,事件层出不穷,许多现象几乎是不可触摸、不可眼见以及不可思议的。
但是,我们既然生活于这个世界中,就要与之发生关系。交流的平台是什么?依靠怎样的凭借物?这就需要我们创建一个脑海世界(虚拟环境),它产生于大脑对现实环境的再造和再现。正如《舆论学》在开始时提到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讲述过的有关洞穴的比喻,在此借用罗素对它的概括:“那个比喻是说,那些缺乏哲学的人可以比作是关在洞穴里的囚徒,他们只能朝一个方向看,因为他们是被锁着的;他们的背后燃烧着一堆火,他们的面前是一座墙。在他们与墙之间什么东西都没有;他们所看见的只有他们自己和他们背后的东西的影子,这些都是由火光投射到墙上来的。他们不可避免地把这些影子看成是实在的,而对于造成这些影子的东西却毫无观念。”如把这一比喻用于对身外世界和脑海世界的描述中去,那么“背后的东西”就是现实世界,而燃烧着的火就是大众媒介,囚徒是受众,墙上的影子则是脑海世界。
正如李普曼所描述的,脑海世界即是媒介环境,指的是一个由许多真假不一的影像所组成的虚拟世界。美籍华裔著名的传播学者居延安也曾说过,“我们看不到世界本身,看到的是被大众媒介选择和解释过的世界。”
那么这种虚拟环境的作用是什么?李普曼在《舆论学》中认为,所谓的虚拟环境,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虚拟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在这整个过程中,作为传播者的新闻媒介以他们所理解的方式精心编织与绘制了一个关于这个世界的图景。广大的受众大多在不曾意识这一过程的情况下欣然接受和认可这幅世界图景以及(更重要的)附着于这幅图景背后的关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意义与想象。由此产生了历史与现实中的道德说教、美化宣传与愚民政策。李普曼在对社会的民主自由深切向往与渴望的同时,却对于“民主自由”旗帜下的新闻传播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舆论怀着深深忧虑与戒惧。现在的我们是否也会有如此的忧虑呢?李普曼是把他的这种忧虑建立在传播者和受众的绝对对立的前提之下的,而当代社会民主与自由作为观念形态已经普遍深入人心,作为新闻传播之根本前提的言论自由与表达自由不仅作为基本权利写入各国宪法,而且更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得到充分的保障施行。以当代美国社会为例,联邦最高法院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确立的“明显而急迫危险”的言论自由原则以及“实际恶意原则”,在制度层面极大地扩展了新闻传播的自由空间,有了宪法权利的保障,传播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对于权力的依附以及强制性力量的宰制,实现其真正的“自由言说”。社会趋向多元化,这意味着社会的个体自立、利益分化与结构均衡。社会多元化的实现恰恰打破了传播者与受众的截然分立,随之而来的正是传播主体的多元化、利益表达的多元化、社会关切的多元化,促成了传播者从“精英取向”到“大众取向”、传播内容从“一元文化”到“多元文化”乃至“平民文化”的转变。这就体现了虚拟环境所带来的平等性和民主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以网络为平台的个人网站、网页、bbs平台、个人博客等等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个人传播方式以其极低的技术门槛、极宽松的自由环境、极广阔的传播范围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体传播方式的界限与范围。普通的民众既可以是互联网媒介的传播者、也可以是受众。因此,在互联网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成为传播者的广大受众,在其充当传播者为别人“编织关于这个世界的意义与想象”时,已经越来越开始认清他们以前所不曾意识到的这个虚拟环境的过程,虚拟环境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交流的空间。
2 媒介人物
媒介人物和媒介事件是构成媒介环境的主体。媒介人物就是经过大众媒介传播而被人们所熟知的人物。这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平民通过传播媒介而认知现实中的名人。但没有几个人曾亲身接触过这些名人,大多数人所见的还是通过媒介而熟知的。倘若没有媒介呢?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奥唐奈在《希特勒暗堡》一书中曾记述过一件事:“1976年秋天,我和斯配尔(即希特勒的军备和战时部长)在这些重新栽种的树下散步,进行我们最后一次长时间的采访谈话。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柏林市民几乎没有人认得这个高高的浓眉男子,而他曾是这座城市的规划师,在战争的危机的三年中,他作为军备和生产部长,曾经管理过欧洲大陆大部分国家的经济。”[3]
媒介人物另外一种就是建立了较著名的传播媒体的人物。如凤凰卫视的创始人刘长乐、贝塔斯曼的创始人卡尔·贝塔斯曼、慧聪媒体研究中心的董事长兼CEO郭凡生等。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对媒介有着自己的一套独特的思考方式,注意分析市场,采取合适的战略。如,慧聪媒体研究中心的董事长郭凡生在竞争中采取“终结性行动”,即避免面对面的挑战,在与竞争对手进行周旋的过程中,抓住那些没有被占领或竞争不够激烈的市场领域,改变竞争规则,并使其对行动的发出者有利。这套策略的运用使得慧聪研究中心在短短三四年的时间里声誉鹊起,在广告界可以与央视—索福瑞相提并论。
此类人物都有着不凡的经历和知识积累,深谙媒介的运行规则。如凤凰卫视的创始人刘长乐在对电视台的市场进行调查之后,得出要走中文台、国际化、热点化的道路,始终坚持“东西南北大荟萃,为观众提供另类选择”的项目定位原则和遵循“剪刀+口水”的模式,创立了一种低投入、高产出的运行机制。刘长乐在创办凤凰卫视之前曾控股今日亚洲控股公司,丰富的工作经验有助于创台的顺利进行。慧聪媒体研究中心也集聚了一大批学者型的高管,董事长兼CEO郭凡生研究过企业股份制改革和西部发展的问题,曾在1984年5月提出的“反梯度理论”、中国东西部差距拉大的分析报告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西部学派”在当时的理论界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著有《贫困与发展》、《摆脱贫困的思考》等。慧聪媒体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姚林曾任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副主任,在日本做过访问学者,在社会主义经济学、价格学、市场营销及现代流通理论等方面都颇有建树,加盟“慧聪”后壮大了“慧聪”的实力。
另外一种是平常人成为媒介人物。其中有以网络音乐而出名的网络歌手,还有以“下半身写作”而成名的木子美、竹影青瞳,以“超常的表演欲”而被熟知的芙蓉姐姐、水仙妹妹,更有甚者如凤姐竟以征婚炒作而出名。对这些人物人们褒贬不一。
3 媒介事件
媒介事件是指“一种特殊的电视事件”,但它不同于一般的电视节目、电视新闻。它范围更大,是国家级或世界级的“大众传播的盛大节日”,同时也是群体情感的一种宣泄。
媒介事件通过对日常事件的干扰,如对消费主义的抵制、对以往社会中矛盾与冲突的化解或搁置等表现出 “垄断性”的特点,这是其他传播活动所无法比拟的。媒介事件的主要特点是把事实从其发源地剥离出来,改为演播室。有的事件根本没有原发生地,播出的是同时发生于几个不同地点的事件的蒙太奇组合。如肯尼迪和尼克松,一个在纽约,另一个在加州,他们的辩论“事实”并没有因为在空中和在起居室而被贬低。
媒介事件的生产及其故事的讲述过程还与电视艺术、新闻艺术及叙事艺术有一定的关系。对于传播节庆、号召参与及统一意志所采用的修辞手段的研究,要求电视在“理解事件——以及观众准备随时承担仪式角色——关键在于对下列方面进行分析:如何建构故事,如何保持兴趣,如何博取支持,如何深化内容,如何使观众与银屏互动,以及应当给观众分配什么样的任务”等。北大百年校庆是一个媒介事件。国庆文艺晚会播出时间是国庆节晚上的黄金时间,而实际举行时间则是在9月30日晚。这是传播媒介有意安排的。即“媒介事件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重大新闻及突发事件,还在于媒介事件通常是‘经过提前策划、宣布和广告宣传’,在一定意义上大众是被‘邀请’来参与一种‘仪式’,一种‘文化表演’。尽管人们的正常活动与社会秩序由此受到了干扰,但是媒介事件‘自己却不能被干扰’(除非有另一媒介事件与之竞争),尽管不同的社会结构与不同的文化传统,对媒介事件会有不同的表达和解读,但媒介事件所发挥的作用与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巨大冲击力,乃至在某种时刻‘充当了引起社会变革的遥控代理’,而却十分相似,或者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4]处于日常生活中的老百姓,不可能都在国庆节前夕亲身参与这场晚会,毕竟场地和人数都是有限制的。然而,广大民众都可以在大众媒体的盛情“邀请”下,在一定的特定的时空条件之下,共同参与了一种“仪式”的盛宴,虽然不是亲临现场,但是民众也在电视机旁,在国庆节晚上安静、祥和的气氛之中,想象性地体验了一次精神的洗礼和畅游。在传媒的引导和塑造之下,在全体民众的积极参与之下,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得以再次被建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荣誉感也同时得到了认同,大众媒介创造了这种身临其境的“节日仪式”的感觉,国庆节在此更能说明它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节日,也是大众媒介自身的节日。
媒介事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在其著作《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中又将之称为媒介事件的效果,分为对参与者的内部效果和对机构的外部效果。对参与者的内部效果分为:对组织者和主演者的效果、对记者和播出组织的效果、对观众的效果。其中对组织和主演者的效果是“事件的直播创造了对事件成功的压力”。电视台可以通过炫耀大众反应的证据向主演施加压力,通过此种方式来控制大众反应。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把萨达特之行描述为一次牺牲的过程中唤起了互惠的准则——这就是说他应该得到某种回报——这作为“大众舆论”被反馈给主演并且被用以向以色列组织者施加压力。这“显然有对失败的强烈恐惧。”[4]对观众的效果则首先表现在“媒介事件干扰人民生活的节奏和焦点。”[4]1989年2月,美国电视节目《60分钟》报道了这样一条消息:施用过化学药物Alar的苹果对孩子有害。一阵苹果恐慌接踵而至。洛杉矶、芝加哥和纽约的一些学校的自动餐厅都下令把苹果从菜单和储藏室里撤掉。在华盛顿州,这个种有全美国苹果量50%的地区面临着减产的经济损失。这一媒介事件成为日常生活的焦点,人们谈苹果色变。女演员梅丽尔•斯特里普立即把这则消息作为她坚持不懈地反对农药运动的原因之一,并因此被邀请参加“Donahue”节目和其他的脱口秀电视节目。一位校领导则说:“正是过激反应和愚昧无知才导致这种愚蠢的论点。”加利福尼亚保健部门的董事肯尼恩•凯泽也说这场恐慌造成了一个有毒的魔鬼。
显然,媒介文化的形成与大众文化的出现、大众媒介的发展和平力量普及密切相关。媒介文化以一系列的媒介元素如媒介环境、媒介人物、媒介事件发挥着它的社会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制约着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和判断。
[1]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 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4.
[2] 孟繁华. 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3] 李彬. 传播学引论[M]. 北京: 新华出版社,2003.
[4] 丹尼尔•戴扬, 伊莱休•卡茨. 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M].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