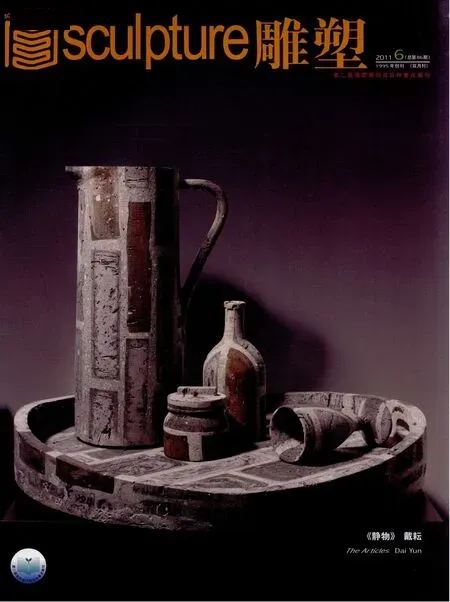穿越时空,穿越记忆——雅尼斯·库奈里斯访谈
■ 黄笃 翻译:郝志蓉 by Huang Du,t ranslater:Michel le Coudray
黄笃:库奈里斯先生,据我所知,您早年在希腊渡过,曾亲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希腊内战,这两场战争进行了大约10年之久。您大约于1956年移居罗马,进入美术学院学习。但我想了解,您从希腊去罗马的原因是什么?
雅尼斯·库奈里斯:当一个人18岁的时候选择是很单纯的。坐上火车,就去了意大利。这不是很麻烦。但我在意大利遇到了一些艺术家,我们一起努力创造了一种带有批判性的艺术语言,这才是重要之处。
实际上,我一直在欧洲艺术圈内。而早年意大利的经历开始使我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观,这至今对我仍至关重要。是的,我出生于希腊,并亲历过战争,所有这些经历对我的人生来说都是重要的。但是,我在意大利找到了一种逻辑和一种语言。而作为艺术家,我又认为自己诞生在意大利。所以,我觉得意大利比希腊对我而言更亲近。


黄笃:1960年,您在罗马的Tartaruga画廊展出的作品《无题》。作品由“数字”“字母”“箭头”和其它符号组成。它们背后的观念是什么?
雅尼斯·库奈里斯: 1960年,我有幸在Tarta ruga画廊举办了首次展览。我当时非常年轻,还是美术学院的一名学生。重要的是,这些对我来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绘画,有我的房子墙壁那么大的尺寸。我把一张张纸贴到墙上,从一面墙贴到下一面墙,墙与墙之间不留缝隙。由此,尺寸已与空间衔接起来,因为它们的大小取决于空间。
于是就有了一种节奏的尝试,这些纸张就像音乐中的音符。实际上,我的确在吟诵它们。意大利曾产生了一位举足轻重的诗人朱塞佩·翁嘉雷蒂,他的富于节奏感和隐逸感的诗影响了我。他的诗歌散发着古罗马赫尔墨斯主义。(赫尔墨斯主义或西方的赫尔墨斯传统是一套基于希腊化的埃及伪经作品的哲学和宗教信仰。这些作品据说是赫尔墨斯· 特利斯墨吉斯忒斯的秘密教义,他是埃及智慧之神图特和希腊赫尔墨斯融合的化身。西方神秘宗教传统深受这些信仰的影响。这些信仰在文艺复兴时期亦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可以说,我的早期作品创作于1959年和1963年间。1960年,我的作品首次在Tartaruga画廊展出。从一开始,“空间”就在我的作品中占据了中心位置。
黄笃:在1967年,您似乎开始放弃绘画,而转向装置。在一个叫L’Attico的新画廊中,您展出了一些装置作品,它们包含了三种要素:涂有清漆的铁板结构夹控着棉花、四个铁制容器盛有土和仙人掌、涂有清漆的铁板上的栖木伴有活的鹦鹉。什么原因使您从二维创作转向三维装置作品,甚至包括作品中对动物的使用?
雅尼斯·库奈里斯: 这些早期作品已经产生了空间问题或对空间的忧虑。我从未认为这些作品是绘画,也就更谈不上从二维转向三维。从一开始,我就没有企图做画。它们不是“画”上的,而是“贴”在表面上的。所以,对我来说,数字、字母与鹦鹉等的作品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看数字、字母作品的人“解读”作品。然后,第二步是面对于鹦鹉的作品,观众不再解读了,而是鹦鹉对这位观众说话。因此,在我看来,鹦鹉更像是作品的一种延伸,而不是作品方向的改变。
这些作品的确是在当时那样一个重要的政治时刻问世了。材料通过自身的重量得到呈现也在观念中体现了出来。例如,所谓的“煤”,煤确有其重量,因为重量是作品存在的条件。同样,它还表明了一种流动性,即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如此以来,我们开始一边旅行,一边创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创作作品”。这也是“这类作品自由”的组成部分。因此,它不仅仅局限于工作室的创作,更多的是与场合、关系、联系和诸如此类的事相关联。

黄笃:1969年,您在那不勒斯的卢西奥·阿梅里奥(Lucio Amelio)画廊展出了一件多媒体装置作品,其上下垂挂的8个金属天平上盛有咖啡粉。这件作品的核心观念是什么?您所用的媒介与情况、语境或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雅尼斯·库奈里斯: 显然,当时并不存在经济方面的问题。重要的一点是它与艺术家的作用有更多的关联。我们正在寻求更多自由,例如,我将小的固体乙醇片放在一块铁板货架上,一旦点燃生命很短暂,仅仅3分钟就消失了。这件作品在那不勒斯举办的一个展览中展出。所以,这些作品既不仅仅是幻觉,亦非乌托邦,而是蕴涵着意识。尤为重要的是,我们主要的问题是创造一个更强大的艺术家形象,这已经是政治了。艺术家是作品的核心。

黄笃:那么,您的意思是想在材料中找到能量及其转化的过程吗?
雅尼斯·库奈里斯: 许多是关于能量的。当时就有这样巨大的能量。艺术家拥有能量,他们一直在发现和体验。我并不喜欢用“正在体验”这个词,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根本不是一个有实验性的人。我的作品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不是一个实验品。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黄笃:现在,我有一个颇为迷惑的问题。1969年以前,您的一些作品中已使用了动物。而在1969年,当您将12匹马拉进罗马的L’Attico画廊时,并非毫无缘由,而是遵循着自己的艺术逻辑。然而,众所周知,在20世纪60年代末,意大利精神病学家弗兰科·巴萨格利亚提出了“民主的精神病疗法”的思想,并在都灵的戈里齐亚建了一家精神病院。当时的想法是要打破医院界限。因为这种医院在功能上一直是把精神错乱的人规定、限制和禁锢在某一固定空间。巴萨格利亚的思想就在于要解放或开放医院,以建立患者与人、社群乃至社会的交往。
显然,您的这件作品像杜尚的作品一样具有颠覆性。因此,我想知道,您于1969年展出的12匹马的作品是否与“打破医院界限”的思想有关联。倘若与其思想无关,那么,该作品背后的理念是什么呢?
雅尼斯·库奈里斯: 对我来说,重要的不只是将12匹马牵入画廊,而是将它们拴在画廊四壁,并界定了眼睛平视高度的空间周长。也就是在1969年,我还在巴黎一家画廊创作了一件类似的作品,是一个环绕画廊墙壁燃烧煤气的装置(注:用金属管以吊钩的方法悬挂着喷射的火焰,地上放着煤气罐)。所以,画廊空间被以戏剧艺术(d ramm atu rgia)的要素所利用和发挥,如此这般独特效果和姿态,从卡拉瓦乔直到现在, 像意大利许多艺术大师那样,“戏剧性”在作品中至关重要。


黄笃:那么,您的意思是这一作品与传统意大利作品有关,是吗?
雅尼斯·库奈里斯: 可以说,戏剧性一直是这类意大利传统的条件,像毕加索的绘画《格尔尼卡》也遵循了这一传统。
黄笃:我要回到您于1973年创作的有火的作品。“贫穷艺术”强调即兴事件、偶发事件和不可预知的理念。这些理念是否受 “游牧”思想影响?在您之前,有像路西奥·冯塔纳、皮耶罗·曼佐尼和阿尔伯托·布里这样的艺术家,比如:布里也在其作品中用火。您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与这些艺术家有关吗?
雅尼斯·库奈里斯: 我的大部分作品都基于元素间的某种辩证关系,如:火与铁(就是这种辩证关系)。因此,这种矛盾或争斗存在于感受力(火)和结构(铁)之间。而在煤、金属、鹦鹉等作品亦可看到感受力和结构之间的类似关系。因此,材料之间也有这种的对话。只有如此,感受力才会变得更强大。作品不是“被再现”,而是要“被呈现”。所以,它是一种姿态,速度也非常快。重要的是不要再现,而要一种直接的姿态。此外,马就有类似的直接影响。
现在,回到您刚提的第二个问题。是的,冯塔纳、布里、翁贝托·波丘尼,我们是同属一个家族血脉。但不仅仅是他们,还有像杰克逊·波洛克、乌姆博托·波丘尼和许多其他的艺术家都在我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关于游牧,上世纪80年代罗马曾有过一场大争论。我从没有把自己视为游牧者。在我看来,诗人兰波也不是游牧者。然而,如果我不是游牧者,那我的确是一个旅行者。我去过很多地方。在我的灵魂深处,我是一个游客。我希望自己是一个能与人沟通的,思辨之人。例如,如果我来中国,我想把某些东西带到中国,也能从中国带走某些东西。我是那类浪漫之人。

黄笃:从某种意义上说,您是乌托邦式的艺术家。
雅尼斯·库奈里斯: 当然,艺术家不得不乌托邦式。
黄笃:刚才您提到您的作品和传统艺术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贫穷艺术”的艺术家不同于未来主义的艺术家。例如,米开朗基罗·皮斯特雷多和您本人的作品都非常尊重历史和传统价值,而未来主义的艺术家对传统则颇多微词。您在1984年曾写过一篇文章,文中写道“没有历史感,便很难作画。”您如何看待历史意识和现代观念之间的关系?
雅尼斯·库奈里斯: 在我看来,波丘尼的《行走的人》(1913年,铜雕,《空间中连续性的独特形式》)让人联想到希腊雕塑《胜利女神》(Nikedi Samotracia)。未来主义的艺术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运动有密切关系,他们是介入者(in terven tisti)。他们颂扬现代,憎恶传统。这就是未来主义。(未来主义是一场艺术和社会的运动,20世纪初起源于意大利。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意大利现象。不过,类似的运动也同时在俄国、英国和其它国家发生。未来主义者运用任何艺术媒介进行实践,涉及绘画、雕塑、陶瓷、平面设计、工业设计、室内设计、戏剧、电影、服装、纺织、文学、音乐、建筑甚至美食)。
我是属于接近二战结束的一代,也是带有战后问题的最后一批艺术家。未来主义的艺术家创作深陷一种“颂扬战争”之情。之后,未来主义和“贫穷艺术”的艺术家一起目睹了战争的终结,我们出现了如罗伯托·罗西里尼和维托里奥·德·西卡的电影,他们的电影恢复了戏剧,同时也恢复了传统,使意大利人回想起了苦难。很显然,曼佐尼创作的《大便:意大利制造》表明,他并不是一个未来主义者。

黄笃:这个时期意大利产生了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包括德·西卡、罗西里尼、安东尼奥尼和费里尼。我的问题是,如果新现实主义电影和“贫穷艺术”的确存在关联,那它们之间是什么关联呢?
雅尼斯·库奈里斯: 罗西里尼和德·西卡等是那个时期的大知识分子。他们积极应对意大利人的战后问题及其损失。他们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我们的大师。
我相信,关于“贫穷艺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建构并找到了呈现我们作品的方法,这种语言的命运就是向世界开放,决不能局限于意大利本土。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贫穷艺术”是欧洲人提出来的,用于辩证地对抗美国人提出的“极简主义”和“波普艺术”。1969年,哈罗德·史泽曼策划了一个重要展览《当态度变为形式》,汇集了来自美国和欧洲的艺术家。从此以后,双方开始了一场大对抗。上个世纪70年代,亦有其他许多展览发生,将美国和欧洲艺术家汇集一堂,包括德国的博伊斯和一群严肃的意大利艺术家,他们现在仍在努力创作。所以,这个目标,也是我们冒险的出发点,与我们所谈论的(包括战争、新现实主义、布里、冯塔纳等)都有关。
黄笃:另一个问题是切兰(Celant)先生在1967年写的《贫穷艺术》一书中提到了意大利艺术家马里奥·梅兹、您、鲍里尼和皮诺内,还包括德国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荷兰艺术家迪贝茨以及美国极简主义艺术家卡尔·安德烈和理查德·塞拉。他把这些艺术家都纳入“贫穷艺术”的范畴。您对他的观点有何看法?
雅尼斯·库奈里斯: 很难将这些艺术家放在一起。例如,卡尔·安德烈是一位令我敬佩的艺术家,但他绝然不同。他教条,而我们却不。而艺术家理查德·朗的观念更接近于“贫穷艺术”,因为他具有同样的流动性。
黄笃:切兰在一篇文章中把“贫穷艺术”的艺术家形容成游击队员。一个特别的问题是关于马里奥·梅兹于1968年创作的《静坐》和1969年创作的《干什么?》。这些作品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如1968年法国五月暴乱)有关吗?
雅尼斯·库奈里斯: 我不能替马里奥·梅兹回答有关问题,但我认为曼佐尼的《大便:意大利制造》确与政治有关。我还认为俄罗斯艺术家马列维奇的绘画也与政治有关,因为他的黑色方块的确是与民粹主义的对立。
今天对我而言,我喜欢德拉克洛瓦的绘画《摩洛哥的犹太婚礼》(1839)。我喜欢这位来自法国巴黎的艺术家的想法。他去了阿尔及利亚,受邀请到一所房子里,那里正举办这个犹太人的婚礼,于是,他创作了这幅画。我觉得这幅画画得很美。德拉克洛瓦画这幅画时,这种自由是一种很新的事物。对我来说,今天仍然很新,因为仍有同样的旅游精神,充满着文化的汇集与交流。
黄笃:1992年,您在德国的施瓦本格明德(Schwabisch Gmund)创作了大型装置,竖起一个36米高的T字形木架装置,从上端垂吊下一个巨大的装有老家具的麻袋。这件作品的观念是什么?
雅尼斯·库奈里斯: (以天主教堂为背景)这件作品的尺寸与教堂成比例,在教堂的前面安放着那件雕塑作品,如此的安放将这件作品与教堂并置于同样重要的位置。说到观念,这是一个沉重的观念。它来自于文艺复兴早期艺术家多那泰罗的雕塑《圣·乔瓦尼的头》,左手托着、展示着头,一个非常明确的举动告知 “我做的事,我负责!”要不是在德国,我绝不会创作这件作品。
我非常喜欢德国,我在德国(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教过8年书。德国对我一直都很重要,也许甚至比意大利还重要。
黄笃:我们谈一谈1989年在巴黎的《大地魔术师》展览吧。您对该展览的见解很有趣,因为您的观点与我之前的理解完全不同。在您看来,这个展览的意义或真正价值到底是什么?
雅尼斯·库奈里斯: 康斯坦丁·布朗库西住在慕尼黑。他决定离开慕尼黑去巴黎,后来他留在了巴黎。我很赞同艺术家决定自己的命运,而非由别人决定。这恰恰是我提到毕加索的作品《阿维农的少女》时想要表达的意思,因为由此可看出艺术家革命性态度的端倪。

黄笃:这是您第一次来到中国。您已去过很多地方,像云南、北京、上海。您对中国的印象怎么样?
雅尼斯·库奈里斯: 我所看到的都很美。人们都很有礼貌,很乐观。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
黄笃:我知道您此次中国之行是准备一个项目。能否告知一二?
雅尼斯·库奈里斯: 我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看中国,它迄今为止是如此奇妙。不管怎样说,我正在中国创作一系列作品,希望能在中国展出这些作品。
黄笃:这些作品是按部就班地创作还是为某一特殊场景而创作呢?
雅尼斯·库奈里斯: 兼而有之。例如,一些作品是在北京的一家工厂里创作,运输工作已准备就绪。接下来,我正在着手根据空间的情况创作一些作品。
黄笃:那么,我们衷心祝您在中国的艺术项目大获成功。由于采访时间较长,感谢您的耐心和慷慨。
雅尼斯·库奈里斯: 不用客气。我将很快回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