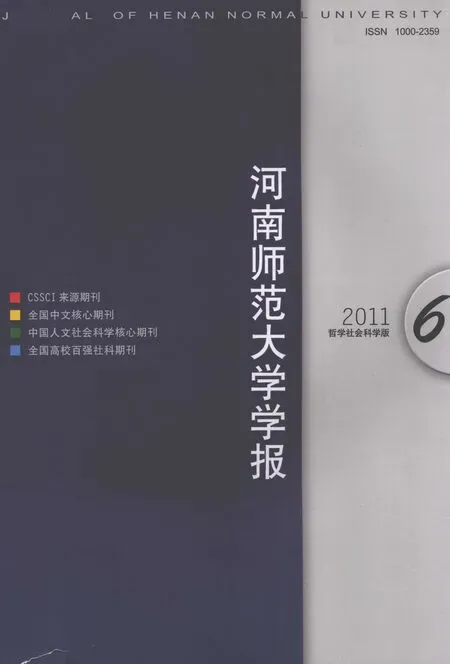普鲁斯特·博尔赫斯·纳博科夫
—— 构筑时间的乌托邦
李 茜,丰 云
(1.湖南女子学院 外语系,湖南 长沙 410004;2.德州学院 中文系,山东 德州 253023)
普鲁斯特·博尔赫斯·纳博科夫
—— 构筑时间的乌托邦
李 茜1,丰 云2
(1.湖南女子学院 外语系,湖南 长沙 410004;2.德州学院 中文系,山东 德州 253023)
普鲁斯特企图以反复的记忆留住时间,博尔赫斯以空间并置的方式诠释他的花园式时间观,纳博科夫因不能留住时间而精神焦虑。时间既是哲学家也是艺术家思考的对象,小说是关于时间的叙事,对时间的思考使艺术家在文学殿堂里构筑一个时间的乌托邦,或许这是人类能够用以对抗时间流逝的唯一武器。
普鲁斯特;博尔赫斯;纳博科夫;时间;乌托邦
小说叙事是时间的叙事,也是关于时间的叙事,时间作为宇宙存在的一个维度,即使在霍金那里也不是绝对物理的线性的矢量存在,艺术家对时间的哲学思考,无不是在以文化“谎言”的方式对抗时间的流逝,通过对时间的反复的然而是不同形式的书写挽留时间,在书写时间中寻求生命的意义与存在的永恒,以对时间的神话学、宗教学、哲学的思考来对抗“时间的线性流逝和生命的一次性”[1]的恐惧。于是,我们有了线性时间与圆形时间的区分。“圆形时间是一种最为古老的时间意识,它具有共时性特征,它把时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置于同一个层面上,把个体生命的不可逆转性融入和消解到永恒的轮回之中”[2];也有“时间创立者”[3]的犹太人的创世时间观数千年对人类精神的影响——时间是由创世之初开始的,时间也终于要回归到创世者那里,此岸天国观念或许是这种时间观的宗教学解释;也有了普鲁斯特以记忆留住时间的企图,博尔赫斯的空间并置的花园式时间观以及纳博科夫因不能留住时间的精神焦虑。
一
“追忆似水年华”是一个听起来富有诗意的汉语译名,但它的另一种较为直接的译名“寻找逝去的时间”,也许更能见出作品的真意。普鲁斯特终其一生追寻的宝贵事物就是时间,他认为人们在时间中占有的地位比他们在空间中占有的微不足道的位置重要得多,他为周围的一切都处在永恒的流逝和销蚀过程之中而感到困扰,遗忘会淹没他们最美丽、最宝贵的记忆。所以,他希望时光能够重现,希望在他心中如潮涨潮落般涌动的往事不会消逝于无形。他从对生活的观察中感到:一切事物,包括人类都将被时间冲刷得失去光泽、色彩,最后烟消云散,或许只有一种东西可以免受时间的侵蚀,那就是人的心灵、精神凝成的艺术创作。所以,他要写作一部“表示时间之外的现实”的作品,决心在作品中“铭刻时间的印迹”。《追忆似水年华》真正的主人公是时间和自我,作者通过自己的有意识记忆和无意识记忆追忆,在厚重的岁月积淀下搜索与挖掘一段段逝去的时间,并用文字将其结构于作品之中。这部巨著中充满了一段段特定的时间以及与之相关的空间、场景、人物与感受的再现。作者以细腻入微的描写复活了这些时间及相关的一切。作者常以某种“顿悟”,即对现时的种种感受与过去的种种回忆在心头的交汇,来展开对一段时间的描绘。马塞尔在反复分析自己吃“小玛德莱娜”点心的感觉,相同的味道触到了旧日生活的开关,姨妈当年住的那栋灰楼便像舞台布景一样展现在他的眼前,随之而来的是他幼年玩过的广场、奔走过的街巷,自己家和斯旺家花园里的花,河塘里漂浮的睡莲,善良的村民,教堂,以及整个贡布雷及其市镇周围的景物,全都在这杯茶中奇迹一般地复活了,“我们想方设法追忆,总是枉费心机,绞尽脑汁都无济于事。它藏在脑海之外,非智力所能及;它隐藏在某件我们意想不到的物体之中(藏匿在那件物体所给予我们的感觉之中),而那件物体我们在死亡之前能否遇到,则全凭偶然,说不定我们到死都碰不到”[4]。
在小说末卷《重现的时光》中,疾病缠身的马塞尔怀着绵绵愁思,走进盖尔芒特公馆的大院,去参加盖尔芒特亲王府邸的下午茶聚会。结果,就在不经意间,他一连受到了三次精神震动。先是在公馆门口,他因躲避电车而踩到不平的铺路石板,一瞬间,他沮丧的心情一扫而空,一种至福的感觉如同他当初在品尝到“小玛德莱娜”点心时产生的感觉一样涌上心头。接着,他在小书房客厅里,听到了一个仆人把汤匙敲在碟子上的声音,于是,“与高低石板所给予我的同一类型的至福油然而生”。因为这个声音,令他想起某一次乘坐火车停在一个小树林边上时所听见的“铁路员工用锤子捶打车轮调整什么东西的声音”[5]。只有这种超乎时间的生命,才能使他找回过去的日子,找回似水年华。因为“它既使我的想象力领略到这种感觉,又使我的感官因为声音,因为布料的接触等等而产生确实的震动,为想象的梦幻补充了它们通常所缺少的东西,存在的意识,而且,幸亏有这一手,使我的生命在瞬息之间能够取得、分离出和固定它从未体会的东西:一段处于纯净状态的时光”[6]。马塞尔感受到,自己在这种精神震动中体味到的是逃脱了时间制约的存在片段,它带给人的欢乐是丰富和真实的,他要全力以赴地把它固定下来,而固定它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制作一部艺术作品。
《追忆似水年华》这部巨著,所捕捉的正是这些逃脱了时间制约的、逾越了时间序列的存在片段,这些大量的片段组接成一幅巨型的意识的流动画卷。通过这幅画卷,他找回了逝去的时间,确认了自我,也为世人建构了一个独特的时间艺术的世界。于是,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得以透过这个独特的时间艺术而感知属于他的那一段“纯净状态的时光”。由此,普鲁斯特获得了永恒。
相比普鲁斯特以作品来艺术地挽留时间,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和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这两个20世纪的伟大作家则更关注时间的哲学意蕴。
二
时间是可以找回的,时间也是破碎的、凌乱的、交叉的花园式的。博尔赫斯也在寻找时间,他否认时间的连续,他说我们的命运之所以令人恐惧正是因为它不能倒转,时间是一条载人飞逝的大河,是一只毁灭的老虎,是一堆吞噬人的火焰,然而他似乎又不甘心时间就这样永恒的流逝,他个人企图用空间并置的方式抓住一瞬间即逝的时间,在这样的努力中,《交叉小径的花园》是一个成功的尝试。表面看起来,这篇小说是一个侦探或传奇故事。“一战”期间,一个住在英国为德国服务的华人间谍俞琛,为了向柏林传递情报,决定杀死一个与英军大炮阵地地点“阿尔贝”同名的人,以此传递信息给德国人,这是德国人轰炸的目标所在。当俞琛找到史蒂芬·阿尔贝时,发现他是一个汉学家,正在研究一个迷宫般的中国古代小说,即交叉小径的花园。这个迷宫般的小说恰恰是由俞琛的祖先崔朋创造的,在崔朋被杀后,始终无人理解其内涵。阿尔贝认为他已经破解了这个文本迷宫,并为俞琛解释交叉小径的花园并不是空间上的交叉,而是时间上的交叉。崔朋创造了各种未来、各种时间,它们各自分开又互相交叉,小说故事本身只是一个外壳、一个载体,蕴藏其中的是关于时间的哲学意蕴,作者借阿尔贝博士之口,把他关于时间的观点传达出来。
《交叉小径的花园》本身就是一个寓言,它的主题是时间。这种缜密的游戏,禁止提到它本身的名字。……《交叉小径的花园》是崔朋所设想的一幅关于宇宙的图画,它没有完成,然而并非虚假。您的祖先跟牛顿和叔本华不同,他不相信时间的一致、时间的绝对。他相信时间的无限连续,相信正在扩展着、正在变化着的分散、集中、平行的时间的网。这张时间的网,它的网线互相接近、交叉、隔断,或者几个世纪互不相干,包含了一切的可能性。我们并不存在于这种时间的大多数里。在某一些里,您存在,而我不存在;在另一些里,我存在,而您不存在;在再一些里,您我都存在。在这个时间里,我得到了一个好机缘,所以您来到了我的这所房子;在另一个时间里,您走过花园,会发现我死了;在再一个时间里,我说了同样的话,然而,我却是个错误,是个幽魂。[7]
作者通过这个迷宫般的小说结构,通过阿尔贝博士对一个迷宫般的中国古代小说的解读,传达了自己对时间的一种特殊认知:时间可以包含一切可能性,一切的结局都并行存在。时间不是一维的、单向的、线性的,它像空间一样是可切分的,是立体交叉的网状结构,是不断分岔的迷宫。这种对时间的解读,几乎可以视做是一种文学版“相对论”。它说明博尔赫斯的思考并非空穴来风的奇思异想,而是与20世纪的科学哲学发展密切相关的。
三
时间可以通过特殊的方式寻找,时间也可以是空间般并置的,但人类的永恒难题是如何留住时间,以实现对生命消逝的对抗。然而时间运动的永恒性似乎在不断提醒天真的人类:我们并不能像用绳子拴住小鸟一样拴住时间。一生流浪过德国、美国、瑞士等多个国家的纳博科夫将时间定义为牢狱,他在自己的回忆录《说吧,记忆》中,自称自己四岁时就由于父母的年龄而体会到时间的神秘,从父母的年龄中第一次意识到了自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时间。1919年的被迫流亡,使他对时间有了更加透彻的认知。他感到无边无际的时间是一座牢狱,这座“时间的监狱是环形的,并且没有出路”[8]2。他的名作《洛丽塔》就是以反讽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时间和永恒的认识。在故事的表层结构之下,隐喻的是人类对于时间的紧迫感、对时间流逝的不可抗拒的绝望感,以及对人类企图求取永恒而不得的凄凉感。
《洛丽塔》是一个变态的情爱故事,主人公亨伯特把他所热爱的性感少女界定在9—14岁之间,这其实是个时间的虚渺岛屿。亨伯特却企图将一生的幸福快乐安置在这个时间的虚渺岛屿之上。他实际上爱的是一个时间的滞留、一个强迫的幻象。洛丽塔就是时间的化身和替代物。亨伯特为自己设计了一场企图与时间作对的悲剧,把一生绑缚在一个不可能永恒的虚幻上。但时间对于生命而言是极端残酷的。人在时间面前终究是无力的,企图让青春永驻、生命永恒,是人类逾越自然法则的追索,注定是悲剧的,个人是无法逃脱自然法则掌控的。亨伯特无法将他的痴爱拘囿在时间魔岛上,最后为现实的牢狱所监禁,并死于其中,正是人不可能挣脱时间牢狱的一种象征。
纳博科夫还有一部以时间为主题的小说《斩首的邀请》。主人公辛辛那图斯以莫须有的罪名入狱并被判死刑。他想知道行刑的确切日期,但从狱卒、狱长、律师到图书管理员,以及狱长的女儿,都躲躲闪闪地拒绝告诉他。这种悬而未决的紧张焦虑自始至终弥漫于文本中,辛辛那图斯从被判死刑到上刑场,一直想知晓自己的死期,但却最终也没有办到。这似乎就是人类固有的、不能摆脱的对时间的焦虑感,人的一生就一直弥漫着这种悬而未决的紧张与绝望,这是人在时间牢狱之中的困顿无奈,这也是人类在试图抓住时间而不得的无奈,是人类永恒的悲剧性宿命之一。辛辛那图斯事实上坐的就是一座时间牢狱。辛辛那图斯最后逃离了他的牢狱,进入了另一个维度,实际上是纳博科夫建构的又一则童话,或者说是一个时间的乌托邦,以适应他的挣脱时间牢狱的欲望和要求。正如他一贯认为的那样:“倘若在事物的螺旋形旋开之中,空间扭曲成了某种近似于时间的东西,而时间也继而扭曲成某种近似于思想的东西,那么,肯定会有另一个向度随之而来——也许是一个特殊的空间。”[8]293显然,在他的观念之中,时间与空间都是异于常态的,甚至是可以转换的。
文学因“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律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而“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性,更严肃”[9],根据可能然律或必然律发生的事就是一种应该如此的事,是人类生存的本真状态,如果应然与必然是统一的,“本来如此与应当如此的生活是融合的”[2],那么这样的生存状态就是人的理想的存在状态,然而文明的进步文化的发展把这种统一对立起来,把这种融合割裂开来,于是,世界的真实面目与人们理想的应然状态永远分裂了。当现实世界不再是应然的理想时,人们便不断地诉诸文学来表达对这种不统一的思考与追问,或许正是自在世界的不完美才使得艺术家努力营造一个自为的应然世界。这是一个乌托邦的世界,也是人类精神应该皈依的世界。在这一人类苦心经营的世界里,时间也应该和必然获得它的永恒,获得它的“哲学性”。于是,艺术家们在时间叙述的同时也叙述时间,对时间的叙述是在努力构筑一个时间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的建构,或许是人类能够用以对抗时间流逝的唯一武器。
[1]耿占春.叙事美学[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204.
[2]王振军.《奥德赛》:追寻西方小说的精神原点[J].海南大学学报,2011(1).
[3]路易·加迪,等.文化与时间[M].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200.
[4]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1部,第1卷[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28.
[5]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5部,第1卷[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503.
[6]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7部,第2卷[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505.
[7]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81.
[8]V.纳博科夫.说吧,记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9]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81.
[责任编辑海林]
I106.4
A
1000-2359(2011)06-0225-03
2011-05-12
——读《博尔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