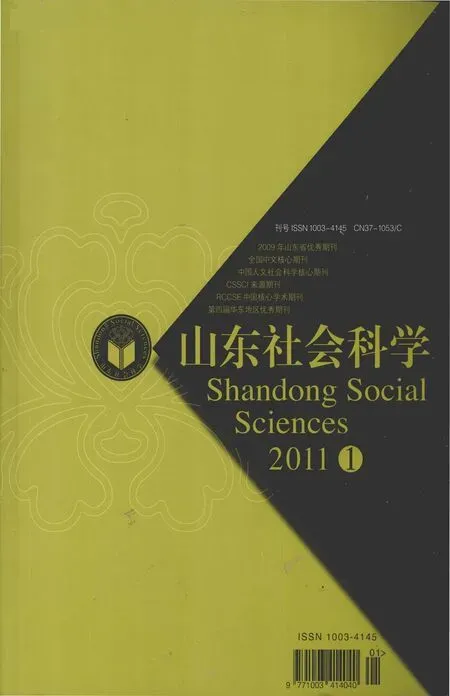从激进到保守:20世纪美国纽约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
祖国霞
(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北京 100083)
从激进到保守:20世纪美国纽约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
祖国霞
(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北京 100083)
纽约知识分子是20世纪美国的一群重要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作为群体的纽约知识分子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他们共同的政治思想起点。但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国内、国际政治局势以及纽约知识分子自身地位的变化,他们的思想逐渐失去激进性,其中的一些知识分子成了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只有少数人还在坚持社会主义理想。
纽约知识分子;反斯大林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去激进化;新保守主义
在美国历史上,知识分子们大多孤立地进行自己的工作,他们很少聚集在一起,因此很少有相似的经历、类似的观点,但纽约知识分子似乎是个例外。纽约知识分子指的是20世纪纽约城里的一群美国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他们提倡左翼政治,同时强烈地反对斯大林主义;他们都喜爱文学批评,而且在文学批评中都以社会为核心,努力将文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相融合;他们都喜爱辩论,常常进行公共演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出身犹太家庭,是犹太移民的后裔;而且他们大多是30年代在纽约城市学院或哥伦比亚大学接受的大学教育,而且都是《党人评论》、《异见》和《评论》等政治和文学评论期刊的撰稿者或编辑。纽约知识分子或许是美国历史上唯一可以被描述为知识阶层(intellegentsia)的群体。①Irving Howe,“TheNew York Intellectuals”.in(Irving Howe,ed.)Decline of theNew.New York:Harcourt,Brace&World,1963,pp.211, 212.他们以思想批判为武器,对社会问题进行独立的、不受干扰的思考,抨击社会中的不公现象,成为民族的“智识”或“良心”的体现。
纽约知识分子通常被认为包括以下二十多位人士:菲利普·拉甫(Philip Rahv),威廉·菲利浦斯(W il2 liam Phillips),玛丽·麦卡锡(MaryMcCarthy),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Macdonald),汉娜·阿伦特(Han2 nah Arendt),德尔莫·施瓦茨(Del more Schwartz),威廉·巴雷特(W illiam Barret),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戴安娜·特里林(Diana Trilling),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哈罗德·罗森堡(Har2 old Rosenberg),理查德·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哈维·史威多斯(Harvey Swados),理查德·蔡斯(Richard Chase),索尔·贝娄(Saul Bellow),艾萨克·罗森菲尔德(Issac Rosenfeld),悉尼·胡克(Sidney Hook),欧文·豪(Irving Howe),艾尔弗瑞德·卡赞(Alfred Kazin),罗伯特·华肖(RobertWarshow),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纳森·格雷泽(Nathan Glazer),诺曼·波德霍雷茨(Nor man Podhoretz),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 man),以及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Walzer)和西摩尔·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Martin Lipset)。②AlanM.Wald,TheNew York Intellectuals-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Anti-StalinistLeft from the1930s to the1980s.ChapelHill:University ofNorth Carolina Press,1987,p.11.
作为敏锐的社会观察家和思想者,纽约知识分子们的政治思想一直随着美国社会和美国思想界的变化不断演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国内外政治局势和社会的发展,他们的政治观点逐渐产生了分化。本文将对这一群体走上激进道路的原因和二战后他们在政治上的逐渐转向进行评述。
一、激进主义——纽约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开端
纽约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群体,在于他们共同的诉求: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文学上的现代主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纽约的这批犹太裔青年知识分子相继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投身社会主义的激进政治,激进主义成了联结他们的坚强纽带。在文学上,他们批判虚伪的、物质主义的资本主义文化带给人们的异化感,强调新的价值秩序的重建。他们的集体激进化源于以下三个因素。
首先,大萧条带来的贫困让纽约知识分子们普遍感觉到了人生的艰辛和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恶劣。20世纪20年代末,在经历了一战以后的暂时繁荣后,美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1929年,随着纽约股市的崩溃,美国开始了其历史上最黑暗的经济危机和萧条时期。出生在1910至1920年代纽约犹太社区的知识分子对这场危机感受至深,因为经济危机对移民社区的打击更为沉重,犹太人的生活更为艰难,他们聚居的布朗克斯、布鲁克林和曼哈顿等地的移民社区都笼罩在对经济滞胀的恐惧和焦虑之中。可以说,贫困是纽约的犹太家庭在30年代的集体经历,这使得他们格外向往美好的生活,激进政治成了他们追求幸福生活的途径和手段。
其次,纽约的工人运动让这批知识分子看到了工人阶级力量的巨大。青、少年时期的经历让他们刻骨铭心的不仅是贫困,还有犹太工人阶级的力量。19世纪末,为了逃离欧洲的贫穷和迫害,大约有两百万犹太人离开家乡到了纽约。20世纪初,纽约城约三分之一的居民为犹太移民。①Joseph Dorman,Arguing theW orld:TheNew York Intellectuals in TheirOwnW ords.Chicago andLondon:The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2000, p.25.他们憧憬能在美国得到财富和政治自由。然而,由于缺乏技术和英语语言能力,他们很难找到好的工作,因此纽约的制衣业吸引了大批犹太工人,欧文·豪的父母、丹尼尔·贝尔的母亲、纳森·格雷泽的父亲都曾在制衣厂上班。
纽约的制衣厂内环境恶劣,拥挤不堪,安全性差。它们的木质地板、原始的电线使工人们随时面临着火灾的威胁。在1911年3月25日发生的三角地制衣厂火灾(Triangle Shirt waist Factory Fire)中,共有146名工人丧生。为了保护工人们的权益,抗议血汗工厂的恶劣境况、低工资和沉重的劳动负荷,早在1900年工人们就成立了国际女装工人联合工会(International Ladies Gar mentWorkers Union),多次组织制衣工人的罢工活动。1909年,两万制衣厂工人在国际女装工人联合工会的旗帜下发动罢工,争取到了每周52小时工作制。1933年8月16日全纽约的服装业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参加的工人达到了7万多名。
除了国际女装工人联合工会外,其他的劳工运动在30年代也非常活跃,仅1934年在美国就爆发了1856次罢工。在罗斯福新政期间,所有工人(不仅是少数行业工人),包括黑人、妇女和其他少数民族工人都取得了组织工会、通过自选代表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工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发言权,再也不像从前那样让资方任意摆布了。②刘绪贻:罗斯福“新政”、劳工运动与劳方、资方、国家间的关系.http://ias.cass.cn/show/show_mgyj.asp?id=710&table=mgyj日益壮大的劳工运动让纽约知识分子亲身感受到了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
第三,除了饥饿和贫困的阴影外,30年代的纽约犹太青年还承受着心理上的焦虑感。作为第二代的犹太移民,他们必须努力同外部世界进行融合。然而,他们居住的犹太社区是个封闭的小团体,那里的人使用的是意第绪语,即便有个别讲英语的年轻人,也都带有浓重的移民口音。人们仿佛与世隔绝,有些人甚至终生都难以同非犹太人有重要的接触。除了家庭外,其他任何一切对于他们都是可怕的,陌生的,难以理解的。③Irving Howe,A M argin of Hope: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New York:HarcourtBrace Jovanovich,1982,p.5.在犹太移民看来,纽约城粗暴、丑陋、令人畏惧,是异化的世界的体现。犹太社区的孩子们既渴望、又害怕同外界联系。④Irving Howe,“New York in the Thirties-Some Fragments ofMemory”.Dissent,Vol 8.No.3(Summer 1961),p.241.与此同时,犹太人在国际上所处的情形加剧了他们的焦虑感。犹太人在欧洲受到的残酷迫害,使纽约的犹太青少年心中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悲痛。他们感觉社会正处于混乱之中,自己则像漂在空中,他们需要重新界定自己的世界观,找到生活的意义和发挥自己才能的平台,投身激进政治运动恰好可以平息他们的孤独感,使他们找到精神的避难所。
第四,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使纽约知识分子在青少年时期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另一个因素是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在纽约的影响。社会主义思想虽然从未成为美国的主流思潮,但在20世纪初曾在美国社会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912年,美国社会党(American Socialist Party)的党员数量达到了118,000人,在当年的大选中得到了879,000张选票,占总选票的约6%。①Irving Howe.Socialism and America.New York:HarcourtBrace Jovanovich,1985,p.3.此外,还有三百多种出版物在散播社会主义的信息,总发行量超过了两百万份。它们向人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呼吁人们对枯燥乏味的基督教说教采取直接的革命行动。
在美国受社会主义影响最深的是犹太移民。贫困的生活、低微的地位、繁重的工作和对美国主流文化潜在的敌视使他们更易接受激进主义左派的影响。欧文·豪观察到,在东布朗克斯,激进主义不再是处于边缘位置的新奇事物。纽约似乎成了“党的中央”,在这里,人们可以听到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们慷慨激昂的讲话,演讲厅里面总是坐满了犹太听众,他们只有在这里才能忘掉自己是多么渺小、多么无用的想法。社会主义运动为他们带来了一丝安全感,让他们感觉到在资本主义的冷风中,自己还能找到一个避难所。因此对于这里的犹太移民来说,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政治或一种思想,而是一种包含一切的文化。②Irving Howe,A M argin of Hope: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New York:HarcourtBrace Jovanovich,1982,p.8.
社会主义运动为生活在纽约犹太社区的年轻人们提供了生活的“目的”,在他们的生活中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子。丹尼尔·贝尔回忆道,社会主义运动使他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使他突然意识到除了自己狭小的犹太社区外,还存在着一个思想的世界、经验的世界、想象力的世界,年轻人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渴望,他们贪婪地去触摸它。③Joseph Dorman,Arguing theW orld:TheNew York Intellectuals in TheirOwnW ords.Chicago andLondon:The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2000, p.33.
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些年轻人在30年代都不约而同走上了左翼激进道路。而在社会主义的众多流派中,他们普遍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是俄国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列昂·托洛茨基提出的理论。托洛茨基认为自己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倡导者。他一方面反对斯大林主义,强调废除斯大林主义的官僚统治,同时也反对社会民主主义,倡导战斗性的工人革命。
在这些青年人的眼中,托洛茨基主义者似乎比其他社会主义者有更广博的、更为确定的知识,他们知道为什么俄国革命能够胜利,为什么会被背叛,甚至能够预测俄国革命的未来;他们对一切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自信地认为在未来他们将是先锋队中的先锋。④Irving Howe,A M argin of Hope:An 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New York:HarcourtBrace Jovanovich,1982,p.33.因此,托洛茨基主义对于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他们大多以校园为阵地,宣传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思想。纽约城市学院(City College of New York)是他们的聚集地之一。由于不收学费,而且对犹太学生的人数没有任何限制,该学院在三四十年代吸引了纽约城大批有才华的犹太青年,如阿尔弗雷德·卡赞(1931-1935),丹尼尔·贝尔(1935-1939),欧文·克里斯托(1936-1940),纳森·格雷泽(1940-1944),欧文·豪(1936-1940)。因此它常被称作“穷人的哈佛”。⑤Joseph Dorman,Arguing theW orld:TheNew York Intellectuals in TheirOwnW ords.Chicago andLondon:The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2000, p.41.在这里,他们加入了美国社会党,开展各种政治宣传活动,并经常同信奉斯大林主义的其他左翼团体进行辩论。他们一方面猛烈地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批评苏联体制中的专制主义倾向。同时,他们以《评论》、《新国际》(New International)、《劳工行动》(Labor Action)、《党人评论》等报刊为阵地,对美国文化展开了激烈的批判。
二、50年代纽约知识分子的去激进化
20世纪50年代,纽约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较40年代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们纷纷抛弃了托洛茨基社会主义,转向了自由主义。“去激进化”成了该时期大多数纽约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这一趋势的产生源于两个因素。
首先,莫斯科大审判以及斯大林政权对苏共各级领导和普通党员的大清洗,让纽约知识分子普遍将苏联共产主义同纳粹主义一道看作是极权主义,这一时期英美国家出版的有关极权主义的著作使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发展极为恐惧。共产党在中国、东欧的胜利,苏联的原子弹、氢弹试验的成功使他们的讨论重心不再停留在资本主义的本质或工人状况等老左派曾最为关注的问题上,而是转向了如何抑制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思想已不再能够承担挽救世界的重任。其次,美国在战后的经济繁荣使美国的模式看起来比苏联的模式更具吸引力。二战后,美国经济不仅没有像人们所担心的那样走向萧条,而是迎来了全面的发展,汽车、航空、电子工业大步前进。在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们对于冷战自由主义由反对变为容忍,甚至开始赞赏,认为美国是对付苏联独裁政权扩张的最强大的力量。
在该思想的指导下,众多的美国左翼知识分子开始认同美国政治和文化,纽约知识分子主办的老牌左翼杂志《党人评论》大胆宣布:“在政治上,我们应该看到存在于美国的民主有着内在的、积极的价值:它不仅是个资产阶级的神话,而且是一个我们必须保卫、从而避免俄国极权主义侵害的现实。它的文化后果肯定是深远、复杂的,其中的一些现在已经明显出现。无论如何,大多数作家都不再接受艺术家在美国被异化的命运,相反,他们非常想成为美国生活的一部分。”①Gregory Edmund Geddes,Literature and Labor:Harvey Swados and the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Left.Unpublished DoctoralDissertation of State University ofNew York,2006,p.120;p.122;pp.121,122.美国工人党的前领袖悉尼·胡克指出,知识分子们不能对美国社会环境的好转、物质条件的改善视而不见,没有必要为自己同美国社会的妥协而道歉。②Gregory Edmund Geddes,Literature and Labor:Harvey Swados and the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Left.Unpublished DoctoralDissertation of State University ofNew York,2006,p.120;p.122;pp.121,122.甚至美国前托洛茨基派领导人詹姆斯·伯汉也指出:“只有在美国力量的帮助下才能阻止苏联的胜利,美国的武力是次一级的恶,如果发生了全面的战争,如果美国领导下的反苏联盟能够取得胜利的话,那么对美国武力的使用就是正义的、正确的。”③Gregory Edmund Geddes,Literature and Labor:Harvey Swados and the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Left.Unpublished DoctoralDissertation of State University ofNew York,2006,p.120;p.122;pp.121,122.
知识分子在该时期的去激进化甚至使他们对麦卡锡主义这股极端右翼思潮也出现了“顺从”的趋势。在麦卡锡时代,美国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权利受到了严重的侵犯。华盛顿大学的开除教师案便是其中的一起重大案例。1948年7月“非美活动真相调查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在华盛顿大学举行教师成员“颠覆活动”听证会,最后在1949年初的校董事会上决定解除三位拒绝合作的教授职位,其中的两位教授是共产主义者。华盛顿大学的这一做法在整个美国学术界引起了极大反响。然而,一些纽约知识分子此时坚信共产党是一个阴谋集团,认为它的成员根本不适合教书,故而支持华盛顿大学的决定,其中的典型人物是悉尼·胡克。在华盛顿大学的事件发生以后,胡克立刻撰文支持校方的决定,他指出,共产党要求它的党员们服从严格的纪律,要求他们利用课堂进行政治宣传,因此,教师中的共产党员不是一个自由人,而是一个极权主义工具的代表。他们加入共产党是“不端行为”。④Sidney Hook,“Academic Integrity and Academic Freedom-How to DealW ith the Fellow-Travelling Professor”.Commentary,Vol.8,No.4 (October 1949),p.334.胡克认为,在处理这些有“不端行为”的教授时,最好不应由国家出面干预,但是如果教师队伍未能及时地清理自己身上的这块“疮”,那么这样的干预也是应该的。⑤Sidney Hook,“Academic Integrity and Academic Freedom-How to DealW ith the Fellow-Travelling Professor”.Commentary,Vol.8,No.4 (October 1949),p.334.尽管胡克认为,错误的根源不在那些教授,而在于共产党这个组织本身,并对被开除的教授基本抱同情的态度,但他对共产党的严厉斥责和对立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们对那些必须证明自己清白的教育者的猜疑和不信任,顺应了麦卡锡主义的思想。
拥护冷战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此时占据了纽约知识分子的多数,他们主编的《党人评论》、《评论》和《撞击》等杂志在政治立场上越来越为保守。1951年,在悉尼·胡克的领导下,他们成立了“争取文化自由委员会”(Committee for Cultural Freedom),组织知识分子进行反抗共产主义的宣传,并鼓励知识分子批判苏联、批判共产主义,它附属于“争取文化自由大会”(Congress forCultural Freedom),是它在美国的分支。⑥“争取文化自由大会”成立于1950年,总部设在巴黎,曾在35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表面看来,它是一个争取文化自由的组织,但实际上它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和操纵,成了冷战中被美国利用的反共文化工具。许多纽约知识分子,如玛丽·麦卡锡、德怀特·麦克唐纳、丹尼尔·贝尔都是它的成员,欧文·克里斯托成了它的第一任执行主席,甚至前美国社会党领袖诺曼·托马斯都加入其中。
50年代,在纽约知识分子中,只有以欧文·豪和刘易斯·科塞为代表的寥寥几个纽约知识分子坚决抵制冷战自由主义,他们虽然也批判斯大林主义,但他们并没有走向社会主义的对立物——资本主义,而是开始转向民主社会主义,因为苏联社会中的种种弊端让他们意识到民主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具有的重要地位。1954年,欧文·豪和刘易斯·科塞联合创办了激进政治期刊《异见》。从此,他们以《异见》为阵地,坚持宣传社会主义、批判美国现行制度。1954年初,豪在《党人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这个顺从的年代》的文章,指出50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已经静止麻痹、物质主义繁荣兴旺、顺从主义威胁着每一个人的时代,对美国许多重要的知识分子和杂志提出了批评,“顺从的年代”(Age of Confor mity)随后成了20世纪50年代的标签。
三、转向新保守主义
20世纪60年代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复杂的年代,一方面,美国发生了轰轰烈烈的新左派运动,另一方面,美国的保守主义思潮悄然复兴。尽管许多研究这一时期的学者都将注意力转向了新左派运动,认为这是一个激进者的年代,但实际上它也是美国保守主义复兴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不仅自由主义者和激进者之间进行着观点的碰撞,而且保守主义者也在努力地吸引美国选民的注意,积攒自己的政治力量,并最终在七八十年代使自己的候选人尼克松和里根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许多重要的美国知识分子投向了保守派阵营。当年轻的新左派激进者们猛烈地抨击民主党的政策,批判它的社会改革力度不够时,以欧文·克里斯托、诺曼·伯德霍雷茨、丹尼尔·贝尔和纳森·格雷泽为代表的一些纽约知识分子却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民主党政府的改革步伐太快了,因为约翰逊政府为了打击贫困和不平等,采取了总称为“伟大社会”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于是,1965年,他们创办了一份新的刊物《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政府政策的后果。尽管“新保守主义”一词是70年代才出现的,但该杂志的创刊被许多人看作是新保守主义兴起的标志,欧文·克里斯托更是被誉为“新保守主义的教父”。①Michael J.Thompson,Confronting the New Conservatism:the Rise of the Right in America.New York and London: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7,p.30.
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国际政治上,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们相信美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优越性使它有能力也有义务在世界上起主导作用。克里斯托对此毫不怀疑,他坚持认为:“世界确实依赖美国的实力,”美国必须领导世界,因为这是它的“责任”。他强调:“对这些责任的逃避或不承认是对权力的一种滥用。如果在经历越战之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信,美国不能再胜任它这个世界第一强国一直以来所执行的这种‘警察’的工作,我们毫无疑问将看到到处都会出现令人惊恐的国内犯罪和国际骚乱现象的猛增。我们不会因为呆在镀铬的美国城堡内就不受影响。”②Irving Kristol,“We Can’t Resign As‘Policeman of theWorld’”.The New York TimesM agazine,May 12,1968,p.27.
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上,他们支持政府采取强硬的立场,尤其是对待共产主义。他们坚信,共产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美国不仅应该遏制共产主义,而且应彻底打败共产主义,与它的协商和对它的迁就等同于绥靖,美国只能“在作战和投降之间进行选择”,为此美国应大力加强军事力量,采取新干涉主义的外交政策。③MicahelW.Flamm,Debating the1960s:Liberal,Conservative,and Radical Perspectives.Laham: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8, p.116.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美国1980至1985年间的军备开支增加了一倍。
在苏联解体以后,新保守主义者们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产生了许多的分歧,多数知识分子,如克里斯托和珍妮·科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认为,新保守主义应放弃他们为全世界的民主进行的奋斗,采取更为克制的实用政治,因为美国和新保守主义都不需要超越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世界使命。④GaryDorrien,“Inventing anAmerican Conservatism:TheNeoconservative Episode”.in(Amy E.Ansell,ed.)Unravelling the Right:TheNew Conservatism in American Thought and Politics.Boulder,Colorada:Westview Press,1998,p.63;p.64.也就是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应以维护国家安全为中心,有选择地使用力量和资源,以免付出得不偿失、代价过大。但另外一些新保守主义者认为,这样的外交政策是在给他人方便,是一种偏狭的政策,美国需要的不是这样的政策,相反,它应该将向全世界输出资本主义的民主看成是自己的道德义务。例如波德霍雷茨等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新的泛美时代已经来临,美国应该用自己的实力按照美国的设想来塑造新的世界秩序。⑤GaryDorrien,“Inventing anAmerican Conservatism:TheNeoconservative Episode”.in(Amy E.Ansell,ed.)Unravelling the Right:TheNew Conservatism in American Thought and Politics.Boulder,Colorada:Westview Press,1998,p.63;p.64.同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这部分新保守主义者轻视、不信任联合国的作用。他们认为,当涉及到一些关键利益和国家安全问题时,美国政府可以不经过联合国的同意就对一些国家采取单边军事行动,90年代的伊拉克战争便是一个实例。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们外交主张的不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保守主义思想内涵的复杂、多变。
其次,在经济上,哈耶克、密尔顿·弗里德曼以及其他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对传统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的批判越来越深入人心,老左派的经济思想遭遇了彻底的失败。由老左派转变而来的新保守主义者自然而然地转向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他们尤其支持供应学派的经济观点,在80年代时支持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克里斯托等新保守主义者推崇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说,主张政府尽可能少地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让市场经济自由运行,只有当一些问题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得以解决时,才可以借助政府的力量。因此,他们提出,政府应尽量缩减成为“小政府”。
第三,纽约知识分子们开始主张削减社会福利。1963年,在林登·约翰逊总统上台后,他发誓要深化美国福利社会的改革,进行一场“对贫困的战争”。对于新保守主义者来说,“对贫困的战争”无异于一场噩梦。他们担心这样的“战争”会带来庞大的政府机构和更高的税收,从而影响个人的主动性和经济的正常运转。但同传统保守主义者不同的是,新保守主义者认为应保留最低限度的福利社会,支持传统的福利政策。但是,他们反对继续扩大福利政策的范围,反对约翰逊政府的社会改革,认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福利政策代表着“最佳的意图,最差的结果”①Irving Kristol,Neoconservatis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5.p.43;pp.202,203;p.167;p.168;p.169.。
克里斯托是这部分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指出,美国政府在19世纪引进的一些福利政策无疑是成功的,例如免费的公立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但60年代的社会改革只会使问题更糟,“对贫困的战争”造成了“福利爆炸”(welfare explosion)。
克里斯托认为,以此方法对贫困展开的战争是非常愚蠢的,政府是在采用错误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因为在处理贫困这一问题时,给穷人发放津贴会引起许多麻烦。第一个麻烦在于,政府必须判断究竟谁是穷人,而政府所做出的判断经常是武断、有争议的,因为社会中的穷人与残疾人不同,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群体,他们只不过是收入低于某个官方数据的人群,而这个数据应该是多少,人们不可能达成一致的意见。第二个麻烦是如果只给穷人补贴,会很快将穷人囚禁在“贫困陷阱”内,因为当他们努力改善自己的状况、提高收入后,他们就会失去享受政府津贴的资格,整体的生活水平反而会下降,因此,凡是有点理性的人都会知道这样做是不划算的。既然已经被列入了穷人之列,他们觉得就应该一直贫困下去。这样做的后果是这部分人会逐渐失去道德。克里斯托观察到,自“伟大社会”的计划实施以来,尽管纽约城的穷人们得到了更多的钱、更好的住房、更完善的医疗,但他们中也滋生了更多的犯罪,吸食毒品和青少年犯罪等其他一些社会疾病的比例也在上升,而这些都是依赖心理所产生的。②Irving Kristol,Neoconservatis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5.p.43;pp.202,203;p.167;p.168;p.169.
在克里斯托看来,社会上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他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在一个正义、合法的社会里,公民们普遍知道财产、地位和权力的不平等对于维护共同的利益是必要的。③Irving Kristol,Neoconservatis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5.p.43;pp.202,203;p.167;p.168;p.169.他批评说,在当今美国,大多数百姓的政治判断和政治期待都比知识分子更为“有理性”,但麻烦在于,我们的社会正在产出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的普通人。④Irving Kristol,Neoconservatis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5.p.43;pp.202,203;p.167;p.168;p.169.言外之意,美国的贫困问题并不是现实存在的问题,而是知识分子们造出来的,他的批评矛头直指那些坚持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如迈克尔·哈林顿。1962年,哈林顿出版了《另一个美国》,揭露了美国的贫困状况,指出美国大约有25%的人口都处于贫困之中。他的书不仅在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而且直接影响了美国政府的政策,促使肯尼迪政府扩大对穷人的福利。而克里斯托在70年代初写道,同20年前相比,收入的不平等问题已经减少了很多,而且自二战以来,地位和机会的不平等也因为免费或接近免费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而明显减少,那些批评美国社会不平等的人大多是在诡辩,是在没有经过审慎调查的情况下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⑤Irving Kristol,Neoconservatis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5.p.43;pp.202,203;p.167;p.168;p.169.
同克里斯托一样,贝尔和格雷泽也提出了对60年代社会改革的批评。贝尔指出了改革的难度:“无论进行什么样的福利改革,如学校改革,住房改革等,问题都会存在。”⑥Joseph Dorman,Arguing theW orld:New York Intellectuals in TheirOwnW ords.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p.159;p.106;p.173.格雷泽对福利改革进行了直接的批评,他指出:“确实,在过去,当纽约很贫困的时候,它有十分之一的人口获得福利……但同时他们可以从许多的慈善协会、私人组织和亲戚朋友那里获得帮助……我并不想将过去理想化,但是其它的慈善机构确实有被取代的趋势。这正是政府的各个项目在做的事情,他们促成了社会特点的转变,取代了那些依然能够促进社会团结的传统机构。那些有着最佳意图的项目有可能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不仅有一些项目实施不了,而且还有一些产生了消极的后果。”⑦Joseph Dorman,Arguing theW orld:New York Intellectuals in TheirOwnW ords.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p.159;p.106;p.173.同克里斯托一样,格雷泽也强调福利改革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后果”,事实上,“意想不到的后果”几乎成了《公共利益》所有作者们的口号。
克里斯托这样总结新保守主义者:“我们新保守主义者从来不反对罗斯福新政,从来不反对新政中的许多项目,从来不反对新政中的一些原则,但我们反对侵入性的、过度官僚化的联邦政府。”⑧Joseph Dorman,Arguing theW orld:New York Intellectuals in TheirOwnW ords.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p.159;p.106;p.173.以此显示新保守主义同传统保守主义的区别。
对于新保守主义者来说,美国政府的“肯定性行动”计划是“意想不到的后果”的一个典型例子。1965年,约翰逊总统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努力倡导这一计划。它起初只是旨在解决长期以来黑人在就业方面遭受的歧视,后来又将其他少数民族和妇女容纳进来,在就业、教育等领域对少数民族、妇女等社会弱势群体给予了一些优待和照顾。然而,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肯定性行动计划只会帮助那些不值得帮助的人,而同时对那些应取得某些成就的人带来逆向的歧视。在贝尔、格雷泽和克里斯托看来,许多“肯定性行动”的项目在补救对黑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歧视时,损毁了公平的原则和个人的权利。政府在努力保证少数民族的工作和教育,从而达到机会均等的同时,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
克里斯托说道:“起初我们并不敌视它。我们说为什么不弥补过去的不公平呢,为什么们不能给予黑人一些帮助呢?我们从未想过要雇佣不合格的人,我们只想将合格的人放在名单的最前头。但很快我们发现事情不是这样的。当定额出现后,当突然间大学被告知他们的学生中必须有更多的黑人时……我说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教育体系。”①Joseph Dorman,Arguing theW orld:New York Intellectuals in TheirOwnW ords.Chicago andLondon:The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2000, p.162;p.163;p.163.格雷泽对它的反应更为强烈,他指出,政府的“肯定性行动”计划违背了1964年的《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阻止雇主根据能力选拔员工,在“肯定性行动”计划下,在许多方面,政府只根据个人的种族和肤色来判断该给谁更多的优惠条件,例如就业、大学招生、住房。在格雷泽看来,这是不必要的,是反生产力的。②Joseph Dorman,Arguing theW orld:New York Intellectuals in TheirOwnW ords.Chicago andLondon:The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2000, p.162;p.163;p.163.贝尔的态度更为温和一些,他指出,“肯定性行动”计划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但它后来演化为了配额制,对于社会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③Joseph Dorman,Arguing theW orld:New York Intellectuals in TheirOwnW ords.Chicago andLondon:The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2000, p.162;p.163;p.163.
总之,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对美国60年代中期以后民主党政府进行的许多社会改革都进行了指责,并且相信政策的失误是由错误的或不完善的社会理论造成的。克里斯托在1968年时批评道:“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已经发现,要想解决少数人群的问题,单靠通过一条法律是不够的……不知怎么的,钱似乎从来到不了应受资助的那些人的手中——即便到了他们的手中,它也达不到它本该达到的效果。”④Irving Kristol,The Old Politics,the New Politics,the New,New Politics.The New York TimesM agazine,November 24,1968,p.174.对新保守主义者们来说,要想改变这一状况,自由主义政府的社会理论显得苍白无力,新保守主义才是更有效的解决工具。
这一时期,许多纽约知识分子开始公开承认自己的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悉尼·胡克成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成员之一,为共和党政府起着智囊团的作用,1985年里根总统亲自为他颁发“总统自由奖章”;欧文·克里斯托毫不犹豫地称呼自己为新保守主义者,是共和党的忠诚拥护者;诺曼·波德霍雷茨也不例外,他热诚地主张美国在外交上持强硬的立场,一直对越战、伊拉克战争持肯定的态度;纳森·格雷泽虽然认为自己不像克里斯托那样的意识形态化,但承认在“许多问题上他都站在共和党一边”。⑤Joseph Dorman,Arguing the W orld: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in Their Own W ords.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p.173;p.174.他们中也不乏政治上的中间派:丹尼尔·贝尔否认自己是新保守主义者,把自己定义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⑥Joseph Dorman,Arguing the W orld:Th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in Their Own W ords.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p.173;p.174.西摩尔·李普塞特成了美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玛丽·麦卡锡坚持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批判文化和政治。他们中还有一些只专注于文学创作或文学批评的作家、学者,如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索尔·贝娄、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只有欧文·豪等个别知识分子还在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理想。
四、讨论
纽约知识分子为何在二战后出现了集体右转的现象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三个原因造成的。第一,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一些失误使纽约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运动失去了信心。马克思主义思想曾是将他们连结在一起的坚强纽带,青年时代的纽约知识分子们坚信,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可以理解世界上的一切问题,马克思主义是解开一切问题的钥匙,是未来的希望。然而,30年代苏联的“大清洗”和僵化的经济模式彻底打破了美国知识分子对共产主义的幻想,使得他们集体成为了反斯大林主义者。但是,一些人的仇共情绪更为极端,在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影响下,他们谈共色变,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甚至主张社会公平的新自由主义都被他们视作反动的思想。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再一次让他们看到了左派运动的种种缺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对一部分知识分子失去了吸引力。其次,二战后国际经济局势的发展对纽约知识分子政治观点的分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在二战后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这些国家普遍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西方的社会民主国家在实行福利社会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福利制度对国家财政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带来的压力。现实的状况使得知识分子们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愈加反感,市场经济、小政府成了一些人心目中唯一能够挽救大局的手段,新保守主义成了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政治选择。第三,纽约知识分子自身地位的改变使他们失去了共同的奋斗目标。二战以前,纽约知识分子们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中,犹太移民的身份使他们很难跻身到大学等文化圈子中,因此,他们大多围绕在《党人评论》、《新共和》、《评论》等为数不多的左翼杂志周围,做这些杂志的编辑或自由撰稿人,他们的经济状况也大多十分拮据。事实上,如波德霍雷茨所言,在当时,即使那些来自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家庭的美国知识分子都有种异化的感觉,都感觉是这个国家里的“外国人”。①Norman Podhoretz,“A Letter toMy Son”,in(ThomasL.Jeffers ed.)TheNo rman Podhoretz Reader:A Selection of HisW ritings from the1950s to1990s,New York:Free Press,2004,p.121.然而,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日渐富裕,纽约知识分子们发现美国的文化较之前更为开放,曾经歧视他们的出身、背景的大学由于招生数量的大幅增加开始纷纷向他们抛出橄榄枝,曾对他们的才华和思想不屑一顾的一些主流杂志也发现它们需要这批有思想、有见地的作者,以便迎合读者们越来越复杂的趣味。于是,纽约知识分子不必再在以往的夹缝中艰难行进,他们既可以到大学中寻觅到一个不错的职位,也可以为更多的杂志撰稿,根据卡杜辛1969年的统计,美国当时至少有20种重要的思想期刊供这些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思想见解。②Charles Kadushin,The American Intellectual Elite.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4,p.18.这个群体开始成功地登上美国的文化舞台,他们不再是孤立的小团体,而是同化于美国这个大群体之中,他们的社会地位日趋提高,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崇拜和尊敬。于是,他们越来越认同美国政治。在以上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纽约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最终转向。然而,我们也看到,尽管坚持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已成少数,但他们的“异见”之音依然不可低估,他们利用社会主义的道德武器对现实社会和政治中依然存在的不合理现象进行着冷静的批判与反思,促使当权者、知识界以及公众不断地思索“平等”、“民主”、“自由”等政治概念在当今的含义,以使现实中的社会越来越接近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责任编辑:蒋海升)
K091
A
1003—4145[2011]01—0041—07
2010-09-21
祖国霞,北京林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本研究受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科振兴专项计划的资助,课题名称“美国学视野下的美国历史专题研究”,项目编号200-121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