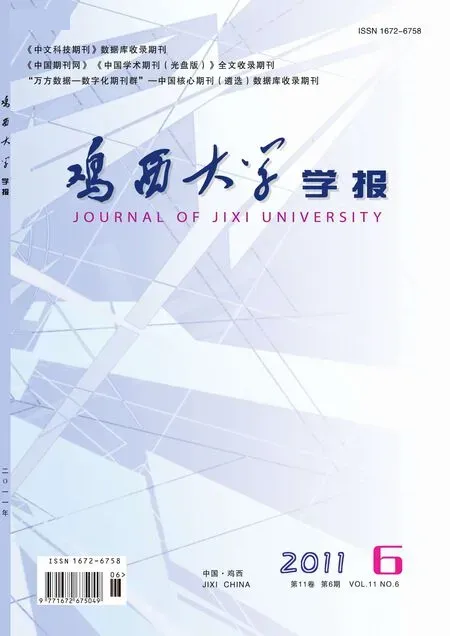试论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与民盟改组的政治发展路径
阿牛曲哈莫 罗登华
一 1944年的民盟改组
抗战烽火肆起之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确立,抗日救亡运动波澜起伏。1939年10月,中间党派参政员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及青年党、民社党参政员发起组织了民主宪政运动和统一建国同志会,为民盟的诞生提供了政治和组织准备。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共两党摩擦增加,中间党派出于加强联合的形势需要,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成立,并于次年形成了“三党三派”合组“同盟”的局面。3年以后,随着抗战局势的明朗和第二次宪政狂澜的掀起,围绕战后建国、避免内战、争取联合政府等问题,社会各党派、各方力量、各种思潮出现新的变动。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全国代表会议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经过认真讨论,会议决定取消民盟的团体会员制,以后一律以个人名义入盟,组织名称亦由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此即史家所称的1944年民盟改组。
民盟改组后,由于“三党三派”以外的民主分子大量参加民盟,民盟得到了迅速发展。由于新入盟的无党派盟员“有些在学术界有地位,有些在社会上有威望,有些在斗争中有经验”[3],所以,他们入盟后纷纷被选进民盟的领导层,担任各级职务,无党派盟员开始成为民盟主流,并由此引起了民盟性质的变化和内部结构的重组。民盟副主席、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叶笃义对此有评:“这次代表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在组织上是一个大跃进”[4]。可见,1944年的民盟改组,在民盟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民盟改组原因的探讨,也因此成为一个必须考察的历史问题。
二 国共关系成为影响民盟改组发展的重要因素
实际上,1944年的民盟改组有一个强大的外部政治环境,正如载于1946年《再生》第5期的《中国民主同盟》一文所言,从统一建国同志会到中国民主同盟,这5年的历史恰是一部中国抗战时期的政治简史,因为“从其中已经可以见出吾国在抗战期中的政治的发展情形和其趋势”,此语无疑道出了一个事实,即民盟在1944年的改组与中国从1939到1945年间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抗战时期的政治环境如同阳光之于树林一样,影响着民盟的政治生命。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环境的晴雨表无疑是不断震荡的国共关系。抗战后期国共摩擦加剧,为争取联合政府、和平建国,为避免内战而进行苦心斡旋,民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改组的。
国共关系经历了1939年、1941年、1944年的三次大震荡(三次反共高潮),每一次震动以后,皆有各种民主党派、政治团体的诞生和不断发展,民盟前身统一建国同志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就分别缘起于1939年和1941年,民盟进行改组亦发生在1944年,这应该不是偶然。可以推断,国共两党关系的演绎,恰是各中间党派、政治团体产生发展的土壤。国共两党的合作、分裂、对峙,为各民主党派的产生提供了机会,也为其发展壮大开拓了广阔的中间地带。国共关系在各时期呈现出的不同特点,也直接影响到处于中间地带的各民主党派,使他们在不同历史阶段担负起不同的政治使命。民盟在不同时期的政治任务的变更,在一定程度上对1944年其组织的改组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 抗战时期国共关系与民盟的产生和改组
作为一个政党(或者政治团体),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所作的关于政治发展路径的战略决策,必须对过去、现在和未来有相当清醒的政治洞察。
1939到1944年,正是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前期和中期。武汉失陷后,日本改变了侵华策略,基本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改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的政策,国民党亦将其政策的重点由对外转向了对内,竭力加强其一党专政。国共关系开始变得紧张。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反共、溶共”的政策,颁布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法令,规定“已准立案之各种灰色社团地方党政机关应重新切实办理登记严格考核其活动”[5],将抗战初期全国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得的某些民主权利基本取消。国民党的政策,引起了各中间党派对国民党的失望和愤恨,并由此引发了宪政运动高潮的到来。为了更好的推动民主宪政运动,调解国共两党的关系以促进团结抗战,各民主党派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决定采用适当的组织形式联合起来,统一建国同志会便于1939年10月在重庆应运而生。
两年后(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国共关系再度呈现危机。抗战中期国共关系的紧张,使每一位民主人士都不由得对抗战前景和中国命运深感担忧。所以当皖南事变发生后,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就纷纷表示:“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皖南事变不仅是国共两党问题;而且是民众与反动势力斗争问题”[6]。只有国共团结合作,抗战胜利才有希望,两党再开内战,后果则不堪设想。因此,促进国共合作、居中调解国共纷争便成了此时期各民主党派的首要任务。而各民主党派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强大的具有“第三者”意义的政治集团从中进行调停,则成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诞生的迫切需要。正如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1941年成立时的宣言中所说:“爰自为结合,以作团结全国之始,将以奉勉国人者,先互勉于彼此之间。以言结合动机,端要如是”[7]。
1944—1947年是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后期和国共不断磨擦并最终爆发内战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抗战局势渐已明朗,战后如何建国、如何处理国共两党的关系变化、如何避免再开内战、以及民盟自身如何发展等问题,成为民盟高层必须面对的政治抉择。
1.调解国共关系的任务与民盟组织成分的变化。在抗战胜利前后,如何治国的问题成了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头等大事,而主宰中国政局的国共两大党的政治主张,又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在中间党派看来,只要将国民党“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把共产党“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况下,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8]。于是,民盟在1945年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便提出其建国方案,即政治上实行英美式的议会制、责任内阁制[9],经济上则多采取苏联式的经济民主[10]。对于这种被后人称为“第三条路线”的理想本身,本文在此不作评论。但有一个事实,就是中间党派在国共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出于继续抗战、避免内战的政治目的,就必须用这种可能为国共双方所“接受”的政治纲领去影响中国政局。而要增加民盟对国共两党施加影响的力量,就必须寻找社会大众的理解和支持。民盟要让这种“英美的政治民主、苏联的经济民主”的方案为更多人所接受,自然有必要从组织基础上去寻求更多的支持者。
在民盟领导上层看来,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小私有者的农民和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是极大多数,这个极大多数就是中间层。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是代表中间阶层的。基于这种认识,民盟领导人在国共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亟需要抛出一套为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并从中进行调和,就必须使其组织基础奠定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之上。因此,只有大量吸收“代表中间阶层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充实其组织,才能使民盟组织成分与迅速变化的政治局势相适应。而1941-1943年的民盟(政团同盟时期)盟务恰为青年党所把持,该党把大量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拒于门外。显而易见,不改变政团同盟的性质,不进行组织改组,壮大第三者的力量就无从谈起,也无法进行国共调解。可见,时局与政党的历史担当,促使民盟的组织成分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2.内战的预见、国共与民盟的关系与民盟的政治抉择。在抗战胜利前后,为杜绝内战,民盟中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如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等为斡旋国共关系而奔走于重庆和延安之间。在调和国共的过程中,民盟充分显示着自己的存在,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政治作用,但是正如左舜生所言:“我们越是怕内战,内战越是不能避免”[11]。全面内战爆发后,民主人士在抗战胜利前后为消释内战而进行的努力终以失败而告终。面对这种现实,民盟做出自己的政治判断和抉择也就迫在眉睫。“或是靠近国民党,或是靠近共产党而不能有其它道路时,他就不能不放弃它的中间立场身份”[12]。
在民盟自身开始思考对国共两党的政治抉择时,国共两党对于民盟的不同态度,则成为民盟本身变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此,左舜生有过这样的言论:“国民党对‘民盟’的态度是始而怀疑,继而冷淡;中共则表面加以敷衍,而内则希望其逐渐演变,完全成为他们的一种工具;其不愿意真正有一个制衡力量可以左右于二者之间,可以说国共两方面是大体一致。不久因为救国会的分子逐渐加入了民盟,伪装的中共分子混进来的也有少数,其倾向中共的意味既已加强,青民两党便只好退出”[13]。虽然左氏所言带有强烈的个人偏见,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国共对于民盟的态度有一个不断变化选择的过程,即:国民政府对民盟始而怀疑,继而冷淡;而中共对民盟则始而怀疑、继而鼓励,再而信任与合作。
有学者指出:从统一建国同志会在国共间进行第一次调解[14]开始,国共间进行的一系列谈判都仅限于国共双方而未让外界插手。这是因为国民党始终没有把民盟(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时期)视作一个实体性的政党,而仅仅摆在利用的位置;中共则出于当时的民盟中央实际是由与国民党关系暧昧的青年党所把持,所以不能不抱有怀疑态度。这种状况一直到1944年才有所改变[15]。
到了1944年,由于民盟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态度越来越明朗,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加之民盟地方支部吸收了大量的无党派人士乃至少量中共党员入盟,中共对民盟的信任增加。民盟“倾向中共的意味既已加强”,就必然会遭到国民党的压制,而国民党对民盟的压制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反抗,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中共对民盟的顾虑,从而增加对民盟的信任度。虽然此时民盟的组织“还不够广泛,力量还没有充实,但前途是很广大的”[16]。正是出于这样的判断,中共在提出联合政府的建议之前,不仅特意征求了民盟的意见,而且将其列为党派会议的一方,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把民盟当作了重要同盟军。国共与民盟之间的三方互动关系在1944年开始形成。
在国共关系的后续演变中,民盟将不再置身局外,而要努力成为一名“局中的斗争者”。张澜在《中国民主同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一文中,亦明确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17]的主张。
也就是说,民盟在国共于己的态度及所作所为上的对比,很自然地成了其改变第三者立场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国共、民盟三者的关系演变中,民盟由“裁判员”变为“局中的斗争者”,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中国的十字路口,将政治选择定格在与中共携手的基石上。时人有评:“要知道实际政治不能完全摆脱权术,从战略上说,民盟和共产党互为呼应,实为必然。两者的目的都要削弱国民党,在这个前提下,两者当然要并行联系的”[18]。
3.民盟的政治抉择与民盟的改组。民盟响应中共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成为“中共尾巴”后,便与中共风雨同舟,一起面对着抗战胜利前后行将到来的政治波澜。而要成功地制止蒋介石政府对民盟的分裂、反对蒋介石政府发动之内战,就必须动员一切反对内战的力量,开展民主政治运动。“将‘政团’两个字取消,其意义是认为以往各中间民主党派的联合努力,还不足以争取民主政治的实现。今后必须联合各界各阶层的人民共同努力,才可以达到民主政治的目的……中国民主同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地开展民主运动。”[19]
回顾民盟的发展历程,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宗旨是在沟通各方意见,以利抗战建国之进行[20];民主政团同盟的动机,则是在调解国共两党,以求全国的团结抗战[21]。到了1940年代中后期,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国内政治力量开始出现消长变化,当避免内战希望渺茫,而国统区政治军事日益败坏、财政经济出现溃竭、人心涣散的时候,人们将其症结诊断为“未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19]。民盟在1944年改组,就是为了顺应这种时代要求,把“广泛地开展民主运动”作为自己的政治任务。而要实现这一政治任务,就需要不断扩大组织,不断增强力量,唯如此,才能不断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
可见,当民盟把“广泛地开展民主运动”作为自己政治责任后,扩大组织,吸收广大的无党派人士,便成了民盟应对形势、实现此任务的保证,这不仅是国共关系变化影响的结果,也是民盟政治选择的必然。
综上所述,民盟不断调整其组织成分,扩大组织基础,就是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的需要。在当时中国的政治风云中,国共关系成了影响抗战时期各民主党派的重要变量。抗战相持阶段的前期、中期,民盟以调解国共关系、促进团结抗战为己任,民盟得以产生和发展;进入抗战后期,在中共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方针的鼓舞及中共统战政策的影响下,民盟与中共在政治上开始进行更为紧密的协商合作。然而,在可以预见的胜利面前,却发现“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太多了,也太复杂了。政治与经济的复员,这不是简单的问题。军队的复员更不简单。而相连而至的一大串问题……乃至国共两党及各党各派间的问题,一切一切的严重而烦难的问题,都随胜利以俱来”[22]。当人们把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归于国内民主政治的症结时,大力发展民主运动就成了解救中国的唯一药方,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遂用这一历史使命代替以前在国共之间进行的徒劳无益的调解,重新定位本政党的任务。对民盟而言,不断扩大组织、吸收“各界民主人士参加同盟,尤其是要吸收富有声望的社会贤达,并培育青年干部”[23]便成了民盟适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正是在这种外部环境的催化作用下,民盟改组才成为历史现实。
[1]关于民盟的称谓,有的专指1944年改组后的中国民主同盟,有的合指1941年在统一建国同志会基础上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和1944年改组后的中国民主同盟。为求统一,现借鉴民盟有关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本文采用后者。
[2]赵锡骅.民盟史话(1941-1949)[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周新民.民盟成立的经过和今后怎样做好盟的工作[A].姜平.中国民主党派史[C].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
[4]叶笃义.略谈中国民主同盟历史[A].于刚.中国各民主党派[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5]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1937-1945)第五册(下)[G].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6]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后各小党派及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左派的反应[A].皖南事变资料选辑[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7]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A].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G].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8]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A].档案史料与研究[G].重庆市档案馆,1995(2).
[9]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1945年10月11日)[R].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G].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10]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A].文史资料选辑[G].1960(20).
[11]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A].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五辑第49—50种)[G].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
[12]叶笃义.略谈中国民主同盟历史[A].于刚.中国各民主党派[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13]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A].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五辑第49—50种)[G].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
[14]即1940年4月梁漱溟在一届五次参政会上提出《请厘定党派关系求得进一步团结绝对避免内战以维国本案》,要求组织特种委员会研究解决国共争端,黄炎培、左舜生、张澜等统一建国会的负责人联名提出《关于战区自相冲突事件之处置办法》询问案。
[15]闻黎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第三种力量[A].抗日战争研究(京)[C].1998(2).
[16]董必武.关于大后方各党派问题(1945年3月)[A].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抗日战争时期(下)[G].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7]张澜.中国民主同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A].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G].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18]储安平.中国的政局[A].观察[J].1947 年第二卷第二期.
[19]四川省档案馆.中国民主同盟[A].全宗名.再生[G].历史资料,卷号:2-15-1/3(1),1946(5).
[20]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A].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G].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21]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1941年10月10日)[A].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G].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22]张澜.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对抗战胜利结束后发表谈话(1945年8月12日)[A].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G].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23]崔宗复.张澜先生年谱[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