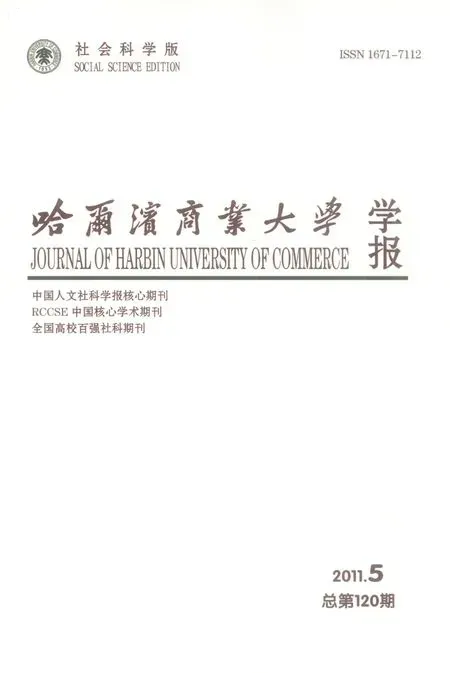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考证
张新知,王学文
(哈尔滨商业大学,哈尔滨 150028)
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随即占领了整个东北。1932年3月1日,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建立了以满清溥仪为头子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开始实行“民主共和制”,溥仪为“执政”,年号为“大同(取之于《诗经》中的‘天下大同’)”,“国旗”为新五色旗,“首都”为长春。因其主子日本的首都为东京,故改称长春为“新京”。两年以后的1934年3月1日又实行帝制,即君主政体,溥仪登基做了皇帝,改年号为“康德(即‘继承康熙之德’的意思)”,“满洲国”也改称“满洲帝国”[1]。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为了控制东北经济,操纵和独霸东北金融市场,于是又开始策划建立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货币,以统一东北币制。2011年是九一八事变80周年,值此之际,笔者试根据史料及哈尔滨商业大学货币金融博物馆馆藏伪满货币实物,对伪满洲中央银行及其发行的纸币种类及版别进行研究和考证。
一、伪满洲中央银行的建立过程
早在1915年,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就提出在我国东北创设“满洲中央银行”的构想,并称:“满蒙地利丰腴,物产富饶,对日本的经济价值,较诸台湾、朝鲜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台湾、朝鲜尚有专设的银行,而满洲却反无此组织,诚属不可思议之极”[2]。但由于条件尚不具备,未能实现。伪满洲国建立后,“为统一币制,稳定通货价值,必须有强力的中央银行,以此为中心,满洲国的政治经济才有可能顺利运转下去。中央银行之所以出乎意外地迅速建立,乃是由于关东军统治部早在建国之前,即对这件事进行了准备”[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沈阳、长春、吉林、齐齐哈尔等城市,同时抢占了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黑龙江省官银号(简称“四行号”)和辽宁省城四行号联合发行准备库、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及其所属机构。并在沈阳组建了由日本关东军、金融界头面人物及汉奸走狗们参加的所谓“金融研究会”,首先审议了对东三省官银号和边业银行的《管理办法草案》,把“四行号”等金融机构完全控制在日本手中。为了适应经济、金融侵略的需要,日本关东军于1931年12月16日设立了“统治部”,驹井德三任部长,并由该部伙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共同谋划建立伪满洲中央银行。首先草拟《满洲中央银行工作纲要》和有关法令以及《满洲通货金融方策》等文件,又责成统治部的财务课长五十岚保司负责筹建一切事宜。五十岚保司主持召开建立伪满洲中央银行的协商会议,对《货币法》、《满洲中央银行关系法规草案》进行了审议,研究了建行的各项准备及职制、人事配备等有关事宜。1932年3月15日,在长春城内被服厂召开建立伪满洲中央银行准备会议,关东军统治部部长兼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驹井德三代表伪国务总理宣布“设立满洲中央银行,将各官银号及边业银行合并进来”的决定。会议还内定了五十岚保司为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并设委员11人(日本人7人;中国人4人,均为“四行号”的顾问或负责人)。此后关东军统治部即将其筹建事项及原立案的一切法规都移交给建设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了按关东军的反动意图并由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和朝鲜银行、横滨正金银行配合下草拟的《货币法》、《满洲中央银行组织办法》、《旧货币清理办法》,6月11日由伪国务院会议通过公布。经过一系列阴谋策划,1932年6月15日伪满洲国政府任命了伪满洲中央银行的主要头目:总裁由伪财政部总长熙洽的亲信、原吉林省财政厅长荣厚担任;副总裁由台湾银行理事、伪国务院总务长官驹井德三的亲属山成乔六担任,他依靠驹井德三的势力,控制了伪满洲中央银行的实权;伪满洲中央银行理事共6人,中日各半,另设监事一人;总行的课长、部长握有实权,因为在这些职位的配备上,几乎全为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派出的日方人员所据有。此外,凡大中城市和边境地区分支机构的经理,几乎全由日本人担任。
1932年7月1日伪满洲中央银行正式开业,当时,伪满洲国执政溥仪、伪国务总理郑孝胥、伪国务院总务长官驹井德三、伪财政部总长熙洽、伪立法院长赵欣伯、伪实业部长张燕卿等都到场祝贺,由此可以看出日伪政权对控制金融的重视[4]。伪满洲中央银行成立后资本金定为3 000万元(伪币),实缴750万元;1933年7月1日又增缴资本750万元,实缴资本增至1 500万元;1942年资本金增至1亿元,实缴资本增加至2 500万元[5]。总行设于“新京”(长春)城内北大街原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长春分号旧址。由于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长春分号属于旧式银行,其功能满足不了新式银行需要,而且将其作为伪总行略显寒酸,于是1934年春将其拆除,在原址重建两层大楼。虽然新建大楼规模仍不大,设施也简陋,但伪满的许多经济方面的政策、法规大多出自于此,伪满洲中央银行早期发行的股票、债券及货币也均发行于此。同时也为后来建造更高标准的总行新大楼积累了经验,并为以后各地陆续建立的分支行大楼树立了样板。为炫耀和标榜伪满洲中央银行作为整个东北金融、经济命脉的中枢机关的地位,伪满洲国国都建设计划把新行楼也列为第一期的重点建设项目,从1934年4月23日至1938年8月用了4年多时间,实际花费伪币1 000万元,于市中心又建起了被日本人称为“亚洲第一坚固建筑”的银行新大楼,并将其总行由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长春分号址迁移至此,旧总行也随之改为伪满洲中央银行北大街分行。
伪满洲中央银行的分支机构遍及伪满洲国,其下设奉天、吉林、齐齐哈尔、哈尔滨4个分行,在伪满洲国各地设有众多支行,在重要的地区还设有办事处。1932年6月设立之初,分、支行达127家;至1938年增至142个分、支行和办事处。
二、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纸币的种类和版别
伪满洲中央银行成立后,进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强行收兑原有的各种货币,极力推行本行伪币,以达到“统一币制”的目的。哈尔滨商业大学货币金融博物馆藏有一张伪满洲中央银行康德元年的布告,该布告长为78cm,宽为55cm,彩色印制。布告上方印有“旧币将废,快换国币”八个大字,并有详细说明文字:“查后列各旧官银号、边业银行发行之纸币,依据满洲国法律自本年阳历七月一日、阴历五月二十日起,即一律失去其通用效力,期限已迫眉睫,凡有手存旧币者,希速来交换永远通用之国币”。后面详列各旧官银号、边业银行纸币为:“现大洋票、哈大洋票、奉大洋票、奉小洋票、吉林官帖、吉大洋票、吉小洋票、江省官帖、江大洋票、江省四厘债券”。中间印有手绘彩色各旧官银号、边业银行纸币图样。下方印有“满洲中央银行”和“康德元年三月”落款。这是伪满洲中央银行强行回收旧币,肆意推行伪币,以此掠夺东北人民的铁证。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面额主要有5分、1角、5角、1元、5元、10元、100元、1 000元等8种,因其中的100元券背面有一群羊,故俗称“绵羊票子”。从1932年7月1日开始发行到1945年伪满洲国灭亡止,伪满洲中央银行发行伪币共6套25种票券,发行总额达136亿元。伪满纸币按照伪康德二年十月六日《满洲中央银行行报》中《关于纸币名称由》的规定,纸币的套别须按“改造券”、“甲号券”、“乙号券”“丙号券”称呼,并以此类推,顺次冠以甲、乙、丙、丁……等字样。这些伪币开始发行时,票面上印有殖民地标志,如伪满洲国五色旗,伪皇宫等,后来为麻痹中国人民反满抗日情绪,便于扩大发行,又在票面上设计有中国人尊崇的孔子、孟子、财神爷等像,足见日本侵略者的险恶用心。
(一)改造券种类和特征
1932年6月11日伪满政府颁布的《货币法》规定:“货币之制造及发行权属于政府,由满洲中央银行代行之”。1932年7月1日伪满洲中央银行成立时,“伪满政府乃委托日本内阁印刷局印制伪货币法所定之纸币,惟印刷需要相当时日,在伪币未印成之前,临时取旧东三省官银号之壹元及拾元现洋票之未盖印章者而改造之,即此等票面加盖红色‘满洲中央银行’字样及发行根据字样,于伪中银开业之日发行”[6]。这种临时改制的纸币称作“改造券”,即临时利用东三省官银号民国18年美钞版1元和10元现大洋兑换券未盖印章的币料改制而成。此项改印工作由原东三省官银号所属奉天东记印刷所承担,改印的内容是:在票券上面“东三省官银号”行名下加印六个红色隶体字“满洲中央银行”;在图案北京香山双清别墅下方印有红色“依据大同元年满洲货币法发行”字样;下边原来盖章处重新加盖“满洲中央银行之印”和“总裁之印”两枚篆书方章,并用两条红线划去原券上的“中华民国十八年印”字样。背面上方加印黑色英文“The Ctntral Bank ofManchou”满洲中央银行行名,下边增加了总裁荣厚(右侧)和副总裁山成乔六(左侧)的黑色英文签名。据有关资料记载,到1932年8月23日,奉天东记印刷所共改造1元券170万张,10元券260万张;至该年末,共改造1元券319万张,10元券301万张[7]。此外还见有改制后5元券样票,属于未发行券。
(二)甲号券种类和特征
在改造券发行两个月以后,委托日本内阁印刷局承印的伪币陆续运抵,面额有5角、1元、5元、10元、100元5种。遂于1932年9月10日发行5角券,继而于11月10日发行10元券,12月20日发行1元券,翌年4月10日发行100元券,6月1日发行5元券。并以此陆续收回“四行号”旧纸币及开始发行的改造券。此套伪币称为“甲号券”,钱币界称其为“五色旗”票券。这是一套带有明显殖民地标志的伪满纸币,其明显特征是五种面额的票券除5角券外,其他票券正面左侧均印有一面伪满洲国“国旗”——五色旗,右侧印有伪皇宫中的“勤民楼(伪满洲国元首溥仪的办公楼,取自‘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之清宫遗训)”图案。各票券背面均印有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亲笔书写的说明,其中5角券说明内容是:“此票依据满洲国政府于大同元年六月十一日施行之货币法而发行者”;1、5、10、100元券除上述说明外,还增加:“货币法摘要,第1条,货币之制造及发行之权属于政府,而使满洲中央银行代行之;第2条,以纯银重量23.91瓦为价格之单位定名为圆”。此套票券无论从图案采用上,还是颜色配置,纸张选用上都完全不同于以后印发的各套纸币(后又发行乙号券、丙号券、丙改券、丁号券等)。票券上的“五色旗”是伪满洲国成立时确定的,是伪满洲国“国体”的象征。但“五色旗”的含义却有多种解释:按照日本人的用意,伪满洲国的建立并不是清朝的复辟,正如伪满洲国“国歌”所说:“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可见,新天地不是后清,所以不能恢复清朝的黄龙旗。但又不能脱离中国的正朔,露骨地表现出是日本扶植的傀儡。于是在辛亥革命时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五色旗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变成了新五色旗。“伪满洲国的组织成员,模仿旧中华民国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蜕化成为:满族、汉族、蒙古族、大和族(即日本)、朝鲜族‘五族协和’,‘国旗’定为黄色代表满族,在左上角四分之一的位置并列红蓝白黑长条,牵强附会地‘代表汉、蒙、日、朝’等四民族”[8]。日本史学界又从另一方面解释为:五色旗纵五横七,黄地,左方占全面积四分之一,自上分别为红、青、白、黑四色。“中国人素来尚黄,以黄色为地表示满洲广阔的沃土和福庆,左上角的太阳色表示热情、赤诚;青色象征青春、活泼;白色代表博爱和平、纯真公正;黑色表示克己和坚忍不拔。全五色又是五族协和的国是象征”[9]。此外还有一种解释:五色旗左上角四分之一面积依次为横条形红、蓝、白、黑四种颜色,其他四分之三面积为黄色,形成红蓝白黑四色依托于黄色,黄色包围着其他各色的格局。这里红、蓝、白、黑依次代表着汉、满、鲜、蒙各民族,而黄色代表日本“大和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看来,伪满洲国就是这样以日本大和民族为核心的“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这是多么赤裸裸的殖民统治。由此可见,伪满洲国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附属国[10]。
现在有的资料认为,“五色旗”票券是“该行开业当时草草设计印制者,其纸质、图案、彩色等均极粗劣。”[11]故后来又发行乙号券、丙号券等代之。但笔者就收藏的实物看,“五色旗”票券无论从图案设计、纸张选用及颜色配置上均为上乘:图案形象逼真,颜色鲜艳明快,尤其是采用了面值文字和花纹固定水印纸,且纸张内有红蓝海藻丝无规律分布,具有极高的防伪效果,质量完全可与后几套票券媲美。鉴于此,笔者认为,“五色旗”票券的收回并非质量问题,而是由于其图案有明显的殖民地标志,随着各地反满抗日情绪的高涨,出于发行便利考虑改用了后来带有明显麻痹反满抗日情绪,宣扬孔孟儒家思想的票券,这从后几套票券上带有孔子、孟子、龙、凤、财神爷等图案的纸币上可以得到证明。据我们对收藏的甲号券实物统计可知:5角券共发行1—10个批号;1元券共发行1—90个批号;5元券共发行1—15个批号;10元券共发行1—27个批号;100元券只发行1个批号。
(三)乙号券种类和特征
从1935年11月至1938年4月又发行了乙号券,面额有5角、1元、5元、10元、100元5种。因此套票券最明显的特点是各票券背面的面额文字均采用实心字体,故也称“单线券”。各票券图案设计基调与日本纸币相似,正面上方增加了伪满洲国国徽“兰花御纹章”②,背面上方增加了伪满洲中央银行行徽③。5角券和10元券正面图案均为财神爷赵公元帅像,背面分别为门楼和行楼图,发行时间分别为1935年11月1日和1937年7月;1元券正面为孔子戴冠半身像,背面为庄园图,发行时间为1937年12月;5元券正面为孟子戴冠像,背面为伪满洲国国务院大楼,发行时间为1938年1月;100元券正面为孔子免冠像和哈尔滨文庙大成殿,背面为羊群,所谓“绵羊票子”称呼即源于此票券,发行时间为1938年4月。据说100元面额的“绵羊票券”印有绵羊100只,在当时可购买100只羊,说明伪满洲中央银行纸币在最初发行时价值还是很高的[12]。各票券的共同特点是在票券正面两侧均印有龙图。其实,日伪当局在伪满纸币的设计上确实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地想找到一个既不过多地暴露其侵略野心,又能使中国和本国民众都能接受的且对中日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人物。于是就将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以及中国民间传说中的主管财富的神明财神像印于伪满纸币上,以蒙蔽民众,实现其独霸中国的野心。其目的就是借推崇孔、孟之道,宣扬封建正统观念,从而标榜伪政权的合法性。此套票券采用雕刻版印制,主要图案均由日本著名雕刻师加藤仓吉雕刻,钞纸采用“满洲中央银行”固定文字水印或财神爷半身肖像水印,印制质量较高。与甲号券比较,乙号券背面说明文字有些变化:除5角券仍采用郑孝胥书写的说明文字外,其他票券说明文字均改成了印刷体,且内容也变成:“此票券依据满洲国政府于大同元年六月十一日施行之教令第二十五号货币法而发行者”。从票券冠号看,乙号券除5角券采用6位号码外,其他票券均有6位号与7位号两种。据我们从收藏的实物统计可知:5角券共发行1—71个批号;1元券共发行1—385个批号;5元券共发行1—61个批号,其中1—23批号为6位号码,24—61批号为7位号码;10元券共发行1—237个批号,其中1—104批号为6位号码,105—237批号为7位号码;100元券共发行1—37个批号,其中1—5批号为6位号码,6—37批号为7位号码。
(四)丙号券种类和特征
从1941年至1944年开始发行丙号券。因此套票券最明显的特点是各票券背面的面额文字均采用空心双线字体,故也称“双线券”。丙号券增加了1角券,号码为短号,正面为花卉图案,背面为伪满洲国新京“建国忠灵庙”,无水印,发行时间为1944年8月14日。根据我们对收藏的实物统计,1角券共发行1—316个批号。可按照伪满洲中央银行《货币法》的规定,1角以下面额采用金属铸币,“可是由于金属原材料的紧迫,1角的也变为纸币了。这种1角券发行时,《货币法》是否以相应地修改过,不详”[13]。该券改由“满洲帝国印刷局”印制,但票券上的厂名却有“满洲帝国印刷局制造”和“满洲帝国印刷厂制造”两种,且颜色差异较大,可区分为多种版别。此票券还见有未裁切整版票券。其他5角、1元、5元、10元、100元5种面额票券与乙号券比较,除正面主图未变外,其他方面均有一些调整:5角券颜色变成了绿色,长号变成了短号,发行时间为1941年8月,根据我们对收藏的实物统计共发行1—151个批号;1元券颜色变成了棕紫色,背面去掉了庄园图,号码只有7位号一种,发行时间为1944年4月,据我们对收藏的实物统计共发行1—59个批号;5元券背面颜色改成绿色,号码只有7位号一种,发行时间为1944年4月,据我们对收藏的实物统计共发行1—24个批号;10元券正面中间变成了绿色,背面变成了蓝色,号码只有7位号一种,发行时间为1944年4月,据我们对收藏的实物统计共发行1—115个批号;100元券正面中间变成了蓝色,背面图案变成了粮仓图,且颜色也改成了棕色,号码只有7位号一种,发行时间为1944年11月,据我们对收藏的实物统计共发行1—50个批号。除1角券由满洲国印制局采用胶版印刷外,其他各票券均由日本内阁印制局印制,正面采用雕刻版印刷,背面采用石版印刷。
(五)丙改券种类和特征
伪满洲中央银行的纸币一直是由日本内阁印刷局印制的。在伪满洲中央银行刚成立时,“关于满洲中央银行券之印制,日、法、德等国公司,曾提出承印要求。但是,当时参与中央银行创建事务的人们,主张从机会均等主义出发,在形式上实行投标,而在暗地里却指定日本印刷局承印”[14]。“民国30年(1941年)以后,因战局关系,在日本印制钞票所需原料及运输等,均感困难”[15]。而且当时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华中、华南以及印尼、缅甸、太平洋各岛屿占领军为了确保新统治区的纸币发行,陆、海军都争先给日本内阁印刷局施加压力,纷纷争取优先印刷。这样曾一直在日本内阁印刷局印刷的伪满纸币,排到了最后一位。由于伪满纸币逐渐减少,库存见底,伪满的日本统治者十分头疼。加上当时下关至釜山间的运输联系受到美国潜水艇的严重威胁,由日本印制的伪满纸币几乎已陷于绝境。时任伪满洲中央银行总裁的西山勉等4人为此专程回日本商议,最后决定把印刷机器转运到长春,就地印刷。于是,由日本内阁印刷局让出凸版,大日本印刷公司等让出凹版、凸版、平版等机器几十台,1944年9月搭乘潜水艇,经过北朝鲜紧急运到长春。
决定由伪“满洲帝国印刷局”印制伪满洲中央银行纸币后,遇到的另一难题是纸张的选择。当时使用的纸张是由两家造纸厂提供的:一家是吉林特殊制纸厂,另一家是用豆秆纸浆生产纸张的四平伪满洲直辖造纸厂。为了从纸张质量上提高防伪能力,当时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把原来残破回收的伪满洲中央银行纸币溶解后,收回黄瑞香原料混入纸浆用以制造专用纸张;二是由日本金融专家、伪满洲中央银行总裁西山勉借助了当时纤维业界的最高权威“大陆科学院院长”志方的力量,把内蒙古地区盐湖湖底生长的水藻,经过着色、提炼、过滤后,也掺入伪满洲中央银行纸币的纸桨里。这种藻在世界上只有这个湖里出产,这对防伪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6]。
伪满洲帝国印刷局开始印制纸币后,“先印刷5角票、1元票、10元票,成绩颇佳,遂着手印刷100元票”。1944年11月,伪满洲中央银行在长春就地印刷的1元、5元、10元、100元券开始发行,“继因发行额增加,由以往之七色印刷,渐次减为五色印刷、三色印刷,其后又用凹版(橡皮版)印刷100元票、1 000元票、500元票,1 000元票已印就10亿元左右,均未及发行而伪满瓦解”[17]。
上述由伪满洲帝国印刷局就地印制的纸币即是“丙改券”。此套票券的1、5、10元券只是将原丙号券中的同面额券的长号码改成了短号码,由于印刷仓促,印刷厂名都未及改正,仍印“大日本帝国内阁印刷局制造”厂名,批号也接续丙号券已发行的批号继续排列。据我们对收藏的实物统计:1元券共发行60—105个批号;5元券只见样票,未发行;10元券共发行116—128个批号。100元券正背面图案未变,但号码改成了6位号,印刷厂名也改成了“满洲帝国印刷局制造”,背面颜色变成了紫红色;此券只发行1个批号,较为珍稀。同时增加了1 000元券,此券正面右侧印有戴冠孔子像,但不同于1元券上的戴冠孔子像,左侧为哈尔滨文庙大成殿,票券两侧改成了双凤图,下方印有“满洲帝国印刷局制造”厂名;背面印有伪满洲中央银行总行大楼;此券只见1个批号,存世量极少。“丙改券”各面额均发行于1944年11月。据资料介绍曾印有500元券,但目前未见实物。丙改券正背面多采用平版印刷,印色粗制模糊,质量较差。
(六)丁号券种类和特征
丁号券有5分、5角两种面额,均由伪满洲帝国印刷局制造,采用短号码,票幅较小,颜色浅淡,设计风格独特。5分券背面为伪满洲国新京忠灵塔图,无水印,从我们目前收藏的实物看共发行1—2个批号;5角券正面为哈尔滨文庙大成殿图,有满版“满”字水印,从我们目前收藏的实物看共发行1—4个批号,还见有未裁切整版票券,估计是日本投降后从印钞厂流出的。
三、伪满洲中央银行纸币的回收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苏军进军东北后于8月19日占领长春,并对长春实行了军事管制。8月21日苏军当局接管了伪满洲中央银行,将库存国币悉数没收,并利用没收的国币来支付各种开销。同时下令“从今以后,所有现金支付,不闻其情况如何,都须经苏军批准。”随后又发布命令:从今以后营业部一切对外交易均应停止。而后各金融机关、特殊公司等对存款人的非常支付或对申请支付救济款者,一件也没有被批准。11月15日,苏军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深夜悄然撤出伪满洲中央银行,随之八路军迅速接管了伪满洲中央银行。但因为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曾决定,苏军进驻东北后,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都由苏军交与国民党部队接收。于是国民党当局向苏军提出交涉,苏军迫于压力,只好限期要求八路军撤出长春。11月23日八路军被迫撤离了伪满洲中央银行,24日由国民党当局接收,12月12日国民党成立伪满洲中央银行清理处。至12月末,设在长春的总行及沈阳、吉林、锦州等分支行陆续被国民党中央银行接收。但鉴于当时东北地区政治形势较关内复杂,因此,伪满币迟迟未能收兑。1946年1月,国民党政府指令中央银行在东北地区(当时划分为九个省)发行东北九省流通券,发行地区仅限于国民党军队占领区。因此,伪满币的收兑也仅限于国民党占领区的长春、沈阳等大城市,而在其他地区,伪满币仍在市面流通,后虽有收兑,但数额甚微。对于已接收及已收回的伪满币,国民党中央银行依令进行销毁,其中数额较大的销毁是1947年4月7日至4月28日的几次销毁,共销毁各种票券总计6.21亿元,其中100元券1.5亿元,10元券3.85亿元,5元券0.38 亿元,1元券0.09 亿元,5 角券0.03 亿元,1角券0.17亿元。此外,还销毁已印竣尚未发行的5角券0.02亿元,已打孔尚未销毁的1元券0.04亿元。至1947年10月31日,国民党中央银行东北区各分行收兑伪满币共计69.7亿元,占1945年9月22日止伪满币发行总额136亿元的51%,尚有近半数的伪满币滞留在民间,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害[18]。
[注释]
①“满洲国”源于中国文献,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上谕中有:“我朝肇兴时旧称满珠,所属日珠甲,后改称满殊,而汉字相沿为满洲”。由此可见,称“满洲国”是别有用意的:“满洲”为清朝发祥之地,清逊帝统治其祖先旧疆内各民族名正言顺,日本只是辅助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并非侵害中国的领土和主权。
②伪满洲国国徽也称“兰花御纹章”,是以东北特产高粱穗的横截面为设计原型,其象征伪满洲国的皇权高高在上,也预示着伪满洲国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徽章上的花瓣、花茎和花蕊的数目均为5个,因此也寓意“五族协和”。
③1933年(大同二年)10月3日《满洲中央银行行报》第33号公布了伪满洲中央银行行徽和行旗的样式、书写及具体制作规定。行徽也称“行章”,主色为黄色,代表满族;行徽采用由四个满洲(Manchu)首位大写英文字母“M”而组成“四面八角”的“中”字形(伪满时期的各种徽章几乎都以英大写文字母“M”为主体而设计)。四个“M”分别代表原东北“四行号”,即东三省官银号、吉林永衡官银钱号、黑龙江省官银号、边业银行;“中”字代表“满洲中央银行”。其寓意是:伪满洲中央银行是在“四行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四面八角”的
“中”字形则预示着伪满洲中央银行作为伪满洲国的金融中枢,将“兴旺繁盛,四通八达”。
[1]文 斐.我所知道的蒙疆政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206.
[2]黄汉森.日伪政权的金融与货币图说:伪满洲国卷[M].亚洲钱币学会出版社,2003:36.
[3][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满洲国史》总论293页,哈尔滨,1990.
[4]吉林省金融研究所.伪满洲中央银行史料[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1-3.
[5]李 重.伪满洲国货币研究[M].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2.
[6]吉林省金融研究所编.伪满洲中央银行史料[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103.
[7]胡学源.东北近代币钞考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97-98.
[8]文 斐.我所知道的伪满政权[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13.
[9][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满洲国史》,哈尔滨,1990.
[10]张新知.一套带有殖民地标志的伪满纸币[J].成都钱币.2000,(2):54-55.
[11]吉林省金融研究所编.伪满洲中央银行史料[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103.
[12]徐 枫,赵隆业.日伪政权银行货币图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0.
[13]吉林省金融研究所编.伪满洲中央银行史料[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309.
[14]吉林省金融研究所编.伪满洲中央银行史料[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121.
[15]吉林省金融研究所编.伪满洲中央银行史料[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104.
[16]刘长福.伪满最后的纸币印制[J].中国钱币,1989,(4):66.
[17]吉林省金融研究所编.伪满洲中央银行史料[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104.
[18]江苏钱币学会编.中国近代纸币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980-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