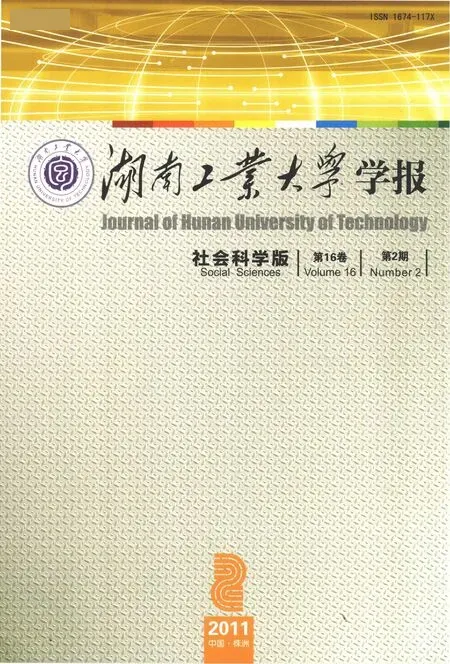从《水云》版本看沈从文文学思想的衍变*
龙智慧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长沙,410131)
从《水云》版本看沈从文文学思想的衍变*
龙智慧
(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长沙,410131)
沈从文的重要散文《水云》主要有选集本和全集本两个版本。对两个版本进行比较,通过研究其文字校改所引起的文本效果的差异,尤其是通过研究那些几乎足以改变初刊本原貌的重要修改之处,可以从中发现沈从文文学思想和审美理想衍变的历史轨迹。
沈从文;《水云》;版本比较;文学思想;审美理想
Abstract:One important essay named“water-clouds”by Shen Congwen has two versions of the complete work and the main selection.By comparing these two versions,we can find Shen’s ideological and aesthetic ideal of history evolution by studying the text modifying which caused by differences of text effect,in particular through the research that is almost enough to change the important points for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first printed edition.
Key words:Shen Congwen;water-clouds;versions comparing;literary thought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他的人生跌宕起落,文学生命也坎坷曲折。他醉情于自然山水,自然与人相依相存的风情是他人生的寄托,将山水的自然性与文艺的审美性乃至人类生命的哲理性相融合,是其文学思想与审美追求的重要向度。在沈从文创作的70余种小说、散文集中,《水云》是研究者们不可不提的一个特殊文本。所谓“特殊”,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扑朔迷离。自其传世以来,学界对其便有多重解读:张兆和作总序,刘一友、向成国、沈虎雏编选的《沈从文别集》,把《水云》编入“友情集”;金介甫认为它是“沈从文婚外恋情作品”[1],着重从创作实验、讲述故事的角度去分析它;而大多数研究者则根据沈从文在青岛及昆明时的心境和情绪来解读它。笔者认为,借助心灵独白与自我对话的方式,沈从文在《水云》中对自己的文学思想和审美追求作了重要阐释。《水云》三种版本的文字差异,真实反映了沈从文文学思想和审美追求在不同时期的衍变轨迹。
一
《水云》最初于1943年1月连载于《文学月刊》1卷4-5期,分两次刊完,署名沈从文。现收入《沈从文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1卷中的《水云》,即此初刊本,篇名为《水云——我怎么创造故事,故事怎么创造我》。而收入《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2卷《七色魇》集中的《水云》,则是沈从文于1946年5月在昆明重校,并于1947年8月28日再次校注后的版本。这是目前《水云》最有代表性的两种版本。作为“一篇心理自传”,[2]385《水云》是理解沈从文20世纪30至40年代创作心理流程的重要散文作品之一,它与后来被称为“七色魇”的散文,“已经从30年代对外部世界的客观叙写转入对社会人生的内心观照,对人生带着普遍性的哲理思考在作品中占据了压倒的优势”,从而体现了“沈从文寓居云南以后整个散文表现形式的特点”。[2]385同时,沈从文还在《水云》中提出了一些能充分展示其创作倾向和审美标准的重要观点。如“情真事不真”,“美丽总使人忧愁,然而还受用”,以及他所谓的“新道家思想”等等。毋庸置疑,在以往的研究中,《水云》是“曝光率”较高的作品之一,文中的许多关键性文字被人反复引用,用以鉴赏和阐释沈从文的其它作品,分析和探究沈从文的文学思想和审美理想。但是,迄今为止,《水云》的两种版本异同之间的比较,却未曾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关注,这不能不说是沈从文研究中的一个缺憾。有鉴于此,本文将对《水云》的初刊本与全集本作一比较,重点研究其校改所引起的文本效果的差异,尤其是研究那些几乎足以改变初刊本原貌的重要修改之处。希望这一繁杂琐屑,需要细心和耐心的工作,能引起学界对于《水云》版本变迁的关注,进而探究其版本变迁背后的深层意义。
二
《水云》中有一段很重要的文字,沈从文自称是“几行关于小说的意见”。这是一段论述美、善、真三者辩证关系的文字,对理解沈从文的文学思想和审美取向有着重要意义。沈从文在自己的文本中反复书写过三次,按时序它们呈现出同中有异的三种面貌:首先是《水云》初刊本(1943年,下文简称“初刊本”),其次是《看虹摘星录·后记》(1945年,下文简称“后记本”),再次是《水云》全集本(1846——1947年校后本,下文简称“全集本”)。鉴于这段“意见”对于研究的重要意义,此处将其三种版本摘录如下,并试作对比分析。
初刊本:
什么叫作真?我倒不大明白真和不真在文学上的区别,也不能分辨它情感上的区别。文学艺术只有美和不美。精卫衔石,杜鹃啼血,情真事不真,并不妨事。你觉得对不对?
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是罪恶,可是总不能令人愉悦。我们活到这个现代社会里,被官僚、政客、银行老板、理发匠和成衣师傅弄得到处是丑陋,可是人应当还有个较理想的标准,也能够达到那个标准,至少容许在文学艺术上创造那标准。因为不管别的如何,美应当是善的一种形式。
……美丽总令人忧愁,然而还受用……
后记本:
我不大明白真和不真在文学上的区别,也不能分辨他在人我情感上的区别。文学艺术只有美或恶劣,道德的成见与商业价值无从掺杂其间。精卫衔石,杜鹃啼血,事即不真实,却无妨于后人对于这种高尚情操的向往。
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从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我们活到这个现代社会中,已经被官僚、政客、肚子大脑子小的富商巨贾,热中寻得出路的三流学者,发明烫发的专家和提倡时髦的成衣师傅,共同弄得到处丑陋!一切都若在个贪私沸腾的泥淖里辗转,不容许任何理想生根,这自然是不成的!人生还应当有个较高尚的标准,也能够达到那标准,至少还容许在文学艺术上创造几个标准,希望能从更年青一代中去实现那个标准。因为不问别的如何,美就是善的一种形式,文化的向上也就是追求善或美的一种象征。竞争生存固十分庄严,理解生存则触着生命未来的种种,可能更明白庄严的意义。
美丽总令人忧愁,然而还受用。
全集本:
什么叫作真?我倒不太明白真和不真在文学上的区别,也不能分辨它在情感上的区别。文学艺术只有美和不美,不能说真和不真,道德的成见,更无从羼杂其间。精卫衔石,杜鹃啼血,情真事不真,并不妨事。你觉得对不对?我的意思自然不是为我的故事拙劣要作辩护,只是……
不管是故事还是人生,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是罪恶,可是总不能令人愉悦。我们活到这个现代社会里,被官僚、政客、银行老板和伪君子、理发匠和成衣师傅,种族的自大与无止的贪私,共同弄得到处是丑陋!可是人生应当还有个较理想的标准,也能够达到那个标准,至少容许在文学和艺术上创造那个标准。因为不管别的如何,美丽当是永远是善的一种形式,文化的向上就是追求善的象征!
……美丽总令人忧愁,然而还受用……
后记本的这段文字出于《看虹摘星录·后记》(原载1945年12月8日和12月10日天津《大公报》),作者说是“引用”,实则在原文(即《水云》初刊本)的基础上作了不少发挥。就这段“意见”本身的变迁而言,“后记本”的文字实可视为一种过渡。由于是校改,“全集本”则一方面仍与“初刊本”大同小异;另一方面也沿袭了“后记本”中的一些发挥处,并且有所增。但就整体而言,“意见”则是基本一致的:一是否认所谓文学上的“真”,认为文学可以“情真事不真”,指出文学的评判标准应是“美和不美”;二是认为“美是善的一种形式”,从而实际上点明了文学的价值取向;三是强调“美(丽)总使人忧愁,可是还受用”,坚持自己的审美理想。
同时,当把这三种版本的“意见”并列对照时,我们还可以看出:首先,对于文学的“商业价值”,沈从文似乎有一种游离或者说矛盾复杂的情感态度,这表现在他对涉及这一问题的相关文字的先增又删的具体操作之上。对于文学商业运作方式,沈从文认为商业化是纯粹的文学创作的天敌,但同时他似乎也没有全盘否定商业运作在文学传播过程中的作用。都市商业使得文学作品的传播渠道更加多样化和流畅化,使越来越多的读者认识到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品,同时,这对于作家而言也是一种鼓舞和激励。从这一角度看,沈从文已初步意识到了文学流通领域的商业运作的双刃剑属性。
其次,尽管沈从文对社会丑陋现象及其产生根源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但由于他那“乡下人”的局限性,他对社会的认识更多是停留在表象之上,而对其本质的认识有严重不足和相当的片面性。在沈从文的许多自述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总是以“乡下人”自居:
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乡下人。[3]
我们姑且称之为“乡下人情结”,这种情结不仅促成了他个性化的题材选择和艺术思维模式的建立,也使他触及了原生态的生命个体,使得他的这部分作品具有超越性的哲学意义。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乡下人情结”的矛盾性蕴育了沈从文“美丽总是使人忧愁”的美学风格。而另一方面,这种情结在沈从文的都市题材小说创作中则表现出了极大的负作用,他对都市强烈的厌恶甚至憎恨,犹如一面哈哈镜,其焦点就是批判都市。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物性格被平面化、简单化、绝对化处理,甚至吝惜一个名字,而经常用绅士、太太、甲、乙、丙、丁等来指称。这恰恰表明这些人物是沈从文心目中都市人的抽象化符号,是其客观认知与主观情感的传声筒,而非一活生生的个体。这也提醒研究者们,在探析沈从文的创作及文学思想时须保持清醒、辩证的态度。
第三,全集本中对于“也能够达到那个标准”的删改,正与沈从文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未来人生的焦虑感相契合。全集本《水云》与初刊本的重要区别之处,还在于二者结尾在文字上的截然不同,这种文字差异几乎可说直接影响到《水云》文本的面貌。本文将在分析比较这两种结尾的同时力求考察作者作此修改的良苦用心。现摘录两种结尾如下:
初刊本:
……一切皆近于抽象。我所有作品大多都出于抽象的抒情,情绪的散步,只能在少数又少数人的情感中发生共鸣,却不会在多数人生活上产生价值作用。
全集本:
灯光熄灭时,我的心反而明亮了起来。
一切都沉默了,远处有风吹掠树枝声音轻而柔,仿佛有所闻问:“X X,你写的可是真事情?
我答非所问:“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
从表现方法上看,初刊本结尾是议论的,而全集本结尾则是记叙性的。综合全文考察,全集本结尾在两个方面的作用比较突出:其一,它与整个文本的心理叙事氛围更为融洽;其二,它与作者在文本开端时所增补语句:“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生命也不能在风光中静止,值得留心!”形成一种呼应关系,在结构上更加缜密完整。然而,初刊本的结尾在原文中也并不见突兀与不和谐。那么,作者主要是基于何种考虑而作此修改的呢?这就需要具体考察两种结尾的关键话语的内在联系,并进而考察作者作此更改的真实意图所在。
三
初刊本结尾的核心概念是“抽象的抒情”和“情绪的散步”。沈从文于1961年曾作过《抽象的抒情》一文,虽然这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但是从它现存的文本我们还可以找到作者对于“抽象的抒情”这一概念的某些解释。在这篇文章里,沈从文仍然坚持自己一贯的文学主张,极力反对“用个人权力或集体权力压迫其他不同情感观念反映方法”,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气候里,沈从文竭力为文学艺术作辩解,强调文学“其实质不过一种抒情”,“事实上如把知识分子见于文字、形于语言的一部分表现,当作一种‘抒情’看待,问题就简单多了。”[4]12他不赞成把作家的情感以及文学所表现的作家的主观精神世界理解得简单化、狭窄化甚至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对于有些“对生产对斗争知识并不多的知识分子,说什么写什么差不多都像是即景抒情”,“这种抒情气氛,从生理学或心理学说来,也是一种自我调整,和梦呓差不多,对外实起不了什么作用”[4]11;“从国家来说,也可以注意利用,转移到某方面……但是也可以不理,明白这是社会过渡期必然的产物,或明白这是一种最通常现象,也就过去了。”[4]13毫无疑问,沈从文的“抒情说”,是其文学与政治保持距离思想的另一版本。当沈从文说他的作品是出于“抽象的抒情”时,他想说的其实就是,“我以为人生追求抽象原则,应超越功利得失和贫富等级,去处理生命与生活。”(《水云》)对沈从文而言,只能这样才有可能“重造经典”。可以说,“抽象的抒情”正是沈从文追求的“当代经典”所应该表现思想内容。至于“情绪的散步”,沈从文在《情绪的体操》一文中如是阐释:
你不妨学学情绪的散步,从从容容,二十米,两百米,一哩,三哩,慢慢的向无边际一方走去。只管向黑暗里走,那方面有得是眩目的光明。你得学会控驭感情,才能运用感情。你必需静,凝眸先看明白了你自己。你能够冷方会热。
也即所谓“一种使感情‘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4]13可见,“情绪的散步”指的是创作心态的调整。这两者紧密结合,构成了沈从文创作思想和审美理想的有机整体。
可以说,“抽象的抒情,情绪的散步”是沈从文创作的内容和心态两方面神往的理想境界。那么,作为全集本结尾中心理念的“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又是什么意思呢?在全集本中,我们至少可以从作者在文本修改的两处地方找到深层次理解这一中心理念的线索,其一,是作者增补的一段话:
我的目的正是让不能静止的生命,从风光中找寻那不能静止的美。我得寻觅,得发现,得受它的影响或征服,从忘我中重新得到我,证实我。
这里,作者主要传达了两层意义:其一是让生命找寻美,这不正是“抽象的抒情”所要表述的意思吗?其二是从忘我中得到并证实我,这不正中“情绪的散步”的同义替换吗?另外一条线索是全集本中第二节最后一个自然段中有这么一句:“……注入我生命中属于抑压的种种纤细感觉和荒唐想象”,其中“抑压”是由初刊本的“情绪的散步”改成的。作者为什么要这么改?他有什么良苦用心?我们知道,沈从文曾经学习过精神分析学说,熟知弗洛伊德的“压抑”说:
吾人的生命力,是在一个无形无质的“社会”压抑下,浸润泛滥于一切社会制度,政治思想,和文学艺术组织上,形成历史过去而又决定人生未来。这种生命力到某种情形下,无可归纳挹注时,直接游离成为可哀的欲念,转入梦境,找寻排泄,因之天堂地狱,无不在望,从挫折消耗过程中,一个人或发狂而自杀,或又因之重新得到调整,见出稳定。[5]
毫无疑问,全集本中的“抑压”正是“情绪的散步”的同义替换。这种同义替换不仅强化了原来“情绪散步”所包含的全部内容,而且从更高的角度传递了沈从文这位“讨厌一般标准”,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最后一个浪漫派”,坚持不懈地写“最后一首抒情诗”的深层心理。因此,尽管全集本的结尾以“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取代“抽象的抒情,情绪的散步”,在文字上截然不同,但是作者其实并没有改变和放弃自己独特的审美理想追求。他的作品所反映的客观艺术效果与他的这种审美追求密切相关。他以真挚而诗意的心灵感悟自然和社会,造成了他作品中充斥的大量感官的、直觉的、情感的、想象的因素,而理性因素则往往居于次位。如果说这种结尾变更对文本的面貌有所影响,那也只是更趋完美,更加诗化而已。
从以上对《水云》的版本校读中,我们不难看出沈从文对艺术的精益求精,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个性的坚持不懈。时光流逝,这一切只留下一道历史的痕迹。在沿着这条痕迹对前人的文本进行近乎考古的研究时,我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一篇篇满含历史沧桑的优美文字,也不仅仅是一位在艺术之路上艰难跋涉的精神偶像,而是于这沧桑历史和精神跋涉之中传递下去、生生不息的那种沉甸甸的精神寄托和孜孜不倦的生命追求。而这些却正是我们这些生活在所谓“后现代”,所谓“消费社会”,所谓“信息时代”,饱受各种文学上的粗制滥造和急功近利折磨的人们所最需要的。
“凝眸先看明白了你自己”,诚哉斯言;“能够冷方会热”,信哉斯言。
[1]金介甫.沈从文传[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248.
[2]金介甫.凤凰之子:沈从文传[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
[3]沈从文文集:第1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3:11.
[4]沈从文别集:抽象的抒情[M].长沙:岳麓书社,1992.
[5]罗 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306.
责任编辑:黄声波
On reading the Literary Thought and Aesthetic Pursuit from the Version of Water-Clouds by Shen Congwen
LONG Zhihui
(Hun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of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Changsha,410131,China)
I207.65
A
1674-117X(2011)02-0091-04
2010-12-05
龙智慧(1965-),女,湖南长沙人,湖南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主要从事现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