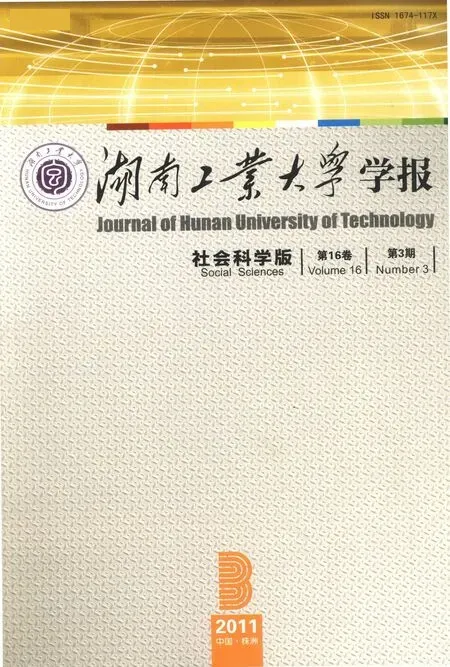论新时期知青题材小说乡恋主题的嬗变*
孔瑞珠
(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南京210019)
论新时期知青题材小说乡恋主题的嬗变*
孔瑞珠
(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南京210019)
20世纪80年代,知青题材小说中的乡恋之歌久唱不衰,90年代乡恋之歌的余音仍可听到,但细细辨听同一首歌音调却不尽相同。相对80年代在乡土上寻找精神家园,90年代的乡村赞美更多的带有一种功利性,这除了与中国经济制度的改革、文化的转型紧密相连,还与作家心态变化密切相关。同时,曾在80年代知青小说中集体失语的农民,对于这种近似单相思的乡村之恋,由他们的后裔做出了迟来的回应——恨。
知青题材小说;乡恋情结;主题嬗变
以情动人是知青题材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其中乡恋情结是其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许多知青小说的主题。
在充满理想主义的20世纪80年代,一切情感都是那么单纯而直接,炽热而鲜明。20世纪70年代末期知青大返城潮流席卷了整个中华。逃离农村,回到城市的知青们,忿忿不平地向世人们展示伤痕,诅咒乡村的一切,甚至发誓永不再踏上那块土地。然而当愤怒发泄完后,知青们很快又集体转向,抒发对乡村、农民的怀念,感激之情喷薄而出,乡恋之歌唱响在各个文本中,且这一乡恋之歌久唱不衰。90年代乡恋之歌的余音仍可听到,但细细辨听同一首歌音调却不尽相同。相对80年代在乡土上寻找精神家园,90年代的乡村赞美更多的带有一种功利性,这除了与中国经济制度的改革、文化的转型紧密相连,还与作家心态变化密切相关。
同时,曾在80年代知青小说中集体失语的农民,对于这种近似单相思的乡村之恋,由他们的后裔做出了迟来的回应——恨。面对农民的指责,社会一边批评知青的话语霸权,一边为多元话语的出现而欢呼,知青们被推入一个尴尬的境界,在爱恨交织中,完成了他们的情感变迁。
一
20世纪80年代知青小说中始终萦绕着挥之不去的乡恋情结,具体表现为对挥洒过汗水的那方热土的眷恋,对善良憨厚的乡亲们的怀念,对大地和人民哺育之情的感恩。翻开小说我们看到的是:史铁生回忆起《插队的故事》,深情地遥望黄土高原上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张承志魂系茫茫草原上的《黑骏马》,在《绿夜》里懂得了《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张曼菱魂牵梦绕着的是《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铁凝让《村路带我回家》,灵魂驻足在冀中平原的《麦秸垛》。
对于这种强烈的乡恋情结,有学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抒情化的乡村描写也多是源于现实压力下的一种情感补偿和心灵松弛愿望……是作者们现实生活中的一种虚构幻梦,是他们借以抚慰在重返城市的拼搏中被创伤的心灵的温柔剂,是他们用以暂时平衡现实文化与他们心理文化的巨大反差的文化工具。它的实质是知青们与城市努力达成和谐过程中的暂时不和谐音。”[1]
经过数十年的磨合,当年的知青们已在城市立足,而乡村仍是他们午夜深处的梦境,乡恋之歌又回响在90年代的文本中。然而唱响这乡恋之歌的不再是那个寻求心灵抚慰的弱者,而是一个已与城市达成默契的强者。强者们用一种怜悯的眼光俯视仍旧贫穷的乡村,向仍然是弱者的农民伸出援助之手,在物质上给予经济帮助。这不是强者对弱者在财富上的炫耀,而是怀着一种报恩或者弥补以往过错的愧疚心态,以求得心灵的宁静、道德的完满。从《王桃》(范小青《上海文学》1991年第11期)中江惠中帮助插队乡村办食品加工厂,《山珍》(陆大献《红岩》1991年第1期)中当年的知青主动要求到当年插队的乡村做蹲点干部以助村民脱贫致富,到《旋转猎场》(王立纯《十月》1990年第9期),《清凉之河——吴越风情系列之一》(陈军《当代》1992年第3期)中未返城的知青带领林场职工、当地农民走上富裕之路,强者的身影已无处不在,他们用站起来的姿态大声地宣告:帮助乡村建设家园是真正的乡村之爱,温情化的乡村描写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南山有鸟》(郭彦《当代》1992年第3期)中小有名气的画家申桦夫妇、大学教师郑飞鸿、女诗人豆豆各怀目的在当年插队的农村集资修建了一幢乡间别墅。它是申桦对都市生活厌倦后在乡村的栖息地,补充能量的加油站。郑飞鸿利用它掀起文化界对文化人生活方式和理论关注的新热潮,作为进入文化界上流圈的梯子。豆豆把它作为保持自己“女妖”风度的新神话,以维持她在诗界的知名度。《三月一日》(潘军《收获》1997年第5期)中右眼突然失明的“我”在接到种种诡秘的暗示后,重游当年插队的农村后,右眼得以复明。《爱的岁月最残酷》(唐颖《上海文学》1997年第10期)中彭家庆与万新在插队地产生纯真爱情,回城后爱情在欲望化的城市中变得暧昧不清,婚姻最终走向解体。小说结尾处情感出轨的万新带着忏悔来到当年的云南小城重拾旧梦,但在情感的瓦砾堆中,旧梦已残缺不全。《最后一名女知青》(阎连科,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中20世纪70年代李娅梅因为城市的家中已容不下她的一张床而与插队地的张老师结婚。但因为始终向往城市,在90年代她又回到了城市,但最终却被冷漠的城市再一次抛弃,她也再一次一无所有地回到了张老师身边。在以上4部作品中,乡村不再是知青们的精神家园,乡村之爱不再是我们曾见到过的对于乡村温情脉脉的歌唱。乡村作为城市的对立面而存在,一如当年沈从文先生用充满人性美人情美湘西世界来抵抗堕落的城市。当代人患上城市焦虑症后,迫不及待地到乡土上寻求药方,而民间土方只能减缓一时病状,并不能治本。虽然乡间别墅的建造达到了大伙的目的,“我”的右眼也复明了,但万新和李娅梅在乡间最终能否找回幸福,小说并没有交待出下文。
此外,王安忆发表的系列作品如《姊妹们》(《上海文学》1996年第4期)、《喜宴》和《开会》(《上海文学》1999年第5期)、《花园的小红》(《上海文学》1999年第11期)等中,我们看到一种不同于以上两种方式的乡村之爱,是一种超越功利层面的审美之爱。王安忆称:“我写农村,并不是出于怀旧,也不是为祭奠插队的日子,而是因为,农村生活的方式,在我眼里日渐呈现出审美的性质,上升为形式。这取决于它是一种缓慢的,曲折的,委婉的生活,边缘比较模糊,伴着一些触角,有着漫流的自由的形态。”[2]作品描绘出一种具有美质的生活形态,小说不以故事为表现中心,而是以知青的视角描绘出一幅幅农村的生活画面,活动在其中的人物连同事件场景,共同演绎着一种有意味的生存形态和关系形态。从“雯雯”系列到《本次列车终点》《小鲍庄》,王安忆对乡村的记忆以乡村的道德美感为内蕴,或深情赞美充满温暖的乡土人情,或频频回眸乡村以借取抚慰心灵的力量,或用审视的目光批判乡村道德。90年代王安忆“从‘淮海路’到‘梅家桥’”的转变,让我们看到她努力地“掀开‘强势文化’播撒的厚厚观念、名词的覆盖层”,“凭感性和诗情去深入生活”,“直接去触摸真的人生”,规避意识形态的影响[3],因而,没有浸染过商业气息的乡村生活,以审美的形式出现在她的笔下,滤去了精神依托的功利性,显得纯真、质朴。
二
不论是知青们在诅咒那片给予他们苦难的土地时,还是知青们用诗意化和温情化的笔调塑造乡村时,我们都没有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本中另一个主角——农民们的相应回应。一方面是知青的话语霸权,一方面是农民的集体失语。我们见到的只有知青的历史,农村的苦难乃至中国的苦难在叙事中被无意地割裂。正如有学者指出:“当年的‘知青’们,作为完成了‘知青运动’的一半,垄断着关于这场运动的全部话语权……在‘知青话语’中,‘知青’总是主体,而农村和农民则只能是客体,被置于受打量、受审视的境地……只听见‘知青’在单方面地说个不休,他们说着当年的自己,也说着当年的农村和农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表现了‘知青’的话语霸权……迄今为止的‘知青’形象都是‘知青’的自我塑造。‘知青’或许并没有资格独自承当对‘知青’这一历史形象的塑造。‘知青’哪怕写下了再多的文字,也只能完成自我形象的一半,而另一半,应由农民来完成。只有当各地的农民写出了自己心目中的‘知青’形象时,‘知青’形象才能说是完整的和真实的。”[4]
20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农民的孩子们向世人讲述了他们眼中的知青,缺失的另一半记忆在叙事中得以缝合拼接。让我们先来听听贾平凹的叙述:“在我的经历里,当时我多么羡慕着从城里来的知青啊!他们敲锣打鼓坐汽车来,从事着村里重要、轻松的工作,比如什么赤脚医生啊代理老师啊拖拉机手啊记工员啊文艺宣传队员啊,他们有固定、偏上的口粮定额,可以定期回城,带来收音机、书、手电筒、万金油,还有饼干和水果糖,他们穿西裤,脖子上挂口罩,有尼龙袜子和帆布裤带,见识多,口才又好,敢偷鸡摸狗,敢几个人围着打我们一个。更丧人志气的是他们吸引了村里漂亮的姑娘,姑娘在首先选择了他们之后才能轮到来选择我们。前几年社会上流行着一首歌曲《小芳》暴露的是时过境迁之后那些知青对于抛弃在乡下的姑娘的一份追忆。我听见那歌曲中的‘谢谢你,给我的爱,让我度过那个年代’,我心里厌恶着小白脸的浅薄,他们在时代中落难,却来到乡下吃了我们的粮食、蔬菜和鸡,夺走了我们的爱情,使原来荒凉的农村越发荒凉了。”[5]
迟到的回应是截然相反的仇恨,知青们在他们本已贫瘠的土地上夺走了粮食,抢走了他们的姑娘,毁灭了他们的家园和爱情,这种乡村之恨在刘醒龙的《大树还小》(《上海文学》1998年第1期)、李洱的《鬼子进村》(《饶舌的哑巴》,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中表现得尤为强烈。《大树还小》中以乡村儿童大树的视角写出了农民眼中的知青。“为什么要喜欢知青?”“你们知青可从来没有喜欢过农村。”“老师在课堂上提过知青,说他们老写文章说自己下乡吃了多少苦,是受到迫害,好像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吃苦是应该的,他们就不应该这样。”连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大树都承受着这份仇恨,可见这恨有多深。故事中当地农民秦四爹在“文革”中和女知青文兰相爱,白狗子等知青认为这丢了城里人的脸,集体诬陷秦四爹强奸女知青,秦四爹被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罪”判入狱三年。而在改革大潮中发迹了的白狗子却“名正言顺”地霸占了进城打工的大树的漂亮姐姐,又一次引发了村民们对知青的恩怨情仇。在《鬼子进村》中知青是被当作“没调教好的驴”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他们是长着小胡子的“鬼子”,他们品行不端经常偷鸡摸狗,还在路上搂着亲嘴,但由于他们是城里人,他们的行为不受惩治,村里的“小芳”们仍追求着他们。小说告诉我们,农民才是上山下乡运动的真正受害者,而知青是乡村的入侵者,是造成混乱的根源。
三
在知青小说中,乡村是知青们寻找中的精神家园。当知青们离开乡村返回城市后,满怀的希望遭遇到城市现实的沉重打击,现实的压力与文化上的不适应让他们陷入迷惘,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选择,追怀起乡村生活,甚至如《南方的岸》中易杰与暮珍一样重返乡村,寻找失落的价值,构建理想的精神家园。但是知青作家这种“归去来”的矛盾心态,主要是他们返城后面临拒斥时自然萌生的一种怀旧情感,尚未有明确的文化回归自觉。这不是对乡村文化真正的认同与皈依,而是对城市文化另一种方式的追怀,诗意的乡村描写多是源于现实压力下的一种情感补偿。因而对于乡野的怀念“只是他们的一种精神需要而不是现实需要;对他们来说,乡野生活是可向往的而不是可达到的,是可欣赏的而不是可经验的。对乡村的怀念使他们有一种情感的完整,对城市的固守则保证了他们生活的完整。这种‘叶公好龙’式的矛盾恰好是城市人正常而和谐的状态。”[6]因而,在知青小说中中我们看到的乡村之恋,是一种城市对乡村在身心疲惫时需要的放松,在心灵受伤后需要的缝合,有时甚至是一种利益上的利用,而不是永恒的精神家园的寻找。
另一方面苦难承受者的知青形象全面瓦解,英雄式的知青人物彻底溃灭,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一片狼藉,如同一枚硬币两面,乡村之恨中的知青走向了历史的反面。米兰·昆德拉曾提出“悬置道德审判”的问题。他认为“悬置道德审判并非小说的不道德,而是它的道德”,“热衷于审判的随意应用,从小说智慧的角度来看是最可憎的愚蠢,是流毒最广的毛病。这并不是说,小说家绝对的否认道德审判的合法性,他只是把它推到小说之外的疆域。”[7]]这种乐于审判的毛病,正是主流知青文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无论是赞颂还是批判,主流知青文学总是在道德审判这个领域乐此不疲,不是在审判别人,就是在审判自己。20世纪90年代,非知青作家用“恨”颠覆“爱”,给予知青小说中道德评判沉重一击,解构了主流知青小说中的道德传统。
长久以来,知青独创的话语体系垄断了对知青历史的描述,他们在解说历史时不由自主地用虚构的历史或历史真实的某些方面代替全部遭遇的历史真实。这虽然符合知青读者的审美期待,但遭到其他历史事件参与者的质疑。“李大卫:我想那是一种策略性的叙事,是一些人通过宣示其罗曼斯化的苦难证明其在八十年代获得的些话语权势的合法性。然而这种叙事恰恰遮蔽了很多至今通行于世的苦难。这就为当下文学留下了大量的‘祛魅’工作……有关知青的一切,在迄今为止的文学中,尚未得到充分确实的表现。”[8]对历史进行反拨,颠覆知青形象,非知青作家的叙事选择了解构知青创造的神话,还原历史真相叙事策略,但他们的叙事“忽略了知识青年生存的那个严酷的历史背景,以及那个时代统治思想给知青和农民所带来的共同历史压迫,乃至这种历史压迫中更深的现实和传统的政治因素。任何丑化和美化知青和农民的创作,都很难真实地刻画出历史的原貌和人性的本真。”[9]
一场灾难性的运动,造就了一部厚重的知青文学史。这部文学史由不同时期、不同身份的作家共同书写,哪个版本才是真实历史的还原呢?开启尘埃遮蔽的历史,我们需要用客观公正的态度,真实地刻画出历史的原貌和人性的本质,才能对它做出准确的审美价值判断。
[1]贺仲明.中国心像:20世纪末作家文化心态考察[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24.
[2]王安忆.生活的形式[J].上海文学,1995(5).
[3]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J].文学评论,2002(3).
[4]王彬彬.“知青”的话语霸权[N].文艺报,1998-06-04.
[5]贾平凹.我是农民——乡下五年记忆[J].大家,1998(6).
[6]李书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文化测量[J].文学自由谈,1989(3).
[7]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7.
[8]张颐雯.寻找命运的契合点——后来者谈知青一代[J].北京文学,1998(6).
[9]丁帆.知青小说新走向[J].小说评论,1998(3).
On Theme Evolution of Country Love Novels with Intellectual Youth in New Era
KONG Ruizhu
(Nanjing Technical Vocational College,Nanjing,210097,China)
In the 1980s,country love themes were occurred in intellectual youth novels and they continued to appear from time to time in the 1990’s.However,a closer look at the subjects may cast light on some differences.In contrast to the 1980’s duty to seek for a spiritual home in the countryside,novels of the 1990’s were more utilitarian than melodious,which were not only related to Chinese reform of economic system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but also connected to the author’s psychological changes.Meanwhile,those farmers or peasants who had all lost their voices in the 1980’s novels were represented by their descendants who answered the unrequited country love with hate.
Educated youth theme novel;the township loves the complex;theme evolution
I207.42
A
1674-117X(2011)03-0054-04
2011-03-02
孔瑞珠(1977-),女,江苏高淳人,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黄声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