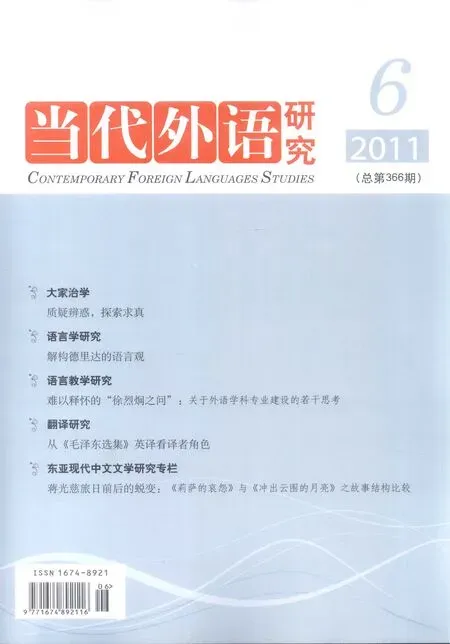韩国诗人李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兼谈李陆史与鲁迅
洪昔杓
(梨花女子大学,[韩国]首尔)
韩国诗人李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
——兼谈李陆史与鲁迅
洪昔杓
(梨花女子大学,[韩国]首尔)
本文从韩国诗人李陆史留学中国并介绍中国现代文学、与鲁迅晤面及进行“文学实践”、以及对徐志摩诗的翻译和认识这三个方面探讨李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李陆史的文学创作受到鲁迅和徐志摩的影响,但同时又克服其中的局限性,在鲁迅“文学实践”观点的指引下,他追求文学艺术性和思想性的完美统一,是韩国民族抵抗诗人的代表。他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反映了内心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对朝鲜文化和东方传统的热爱。
李陆史,民族抵抗诗人,自我意识,朝鲜传统,东方根基,鲁迅
1.留学中国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介绍
李陆史(1904-1944,以下简称“陆史”)与万海韩龙云和尹东柱一起,被称为韩国代表性的民族抵抗诗人。陆史以作品《青葡萄》闻名于世,代表作包括《绝顶》与《旷野》。他在韩国被视为歌颂民族意识的抵抗诗人的典范。他生前未曾出版一本诗集,但死后留存下几十部诗作。其跌宕起伏的一生给人至深的感受。
1924年,陆史曾到日本短期留学九个月,①1925年 1月回到韩国。回国后开始以大邱的朝阳会馆为中心参与社会文化运动,年末加入独立运动团体,此后经常往来于中国。1932年 10月到次年 4月,他在南京近郊的“朝鲜革命朝军校”(以下简称“朝军校”)接受了为期六个月的教育。“朝军校”结业后他在上海逗留,因而得以在 1933年 6月与鲁迅面晤。留学中国成为他人生的重要契机,使他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在以后的活动中与中国结下了深厚机缘。
陆史对中国现代文学和东方的文化传统怀着满腔热忱。曾编撰《李陆史全集》的金东在评价陆史的诗作时认为他大大扩展了诗的空间,为韩国现代诗歌的空间意识开拓出独特境界。而究其原因,或许就在于“他经常来往于中国广阔的大陆之间,这样的空间概念比较熟悉,而且其成就源自根植于其诗歌内部的中国文学的基础”(金东 1992:242)。陆史精通东方文化传统,更有着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刻了解。鲁迅逝世后的第四天,他写出《鲁迅追悼文》,在《朝鲜日报》(1936年 10月 23、24、25、27日)上连载。同年 12月翻译了鲁迅的短篇小说《故乡》,刊登于《朝光》杂志上。1941年他翻译了胡适的学术著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 1至 4章,并以《中国文学五十年史》为题,刊登于杂志《文章》(1941年 1月、4月)上。另外,他撰文介绍中国白话新诗和诗人,翻译了徐志摩的诗歌《拜献》和《再别康桥》,写出带有批评性质的《中国现代诗的一个层面》,刊登于《春秋》(1941年 6月)上。他还翻译过活动于中国长春的作家古丁的短篇小说《小巷》,刊登于杂志《朝光》(1941年 6月)上。②因参与独立运动,陆史曾多次遭到拘捕,在恶劣的条件下其活动范围受到极大限制。尽管如此,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介绍和批评始终不曾间断。
2.与鲁迅晤面及进行“文学实践”
陆史具有与鲁迅相近的精神和创作特征。他的作品表现了“即便是怜悯和同情也可以完全并永远拒绝的悲剧的‘英雄’命运”(李陆史:1986)。③他在现实生活中也拒绝怜悯和同情,没有丝毫的妥协,不断向前进。他的短篇小说《黄叶笺》写“幽灵”,梦中登场的人“紧咬牙关,全力以赴向前迈进”;梦醒时,“幽灵”在“一片漆黑之中,在像是永远寒冷,永远无法放亮的夜晚,独自一人行走”(101-2),这不由让人联想到鲁迅《野草》中的“过客”。
陆史在与鲁迅见面之前,就对鲁迅有所耳闻。1926年秋至 1927年春,他在北京大学学习。鲁迅在1925年 9月至 1926年 5月底 (陆史入学之前的学期)期间曾有两个学期以兼职教授的身份在北京大学执教(参见《鲁迅年谱》1983:246)。在北大就学期间,陆史得到了当时在东京攻读文学、后来北大教授文学课的“Y教授”的指导 (156-7),由此知晓中国文坛的情况和鲁迅。
1933年 6月 20日陆史和鲁迅相会于上海。他与“编辑员小 R”一起,在上海万国殡仪社吊唁被国民党蓝衣社杀害的杨杏佛时,偶遇鲁迅。他曾对当时的情形作了如下回顾:
那时鲁迅从小 R处得知我是朝鲜青年,且总想找机会见上一面,在外国前辈面前和特定的场所我只有谨慎和谦逊,而他再次握住我的手,那时的他是一个非常熟悉而且又和蔼亲切的朋友。啊!当接到他以 56岁结束短暂的一生,在上海施高塔 9号永逝的讣告时,黯然抹去一行热泪者,又岂只作为朝鲜人中的一名后辈而执笔撰文的我一人呢?(209-10)④
陆史在与鲁迅相会的这段时间,正在创作长篇小说《无花果》。此时见到享有盛名的鲁迅,对陆史来说,意义非同一般:鲁迅作品成为他创作的一面可借鉴的镜子,是其“文学实践”的理想典范。这使他把文学创作与民族独立运动结合起来,完成了相互一致的社会实践。鲁迅以“幻灯事件”为契机,由医学转为文学,走上了文学启蒙之路。这使陆史认识到,文学活动是宣传独立思想的重要方式。他在随笔《季节的五行》中说:“不过对我来说,只有行动的连续。因为行动不是言语,对于我而言,想写诗也是行动”(162)。他是这样评价鲁迅的:“鲁迅的小说非公式化,而且没有丝毫不合道理之处,这不能不说明其作为作家的手法非常之高明”(213)。在艺术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对鲁迅而言,艺术不是政治的奴隶,至少在艺术作为政治先驱者的同时,既不混为一体,也不对立。再优秀的作品都只有在创作成进步作品时,才会提升鲁迅作为文豪的地位”(216)。
1939年 5月,陆史发表影评《艺术形式的变迁和电影的集团性》,集中体现了鲁迅文学观对他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他回应了有人就艺术形式上的问题提出来的批评,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创作出优秀的作品,然后问题才会自行解决”(230),而且,较之于理论方面的主张,更重要的是作品的创作。同时,他又针对否定个人主义、追求集团意识、片面强调宣传的重要而否定电影的艺术性的倾向提出,“如果确实是想制作伟大的艺术电影、有良心的电影时,那这些只不过是杞人忧天的事”(241),即“电影文学应不受束缚,应在艺术上予以独立”(242)。他不仅作出这样的批评,自己在创作上也是这样。“即使尝尽各种孤独和悲哀,也将写出‘一首不以此为羞的诗歌’视为最重要”。“我培养自己的气魄,宁愿写出自己发自金刚心的诗歌”(161)。他认为艺术创作的本质就是重大的社会实践,以此追求艺术创作上的完美。这些都体现出他承续了鲁迅的艺术创作理念。
3.对徐志摩诗歌的翻译与批评
在中国现代诗人中,陆史最重视徐志摩的诗歌,曾经翻译并批评过徐的诗歌。他撰文介绍中国现代诗歌,说“如果问中国现代诗歌创作中哪位诗人更重要,那不论怎么说,也不可否认将诗写到接近完美程度的徐志摩。”除了翻译徐志摩的两首诗——《拜献》和《再别康桥》,他更是从诗歌形式上评价徐志摩诗歌,说“他在中国现代诗坛上所留下的业绩,与内容方面相比,在形式和技巧方面更多,在用韵和诗体形式上创造了新规律。仅这一贡献,从中国诗坛整体来看,确实不能不说是历史性的贡献”(270)。同时,陆史也批评了徐志摩诗歌思想方面的不足,认为:“从思想方面来看,他最终无法摆脱作为幽闲诗人的局限,这是他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使然,他没有直面社会现实,无法迈开一步,而是幽禁于自己个人主义的孤城之中”(同上)。
作为诗人,陆史在诗歌创作上既追求徐志摩诗歌那种艺术形式和技巧上的完美,又克服其思想性上的局限,创作出思想性与形象性兼备的优秀作品(沈元燮 1986:405)。广为人知的《绝顶》和《旷野》是他的两首绝唱。这使我们想到鲁迅,鲁迅曾经辛辣讽刺徐志摩诗论只强调诗歌的“音乐性”。徐志摩曾说:“我深信宇宙的底质,人生的底质,一切有形的事物与无形的思想的底质——只是音乐,绝妙的音乐。天上的星,水里泅的乳白鸭,树林里冒的烟,朋友的信,战场上的炮,坟堆里的鬼,巷口那个石子,我昨夜的梦,……无一不是音乐”(徐志摩 1924:6)。把所有的东西都以“音乐”加以理解的徐志摩,借用庄周的话,就是把诗歌的音乐性看成是和“天籁、地籁、人籁”一样的东西,反映了徐志摩非常重视诗歌的韵律这一要素。但在鲁迅 (1924:4)看来,徐志摩的这种说法导致了神秘主义,认为这“大概也不过自欺之谈,还要用粗皮来粉饰的妄想”,并且反问:“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在那里!?”。可见,渴望“怪鸱的真的恶声”的鲁迅的立场和想感知“天籁、地籁、人籁”的徐志摩的立场是明显不同的。
如果说徐志摩的“天籁、地籁、人籁”为陆史追求诗歌艺术性完美作了指引,那么鲁迅渴望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则可以说为陆史的诗歌作了思想性指引。可与此相印证的是,1937年,陆史写出随笔《嫉妒的叛军城》,说“别人肯定的不是我所肯定的”,“我所否定的我就继续否定下去”。他对自己的经历作了如下比喻:“在台风呼啸之夜整个世界犹如创世纪的初夜一般,黑暗天动地摇,雷电交加,大雨倾盆,穿过旷野,奋力跑向海边。在满是荆棘的藤蔓上,磕磕绊绊,像要绊倒,又像要摔倒,文学之路似乎与此类似,手中举着的电灯如我的良心一般,只能照亮我的脚下”(137)。这反映了他所处的苦难现实,同时也反映出他对文学的态度。如果说“在满是荆棘的藤蔓上,磕磕绊绊,像要绊倒,又像要摔倒”的是他的“文学之路”,那么,文学不能脱离苦难的现实独立存在,具有“只能照亮我的脚下”的局限性,决心写“一首不以此为羞的诗歌”的陆史,当然不会像徐志摩那样,仅仅停留在对艺术完美的追求上。他的诗歌创作更像鲁迅那样,是一种执着的人生追求。因此,对于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殖民统治下的独立斗争和抵抗精神的《绝顶》这首诗,金东 (1986:223)评价说,从中可以看到“民族主义的抵抗精神和纯粹诗歌底蕴互相融合,诗歌的纯粹性使时代和时局的现实通过艺术得以升华结晶”。
4.“自我意识”与“朝鲜传统”及“东方根基”
1937年鲁迅去世后,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在上海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其后附录了日本各杂志和报纸刊登的哀悼文,其中收入张赫宙《独特的作风》一文。该文刊登于日本杂志《文学案内》。而 1932年陆史作为《朝鲜日报》社记者曾经采访过张赫宙,并发表了《新作家张赫宙君访问记》。当时陆史对包括《饿鬼道》在内的张赫宙作品很有共鸣,可以说在精神上存在某种共同点。此后不久,陆史辞去报社的工作,来到了中国,后进入“朝军校”,毕业后在上海逗留,见到鲁迅。张赫宙后来则经常往来于日本,和日本作家展开交流。1936年 10月 19日鲁迅去世时,俩人分别发表了哀悼鲁迅的文章。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张赫宙到日本后思想逐渐发生了与陆史不同的变化。以他们各自写鲁迅追悼文的 1936年为界,其后,留学中国并来往于中国的陆史继续参与独立运动,努力创作抵抗诗歌;相反,来往于日本并逗留在日本的张赫宙逐渐写了一些支持日本殖民政策的作品。俩人在精神上产生了无法填补的隔阂,原因之一在于作家个人对民族使命感的觉悟不同;另一重要原因则与他俩这个时期留学或来往的活动空间(中国和日本)不同直接相关。
当时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韩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活动萎缩到极点。在这样的情况下,确立“自我意识”是最为重要的。陆史认为,所有知识分子“都在顺从和模仿”,质疑“何处可看到人高昂的气概”,认为“没有比意识到自我更为强大的”(342)。“自我意识”的确立和强调“金刚心”这一精神态度相同。在《乔木》中他用诗的语言作了意味深长的表达:“像要触及蔚蓝的天空/在岁月中燃烧仍挺拔伫立在此/倒不如春天不要开花//陈旧的蜘蛛网到处遍布/没有尽头的梦之路上/独自激动的心情毫无悔悟//黑色的影子冷森森的/最终深深地栽入湖水中/即便风也无法摇动”(34)。该诗显示了他丝毫不为现实压迫所动摇的坚定信念和精神境界。
陆史的“自我意识”即所谓“金刚心”,这种精神和态度源自何处呢?尽管接受了现代教育,但幼年时代所接受的儒家传统教育在他的意识深处扎下了根,这对他的“自我意识”确立产生了极大影响。他这样讲述自己“非常幸福的童年”(174):“十五岁时学习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骄傲自大,不免从别人的口中听到‘骄童’这样的嘲?”(150),“合上念完的外集,在煤油灯下又开始念起经书来……长长秋夜和书籍较劲,夜深人静到了凌晨 1点,打开窗户,空中飘下薄霜,簸箕星刚穿过银河,远处隐隐出来佛晓鸡鸣”(173)。“朝鲜的传统”和“东方的根基”在他的心里深深扎下了根,成为培养他“自我意识”的精神基础。1941年陆史去庆州疗养时,对那片土地表现出强烈的自豪感。他说:“不曾扔掉一草一木和一土一石,但站在临海殿只剩基石的旧遗址,秋日夕阳下头发随风飘动,朝向东南俯瞰瞻星台,难道没有听到不是发自雅典的圆柱和罗马的圆形剧场,而是发自东方朱栏画阁的古时金带玉佩的琤琤声吗?而对我的精神产生影响的自豪感不正是源于那儿吗”(197)?
陆史的精神骄傲,来自对“朝鲜的传统”和“东方的根基”无限自豪感。他主张朝鲜文化应成为世界文化的“一环”。虽然朝鲜文化未曾经历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般的过渡期,可他认为朝鲜也一直拥有某种形式的文化。他热爱这文化,这份热爱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我们的精神文化的传统中,不管是何形式,有着这样的东西[指的是知性―引用者 ],尽管努力区别西方和东方思想,但现在我们的头脑中不可能有纯粹的东方的东西,在此无需赘言。知性问题在我们悠久的精神文化的传统中有其基础,我们吸收的新精神也有其凝炼,当然重视其问题。换而言之,经历文艺复兴的欧洲文化现在也不仅仅是欧洲的文化,因此他们的精神危机也不能只看作是他们的危机。(344)
陆史明确提出应该从“我们精神文化的传统中”挖掘有用的文化资源这一观点。他准确意识到纯血统的文化是不可能存在于当代现实中的。这种对东西文化的开放态度反而更易于让人觉悟到有必要从“朝鲜的传统”和“东方的根基”中挖掘文化资源。因此,陆史在不拒绝欧洲文化的同时,尝试从“朝鲜的传统”和“东方的根基”中摸索知性的发现。也就是说从“我们的精神文化的传统中”找到“自我意识”的精神依据。
1937年,陆史发表了采访韩国舞蹈家朴外仙女士的访谈文章,其中他借朴女士之口隐隐透露了意味深长的观点:朴外仙女士说“不能说我穿了‘意大利’服装就是在跳意大利舞蹈,或者穿了‘俄罗斯’的服装就一下子说是在跳‘俄罗斯’的舞蹈”(352)。融入现代感觉的朴素的朝鲜古典舞蹈成为新兴艺术,仍然是朝鲜文化精神和传统的具体体现。
在确立“自我意识”的过程中,以“朝鲜的传统”和“东方的根基”为基础,陆史对具有“亚洲”共同的文化传统空间的“中国”感到亲近,也理所当然。他结束为期仅 9个月的日本留学生活,另外选择中国之行,是与这一亲缘性息息相关的。如果说他当时留学日本隐约包含了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憧憬,那么他留学中国就应是以充分信任“朝鲜的传统”和“东方的根基”为前提的。
附注:
①关于陆史在日本的留学,根据日本警察的问讯记录,他曾在东京正则预备校和日本大学文科专门部学习,另外还到东京神田区的锦城高等预备学校学习一年 (参见金喜坤2000:61)。
②陆史还发表过几篇和中国现实有关的时事评论:《五中全会前的外分内裂的中国政情》(《新朝鮮》1934年 9月)、《面临危机的中国政局的展望》(《开辟》1935年 1月)、《中国青帮秘史小考》(《开辟》1935年 3月)和《中国农村的现状》(《新东亞》1936年 8月)等。
③本段引文出自《李陆史全集》第 109页 (《山寺记》)。下引本书只注页码。
④李陆史《鲁迅追悼文》一文首发于 1936年 10月 23日的《朝鮮日報》上,后收录进《李陆史全集》。
金喜坤.2000.新写的李陆史评传[M].知永社.
李陆史.1986.李陆史全集[M].首尔:新文社.
鲁迅.1924.“音乐”?[J].语丝 (5):4-6.
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1983.鲁迅年谱 (第二卷)[S].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沈元燮.1986.李陆史的徐志摩诗歌接受方式[A].原本李陆史全集[C].首尔:集文堂.369-407.
徐志摩.1924.死尸[J].语丝 (3):5-7.
The Korean PoetLee Yook-Sa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y HONG Seukpyo,
I106
A
1674-8921-(2011)06-0049-04
洪昔杓,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电子邮箱:lxhong88@hotm ail.com
(责任编辑 林玉珍)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et Lee Yook-sa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hree aspects:Lee’s studying in China and introducing Chinese literature into Korea;Lee’s meeting with Lu Xun and conducting“literature practice”,and Lee’s translating and commenting on Xu Zhimo’s poems.Though greatly influenced by Lu and Xu,Lee surpassed their limitations and,under the guidance of Lu Xun’s“literature practice”,pursued the harmonious unity of art and mind.Being representative of Korea’s National Resistance poets,he created many excellentworks to reflect his strong self-consciousness and his deep love toward Korean and Oriental cult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