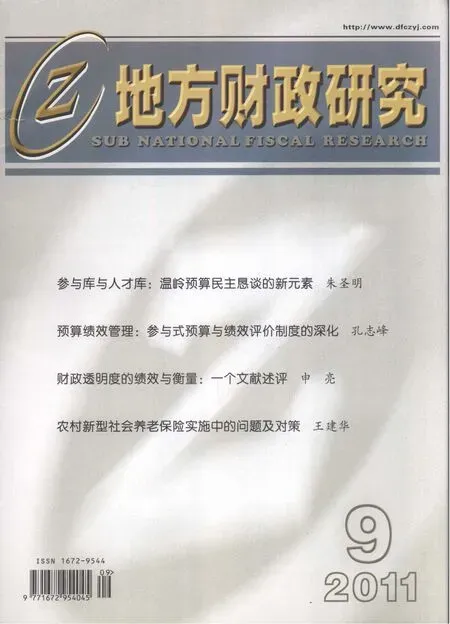财政透明度的绩效与衡量:一个文献述评
申 亮
(山东经济学院,济南 250014)
财政制度的结构和组织安排影响了财政结果。在经济分析和制度分析中,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游戏规则”对政府决策性质的影响,人们确定了游戏规则,同时也隐含地确定了游戏的结果。因此,从财政制度性质的角度看,大部分财政改革都致力于改变“游戏规则”,从而降低系统产生不良财政结果的可能性。
财政透明度是良好财政管理的一个方面,但财政透明本身不是目的,它是促进效率,保障政府和官员担起应负责任的一种方法。欧盟国家首先对财政透明度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将其作为加强财政管理的首要目标。一些经济转型国家,如东欧各国,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贫困问题,公众和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将解决此问题的希望寄托于预算改革,促使政府增加财政透明度和民主参与度。IMF和OECD进一步地制定了财政透明度的最佳做法准则,以此为各国的财政透明度实践做指导。
对财政透明度的绩效的研究是推动财政透明度的动力,对一国财政透明度的衡量则揭示了本国财政透明度的现状和努力的方向和力度。这些对于处于财政透明度较低程度的发展国家有着一定的意义。
一、财政透明度的绩效解释
财政透明度可以帮助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对国民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一方面,透明度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增强了公民影响预算决策的可能性,使得政府为实现职能所需的公共支出、为保证支出所需要征收的收入都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民的共同意志;另一方面,对政府来说,实现透明度不仅方便了公民偏好表露的过程,使得政府决策更贴近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而且也有助于公众理解政府决策,减少政策推行阻力。因此,财政透明度的增强可以促使政府担负起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从而减少各类寻租行为及其造成的巨额内生交易费用。
(一)改善商业环境,降低经济发展成本
Drabek(2001)的研究表明财政透明度的提高,可以提高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Chortarea(2002)发现公开较多宏观经济数据的那些国家通货膨胀率较低。Glennerster(2003)的研究证明新兴市场国家在遵循了国际标准后,主权风险溢价显著地减少。Andritzky(2007)发现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和数据的发布效果减少了不确定性,且有助于稳定传播。Bellver和Kaufmann(2005)进一步对20个国家进行调研,结果表明:透明度与国家的腐败程度低、宏观经济和人类发展指数高、经济竞争力强有关系。Glennerster和Shin(2008)的研究表明,财政透明度高与国家经济境况改观存在某种关系,国债市场借贷成本低就体现了这一点。
(二)提高了政府公信力,改善公共治理
Ferejohn(1999)认为财政透明度的增加提高了选民对在任政治家的信任或有助于选民有能力分辨结果的好坏,使得政治行为的不确定性减少了,政府的行为更规范,这又会使选民愿意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在公共部门。Brautigam(2004)的研究回顾了若干国家的公众参与性预算编制,发现提高财政透明度高是公民参与预算的必要条件。此外,她还注意到,只有随着其他条件的成熟,例如民间社团和执政党及知情媒体制订明确的扶贫日程,透明度对贫穷人群的影响才会出现。Islam(2003)根据世行对169个国家收集到的总体数据研究发现,透明度(包括《信息自由法》的出台以及政府部门更频繁地公布经济数据)与政府治理的优劣存在很大关联。
(三)加强财经纪律,减少财政风险
财政透明度是个复杂的问题,不仅仅包括信息公开,而且还包括对预算中存在问题的揭露,从而迫使政府更负责。因此,直观的认为更高的透明度能够更容易控制政府支出和使政府遵守财经纪律,从而带来较低的预算赤字,降低财政风险。Von Hagen和Harder(1994)对欧盟的研究以及Alesina(1999)对拉丁美洲的研究发现了很强的联系证据,财政透明度能够产生更强的财政纪律。在James Alt和David Lassen(2006)的一项研究中,他们给19个经合组织国家建立了一个关于财政透明度的指数,他们将许多财政表现指标与财政透明度指数一起测试,发现在保持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更好的财政透明度和低的公共债务以及低的赤字相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Hameed(2005)的研究发现,通过调控社会经济因素,透明度高的国家一般都能更好地接触国际金融市场,更严格地遵守财政纪律Gelos和Wei(2005)的研究对财政透明度减少风险的作用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他们的研究表明国际资金乐于在更透明的国家持有更多的资产。
(四)规范政府行为,抑制腐败活动
一般来说,反腐败主要依靠健全的法律和财政制度以及公民社会的改革,通过增强政府部门的责任感来实施的,但是财政透明度也有明显的方式去影响腐败。更高的责任感和更富效率的审计减少了某些腐败的机会,如果政府公布了预算计划和预算执行报告,政府外部的信息使用者、公民社会和政策分析家能够容易促进执行机关的责任性,加强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能够减少公共资金的滥用。尤其在法律不完善的国家,透明度对反腐败有着更重要的意义。
在许多经济不发达和腐败盛行的国家,法律和财政制度的约束力其实是很微弱的,因为它还需要有一套值得信赖的法律机制能够调查和执行现有的法律法规。财政规则和会计系统只能部分约束公共部门管理者和公务人员的自主权力,公共部门执行任务的复杂程度和相对于消费者的信息优势阻碍了抑制各种无效行为的法律和会计系统的设计。于是,那些不是很明显的管理不善的措施没有被发现。结果,审计报告和法律程序对外行很难解释,因此也常常被忽略。因此,Ritva Reinikka和Jakob Svensson(2004)认为反腐败的另外一个思路就是以公共服务的使用者为出发点,使公民能够容易得到关于公共服务提供的信息,而不是单单试图增加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感。于是,公民被授权对公共部门官员和公务人员的工作提出一定要求、监督和挑战他们的滥用职权的行为。在一个案例中,他们证实了这一观点。一项公共支出跟踪调查表明,20世纪90年代乌干达政府给学校拨款的每一美元中,学校只能得到20美分,其余80美分都被地方政府截获了。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中央政府没有仅仅致力于加强财政管理系统,而是自上而下发起了一场信息运动,通过每月在报纸上公布政府对学校的资金转移情况,增强学校和家长监督地方官员处置这部分资金的能力。效果很显著,“政府捕获”从1995年的80%减少到2001年不足20%。
上述研究表明一国财政透明度与财政业绩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透明度确实给国家的财经秩序带来了有效约束,这成为国际社会发展财政透明度的主要动力。既然游戏结果已经初现端倪,接下来重要的就是如何去制订游戏规则以及保护和完善游戏规则了。
二、财政透明度的衡量
(一)国际社会的努力
199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颁布的《财政透明度守则》包含了一系列指导原则,意图建立一个具有指导性意义、具有可操作性的财政政策透明度框架,它围绕着下列目标规定了每一种类的具体要求:(1)作用和责任的澄清;(2)公众获得信息的可能性;(3)预算编制、执行和报告的公开;(4)对真实性的保证。通过四个原则共描述了37种财政实践活动。IMF对各国发放财政透明度调查问卷,根据反馈结果编写《财政透明度标准与规范遵守报告》(ROSCs),考察被调查国家对守则要求符合的程度并对其财政透明度进行说明和指导。参加ROSCs是自愿的,并且成员有权决定是否公开本国的ROSCs。自IMF推广财政透明度ROSCs开始以来,86个国家完成了ROSCs,许多国家早期的ROSCs后来又更新过多次。IMF计划每年制作18-20个财政透明度ROSCs,目标是最终覆盖所有的成员国。目前,ROSCs的参加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IMF的财政透明度评估本质上是定性的,考虑到存在误导的可能,IMF执行委员会明确表示基金组织不会提供定量评估或者给国家的透明度情况评级。但是IMF的一项调查表明(MurrayPetrie,2002),许多私营部门强烈要求财政透明度ROSCs包含财政透明度的定量评级。IMF的努力旨在为各国的财政透明度继承提供指导,它的局限性在于没有表明不同层次的透明度和责任性,这给国际社会扩展其框架创造了机会。尽管如此,它创立的《财政透明度守则》以及《财政透明度标准与规范遵守报告》依然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透明度评价标准。
此外,世界银行、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欧盟等组织也都对财政透明度做出了各自的规定,有的甚至成为成员国资格的要求,为促进国际社会财政透明度进程提供了一个良好平台。
(二)公民社会的参与
在促进财政透明度过程中,公民社会的作用相对被较少关注,但它却显示出了长期的对更有效、更负责的财政管理提供一个稳定机制的巨大潜力。1997年,美国华盛顿特区的非政府组织CBPP组建了国际预算规划(IBP),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新兴民主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和研究者分析预算政策和提高预算程序以及预算机构的效率。1999年IBP同南非的民主机构(Idasa)合作对南非的预算透明度和参与性进行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吸收了IMF的透明度准则,同时把公众的参与程度作为一个核心要素来考察,提出了一个透明度三级评定标准(弱、中、优)。2001年12月,拉美五个团体分别公布了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和秘鲁的预算透明度研究结果,研究采用了专家对各国财政管理法律框架的评估作为评级准则,以及采用立法者、公民社会和其他预算信息的主要使用者对预算透明度的感受构建预算透明度指数。
这些公民社会组织的透明度研究已经达到了准国家标准,尽管他们的预算透明度研究和IMF的财政透明度准则有一些冲突,但IMF的《财政透明度准则和标准遵守情况报告》(ROSCs)已成为共同研究的资源。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目的是发展一种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具有可比性的财政透明度衡量方法,由此去促进国际范围内的政府责任和社会正义。
(三)财政透明度指标体系的设计
最早制作出各种与财政透明程度相关的指标、并综合分析其对财政绩效影响的是Von Hagen和Jürgen(1992)。他们的分析对象是欧盟国家(8国),所制作的指标主要是反映“会计透明度”①Kopits和Craig(1998)认为在“会计透明度”方面,重要的是向公众详细披露有关财务信息,包括各个政府部门的明细报表、部门之间的资金往来等。。指标具体内容有:(1)预算报告中是否明示了特别会计;(2)预算报告是否汇总为一个报告;(3)对于财政透明度的自我评价;(4)预算报告与国民经济统计是否有联系;(5)预算报告中是否明确写出了政府向非政府部门的贷款。
这部分研究的策略是首先确定每个相关变量的模型,然后加入透明度指数来测试是否透明度与这些变量相关。实证部分基本上局限于横截面分析,因为财政透明度指数短期内没有时间变化,如欧盟候选国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已经历了许多重大变化,因此,任何面板分析不得不局限于过去几年内的状况。这确实排除了一些有意义的分析,如果每个国家的透明度每几年重新评估一次的话,那么做财政透明度的变化分析就是可行的。他们的测算结果显示,德国是其中透明度最高的国家,意大利和爱尔兰则是透明度最低的国家。这个结论和各国债务比率等财务绩效情况基本一致。DeHaan et al.(1999)对该指数进行了一些更新。
Alesina,Hausmann,Hommes和 Stein(1999)也分析过拉丁美洲各国财政制度和程度同财政绩效之间的联系,他们所采用的透明度指标是中央政府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债务关系、地方及公共企业的财政独立程度等,只涉及到了“会计透明度”的一部分。
Alt和 Lassen(2006)将着眼点放在“制度透明度”和“指标与预测的透明度”②Kopits和Craig(1998)认为政府不仅要公布与财政平衡相关的若干指标以及政府总负债和净负债等与财政相关的指标,而且还应公布对一些财政分析性指标的测算。上,全方位地对OECD国家的财政透明度情况进行了分析。分析使用了OECD的19个国家1999年对OECD成员国预算中心调查问卷的报告。这次调查包括76项,大多数的调查问题与透明度无关,在相关的大约15个变量中,他们选择了其中的10项能够对国家之间的财政透明度情况提供有说服力的指导。其中的9个变量属于OECD预算透明度最佳做法的内容(OECD,2001)。同其他研究的措施相比,这次调查的数据优点是与透明度直接相关且具有综合性。但该调查结果也存在着两个缺点:(1)报告是自我报告,一些国家可能对自己评估过高。(2)问题集中在正式规则和程序上,这或许同实际不符。但调查者认为这些数据抓住了财政透明度的主要特点,具有一定说服力。10项指标中再加上是否使用应计制会计来准备财政声明共11项指标,构成了一个简单的财政透明度指数。指数包括:
●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较少的文件能够包括较多的信息
○是否有非财政成果数据包含在提交给议会的预算文献中(是=透明)
○在选举之前是否有财政情况的专门报告(是=透明)
○政府是否制订长期财政前景的报告(10-40年)(是=透明)
○政府是否被要求报告或有负债(是=透明)
○在每个财政年度上,政府是否提出不止一个补充预算文件给议会(不是=透明)
●独立核实
○年度财政报告是否被审计(是=透明)
○预算中的经济假设是否服从独立的观点(是=透明)
●用词严谨
○在财政声明中,政府是否使用应计制会计(是=透明)
●更多理由
○是否有法律要求,预算文件中包括两年或两年以上的支出计划(是=透明)
○是否有法律要求预算中要包括计划支出和实际支出的事后比较(是=透明)
○预算是否讨论了关键经济假设的变化对预算结果的影响(是=透明)
指标赋值:回答“是”得1分,回答“否”得零分。
总结1999年政府债务和财政透明度的关系,研究者把这些国家分为财政透明度高、中、低三档国家。在低透明度国家,透明指数≤3,1999年总债务占GDP的72.2%;在中等透明度国家,透明指数=4,债务总额占GDP的66.4%;透明度高的国家,透明指数>4,债务总额占GDP 51.8%。表明透明度较高的国家有着较低的债务水平,尽管高额债务在透明度高的国家继续存在。这个结论与Von Hagen(1992)等的结论比起来存在一些偏差,如德国的透明度评价过低,而意大利得分较高等。但是,在其对不同国家的横截面数据分析中,显示出透明度指标高的国家债务少、而且财政支出也少,这是非常有意义的。Campos和Pradhan(1999)对于新西兰透明度的报告、Wright(1999)提供的关于日本模糊而复杂的预算报告的详细评论则肯定了这个指数的评级。
Farhan Haneed(2005)根据《财政透明度守则》要求构建了财政透明度指数,包括数据可信度、中期预算编制、预算执行报告,财政风险披露四个方面。指标的选择基于三个主要考虑:第一、早期财政透明度文献,第二、信息内容/分类,第三、信息容易处理。在这个指数中,数据的质量和财政风险被赋予了很重要的意义。即使一个政府公布了重要的财政信息,因为数据质量差或表达不够清晰仍然有可能认为它是不透明的。而有多种来源的、能够影响财政状况的财政风险,或者会增加政府责任、或者会减少公共资源,要求政府按照风险来源来披露财政风险能够更加准确地描述财政全貌,减少不确定性增加政府的可信度。
随着对财政透明度研究兴趣的增长,一些组织如国际预算规划(IBP)和牛津研究所也开始研究财政透明度指数。IBP(2004)在研究预算公开过程中,在对其附属组织的详细调查的基础上发展了不同的指数,包括执行预算文件的有效性指数(BUDDOC),监督与评估预算报告的有效性指数(MONEVL)。在指标的选择中,IBP与ROSCs有21处重叠。牛津研究所(2003)研究了财政透明度指数,并作为加利福尼亚公务员退休系统(CAIPERS)报告的一部分。牛津研究所的许多观测值都是基于财政透明度ROSCs,因此,这两个指数之间也有着高度的相关性。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对我国的财政透明度进行了跟踪研究。他们选择各省本级财政的前三年决算数据作为调查对象,按照最低的透明度要求设计了113项信息指标来考察各省财政信息的公开程度。信息指标从流量和存量两个方面考察了政府基金、社会保障基金和公共企业基金的透明度情况。113项指标每项赋值10分,再加上向各省信息公开机构申请信息时各机构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责任心赋值50分,得到各省财政透明度的综合评分。该项指标重在测度信息的可得性,信息的及时性、可靠性和易理解性并未考虑,应该说是一个初级的财政透明度指标评价体系,具有明显的针对性。
三、评述及展望
显然,对推动财政透明度进程来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发达国家主要是希望通过增强财政透明度来化解财政风险,重点在于对信息披露的技术设计,这是在制度上保证公众知情权的基础上,对财政信息披露的进一步要求。发展中国家由于在保障公众知情权上尚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因此,推动财政透明度的意义更主要在于规范政府行为,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对制度上的设计尤为重要。
出于这种考虑,对不同的国家应该采用不同的透明度衡量标准,IMF设计的良好行为准则只是强调其导向性,而不是一项衡量的标准就是普遍可接受的了。回到文章的开头,我们再次强调透明度本身并不是目的,通过增强财政透明度,能够使真正使政府承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才是最需要的。这就要求技术设计和制度安排结合起来形成对透明度指标体系的要求,显然,这必须是因地制宜的,而不能是一种硬性的要求。但是,既然是对透明度的衡量,还应该是有一定的基本标准和发展方向的。一般可从信息披露的可得性,信息披露的范围、内容、具体化程度和可理解程度来衡量。Kopits和Craig(1998)对财政透明度的初始定义是“向公众最大限度地公开关于政府结构和职能、财政政策意向、公共部门帐户和财政预测的信息”。从该定义上看,衡量财政透明度的最直接有效的依据应该是公众可获得的财政信息。然后是信息的范围、内容、具体化程度和可理解程度。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信息的可得性成为目前主要的衡量标准,然后才在技术标准上逐步深入。而发达国家在可得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向信息的具体化和可理解性发展,让公众通过所得的信息能够对政府的行为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从财政透明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来看,信息披露的具体化和可理解性将成为衡量透明度的关键,也是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1〕 Drabek,Zdenek,and Warren Payne,2001,“The Impact of Transparency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taff Working Paper ERAD-99-02.
〔2〕Chortareas,G.,D.Stasavage,and G.Sterne,2002,“Does It Pay to Be Transparent?International Evidence from Central Bank Forecasts,”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Review,Vol.84(July/August),pp.99-118.
〔3〕 Glennerster,Rachel and Yongseok Shin,2003,“Is Transparency Good for You and Can the IMF Help?,”IMF Working Paper 03/132.
〔4〕 Andritzky,J.R.,2007,“Capital Market Development in a Small Country:The Case of Slovenia,”IMF Working Papers 07/229,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5〕 Bellver,A.and Kaufman,D.2005,Transparenting Transparency:Initial Empirics and Policy Applications,World Bank,Washington DC.
〔6〕 Glennerster,R.,Shin,Y.2008,“Does Transparency Pay?”IMF Staff Papers Vol.55,No.1 193-209.
〔7〕Ferejohn,John.1999.“Accountability and Authority:Towards a Model of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in A.Przeworski,B.Manin and S.C.Stokes(eds.),Democracy,Accountability,and Representa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8〕 Br覿utigam,D.2004,“The People's Budget?Politics,Participation and Pro-poor Policy.”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22:653-668.
〔9〕 Islam,R,2003,“Do more transparent Governments govern better?”,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077,World Bank.
〔10〕von Hagen,Jürgen,and Ian Harden.1994.“National Budget Processes and Fiscal Performance.”European Economy-Reports and Studies No.3/1994,311-418.
〔11〕Alesina,Alberto,Ricardo Hausmann,Rudolf Hommes,and Ernesto Stein.1999.“BudgetInstitutions and Fiscal Performance in Latin America.”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9,233-253.
〔12〕Alt,J.E.,and D.D.Lassen,2006,“Fiscal Transparency,Political Parties,and Debt in OECD Countries,”European Economic Review,Vol.50(August),pp.1403-1439.
〔13〕Farhan Hameed,2005.“Fiscal Transparency and Economic Outcomes”,working paper wp/05/225.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D.
〔14〕Gelos,R.G.,and S.-J.Wei,2005,“Transparency and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Holdings,”Journal of Finance,Vol.60(December),pp.2987-3020.
〔15〕Reinikka,Ritva and Jakob Svensson,2004,“The Power of Information:Evidence from the Public Expenditure Tracking Survey,”in Global Corruption Report,2004.
〔16〕Murray Petrie,2002.“Institutions,Social Norms and Wellbeing,”Treasury Working Paper Series 02/12,New Zealand Treasury.
〔17〕von Hagen,Jürgen.1992.“Budgeting Procedures and Fiscal Performance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EEC Economic Papers 96.
〔18〕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10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省级财政信息与部门行政收支公开状况评估[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6.
〔19〕Kopits,George,and Jon Craig.1998.“Transparency in Government Operations,”IMF Occasional Paper 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