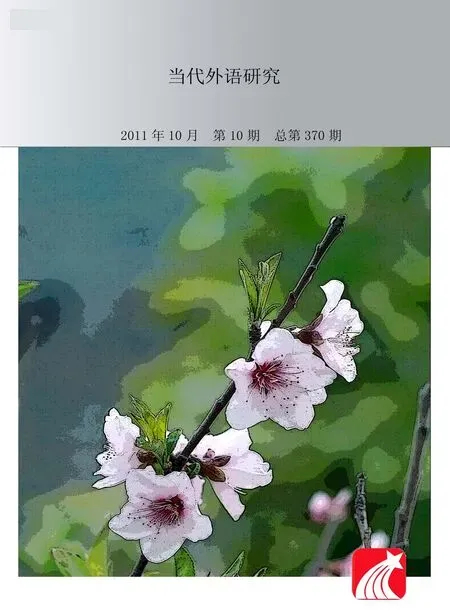以《黑王子》为例浅析艾丽丝·默多克的女性意识①
安 宁 袁广涛
(汕头大学,汕头,515063)
1.
对于女性问题,艾丽丝·默多克的态度比较明确。当被问及其小说作品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为何皆为男性时,她说:
我认为我对男人的认同多于对女人的认同。……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差别并不大。人人皆为人类的一员。我觉得我对男人比对女人更感兴趣。尽管我非常支持妇女解放,尤其是对妇女的教育,但是,对于通常意义上的女性问题我并不感兴趣。即使是对妇女的教育,也是要帮助她们加入到人类这个种群中来,而不是要为世界做出什么女性的贡献。如果说存在一种“人类的贡献”,我认同,但我并不认为有“女性的贡献”这回事(转引自Bellamy 1977:133)。
简单分析这段引文,我们不难看出默多克突出强调了两点:其一,她更认同男性,对男性更感兴趣;其二,她不强调男女之别,而更看重人类作为一个种群的境遇。这就构成了一对表层的矛盾:为何一方面淡化男女之别而另一方面又强调对男性的认同呢?结合另外两篇访谈,默多克对于女性问题的立场可以变得更为清晰。比如她曾表示,自己要呈现的是“人类的境况”(the human case),而非“男性的境况”或“女性的境况”(Ziegler & Bigbsy 1982:217)。但当被追问为何反复采用第一人称男性叙事视角时,她回答说自己要描摹的是这个世界,而我们生活在一个男人的世界。既然她要刻画的是整个“人类的境况”,就应该采用男性视角:“叙事者最好是男性,因为一个男性可以代表普通的人,而女人终归是女人。没办法,现实如此”(Bove 1992:191)。默多克进一步指出,采用男性叙事视角可以看作是她对现实生活中女性社会地位的一种评论。
依据上文所引的三篇访谈,默多克对女性问题的认识和态度皆是在回应为何多次采用第一人称男性叙事视角时流露出来的。对于女性作家采用男性叙事视角这一现象,传统的女性批评有两种不同的解读:要么认为女性作家以此为面具来博取男性世界的认可;要么认为她们通过模仿男性来试图颠覆其对话语权的控制。例如狄波拉·约翰逊(Deborah Johnson 1992)就试图结合罗兰·巴特的相关理论来解析默多克在多大程度上是在逃避身为女性作家的焦虑,又是在多大程度上戏仿和颠覆了男性话语权。谢丽尔·波夫(Cheryl Bove 1992)则从默多克的美学、性别以及政治等立场来分析她对男性叙事视角的情有独钟。然而,两者均未将默多克的女性意识置于其整个哲学体系中进行考量,从而未能合理定位其女性观点,并以此正确认识和解读其作品中刻画的大量女性人物形象。
2.
众所周知,艾丽丝·默多克不仅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还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当今享有盛誉的一些哲学家,如查理·泰勒和玛莎·努斯鲍姆就深受其影响。默多克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三篇作品中:《火与骄阳》(TheFireandtheSun1977)、《善的至上》(TheSovereigntyofGoodoverOtherConcepts1991)以及《反对干枯》(“Against Dryness” 1997)。从这三篇作品中可以梳理出代表默多克思想的若干核心概念,包括人类人格(human personality)、现实、自然、艺术、道德、爱、善等等;贯穿这些概念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去我”(unselfing)。这一系列观点的提出与彰显有它们深刻的社会和时代背景。在默多克看来,经过几个世纪科学与工业的发展,人的生存变得自私而无着(selfish and pointless)、日益与物质世界疏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康德的“理性的人”(rational man)。这个现代人自由、独立、强势而孤独,但他缺失的是人类曾经拥有的肥沃的道德土壤和让人得以超越自我的现实。默多克试图通过回归柏拉图来找到诊治现代人病痒的良药。
默多克称自己高举的是柏拉图的旗帜。从这位先贤身上,她受益最深的是其洞穴理论。默多克利用这个隐喻中包含的多个饱满意象来阐发和延拓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在默多克看来,现代的人类人格是自我封闭的、缺少目的的。她声称人性自私:
人的心灵是一个由历史决定的个体,它一刻不放松地关照着自己。……做白日梦是它最大的消遣之一。它不愿意面对让人不舒心的现实。通常情况下,它的意识不是一面可以观看世界的透明玻璃,而是一片或多或少充斥奇异幻想的云彩;这是一片用心设计让心灵免受伤痛的云彩。它一刻不停地寻求慰藉,要么是通过假想的自我膨胀,要么是通过编造神学性质的故事。即使是它对他人的爱也往往是一种对自我的坚持(Murdoch 1997c:363)。
不难看出,在默多克眼里,现代人被自我蒙蔽,无法透视、正视现实,正如洞穴里被链条锁住的囚徒。默多克认为,如果要像柏拉图理论中的囚徒那样摆脱自私的臆想,踏上追寻现实的朝圣之路,可以通过“美”这条途径。这里的美包括自然之美与艺术之美。一个内心苦闷的人,如果突然被窗外跳跃的小鸟吸引,就会不由得全神贯注地去关注这只小鸟,从而忘记了苦闷,整个身心完全被外在的事物(现实)吸引,达到了一时的忘我甚至是无我。好的艺术作品可以带给我们喜悦,可以使我们猛然惊醒,意识到从未留意过的自身以外的现实。另外,艺术、道德与爱实为一体。真正的爱是使人正视现实、完善自我的最好方式:
附加一定的条件,艺术与道德实为一。它们同质。它们共同的本质是爱。爱是对个体的感知。爱是一种极端困难的认识,认识到除自己之外还有别的东西是真的。爱,连同艺术和道德,是对现实的发现(Murdoch 1997a:215)。
在柏拉图那里,世间万物只是理念的翻版,无完美可言。但默多克认为,当人们用尽全力试图完美地去爱的时候,尽管所爱的并不完美,但人们仍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净化,从而变得无私而公正,进而接近了善。善是朝圣之路的终端,它如令人眩目的骄阳,烛显世间万物的关联,从而让人正确地定位自己、认识到自身与世间万物的联系,由此走出被自我蒙蔽的生存状态。
默多克认为,自己所处的时代与柏拉图的时代相似,都属于后宗教时代,缺少大一统的信仰和价值观。然而,人类的天性是要在破碎芜杂中寻找统一。作为一个哲学家,默多克更是致力于此。她努力找寻的结果是回归柏拉图的善。
3.
在“作者已死”的今天,真实作者的创作背景、思想体系、写作意图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尊重和考量呢?就艾丽丝·默多克的哲学思考与文学创作实践来看,评论家们的意见比较一致,大都认为她的小说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其哲学思想的实验或贯彻。笔者以为,我们要探讨默多克的女性意识,首先要看她的人性意识。在默多克看来,现代人的人性是自私的,他生活在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臆想中,拒绝直视也许会给人带来痛楚或不快的现实,从而丧失了实现自我超越的道德土壤。只有通过自然、艺术之美以及爱,人才能踏上通向善的朝圣之路。由此可见,默多克的哲学思考为现代人的自我救赎描绘了一幅愿景,而她的小说创作却展现了一幅深陷困境、无法自拔的众丑图。默多克秉承柏拉图的观点,反复批评劣等艺术的慰藉功能(to console)。她的小说创作致力于揭开现代人的伤疤和丑态,以期为世人提供一剂苦口良药。默多克对女性人物的刻画基于她对人性的认识,其作品中的众多女性人物只是芸芸众丑中的成员。从女性批评的立场出发,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众女性的丑陋是如何造成的?通过分析默多克的代表作《黑王子》②中的一位女性人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男人的世界”如何造成了女人以及男女之间生活的不幸。
《黑王子》的男性叙事者布拉德利·皮尔逊声称名为雷切尔·巴芬的女子是整个小说中重要甚至是主要的角色。从特定的角度来看,雷切尔的确是事件的核心:她的丈夫阿诺尔德·巴芬是名畅销书作家,与皮尔逊之间关系纠结,爱恨交织。雷切尔为了报复丈夫的不忠,勾引皮尔逊做自己的情人,而后者竟然爱上了她二十岁的女儿,这使得人物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情感矛盾更为激化,最终酿成一场悲剧:雷切尔杀死了自己的丈夫、陷害布拉德利入狱、并与自己的女儿断绝了往来。小说在一场流血的家庭冲突中拉开帷幕:巴芬用凿子打破了妻子的头,以为出了人命,叫来皮尔逊帮忙。风浪过后,皮尔逊与巴芬交谈,试图调和他们夫妻之间的矛盾。当被问到外面是否有女人时,巴芬嚷道:
你是说有外遇?不,当然没有。天哪,我是个模范丈夫。雷切尔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我对她一贯是实话实说。她知道,我没有什么风流韵事。哦,曾经有过,不过我告诉过她的,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为什么不可以间或谈谈她呢?要是她都成了一个禁止谈论的话题,那才是个大笑话呢。……而要是她同她的朋友谈论我的话,我是不在乎的。……她当然不会不跟人谈论的。她的朋友多得很,况且,她不是被关在家里的(cloistered)。……她很聪明(intelligent),要是她想干的话,原来也可以当个秘书什么的。可是,难道她真的想吗?当然不。……她做各种有趣的事情,担任了无数委员会的委员,竞选这竞选那的。她还认识各种各样的人物,包括议会的好多议员,这些人的来头比我大多了。她并不是个失意的(frustrated)人……(默多克2008:42)。
在这段话里,巴芬试图从三个方面为自己辩护:首先,尽管他对妻子不忠,但他事后都会坦诚地对妻子讲,这足以弥补他的过失;其次,他是跟别的女人谈论妻子,但当今的道德并没有禁止他这么做,而且,如果妻子谈论他的话,他也不会介意;最后,虽然没有工作,但雷切尔作为一个聪明的女人并没有浪费自己的才能,因为“她做各种有趣的事情”。简言之,雷切尔是个快乐的家庭主妇,生活平顺。巴芬这一席话表明没有什么能够真正约束他的言行:他只要做到坦诚(sincere),便万事大吉,这体现了现代人道德上的贫瘠。他对妻子的评价只是浮于表面,没有试图去了解妻子真实的生存处境。当巴芬坦言自己有外遇时,作为妻子的雷切尔到底有多痛苦,又经受了怎样的心理历程,小说并未详述。
借助多丽丝·莱辛《十九号房间》中女主人公苏珊·罗林的经历,我们或许可以窥见雷切尔的感受以及丈夫的不忠对她造成的影响;而苏珊与雷切尔的共同遭遇早在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1979)的《美狄亚》里就有了极为深刻的表现。
像雷切尔一样,苏珊很聪明(intelligent)。莱辛(1993:2301)是这样展开苏珊的故事的:“我想,这是一个有关‘理解力’(intelligence)的故事,一个‘理解力’如何失败的故事:罗林夫妇的婚姻是以‘理解力’为基础的。”由于整篇故事都建立在“intelligence”一词上,此词相应地引起了读者的重视。根据《新牛津辞典》的定义,“intelligence”是“获取和应用知识或技巧的能力”,体现的是一个人学习、理解和推理的能力。作为家庭主妇,苏珊和雷切尔能够获取和应用的知识和技能主要是作为家庭妇女的她们对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以及处理家庭事务的技巧和能力。做好这些,她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呢?“如果我们把一切都悉心打理好,/而我们的夫婿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轻轻忍受婚姻的羁绊,/生活就是可羡的了”(Euripides 1979:239-41)。然而,当一个人关照的只是些生活琐事时,生活难免会“有些平板、枯燥”(Lessing 1993:2302)。深陷这种琐碎的生活,苏珊急于寻找令人信服的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何放弃了工作,当起了家庭主妇:
他们对彼此的爱?哦,是的,这是最接近的答案了。如果这不是一切的中心,那什么是呢?是的,正是围绕着这一点——他们对彼此的爱——整个了不起的结构运行着。……就是为了这个东西,这个实体,一切才诞生了,一切才一下子从无到有,一切都是因为苏珊爱着马修,马修爱着苏珊。真是了不起。那么这就是一切的中心,一切的泉源了(同上)。
苏珊想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爱,她就能够忍受家庭主妇的枯燥生活了。然而,如果“爱情遭受了病害”(Euripides 1979:16),那情形将会如何呢?
有天晚上,马修回来得很晚,对苏珊忏悔说自己与别的女子有染。苏珊一下子被抛进了困惑痛苦的深渊,他们婚姻的基石——相互理解——骤然失效:
苏珊宽恕他了,当然。只是宽恕好像不是她要表达的意思。理解,是的。但是如果你理解一件事情,你就用不着宽恕了,因为如果理解了,你就是这件事本身了:只有不理解的东西才需要宽恕。即使是他已经忏悔了——哦,忏悔,这是个什么样的词呀?(Lessing 1993:2304)
这段简短的文字充满情感的张力,满是苏珊难以言表的困苦。对于丈夫的不忠,苏珊的反应本是由第三人称叙事者讲述的,但紧随其后的固定用语“当然(of course)”一下子把读者带入了苏珊的内心。该用语本是用来表述人的自信与心安的,而此处表现出的却是苏珊的困惑和不确定。它让人看到苏珊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情感,但实难做到。作为他们婚姻基石的“理解力”或“理性”告诉苏珊要理解、宽恕,但同时,难以抑制的内心感受让她痛苦不堪。在这里,作者对自由直接思想的运用逼真地刻画了苏珊内心的剧痛和说服自我的徒劳。苏珊的痛苦情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相同处境下的雷切尔经受了怎样的内心煎熬。
如果“爱情遭受了病害”或者妻子受到了“慢待”,后果将如何呢?难道男人真的可以通过坦言就可以逃脱其咎,而时间会医治伤痛?“你真的以为,爱情,对于一个女人,是个轻轻巧巧的痛”(Euripides 1979:1343)?美狄亚展示了一种可能的反应:背叛她的人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而此处,苏珊选择了另外一种表达方式:消沉。丈夫的不忠使他们婚姻的泉源变得枯竭,苏珊觉得“好像生活变作了荒漠,什么都不再重要,连她的孩子都好像不是自己的了”(Lessing 1993:2304)。当爱情变了质,生命变得空落落的,没有什么可以再把它填满时,苏珊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面对同样的背叛,雷切尔如何应对呢?她像敲碎一个蛋壳那样敲碎了丈夫的脑壳,用的正是一开始巴芬将她头打破的那把凿子。
如果雷切尔有工作,投入地工作可以减轻情感上对丈夫的依赖,又可以在经济上让她摆脱一段不再有爱的婚姻,同样的悲剧还会发生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考察在二十世纪中叶,父权制社会能为遭受丈夫背叛的中年妇女提供些什么。
4.
如巴芬所言,雷切尔的社交生活很活跃。然而,在二十世纪中叶的西方,妇女的社交生活在社会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通过参加社交活动,女人能够实现自我的价值吗?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给出了答案:
主要是女人那一方在指导这种社交生活。……夫妻是社会的人,他们取决于自己所归属的家庭、阶级、社交圈子以及种族,通过机械凝聚力的联结,依附于有相似社会处境的群体;妻子可以十分单纯的体现这种关系……妻子无职业要求,能够只交往和她地位相等的人们。况且,她有闲暇通过“回访”和“请客”维持这种关系;这种关系没有实际的用途……(波伏娃1998:597)。
显而易见,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所做的只是对婚姻“内部世界”的一种展示,并没有“实际的用途”。只有男人才是生产者,是社会运行的推动者。女人的所作所为只起装饰的作用:她们的用处在于强化丈夫的地位或成就,与自我价值的实现扯不上边。也就是说,妇女只是男人的附属品,她们不能独立于男人而存在。雷切尔的情况就是如此。正如皮尔逊所观察到的:“雷切尔是个嫁给了名人的聪明女人。这样的女人本能地让自己的行为服务于丈夫,可以说,她把所有的光芒都反射到丈夫身上”(默多克2008:28)。
由此可见,巴芬以为妻子通过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就可以实现自我的价值,她并不是一个失意的人,这种看法是立不住脚的,因为作为丈夫的他才是整个婚姻背后的实质和意义所在,雷切尔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他增光添彩、巩固他的地位和成就。然而,我们无法回避巴芬提出的一个尖锐问题:“难道她真的想吗?当然不。”此处,巴芬的自问自答模棱两可,没有表明雷切尔是真的想工作还是真的想做秘书之类的工作,但不管是哪种情况,当时的社会都不鼓励像雷切尔这样的妇女外出务工,为她们提供的机会少得可怜。
根据比奇和怀特雷戈(Beechey & Whitelegg 1986:85-9)的研究,在整个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叶,妇女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女性居多的行业里,尤其是最低等级的一些工种,比如清洁、秘书、手工制造等,这些工作对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和智力水平要求不高,主要是一些下层妇女在从事。很显然,这都是些没有前途的工作,妇女们都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从事这些工作。像雷切尔这样中产阶级的妇女仍然与维多利亚时期的妇女一样,主要是待在家里,相夫教子。此外,作为一个聪明女人,雷切尔很难通过从事对智力和才能要求不高的手工劳动来实现自我价值。
实际上,雷切尔想出去工作是不太可能的。二十世纪50年代,“‘母爱剥夺’理论甚嚣尘上,造成了一种风气,小孩子的妈妈外出做工会怕受到公众的谴责”(Thane 2001:118),而当时才二十出头、适合找工作的雷切尔却早早地做了妈妈。为了孩子,雷切尔不太可能出去找工作。在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她外出工作的可能性就更小了。英国政府在1938年所做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45岁尤其是55岁以上的女人找工作要比同龄的男性或者是年轻的女性要难得多(同上:211)。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乃至今天)仍无改观。完成养育孩子的责任之后,已经四十多岁的雷切尔再想出去寻找工作,并开始独立的生活,已经不太现实了。
我们不禁要问:难道雷切尔不能通过从事家务劳动获得自我满足吗?家务劳动毕竟也是一种劳动。事实并非如此。比奇和怀特雷戈(Beechey & Whitelegg 1986:77-9)认为,一般情况下,我们对劳动/工作的理解是男性化的。只有那些远离居家、有固定工作时间、能够赚到报酬的劳动才被看作是工作,家务劳动没有明显的产出,是女人理应做的。雷切尔自嘲为“出色的家庭主妇”,而皮尔逊也这么称赞她;但小说的嘲讽之意表明作为家庭主妇的女人很难获得自我满足,因为她们的劳动没有产出,也不被认为是社会发展所必不可少的。
综上所述,由于当时的社会并没有为雷切尔这样的女性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作为家庭主妇的她很难实现自我价值,再加上丈夫的不忠,她无法为自己的困苦生活找到出路。所以将雷切尔生活的不幸归咎于父权社会,并不为过。
5.
但是,女性又该在多大程度上为自己的不幸负责呢?雷切尔挨打后,皮尔逊试图安慰她、让她平静下来。她满含怨怒地驳斥道:
睡觉!在这样的心情下能睡觉?阿诺尔德已把我送进了地狱,已经要了我的命,已经把我们之间的一切都毁了。我跟他一样聪明,可是他处处限制我。我不能工作,不能思想,我什么都不是,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缘故。他把一切都打上了他的烙印。他攫取了我的一切,把它们据为己有。我从来就不是我自己,完全没有过属于自己的生活。我一直害怕他,结果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确,没有一个男人瞧得起女人,没有一个女人不害怕男人。这是千真万确的啊。男人在体力上比女人强壮,这是现实之所在,也是现象背后的全部原因。……他以前就打过我。啊,不管怎么样这都不是第一次。其实,他第一次打我时,我们的婚姻就告终了。……他剥夺了我的生活,而且毁掉了我的生活。他破坏了我的生活的每个细小方面,就像折断了人体的每一根骨头一样。我的一丝一毫、一点一滴都被他摧毁了,糟蹋了,夺走了(默多克2008:35-6)。
这段控诉很有力。短小、简洁而又强劲的话语营造出强烈的情感效果。言语之间,雷切尔用了很多及物动词来谴责巴芬对她的不公正待遇,例如:送进、要了、毁了、限制、攫取、打,等等,而只是用了系动词来描述自己的处境,比如“是”。一系列表示“摧毁”之意的动词,如:剥夺、破坏、毁掉等,被三次重复使用,分别是在句首、句中、句末。三次重复形成排山倒海之势,控诉丈夫的专断、发泄自己的愤怒。这尤不足,在句尾又用了这串动词的被动语态来突出强调自己的无助与不幸。所有这些修辞手法的运用,都是为了强调一点:她的丈夫是个暴君,一切的控制者,所有的毁坏者,而她作为妻子则是个受害者,一切痛苦的承受者,没有身体、精神和社会生活的自由。
由上述引言可知,雷切尔的婚姻一成不变,她一直生活在丈夫暴君般的统治之下,从未有过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存在。然而,为什么这种不平等造成的矛盾没有早日浮现,而是等到她四十多岁之后才激化起来呢?扬-艾森卓(Young-Eisendrath 1997:32)认为,人到中年之后,有一种审视早年选择的倾向,会意识到自身没有实现的“非我”(the other),并萌发实现“非我”所具备的各种潜能的欲望。
扬-艾森卓继承了波伏娃的观点,认为女人不是生就的,而是社会和文化造就的。在她看来,对于独立性和依赖性的不同评价常常反映在两性角色之中。依附性的活动,如哺育、人际关系等,被派定给没有社会地位和特权的女性角色;而与独立和自主性有关的活动就会分配给男人,并被赋予更多的特权和更高的地位(同上:29)。不难看出,巴芬夫妇的婚姻生活就是这个模式:丈夫是主导,妻子处于附属地位。扬-艾森卓进一步认为,如果一个人相信自己的性别完全由其生物属性所决定,就会不由自主地认定一系列生活的机会或可能性与己无缘,只属于异性(同上:40)。雷切尔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种僵化的性别意识的持守者与受害者。然而,她把自己的不幸和对人生的不满足都归咎于丈夫专横的个性,合理吗?
根据扬-艾森卓的理论,很多女性都有意无意地努力成为欲望的对象。她们压制或者是忽略自己也有欲望这个现实,执迷于成为他人欲望的对象。看上去,她们好像是被别人操控,而实际上,她们是受控于被自我压抑的“非我”,并将这种“非我”投射到他人身上。雷切尔的性格特点颇能解释这一点:她抱怨说自己完全听命于丈夫,“他不让我找个工作。我服从了他,我总是服从他。我没有任何属于我的东西”(默多克2008:36)。然而,这种压抑自我迎合他人的做法,恰恰来自于女性向他人示爱、并希望他人也承认这份爱是美好的这样一种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她们总是渴求从对方那里获得肯定,以此来证明自身的价值。
这便能够解释雷切尔为何总是屈从于丈夫:雷切尔习惯于通过丈夫感激和欣赏妻子的自我否定来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表面上,她以为自己是被丈夫的信仰、欲望、需要所控制,而实际上,她是被自己要从他人(尤其是异性)那里获得认可的欲望操控着。她希望通过忠实地扮演自己的性别角色来取悦丈夫。这种企图失败后,就变得怒不可遏,被复仇的欲望吞噬。从这个角度来看,雷切尔其实是自己必须服从特定性别角色的僵化观念的受害者,这种僵化的操守也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为他们夫妻婚姻生活的不幸承担责任。
6.结语
雷切尔说自己被丈夫送进了地狱,而实际上,她也是被压抑的自我和欲望送进了地狱。她以自我为中心看待生活,生活就变成了地狱。雷切尔恰如柏拉图洞穴理论里的囚徒,被自我欲望的链条锁着,没有能力回头、更没有能力步出洞穴、迎来光明。一旦被自我蒙蔽,人就会失去正视现实和他人存在的可能,这条路走到极端,便将酿成悲剧。从女性角度来看,雷切尔的悲剧一方面是她所生活的父权制社会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她所坚持的、僵化的特定性别角色导致的。
艾丽丝·默多克(1997d:461)这样探讨艺术的社会功能:“艺术是一门伟大的国际化的人类语言。它服务于每个人。艺术当然不要扮演正式的‘社会角色’,艺术家也不要觉得他们必须‘服务自己的社会’。如果他们能够专注于真理并尽其所能的创造最好的艺术(制造最美的东西),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服务于社会了”。以此类推,默多克的人文关怀超越性别,她无意专注于女性问题,只是秉着对人性的认识创造了大量女性形象,客观而真实地再现了同时代妇女的生存处境,然而,却在“不知不觉中”为女性批评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附注:
① 本文是在笔者硕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在硕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恩师申丹老师四易其稿,实可谓呕心沥血。在此,特向她致敬。此外,黄梅老师曾对硕士论文提出了宝贵意见,王宁老师审阅了本文全文,在此一并致谢。
② 译文引用自默多克(2008)。行文略有改动。
Abrams, M.H.etal.(eds.).1993.TheNortonAnthologyofEnglishLiterature(6thed.Vol 2) [Z].New York: Norton.
Bellamy, Michael.1977.An interview with Iris Murdoch [J].ContemporaryLiterature18(2): 129-40.
Beechey, Veronica & Elizabeth Whitelegg (eds.).1986.WomeninBritainToday[C].Philadelphia: Open UP.
Beechey, Veronica & Elizabeth Whitelegg.1986.Women and employment in contemporary Britain [A].In Beechey, Veronica & Elizabeth Whitelegg (eds.).WomeninBritainToday[C].Philadelphia: Open UP.77-107.
Botelho, Lynn & Pat Thane (eds.).2001.WomenandAgeinginBritishSocietysince1500 [C].Essex: Person Education.
Bove, Cheryl.1992.New directions: Iris Murdoch’s latest women [A].In Tucker, Lindsey (ed.).CriticalEssaysonIrishMurdoch[C].New York: G.K.Hall.188-98.
Euripides.1979.Medea (Rex Warner trans.) [M].In Mack, Maynardetal.(eds.).TheNortonAnthologyofWorldMasterPieces(4thed.) [Z].New York: Norton.415-49.
Johnson, Deborah.1992.[Iris Murdoch’s] Questing heroes [A].In Tucker, Lindsey (ed.).CriticalEssaysonIrishMurdoch[C].New York: G.K.Hall.48-60.
Mack, Maynardetal.(eds.).1979.TheNortonAnthologyofWorldMasterPieces(4thed.) [Z].New York: Norton.
Lessing, Doris.1993.To room nineteen [A].In Abrams, M.H.etal.(eds.).TheNortonAnthologyofEnglishLiterature(6thed.Vol 2) [Z].New York: Norton.2301-23.
Murdoch, Iris.1973.TheBlackPrince[M].New York: Viking.
Murdoch, Iris.1977.TheFireandtheSun:WhyPlatoBanishtheArtists[M].Oxford: Oxford UP.
Murdoch, Iris.1991.TheSovereigntyofGoodandotherConcepts[M].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Murdoch, Iris.1997a.The sublime and the good [A].In Peter Conradi (ed.).ExistentialistsandMystics[C].London: Chatto & Windus.205-20.
Murdoch, Iris.1997b.Against dryness [A].In Peter Conradi (ed.).ExistentialistsandMystics[C].London: Chatto & Windus.287-95.
Murdoch, Iris.1997c.The sovereignty of good over other concepts [A].In Peter Conradi (ed.).ExistentialistsandMystics[C].London: Chatto & Windus.363-85.
Murdoch, Iris.1997d.The fire and the sun [A].In Peter Conradi (ed.).ExistentialistsandMystics[C].London: Chatto & Windus.386-463.
Thane, Pat.2001.Old women in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 [A].In Botelho, Lynn & Pat Thane (eds.).WomenandAgeinginBritishSocietysince1500 [C].Essex: Person Education.207-31.
Tucker, Lindsey (ed.).1992.CriticalEssaysonIrishMurdoch[C].New York: G.K.Hall.
Young-Eisendrath, Polly.1997.GenderandDesire:UncursingPandora[M].NP: Texas A & M UP.
Ziegler, Heide & Christopher Bigbsy (eds.).1982.TheRadicalImaginationandtheLiberalTradition:InterviewswithEnglishandAmericanNovelists[C].London: Junction.
艾丽丝·默多克.2008.黑王子(萧安溥、李郊译)[M].南京:译林出版社.
西蒙娜·德·波伏娃.1998.第二性(陶铁柱译)[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