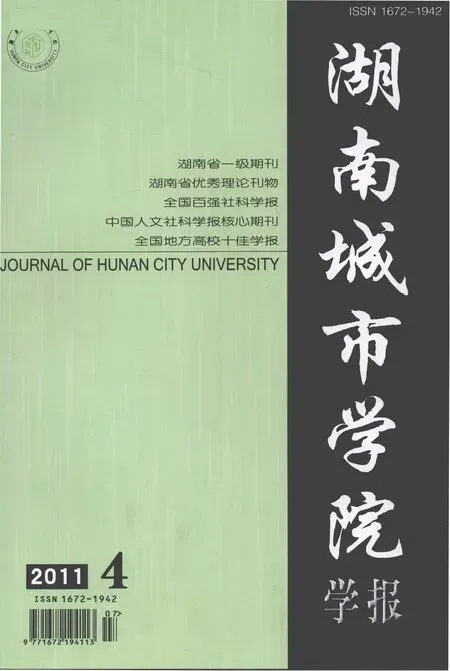论谭嗣同“尽变西法”观
郝俊伟
“尽变西法”在谭嗣同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谭嗣同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提出,又在其变法理论专著《仁学》一书中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后成为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变法的纲领性口号之一。这个口号究其实质,它超越了洋务派的变法思想界限,是主张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全面而系统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
一、“尽变西法”观的形成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惨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全国范围内掀起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受此影响,谭嗣同提出“尽变西法”的口号。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详考数十年之事变,而切究其事理,远征之故籍,近访之深识之士。……,画此尽变西法之策。”[1]226-227可以看出,此时谭嗣同思想发生了巨变,以至于提出“尽变西法”的口号,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对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反应
马克思在分析英中鸦片战争时曾指出:鸦片战争对中国起到了惊醒的作用。同样,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也惊醒了亿万中国人民。当谭嗣同获得《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时,他悲愤至极,认为中国亡国灭种祸在旦夕。他在《上欧阳中鹄书》说:“近来所见,无一不可还骇可恸,直不胜言,转觉平常无奇,偶有不如此者,反以为异,斯诚运会矣。……悲愤至于无可如何,不得不以达观处之。”[2]153他批判清朝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时又说:“及见和议条款。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总之,中国之生死命脉,唯恐不尽授之于人。非为国也,将合含生之类无一家一人不亡。”[2]153-155不难看出,在甲午惨败的巨大刺激下,谭嗣同终于猛省,对晚清中国的国情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
1.从根本上认识到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日甲午战争前,谭嗣同对清政府虽有较多批评和指责,但其思想中仍然有中国乃天朝上国的虚骄观念。但甲午惨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使谭嗣同对清政府完全失望了,也让他彻底看清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他曾清楚的指出,清朝的官吏遇此国难,“不能出一谋,划一策”,[3]155只知道吃喝享乐,哪管国家的存与亡。不仅如此,清朝的军队军纪败坏,武备废弛。将领指挥无能,遇战不前,只知道逃跑。士兵遇战贪生怕死,与敌一触即溃。甲午战中无一不败,“奉天败,高丽败,山东败,澎湖又败;旗军败,淮军败,豫军、东军、各省杂募就地招募之军无不败,即威名赫耀之湘军亦败,且较诸军尤为大败。”[2]158清政府有此官吏、将士与通过明治维新变法后国力空前高涨的日本交战焉有不败之理。
2.认定晚清政府不变法难逃灭亡。甲午惨败后,谭嗣同彻底抛弃了之前的犹豫不决,认为清政府要想改变亡国的唯一途径就是维新变法。“不变今之法,虽周、孔复起,必不能以今之法治今之天下,断断然矣。”[2]161此时的谭嗣同已经把变法维新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途径,是关系华夏民族能否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事。为了变法,“被发左衽,更无待论。”[2]155甚至为变法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从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出谭嗣同此时的思想有了比较明显的提高。
(二)受戊戌思潮高涨的影响
戊戌维新思潮是中日甲午战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民族觉醒的产物。爱国御侮,救亡图存是维新思潮的时代主题。帝国主义国家联合的侵略和瓜分,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惨祸,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初步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这时受到了来自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在这种严峻的国内国际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被迫站在了风口浪尖,面临生死攸关的重大抉择。有识之士不甘于国家的逐渐沉沦,渴望晚清政府实行变法来挽救民族危亡。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在神州大地逐渐开展起来。
此时的谭嗣同深受维新变法思潮的影响,也不甘落于人后,他积极准备在湖南成立强学会分会,同时制订了章程。但在此时晚清政府中的顽固派官僚攻击强学会私立会党,妄议朝政,大逆不道,慈禧太后强迫光绪封禁了强学会。消息传到湖南,谭嗣同悲愤至极,他痛斥清朝政府 “强学会之禁也,实防务华民之强盛,故从而摧抑之,依然秦愚黔首之故智。”[2]483为了把宣传维新变法进行到底,谭嗣同决定顶住压力在湖南成立强学会分会,但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抱有幻想,希望获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借助洋人的保护来组织强学会,开展变法宣传。可这只是谭嗣同单方面的设想,他只看到了国际帝国主义国家表面支持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的一面,没有也不可能看到国际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中国变法维新背后的阴谋。因此谭嗣同的这种希望获得帝国主义国家保护和支持的计划,很快就化成了如幻泡影。
当谭嗣同正彷徨无计时,清政府迫于中外舆论的压力,取消了对强学会的封禁,但将强学会改为专门翻译书报的官书局。实际上是把强学会变成了又清朝政府控制的翻译机关,已经不再是宣传变法维新的政治团体。谭嗣同在开始不了解真实情况下,获此消息,欣喜若狂,还把他称为“近日一大喜事”,[4]457但当他了解这不过是清政府玩弄的手段计策后,非常气愤。毫不客气的批评说:“现今虽开,却改名官书局,不过敷衍了事,羊存礼亡矣。”[5]483-484由此不难看出,此时谭嗣同的爱和憎已经完全与变法运动结合在一起了,这也是戊戌思潮高涨在谭嗣同身上的现实反映。谭嗣同“尽变西法”观,受甲午惨败的巨大刺激和戊戌思潮的影响的双重激励下终于形成了。
二、反对封建君主专制
“尽变西法”观形成之后,为了宣传这一变法观点,指导维新变法的实践活动,谭嗣同对封建君主专制做了无情的批判。
(一)对荀学的批判
谭嗣同在《仁学》中明确指出:“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4]337故秦以后的政治史,实属秦政之史;秦以后两千年之学术史,乃君主专制之史也。“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执托者之大盗乡愿,而责所托之孔,又乌能知孔哉?”[6]337看来,以仁为本的谭嗣同对于主张性恶论的荀学,不可能不持批判的态度;而且他对由荀学衍生的秦汉以后的中国政治史、学术史的批判更是入木三分。但如果仅仅以此来完全概括秦汉以后的数千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就偏离了历史事实。
(二)对封建纲常名教的批判
这是对荀学批判的继续,在谭嗣同看来,数千年为祸中国最甚的非属三纲五常不可。他在《仁学》中就批判说:“君以名桎臣,官以名扼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者得乎?然而仁之乱于名也,亦其势自然也。中国积以威刑钳制天下,则不得不广立名为钳制之器。”[6]299他继续批判说:“君臣之祸亟,而父子夫妇之伦遂各以名势相制为当然矣,此皆三纲之名为害也。名之所在,不惟关其口,使不敢昌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愚黔首之术,故莫以繁其名为尚焉。”[7]348由此看来,数千年来纲常名教残酷地钳制人们的言行,桎梏了人们的思想,封建统治者采取愚民政策的目的不外乎要人们心甘情愿的接受封建君主专制的统治。这些皆不合乎人性,皆不合乎实际,应该统统打倒。
(三)对清政府种族专制的批判
谭嗣同被称为维新派最为激进分子,就在于他的思想中处处透露出常人不敢想、不敢言的内容。他曾指出:秦汉以后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实属荀学衍生而来,而且用专制强制保证纲常名教的实现。他批判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8]337其实君主也不过是普通人,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其所凭借的不过是纲常名教歪理邪说来挟制天下人的身和心。至于那些野蛮的民族,本不知道什么纲常名教之说,他们以野蛮的武力屠杀来窃取中国。像满清入关后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严薙发之令”等等莫不如是。可一旦他们在中原站稳脚跟,便又以纲常名教来治理国家。这些尖锐的批判从根本上否定几千年所宣扬的“君权神授”、“天命所归”的封建理论,可谓大胆至极。
谭嗣同不遗余力地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批判,其目的是为宣传其“尽变西法”理论,并用其变法理论,来指导其一系列变法实践活动。
三、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是谭嗣同“尽变西法”观用于实践活动的具体体现。谭嗣同认为,中国此时的富强之路较为可行的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与西方国家通商。早在《报贝元徵》书中,他就主张中国应发愤为雄,决去壅蔽。在主张兴学校、开议院、改官制的同时还主张兴办工商业,全力发展中国的铁路、水路等交通运输事业,以此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此,他又主张在国内广设商会,开办公司,兴办银行、保险业等国内所需的各种资本主义工商事业。总之,凡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我们都要一一学来。
同时,谭嗣同认为要想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突破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所形成的节俭观念。只有不断扩大生产,促进消费,加速商品货币流通速度,才能使工商业获得快速发展,才有可能使国家逐渐走出贫困,实现中国的富强。正是由于他有了这些西方经济学的知识,所以他才坚决反对顽固派所倡以中国淳朴民风,足以取胜西方国家的论调。认为中国若不改变此种虚骄观念,不出数十年必将面临更大的危机。为何?“生计绝,则势必至于此”。[8]325因此,他认为中国要想走出困境,重新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走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这条道路。
谭嗣同又明确指出,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关键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之前所述他之所以反对传统节俭观念的本质,也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而要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他说:“有万里之程焉,轮船十日可达,铁道则三四日。苟无二者,动需累月经年,犹不可必至。”[9]329所以,有了现代交通工具后,我们可以节省出许多时间来做更多的工作。这种节省时间的观念,不仅是要劝人们不要虚度光阴,更为重要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只有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我们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中国也才有可能实现富强。
对于发展实业,谭嗣同一向十分热心。他曾建议湖南巡抚陈宝箴,利用湖南的丰富资源,大力发展各种实业。为此,他曾主张要把管办企业改为商办,鼓励商民自己筹款开矿办厂,并给予其若干年的专利权。同时他还主张与西人通商,借以学习西方技术,获取资金。为了开办交通事业,他除大力提倡修建湘粤铁路外,还曾自己亲自创办了一家内河小轮船公司。 不仅如此,其他的诸如商务、税收、社会福利事业等等,谭嗣同都十分关心。
湖南历来盛产茶叶,但手工操作,技术落后,发展十分缓慢。谭嗣同曾打算对此作一番改进。恰逢此时张之洞打算在湖南设立机器制茶分公司,他就属意谭嗣同来操办具体事务。这正合谭嗣同心意,他立即热情洋溢投入具体事务当中。着手组织人力,调查行情,联系购买机器,选址建厂。在其四方奔走之下,机器制茶公司有了初步的发展。但由于资金技术欠缺等诸多原因,最终制茶公司还是失败了。
四、发展教育
在民族危亡之际,谭嗣同认为要救亡图存,就不可再“守文因旧”,而应“尽变西法”。“尽变西法”关键在于,培养务实求新的维新变法人才。而人才培养就要变科举,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兴办学校,改变中国的教育制度。因为中国的科举制度培养的士人,只会“鹜空谈而无实济,而又坚持一不变之说,以议论为经济,以虚骄为气节,及责以艰巨,又未尝不循循然而去之”。[10]156这些腐朽顽固的人,只懂得空谈义理,虚骄自大,又无实用之才,专以诋毁别人为能事,真要让他担当重责,他又不能胜任。这些虚骄自大的顽固派胸中所学已经完全不能应付晚清政府所面临的严峻的国内国际局势。要想改变这一状况惟有改变科举制度,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
在谭嗣同看来西方的教育制度比之中国的科举制度有许多优点。其一,西方的教育“以用为学,学以致用”。如西方人注重学习的算数,方便于计算运用,法学方便于审理各类案件,机器制造之学方便于制造各类新式机器,等等。西方所学无不是实用之学。其二,西方的教育内容有利于开阔视野转变传统观念。早在《报贝元徵》中谭嗣同就说过西方人“学某学科即读某专书,而各门又无不兼有舆地之学。”[2]209舆地之学即天文地理学科。而西方普及的天文地理学科,本来就是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时期,资产阶级用于批判反封建教会神学对人们思想束缚控制的利器。在其时,天文地理观念的转变就是世界观、人生观的转变,也是西方近代民主观念形成的基础。而晚清的中国人正需要转变传统的中国“居天地之中”的虚骄观念,以彻底清除传统华夷之辨的影响,从而走“尽变西法”的维新道路。
兴办算学馆是谭嗣同发展教育,实现“尽变西法”的主要实践活动。他认为算学是一门用途十分广泛的科学,是学习其他自然科学的基础。对兴办算学比较积极的唐才常曾说过“惟算学一道,小可为日用寻常之便益,大可为机器制造之根源;即至水陆各战,尤侍以为测绘驾驶放炮准头诸法。中国之所以事事见侮外洋者,正坐全部讲求只故。”[1]209这可以说是概括了当时大力倡导兴办算学的谭嗣同的主要看法。
既然算学如此重要,谭嗣同就与唐才常等变法人士商量在湖南兴办算学馆。于是他就写信给他的老师欧阳中鹄,希望获得恩师的支持。欧阳中鹄看过其信后曾给予大力支持,但其对谭嗣同的“尽变西法”的主张,并不赞同,他只希望谭嗣同的教育贤才的计划能够在封建政治伦理观念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在传统封建教育中加入自然科学的内容,以期望挽救晚清的民族危机。为了兴办算学,谭嗣同联合唐才常、刘善涵等将浏阳南台书院改为算学社。为此事,其先后两次回浏阳策划,拟订算学社章程,呈请湖南学政江标批示。对于谭嗣同兴办算学的计划,江标为开发湖南风气,完全给予支持。不料此事遭到湖南顽固分子激烈反对,他们百般推托阻挠,以致江标的批示不能贯彻执行。
恰逢此时浏阳发生严重的旱灾,饥民纷纷逃荒,嗷嗷待哺,赈灾成了当时压倒一切的大事。欧阳中鹄奉命“办赈”,不得已与顽固派做了妥协,“主张—切‘听之县官’”,[11]110同意把办算学社的经费挪用赈灾。这使谭嗣同、唐才常等“意甚不满”。但这是恩师的意思,谭嗣同也无好的办法。后与唐才常等商议,由几位同仁联合起来筹集“巨款”,在浏阳办起了算学馆。这对开发湖南风气有莫大的帮助,甚至于推动了湖南全省的维新变法活动。
五、总结
综观上述谭嗣同的“尽变西法”观,是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其变法思想是较为全面、激进而又具体的。这表明谭嗣同这时的世界观的主要倾向已经资本主义化,他企图用发展资本主义来挽救民族危机。但是,同以往任何思想家—样,先进的思想和主张总是与一些落后和消极的东西同时并存。谭嗣同的“尽变变法”主张是积极的,但具体实践时又要遮掩一下。他把变法叫做“复古”,即“托古改制”。谭嗣同认为维新就是恢复“周公之法”。他认为周公之法是最好的,但周公之法传之后世而越变越坏,到清朝时期,其所实行的法,已经积两千来之弊病,无法可言,周公时的典章制度、声明文物,皆已失传,现在只是徒有其形,而无实际。因此,不得不采西法补中国古法之亡。何况西法博大精深,较之现行中法先进得多。这些论述,诚然是荒谬多于正确,但客观地看,这种论述方法还是易于被当时大多数未受教育的人所接受,同时有助于反击顽固派的进攻,具有策略意义。当时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者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看问题并阐述维新变法的,这中间固然包含有对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崇拜,但却掺杂着虚骄自大、闭关自守的传统因素,即使思想最激进的谭嗣同也不能完全摆脱其束缚。
还应指出的是,谭嗣同在强调“尽变西法”的过程以及变法实践中,“忽略了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侵略的本性”,[11]106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侵略用中国传统的兵家法则来解释,认为西方国家侵略中国是因为中国太弱。更为荒谬的是,他主张把西藏、青海、新疆、内外蒙古这些荒芜之地卖与英国和俄国。这样,不仅可以避免与英俄在西北发动战争,而且可以为维新变法提供经费。对于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谭嗣同也多采取抨击和指责的态度。谭嗣同在批判清廷腐败无能和赞扬西方国家富强的过程中也有不合实际的部分,即注意了一种倾向而忽略了另一种倾向。不可否认,谭嗣同的一些“尽变西法”思想还不够深刻和成熟,但总体来说,“尽变西法”思想是谭嗣同甲午战争后到期牺牲前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乃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也有其进步意义
[1] 蔡尚思.报贝元徵[M]//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1.
[2] 蔡尚思.上欧阳中鹄书[M]//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1.
[3] 蔡尚思.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 1981.
[4] 蔡尚思.致刘淞芙[M]//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1.
[5] 蔡尚思.上欧阳中鹄·九[M]//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1.
[6] 蔡尚思.仁学·二十九[M]//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7] 蔡尚思.仁学·八[M]//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1.
[8] 蔡尚思.仁学·三十[M]//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1.
[9] 蔡尚思.仁学·二十一[M]//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1.
[10] 蔡尚思.仁学·二十四[M]//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下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1.
[11] 李喜所.谭嗣同评传[M].河南:河南教育出版社,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