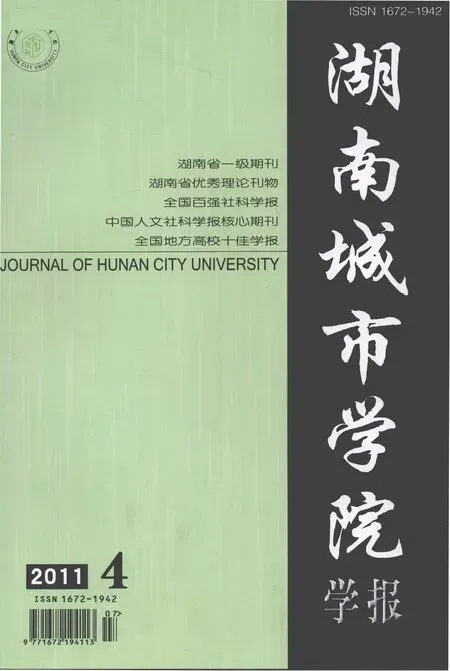身份的焦虑:《村庄秘史》中的认同危机与历史叙事
田文兵
随着全球化和本土化运动的双向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也日益加强,在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荡中,产生了一个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那就是文化身份认同。只要存在强势异质文化的冲击,本土文化就会面临被异化或者取代的境遇,因此身份认同的危机越来越困扰着个人、国族以及种群,已成为当下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2010年 6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村庄秘史》,是作家王青伟在感同身受了国族与个人身份认同的危机和焦虑后,并很好地把握了这一主题,经过 20多年的酝酿与构思,呈现给读者的一部“魔幻史诗”。这部厚重的文本,以揭示南方农村的历史演变为题材,描写了一群在名叫老湾和红湾的村庄里生活的人们,叙述着一个个诡秘而又发人深省的故事,传达着作家对个人、社会和历史的深邃思考。
在王青伟的小说《村庄秘史》中,有一个非常显见的主题就是寻找和证明自己的身份。在老湾和红湾这两个古老的村庄里,生活着一群弄丢了自己身份的人,他们处于一种身份不被认可的焦虑之中,并且生活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忙于寻找和证明自己的身份。小说的第三个故事中有个叫章义的老湾人,早年跟随章小离开村子外出参加革命,一同出去的20来人中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到老湾。那些死去的十几个人的尸骨虽然抛在各个不同的战场,但他们的名字被刻在老湾樟树林的那座高高的纪念碑上,与老湾的历代先辈英烈们永垂不朽。章义不幸做了美国人俘虏,在战俘营里他遭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后背被枪托砸弯成了不能直起腰杆的驼背。和身体的驼背一样,因章义曾经做过战俘的历史污点,他一辈子也只能像狗一样活着,没有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和身份。后来清理历史问题时,章义被清除出队伍回到老家务农,即便回到老家后也不被大家承认是老湾人,他只能趁着夜晚没人的时候站在纪念碑旁向战友们致敬。因为遭受的耻辱经历,章义从不向人说他的历史,一个没有历史的人,怎么能拥有自己的身份?
不仅章义,章抱槐和麻姑也是弄丢了身份的人。章抱槐和章义有着相似的经历,当章抱槐还是叫章大的时候,和弟弟章小先后报考黄埔军校成为军人,后来与弟弟一道从事地下工作。他因为眼睛近视,没看清黑夜里的表示危险的暗号红布而被捕。面对筷刑的恐惧,章抱槐背叛了自己追求的革命事业签下了悔过书。回到老湾的章抱槐也曾想把自己在敢死队写的诗刻在浯溪的石壁上,以证明他曾经当过敢死队的督战官的辉煌历史,于是他翻遍了每一根荒草和每一寸土地,期待着能找到刻下自己文字的空地,但却没有一丁点容身之处。因为背叛信仰这个致命的错误,章抱槐不仅迷失了自己,而且他与章小的人生道路也有了天壤之别。章小做了共产党的高级将领,被村里面的人们奉为骄傲,而章大却只有在舞台上才能迷醉自己,更为痛苦的是他因为自身历史有污点被章小剥夺了教历史的权利。他也成为了一个没有历史也不能开口讲历史的人。对于老湾人来说,麻姑来历不明。其实连麻姑也不能肯定自己的具体身份,只是在祖辈的传说中得知她和她的祖先们来自一个叫千家峒的地方。几百年来,包括麻姑在内的千家峒十二家族姓一直在寻找千家峒,尽管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过那地方,但她们并没有放弃这个信念。后来麻姑被章顺勾引,生下了一个儿子。因为千家峒的女人只能带着自己的女儿去寻找,男孩子只能跟着自己的父亲,所以麻姑带着儿子来到老湾。在老湾,麻姑用女书文字记录下了自己寻找千家峒的历史,但这部只有千家峒的女人才能看懂的女书字稿被儿子章天意烧成灰烬。没有了历史,也找不到千家峒的麻姑不仅没有了身份,也没有了生存下来的意义,彻底疯掉是其必然命运。麻姑的疯掉使章天意明白了母亲已不再是原来的母亲,他自己也感觉到生活在一片迷梦之中,“既没有生命的起点,也没有生命的终点,他不过是在这起点和终点之间在老湾这地方落了一回脚”。章天意知道自己不属于老湾,最终在某一天离开了老湾,去帮他的母亲寻找那个叫千家峒的地方。
其实何止章义、章抱槐、麻姑和儿子章天意,那些生活在村庄里的其他人,如章春、章玉官、章一回等,都面临着没有身份和找不到最终归属的困境。章春,是章义的儿子,当父亲在忙于证明自己老湾人身份时,章春认贼作父。但即便认了章一回作父亲,也还是不能改变自己抛弃身份逃离老湾的命运。章玉官,被老湾人称为最有良知的人,自5岁就离开老湾学戏,唱成了县里的名角。这个曾散了所有家财去救章铁才的地地道道的老湾人,后来因为演戏时被人不小心杀瘸了一条腿回到老湾,他的身份也一样需要等待“上面”证明。更具戏剧性的是被老湾人称为“上面”的章一回,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整理档案来证明别人的身份,然而他自己的来历却是一个谜,甚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来自何处。后来档案室被大火烧毁,包括章一回在内的老湾和红湾所有人都没有了档案,整个村庄的人们都没有了身份,而且都丧失了记忆。
这部小说构思起始于新时期文学复兴亢奋时期,作家王青伟没有专注于社会功利性去创作“伤痕”、“反思”、“改革”等之类的主流作品,也没有沉迷于西方现代派理论和技法去创作具有先锋性质的文学,而是在思考中国社会。他选取了村庄这个最能代表中国农业社会形态的个体,讲述其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现象和面临的问题,并且他所关注的不是社会和物质层面,而是人们所处的这种身份迷失的精神困顿。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再来探讨为什么王青伟小说中的人物都处于一种身份迷失的状态,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迷失是一种不被当下生存环境认可的焦虑感,或者在全新的环境中感受到自己处于一种漂浮无“根”的状态。尤其是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政权的更替、制度的变革,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生存环境的逐步恶化,人们常常会感觉到自己处于一种不安全环境之中,自然会产生一种身份迷失的焦虑感。在《村庄秘史》中,身份的迷失不再是偶然的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于民众身上的社会症候。而且作家还意识到了身份认同的焦虑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解决的问题,在小说中很多人直到死的那天也寻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就像章义、章抱槐、麻姑那样,用一辈子的时间也无法证明自己到底该是谁,来自何处。既然都不知道自己是谁,那么人们又将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呢?
其实,对身份的寻找与认同不仅仅存在于现代社会,以回归故土或寻找精神家园为母题的文学作品就已经隐约表示了人们对身份认同问题的思考。从哲学角度来说,“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此类关于人的存在的追问,至今仍然是一个难以解开的历史之谜。所谓哲学原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这里所说的寻找家园就是寻找自己的精神归属,也就是一种对身份认同的体现。知道了“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才能明确我们存在于这个世上的价值,才能进一步思考“我们到哪里去?”显然,王青伟的《村庄秘史》中对个体身份的迷失与寻找的思考为探索有关人类终极问题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村庄秘史》以讲述老湾的历史为叙事重心,通过五个故事展示了老湾与红湾两个村庄百年来的兴衰转变以及彼此之间的恩怨情仇。这个普通南方古老乡村在历史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值得大肆渲染的重大事件,也没有出现多少足以令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杰出人物,但这些平凡人们的生存状态折射出了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他们的命运和遭遇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詹姆森有个非常经典的论述:“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1]尽管这个关于第三世界文学的结论有些绝对,也并不一定完全适合拿来解读中国文学,但对于王青伟的这部《村庄秘史》来说,詹姆森的第三世界的本文与民族寓言的观点倒是有些契合。尤其是村庄秘史中人们寻找身份的主题,应该可以从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焦虑来理解。对文化冲突影响到文化身份变化的现象,乔治·拉伦有这样的一段论述:“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在相对孤立、繁荣和稳定的环境里,通常不会产生文化身份问题。身份要成为问题,需要有个动荡和危机的时期,既有的方式受到威胁。这种动荡和危机的产生源于其他文化的形成,或与其他文化有关时,更加如此。”[2]这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处于弱势地位,面对强势的西方现代文明,本民族文化可能会主动去包容同化,但是更多的是迎合妥协,那样必然导致迷失自我。
历史的讲述就是一个身份认同的过程。斯图亚特·霍尔所也曾说过:“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3]生活在南方古老村庄老湾和红湾中的人们之所以找不到自己的身份,就在于他们无法讲述自己的历史。没有历史的人怎么会拥有自己的身份?当然也就无法在村庄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所。这是从个体角度来讲述历史之于个人身份认同的重要,同样,如果一个村庄没有自己的历史,那么这个村庄就不复存在;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什么用来证明自己的存在,那么这个民族也将会在人类历史中湮没。章抱槐写下的“历史,有时是一片空白”这句话,既是一句无奈的感慨,也是一句发自肺腑的警示之语。
出版者在封底有这样一段对小说的简介:这部“原始的情感类长篇小说”,“描写了在一个村庄发生的一个接一个近似于动物性的性爱故事”,但同时它也是“厚重的历史类长篇小说”,“揭开了一段震惊中外但又鲜为人知的一个村庄匪夷所思的历史”。其实除此之外,这部村庄秘史还是一部反映百年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历史。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部南方乡村的历史故事,其实质乃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寓言,是一种被投射的政治叙事。出于历史客观原因,北方一直视为民族正统,在这种意义上,王青伟创作了乡村秘史为南方民族证明了身份,南方和北方一样存在于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这就是这部村庄秘史之所以被命名为“秘史”的内涵。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村庄秘史也同样可以看作是一个民族寻找和证明自己身份的过程。而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与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的创作母题也一直存在于百年中国文学的创作中。其实,早在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别求新声于异邦”文化策略的主导下,身份认同的危机就成为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无法释怀的心病。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启蒙文学、20世纪30年代的“京派”文学,还有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等,这些以民族文化重构为创作重心的文学既是“感时忧国”的知识分子个人情感的依托,也是复兴民族国家和文化想象的寄寓。可以说,整个20世纪,知识分子都在致力于建构新的现代中国形象,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与冲击中作出文化与实践的艰难选择,而这一活动贯穿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始终。中国作家作为中华民族文明走向的探寻者,把对过去历史的反思和精神家园的寻找倾注到文学创作中,显示出积极参与民族文化建设的主动姿态。
于是,王德威在《序:小说中国》中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他为何用中国小说这种虚构的文学叙事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缘由。他认为,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小说纪录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种种可涕可笑的现象,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不仅如此,他还强调了“想象”对于民族国家建构以及国史编纂的必要性:“但谈到国魂的召唤、国体的凝聚、国格的塑造,乃至国史的编纂,我们不能不说叙述之必要,想象之必要,小说(虚构!)之必要。”“然而我们如果不能正视包含于国与史内的想象层面,缺乏以虚击实的雅量,我们依然难以跳出传统文学或政治史观的局限。”[4]王青伟的《村庄秘史》其意旨应该就是希望用这种小说想象的形式来建构民族国家形象,而且他采取这种形式也同意此类观点,即秘史可能比历史政治论述的中国形象更为真切和实在。
王青伟的小说讲述的既然是秘史,就必然不同于历史和政治论述,也有别于在明确意识形态导向下叙事的文本。这其中最大的不同就是,不管是老湾和红湾两个村庄之间恩爱情仇故事,还是生活在其中的芸芸众生,并不完全受到社会历史变迁的支配,也就是说社会政治环境并没能对改变老湾人的思想和性格起过明显的作用。那么这部村庄秘史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历史,它们的历史有何特别之处呢?每个村落都有它们自身的隐秘历史,老湾的历史全部隐藏在那片神秘的古樟树林里,而红湾的隐秘历史全在那片红河水里。可见樟树林和红河水不仅仅是两个古老村庄历史的见证,而且还被赋予了深刻的寓意与内涵。就拿老湾河岸边的那棵古樟树来说,这棵古樟可以说是老湾村所有人的命根子,不仅因为它在饥荒时期救过全村人的命,更因为它是老湾祖先曾经兴旺发达的象征,是老湾人潜意识中崇拜的图腾。掌管着所有老湾人档案的章一回,被神秘的力量吸进老湾人的图腾古樟树里,他行走在古樟树下那座被废弃了若干年的空旷的城池中,感觉就像走在一个迷宫里,城池尽管已经废弃,却美丽而壮观。在这座废城池的一间书屋里,他看见了那本记载着老湾人秘不可传的史籍档案的树皮书,但是就连这位档案大师也有许多看不懂弄不明白的地方。樟树里藏着的这部老湾秘史,显然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难怪章一回在面对这部历史时感受到的是神秘和无比壮观。承载着这部秘史的古樟树见证了老湾人的辉煌与耻辱,历经过被砍伐的威胁也遭受过复仇大火的诛杀,尽管枝干枯萎绿叶凋零,但老樟树的心脏依然在顽强地跳动,重新长出了新皮和嫩叶。古樟树作为一个村庄的图腾,一种文化的象征,它曾见证过的辉煌与耻辱,它遭遇过的不幸和历经着的苦难,不也正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真实写照?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与古樟树具有同样象征意义的文学意象曾出现在很多作家的篇章中。沈从文古老边城中,立在河畔的白塔,不也是经历了坍塌和重建的过程?还有废名的桥、师陀的果园城、张承志的北方的河、张炜的古船、贾平凹的秦腔等等,这些意象都是作家们赋予了特殊内涵的民族寓言的投射。可见,王青伟的《村庄秘史》不仅仅是“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又一座丰碑”,而且是继近现代中国作家用文学作品来探索中华民族历史和命运的又一力作。
把《村庄秘史》放入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体系中,从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宏观角度,以现代文明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为着眼点来理解《村庄秘史》的深刻内涵,个人认为应该是较为合适和公允的。《村庄秘史》的出版,也必定会成为王青伟小说写作生涯中,甚至文学湘军的创作中,乃至中国文坛上的一个有意义的事件,对乡村文化的叙事,对国族身份的认同,甚至作家个人情感的归属,有着极具价值的探索和启发。
[1]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C]//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235.
[2] (英)乔治·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M].戴从容, 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194.
[3](美)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C]//刘向愚, 罗钢.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211.
[4] 王德威.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