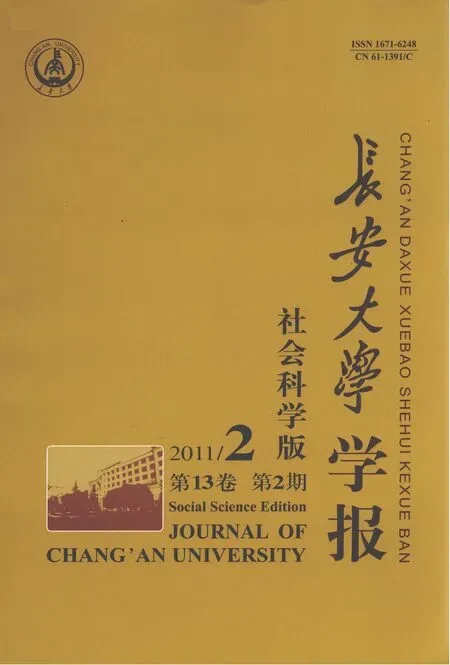元代色目诗人雅琥及其诗歌创作
朱仰东
(1.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2.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新疆 伊宁 835000)
元代色目诗人雅琥及其诗歌创作
朱仰东1,2
(1.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2.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新疆 伊宁 835000)
元代色目诗人雅琥生平资料散见于历代文人文集中,为稽考其生平,考察其诗歌创作情况,运用考证的方法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勾勒其生平概况,并利用分类的方法对其诗歌内容及艺术特征做了精当的概括。分析认为,雅琥诗歌在元代文坛上确实具有相当高的水平,研究他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同时探讨了雅琥诗歌何以儒化的原因。
元代;雅琥;诗歌;儒化
清人顾嗣立在《元诗选》中有言:“有元之兴,西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元代出现了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马祖常、不忽木、贯云石等都为世人所熟知,游国恩、中国社会科学院、章培恒、袁行霈等分别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对这些少数民族作家的诗作多有收录。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作为杰出民族诗人的雅琥则一直鲜为人知,这位在当时名噪一时的作家,不但所留生平资料很少,我们仅能从少数文人的记载中略窥一二,而且尤为遗憾的是在当代重要的文学史著中大都失载,其中也包括了各种版本的少数民族文学史著,就连邓绍基先生主编的有着广泛影响的断代史《元代文学史》也未曾提起。同时,据笔者通过中国知网的统计来看,建国以来对雅琥的研究完全处于空白。这对于作家个人而言是一种不幸,在一定意义上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史而言也是一种悲哀。故而,笔者不揣浅陋,在现有的资料基础上,尽其所能,为这位“标奇竞秀,亦可谓极一时之盛”[1]的杰出民族诗人及其作品作一些简要梳理,意在引起学界对他的关注,使这位被遗忘的民族诗人进入研究视域,不负这位诗人对元代诗学所付出的努力。
一、雅琥生平稽考
关于雅琥,目前资料不多,且大多散见于元人文献中,只言片语,语焉不详。今据《元诗选》二集戊、《元诗纪事》卷17、《元西域人华化考》、《元史·文宗本纪》等相关记载试作钩沉。雅琥(1284~1345),初名雅古,字正卿,也里可温人。所谓也里可温,或称阿勒可温、也立乔、耶里可温等,是蒙古语Erkegü的音译,意思是“有福缘的人”,或“奉福音之人”[1],是元朝人对基督教教徒和教士的通称,后也指罗马天主教。在元朝的公牍中,常以也里可温与各路诸色人户并举,元政府对待也里可温人户,同佛、道、答失蛮和儒户一样,优免差发徭役。这也就是说雅琥当为基督教教徒,关于这一点,陈垣先生辨别有力,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中,他提供了3条理由:第一,雅古为亚伯拉罕之孙,基督教徒恒以此为名;第二,前人多以可温人称雅琥,与称马祖常为可温人同一;第三,元代史书如《元秘书监志》载雅琥本名雅古,雅古为也里克温人。“有此三证,雅琥为基督教世家无疑问矣。”[2]故此,方豪将雅琥收入《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理由全本于陈书。关于雅琥早年的事迹现在难以详考,在《送吴子高还江夏》诗序中诗人写道:“庚申春余在江夏,尝赋诗送子高之沅。庚午,复来会京师,因求偶而还。复作此以饯。”说明诗人于元仁宗延祐七年庚申(1320)居住于江夏(今湖北武昌),湖海飘零,未曾入仕。关于他入仕的时间,即何年登进士第,目前有3种说法:第一,至顺元年(1330)进士,如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即持此说。第二,天历间进士,源于傅若金所作《忆昔行送雅琥正卿参书南归》题下注释:“初名雅古,登天历第,御笔改雅琥”(《傅和砺诗集》卷3)。第三,泰定元年(1324)进士,根据《元秘书监志》卷10著作佐郎题名:“雅古,赐进士出身……泰定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承事郎上”推定。有学者认为:天历进士说不能成立,因为文宗天历时未开科,至顺进士说未注明原始出处,可能是由天历进士说发展而来的,因为天历、至顺都是文宗年号,至顺元年与天历三年同年,但是天历三年的进士不能说成至顺元年的进士,因此雅琥可以肯定是泰定元年考中进士的[3]。
入仕之后,虽然一时颇受文宗赏识,御笔改名为“雅琥”,但雅琥的仕途并不如意。据《元史·文宗本纪》载,至顺二年三月雅琥充奎章阁参书,同年三月便遭御史台弹劾“奎章阁参书雅琥,阿媚奸臣,所为不法,宜罢其职”。贬为静江路同知,结合傅若金《忆昔行送雅琥正卿参书南归》及同一教门著名诗人马祖常《送雅琥参书之官静江》诗序中所言:“雅正卿以文学才识遇知于天子,出贰郡治,馆阁僚友及京师声明之士,各欣然为文章以美其行,而请余为之序。”可知,雅琥获罪实则不然。究其原因,是因为奸臣云云实指泰定宰相倒刺沙乌伯都刺,“文宗尝恶之,目为奸臣”。雅琥显系无辜,清代魏源作《元史新编》予以平反。但贬黜给雅琥所带来的结果便是居无定所,“正卿尝家衡鄂”,“他日正卿以亲老乞高邮便养”等句看,雅琥曾长期逗留于江淮一带。由陈旅《送雅古正卿同知福建转运盐使司事》(《安雅堂集》卷2)、吴师道《送雅琥正卿福建盐运司同知》(《吴正传文集》卷8)等诗可知,雅琥此后曾经改迁福建盐运司同知。此外,其他事迹于史不载,也就无从得知。杨镰先生推测其逝世于至正初年,不知何据。
二、取材广泛的诗歌类型
雅琥的诗歌侥幸存留下来的并不多,清人顾嗣立《元曲选》二集收雅琥诗集《正卿集》共39首,《元诗别裁集》收其诗3首,实选于前者,另外还有《永乐大典》卷9 763收其轶诗1首,即《七星岩》,共计40首。
雅琥的诗歌就其内容而言,大致不出汉族文人所写的传统题材,比如咏史、怀古、游仙、送别、酬唱等等。但因其出自少数民族作家之手,也别具面目。以咏史怀古诗看,如为人所称道的《唐宫题叶》:“彩毫将恨付霜红,恨自绵绵水自东。金屋有关严虎豹,玉书无路讬鳞鸿。秋期暗度惊催织,春信潜通误守宫。莫道银河消息杳,明年锦树又西风。”[4]本诗见于孟棨《本事诗》,又见于《青琐高议》前集卷5、后为鲁迅较录于《唐宋传奇集》中,主人公名字略有差异,但事迹一样,都描写了一个唐代宫女良缘巧合的故事。刘斧《青琐高议》题解中曾言:“流水,无情也;红叶,无情也。以无情寓无情,而求有情,终为有情者得之,复与有情者合,信前世所未闻也。”(《青琐高议》前集卷5)既然“信前世所未闻”,因此其故事本身颇富戏剧性,故而常为历代文人所歌咏,如南宋词人张孝祥《满江红》词:“红叶题诗谁与寄,青楼薄倖空遗迹。”即使在元代,也有不少人,包括一些著名作家都曾以此为题材唱和品评,如卢挚《双调·沉醉东风》“重九”中起句:“题红叶清流御沟,赏黄花人醉歌楼。”要想写出新意,恐怕很难。但雅琥似乎无意于此,全诗旨在描绘女主人公的情态,通过细微的举动捕捉微妙的心理变化,将女主人公无奈、爱恨、希望与失望的心绪全都寄托在小小红叶之上,这一叶落红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物象,它连接着宫里与宫外,深刻反映了宫廷对青春年华的幽闭和残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犹如牛郎和织女之间的那道银河,女主人公渴望美好爱情而不得。瞿佑《归田诗话》(卷下)称“雅正卿有四美人图诗,惟《御沟流叶》最佳。”
又如《汴梁怀古》:“花石岗前麋鹿过,中原秋色动关河。欲询故国伤心事,忍听前朝皓齿歌。蔓草有(一作无)风嘶石马,荆榛无(一作有)月泣铜驼。人间富贵皆如梦,不独兴亡感慨多。”花石纲指北宋末年宋徽宗事。为建“寿山艮岳”,宋徽宗在苏杭专设应奉局,搜罗奇花异石,用船队运往东京,连年不绝,号称“花石纲”。这里象征故都,随着鼎革异代,昔日的繁华不再,面对断垣残壁,作者忧从中来,恍惚中给人以物是人非的历史兴亡感,国之不存,家将何为?富贵荣华也随雨打风吹去,如梦如幻,整首诗基调感伤,苍凉而兴味悠长。
雅琥的游仙诗并不是很多,但写得非常有特色,并非谈玄虚空的游仙诗可比。游仙诗由来已久,三国时期曹操、曹植都有作品传世,而实开大宗者唯有郭璞,此后唐代李白、曹唐等人以其超脱的人生姿态偶有涉及,但从整体上而言,已经少有问津。就其内容而言,历代游仙诗中无外乎蝉蜕羽化、脱离生死、歌颂神仙境界等主题,特别是游仙与道教融合后,所谓的游仙诗基本上沦为道教宣扬教义的工具,功利性逐渐取代了文学性。雅琥的游仙诗上承郭璞,但因为融合了自己的身世而往往有着很强的现实感,如《拟古寄京师诸知己》。作者首句点出神仙福地之所在,“中天悬高台,上有仙人家。”非人力可攀,已与凡间隔开,然后作者对神仙福地的仙境做了详细的描摹,“云窗织流月,石磴凌飞霞。簾萦翡翠丝,壁粲芙蓉砂”。幽静脱俗,仙气十足,在这样的仙境中,仙人姿态悠闲,自由洒脱。如果仅止于此,可谓十足的游仙诗,但作者意不在此而在彼,写仙人仙境实为写现实,写自己。根据诗中的意思,作者此时正被贬谪在外,念亲怀远,落寞孤寂,“而我抱幽独,几年适蛮荆”,“种种履忧患,谁能念伶仃。”现实的味道冲淡了游仙的味道,游仙在这里只是徒具形式而已,裹藏着的则是作者一颗游子落魄的灵魂。
雅琥的送别诗在其创作的诗歌中占有相当大的分量,约占全部诗歌的1/2,也受到诗选家的青眼,如《留别凯烈彦卿学士》:“十年帝里共鸣珂,别后悲欢事几多。汗竹有编归太史,雨花无迹染维摩。湘江夜雨生青草,淮海秋风起白波。明日扁舟又南去,天涯相望意如何。”凯烈彦卿即色目人克列拔实,与诗人身世、经历、处境相似,全诗从同僚之谊、别后悲欢写起,作者淡淡的伤感体现了世事难料的无奈。可以说,这是阅世之深后的感喟,参透世事后的体验。在这些作者写给朋友和同僚的送别诗中,我们不难觉察其价值的丰富:诗歌体现了作者重情重义、感情真挚的性格,而且从民族的角度看,作为少数民族诗人,其所送别对象多为汉族友人,其友情超越了民族界限。李春祥先生在谈到元代民族融合时有言:“他们(汉族作家)对各民族出身的散曲作家和戏剧作家都能一视同仁而不厚此薄彼,畏兀儿族作家贯云石为《阳春白雪》作序,还有各民族作家之间的酬唱往来,都可以说明民族融合已是必然的历史趋势。”[5]雅琥于此堪为师表。如“客心恋恋不忍发,离歌莫唱《阳关》叠。”(《送御》史王伯循之南台》)“月漉漉,泥在水。送君归,几千里。”(《赋得月漉漉送方叔高作尉江南》)“契阔山川将万里,飘零岁月又三年。”(《寄南台御史达兼善二首》)“北上函香去,西南致礼勤。”(《送赵宗吉编修代祀西岳》)等等,或叮咛、或祈祷、或祝福、或盼望等,都包含着作者的一番深情厚谊。他的悼亡诗《鄢陵经进士李伯昭墓》、闺思诗《大堤曲》、咏物诗《二月梅》都能够怀揣人情、寄托遥思、发自心扉、感情真挚,诗歌的传统题材在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笔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拓,雅琥在不景气的元代诗坛上应当占有一席之地。
三、“宗唐得古”的艺术风尚
元人论诗,多崇唐绌宋,主张风雅之义,浑厚之格,诗风温柔敦厚,虞集有言:“所谓温柔敦厚之教,习与性成,庶几学诗之道也。”(虞集《郑氏毛诗序》)王礼论诗:“古者风俗淳美,民情和厚,故发于声诗,虽下至闾阎畎亩,羁夫愁妇,无不由乎衷素,当歌而歌,当怨而怨,其言皆足以动人。”(王礼《魏德基诗序》)雅琥的诗歌主张见于许有壬《至正集》卷73《跋雅琥所藏鲜于伯机词翰》:“鲜于伯机诗,予知之已四十年。吉甫段君慨言:人知其书,诗则知否相伴。予方自幸在知者之中。而夷陵监郡雅琥正卿知之虽晚,爱之甚笃。正卿素言:晋后虽有书,终不能如晋;唐后虽有诗,终不能如唐。……予非好胜,窃喜因正卿之言,使不知伯机之伴,行皆左袒,且以释吉甫之慨焉。”由此可知,雅琥论诗实不出“宗唐得古”之藩篱。
第一,与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相比,雅琥的诗歌内容充沛,现实性很强,确实一扫宋诗之弊,在创作上更趋向于唐人,而不斤斤于“琢句之工”。其咏史诗,能够做到将主观之情与客观事实融合起来,在对历史的凭吊中抒发个人感喟,既有情感浓度,又有历史厚重。如《秦淮谣》:“天险淮南纪,犹隔秦淮水。水上石头城,城头更戍兵。如何爱歌舞,坐待韩擒虎。璧月委琼姿,欢娱能几时?”全诗围绕着陈后主耽于歌舞,荒于政务铺展开去,意在抒写殆政亡国的道理。全诗平实,脉络清晰,毫无晦涩之感,虽写历史往事,但处处立足现实,引人深思,令人警醒,对于统治者更具有借鉴意义。其游仙诗也往往能够于仙乐仙境中点破,将现实生活引入进来,在鲜明的对比中表达个人情绪,明写仙,实写人,看似浪漫,实为最为深刻的写实,前引如此,他者也然。如《洛神》:“邺宫檐瓦似鸳飘,兰渚鸣鸾去国遥。漫说君王留宝枕,不闻仙子和琼箫。惊鸿易没青天月,沉鲤难凭碧海潮。肠断洛川东去水,野烟汀草共萧萧。”作者借曹植《洛神赋》的题意生发点染,因其题材本身带有凄艳的色彩,故而其所虚构的仙人仙境也哀婉感伤,尤其是“肠断洛川东去水,野烟汀草共萧萧”句,给人以物是人非的兴亡感,以上的确可引曹植为同调。其写景诗不多,由于作者身世坎坷,仕途多舛,宦海沉浮中难免萌生隐然林泉、遁迹田园之念,但人在江湖,往往并不如意,写景咏物也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自己对现实人生的思考和焦虑,如《七星岩》:“漓水东边三四山,何年北斗下人寰?天文暗宅蛟龙窟,地脉潜通虎豹关。碧藓自封岩径杳,白云不锁洞门闲。何时得遂烟霞趣?来此幽栖结大还。”作者驰骋想象,天上地下,纵横往复,极尽形容,将七星岩的气势描绘得淋漓尽致:“何时得遂烟霞趣?来此幽栖结大还。”末联点题,道出了作者意欲归隐的念头,如果联系作者远谪在外的实际,此句不无深意,但作者写来韵味悠长,非有相同经历者不能道也。雅琥诗歌无论题材取向大小,都非不食人间烟火般肃穆;相反,处处都闪现着社会现实人生的影子,体现着作者自己的评判与思考,淡淡写来,娓娓生动,这点在刚走出宋诗桎梏的元代文坛难能可贵。
第二,诗风刚健有力,浑厚天成。元代诗歌就其风格而言往往给人纤弱秾缛有余,而刚健不足的感受,衡量其他诗人倒无不可,但之于雅琥似乎应当别论。雅琥虽有清丽柔美小诗,但总体而言往往以豪放为主,比如《题周昉<明皇水中射鹿图>》,起句“开元天子奋神武,一矢功成定寰宇”,大处着笔,格调不凡,总括出唐明皇于乱世力挽乾坤的魄力,以下诸联依次写李隆基诛灭韦氏及其党羽,姚崇以“马前十论”获得重用等等,气势磅礴,笔走龙蛇,也突出了画家周昉画技之高妙,能够再现昔日唐明皇神姿,但作者诗意陡转,以“君不见”三字引出一代英主晚年荒淫失政,“天宝年来事事非,宫中行乐昼游稀”,结果酿成安史之祸,国家隆盛的局面一去不复返,“可怜野鹿衔花去,犹向樽前按舞衣”。今昔对比,转合跌宕,大起大落,欲抑先扬,整首诗前者雄武后者悲怆,巨大的张力无疑给人以劈头棒喝之功效。再如《送赵宗吉编修代祀西岳》:“北上函香去,西南致礼勤。蜀山千丈雪,秦岭万重云。驿骑鸣金勒,宫袍粲锦文。白头抱关吏,自羡识终军”,将路途艰难与对朋友的勉励结合起来,意气奋发,格调高亢,能于逆境中健笔出之,道人所不能道或不敢道,颇能见其胸襟之大,诗史上并不多见。检索唐诗,唯有王勃、高适、王维等人与之并列,如此来看雅琥为其后昆也不为过。明代胡应麟《诗薮外编》卷6《论元诗》除马祖常外,对雅琥褒扬颇多,尤其对其《送赵秉彝亲迎江夏之官临川》一诗赞赏有加,称其“句格庄严,词藻瑰丽,上接大历、元和之轨,下开正德、嘉靖之途。”[6]其着眼点也正在于此,这在明人看不起元人诗歌创作的风气中实为罕见。
第三,明快易懂,饶有民歌风味。周绍祖《西域文化名人志》“雅琥”条中说雅琥之诗“内容比较广泛充实,歌调明快流畅,富有民歌风味”[7]。庄星华《历代少数民族诗词曲选》中也评其诗带有民歌体的特点,清新自然,颇有风味[8]。从民歌中汲取养料并运用于诗歌创作的确是雅琥诗歌的一大特点。应该说,中国诗歌发展的源头本自于民间,《诗经》中的国风大多数采自田间地头,汉魏乐府、南北朝诗坛中民歌都占有相当的数量;正因为民歌不加修饰、雕饰天然、率口而歌,故而明白如话、质朴自然,很多优秀的诗人从中获益匪浅,唐代李白、白居易、柳宗元等都有仿效民歌的优秀作品传世。雅琥“宗唐”,但不泥于唐,能于唐人诗歌中领悟到“真诗在民间”(李梦阳《诗集自序》)的道理,在当时宗唐学唐诗人中可谓佼佼者,就此一点,也当大书特书。比如《大堤曲》:“郎家大堤上,妾住横塘曲。年少结新欢,离别岂所欲。日日望郎归,门前春草绿。嫁时双明珠,系妾红罗襦。纂制远游履,愿谐比目鱼。路长不可数,搔首空踟蹰。”《大堤曲》本乐府西曲歌名,相和歌辞,内容多写男女爱情。雅琥的这首《大堤曲》同样没有超脱传统题材,但写得同样明快清新,将少女恋爱、离别、思念、渴盼等诸多心理变化刻画的细腻生动,如果与南朝民歌中的《西洲曲》、《子夜歌》等加以比较,不难看出雅琥之诗有临摹之痕,甚至有些句子也径直拈自于前人,但作者能够为我所用,依境组合,贴切自然,已非生硬拼凑者可比,可见作者高妙。其他如《秦淮谣》、《赋得月漉漉送方叔高作尉江南》等都是作者虚心学习民歌创作完成的优秀篇章。顾嗣立《寒厅诗话》中将其与逎贤、余阙、泰不华等人并称,同为新声艳体,“并逞才华,极一时之盛”,确为肯綮之言。
合而论之,雅琥在“宗唐得古”实践中,其诗歌内容因为重视写实性,所以也就基本上摆脱了无病呻吟、为文造情的不良习气,重新恢复诗歌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诗风上也一扫宋诗由于过分讲究法度而造成的几近骫骳之病,以刚健有力的气势为当时的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力;虚心学习民歌,抒发真情实感,质朴自然,也防止了堆砌典故炫耀学问,粉饰空虚故作高深的弊端。雅琥的诗歌创作力所能及地实践了他的主张。
四、宗教意味的缺失
需要说明的是,雅琥的诗歌与汉族文人诗歌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这就是说,作为色目诗人,雅琥的诗歌当中的民族成分难以辨别;同时从宗教信仰看,色目人信仰天主教,宗教文化对于人的影响不言而喻,但是雅琥诗歌中看不到这些,正如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雅琥”条中不无感叹地写道:“可惜元代也里克温诗人没有留下带有宗教气味的诗句,令人浩叹!”[9]荡然无存的宗教意味,之于汉族文人诗歌并不足奇,但之于民族作家来说倒是值得思考的事情。
实际上,雅琥并非孤例。这是因为元代社会暗流涌动,儒家独尊之局面已经日落西山,但从本质上看仍然属于封建社会之一环,治国仍然离不开儒家。尽管靠着铁骑及骁勇灭金攻宋,但是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被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10]虽然元蒙的势力范围扩及全国甚至世界其他地域,但起自草原的文明与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农耕文明之间的冲突并未随着一个朝代的覆亡而终止。妄图变良田为牧场无疑于痴人说梦,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云:“自太祖西征之后,仓廪府库,无斗粟尺帛,而中使别迭等佥言,虽得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公即前曰:‘夫以天下之广,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但不为耳,何名无用哉!’”一些对于中原文明知之甚深的统治者意识到儒家文化的摧之弥坚,如要真能一统江山,儒家作为治国理念是不可舍弃的,比如耶律楚材,《元史》本传云:“夏人禅巴沁以善造弓见之于帝,因自矜曰:‘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须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制器者必用良弓,守成者必用儒臣,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窝阔台即位,耶律楚材“时时进说‘周孔之教’,且谓‘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上深以为然。”(《湛然居士文集》卷1《和李世荣韵》)在其推荐下,汉儒陈时可、赵昉等人充十路征收课税钱粮,儒学治国的成效使窝阔台意识到“周孔之礼”、“圣贤之言”的重要,尊儒隆孔,封孔子后裔为衍圣公,宣布“孔子之道,垂宪万世,为有国家者所为崇。”“元兴百年,上自朝廷内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经能文显著当世者彬彬焉,众矣。”(《元史》卷189)两种文化的撞击最终以草原文化的败北而收场。“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已经经过数代儒者的完善与改造,成为历代封建统治的有效工具,它有着极强的稳定性、向心力和完善而缜密的思想体系。”[11]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之下,不少少数民族在东渐过程中心态也渐趋汉化,萧启庆有言:“蒙古、色目文士经由姻缘、师生、座主与同年、同僚的关系与汉族士大夫形成了一个超越族群的社会网络。在文化生活方面,蒙古、色目文士则透过唱酬、雅集、游宴、书画品题而参与汉族士人文化活动的主流”(《元朝多族文士圈的形式初探》)。由是元代诗坛成为一个包容性最为广泛的诗坛,诗人籍贯星罗棋布,有回鹘、西夏、吐蕃等等,甚至广被康里、克列、拂林、大食等数十个欧亚种族,涵盖了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等四大族群。
“民族融合的社会环境,在日常生活中也造成了一种汉文化的气氛,这是更有影响力、更为内在的辐射。这样的环境,使少数民族成员在不自觉中受到感染并接受其同化。”[12]所以在2种文化的撞击过程中,雅琥自身的民族文化经过儒学的改造、浸透,逐渐淡化是很自然的事情,这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基督教色彩渐为儒学元素所替代,进而内化为自己意识的一部分,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五、结 语
作为一个色目诗人,雅琥在元代文坛上做出了杰出的成就,受到后代文人的赞誉。但是由于其留下来的生平资料很少,加之其诗歌散见于后代文献当中,所以,一度为近现代以来治文学史者所忽略。于是也就将雅琥置于一个极为尴尬的处境中:赞誉肯定与冷落忽视。实际上,雅琥的成就值得我们关注,其诗学思想、人生态度及其对儒学的传播、民族诗学的接受等等,都应当深入挖掘,其意义不仅仅止于文学本身,特定的时代、民族、宗教等诸多元素的介入决定其价值的丰富。对于这样一位作家,我们没有理由忽视他。原因在于少数民族作家进行汉族文学创作,本身就具有多元的文化意蕴。
[1] 马建春.元代东迁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2] 陈 垣.元西域人华化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 杨 镰.元诗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4] 顾嗣立.元曲选[M].北京:中华书局,1958.
[5] 李春祥.元人杂剧反映元代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J].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47(2):20-25.
[6] 胡应麟.诗薮外编[M].山东:齐鲁书社,1997.
[7] 周绍祖.西域文化名人志[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8] 庄星华.历代少数民族诗词曲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9] 方 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1] 赵嘉麒,范学新.论哈萨克族思想家不忽木父子对儒学的贡献[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2(1):120-123.
[12] 杨泉良.少数民族作家元曲创作繁荣的原因[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7(2):92-94.
Semu poetYahu in Yuan Dynasty and his poetry
ZHU Yang-dong1,2
(1.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ShandongNo rmalUniversity,Jinan 250014,Shandong,China;2.School of Humanties and Science,YiliNo rmalUniversity,Yining 835000,Xinjiang,China)
The personal information of Semu poet Yahu in YuanDynasty can be seen inmany historical documents.The author in thispaper investigates hispersonal infor mation and creation of hispopetry.W ith the help of these data,the paper classifies the cont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is peotry and has found that theywere of high quality at that time.The paper,at last,discusses the reasonswhy hispeotry have the features of Confucianis m.
Yuan Dynasty;Yahu;poetry;Confucianism
I222.7
A
1671-6248(2011)02-0092-06
2010-12-24
朱仰东(1979-),男,山东郓城人,伊犁师范学院讲师,山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