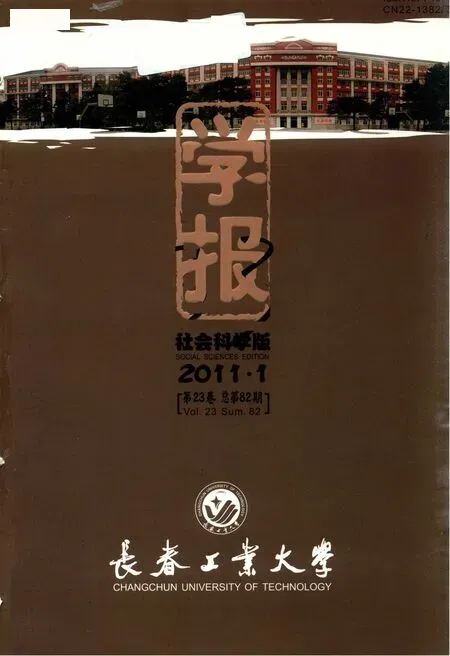真实与虚幻:历史与个体的另类关注
——论《蛙》的叙事艺术
文 娟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真实与虚幻:历史与个体的另类关注
——论《蛙》的叙事艺术
文 娟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虚实相生形构的张力是《蛙》叙事艺术的核心质素,它包括以下三个向度:跨文体联用的虚实张力、平实叙述与魔幻铺排幷置的现实主义式虚实以及“文史互现”式虚实。三者共同营造的叙事场不仅推动着故事的时序进展,而且演绎出了生命和历史诠释的多样性存在。
《蛙》;叙事 ;真实 ;虚幻 ;张力
以“重述历史”为风旗的小说创作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版图中是一个耀目的存在。它代表着一种特殊的美学,即对原有的国家宏大叙事进行颠覆和解构,从而呈现出另类的历史与个体。莫言是这一文学风尚的领军人物,2009年推出的《蛙》凭借叙事上的特色,成为这一序列中的特异存在。文本由叙述人蝌蚪写给日本名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信建构而成,融书信、小说、话剧体式于一炉,在平实的叙述之中穿插夸张荒诞的场景、神秘的民间传说、如梦似幻的话剧等魔幻质素,虚实相生的叙述策略弥漫文本的各个肌理层。跨文体叙述构筑的文学化历史与史书记载的正史间的张力更生发了叙事背后的文学性意义。这种阶梯式推进的叙述结构摹写了乡村妇产科医生姑姑几近六十年的人生经历,并由此勾连出整个高密东北乡六十年的计划生育史,在史的回溯延展中铺排出各色人等的悲欢离合式生活场景,历史与个体复杂缠绕的本真存在也得到了另类的摹写。从虚幻与真实所生成的意义场域角度来看,笔者认为《蛙》文本的叙事特色及意义值得深入剖析。
一、书信、话剧、小说间的文体虚实张力
《蛙》是由叙述者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信建构而成的小说文本,可归入书信体小说的范畴。书信体小说早已有之,而《蛙》的特别之处在于:第五封信的主体内容被巧妙地设置为一部完整的多幕话剧,从而给接受主体造成了强烈的阅读冲击。不管是前四部分的书信体故事,还是第五部分的话剧创作都充斥着虚实相生的种种质素,作为两种不同风格的文体,共同营造了文本肌理表层的虚实相生的叙事结构。
书信体小说的特征之一,即“采取现实生活中使用的书信形式,具有极强的仿真性”,[1](P25)但书信体式亦使写信人,即叙述者获得了极大的叙述自由,可以依据个体喜好进行筛选,随意讲述记忆河流中个体感兴趣的人和事,甚至在某些方面会进行人为的加工修饰。获得解放的叙述者如同全知全能的上帝一样,不受事件发生发展因果链的钳制,自如地对故事进行跳跃式讲述,甚或穿插评说。此外,其还可以依据讲述故事的需要,策略地幻化为故事中的其他人物。这不仅使得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受到破坏,故事的真实性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质疑。比如父亲在第三部分讲述“我”缺席时关于姑姑抱病搜捕王胆的事情,王肝在第四部分第三节讲述他和秦河的生活,姑姑在第四部分的第四节讲述嫁给郝大手的原因,他们都在不同的情节中充当了叙述人。不同人物随时幻化为叙述者是一把双刃剑,在提供真实可信的现身说法之外为故事整体性的真实底色又添加了了一份令人起疑的因子。书信作为文体的一种,要求其讲述的内容要真实,受此限制,前四封信在以真实的个体经历为资源,讲述乡村妇科医生姑姑、剧作家蝌蚪等人的故事时,对于涉及外部世界的尖锐性描述时就不得不有所收敛。
话剧作为文学创作的一个文类,本身就具有虚构的特质。文本第五部分的话剧体式,不仅对前四部分讲述的真实性故事进行了细节的完善补充,而且还在互文性的比照之中,借用艺术虚构的权利把小说要挖掘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史中出现的各种复杂尖锐的问题机智巧妙地传达出来,更把小说人物贪婪自私而又不缺乏向善的卑微灵魂展示了出来。话剧体式自身的虚实相生质地在此凸显。
总而言之,书信、话剧这两种文体的巧妙链接,不仅使得故事的真实性和人物的栩栩如生性令人过目难忘而又反思良多,而且使得事件的惊心动魄、问题的复杂尖锐亦有了真实的底色和虚构的保护衣。二者之间虚实相生的张力推动着故事讲述的时序进展,而且开启了文本肌理深层的虚实相生结构。
二、游走于平实叙述与魔幻铺排间的现实主义式虚实
《蛙》乃书信体小说,其整体的语言风格是娓娓而谈的絮语式,整个故事的叙述基调为朴素的现实主义。但叙述人蝌蚪在平实拙朴的叙述之中会闪现式地穿插夸张荒诞的修辞手法,这使得接受主体在人物形象的细节刻画和残酷事件的场景设置中的拟真感受被阻断,小说的虚构质地自然凸显。第一部的第六小节在叙述大哥作为运动健将善掷铁饼时举了这样的例子:吃过肥羊尾巴,回校后有劲没处用的大哥随手捞一铁饼,用力一撇,铁饼竟然穿过校园围墙飞到庄稼地,碰巧落在正耕地的牛的牛角上,并把牛角给齐齐斩断;无独有偶的是第二部第二小节在刻画新娘王仁美的纯真憨直时有如此的细节:赤着两只大脚的王仁美在不足两平米的小炕上踮起脚尖转圈、跳跃,脑袋把纸糊的天棚顶得“嘭嘭”响,面对婆婆炕塌了哪里睡的挪揄问语嬉笑着回答睡地上。这样漫画式夸张的细节刻画让整体叙述中的真实平凡的邻家大哥、小媳妇形象罩上了一层神奇的面纱,似是生活中的这一个又不是这一个,真实与虚构的张力引逗着读者继续阅读的兴致;在河上追捕耿秀莲和王胆的两个血腥场景中同样运用了荒诞夸张的修辞手法。怀孕五个月的大肚子耿秀莲能够借助一块西瓜皮的屏障在河面宽阔的河流中凫水前行,企图躲过被送进乡卫生院流产的命运。开着机动铁皮船的计划生育工作者们,在后边悠闲地观看说笑着,并用高音喇叭给想要逃脱追捕的孕妇施加心理压力。这样的场景与之前的东风村恶斗和随后的一尸两命相比是那么的轻飘和怪诞。阴雨连绵、河水暴涨时节河中追捕王胆的场景与此异曲同工。但夸张荒诞的场景和语言却无法遮蔽死亡的沉重气息,真实与虚幻幷置的叙事策略背后是对生命卑微、人心冷酷和生活荒诞的存在式显现。
文本第二部的第三节在叙述民间泥塑艺人郝大手出场时插入了他制作泥娃娃贩卖泥娃娃的神奇传说。郝大手的泥娃娃是用手捏出来的,一个一摸样,绝无重复,高密东北乡的每个人都能在泥娃娃中找到小时候的自己;他卖泥娃娃时眼中含泪,似是卖自己的孩子,在仔细端详买者后,伸手从盖着小被子的车篓中朝外摸,摸着那个就卖给你那一个,且拒绝更换;买了他的泥娃娃,用红绳拴着脖子放在炕头供奉,生出来的孩子就会跟泥娃娃一个模样。这样的神秘传说在高密东北乡广为流传,其原因颇值得探究。神秘传说不可能脱胎于日常生活中的真实事件,也不可能是饭后茶余的纯粹无稽之谈,依据王仁美对此的笃信、王肝对马槽中的大师秦河制作泥娃娃的梦境奇遇进行的夸张式讲述以及第四部伊始就描述的娘娘庙的繁盛景象,可以判定类似的神秘传说和求神拜佛是村民们表达他们生子以延续宗族血脉的一种文化吁求。文本借用平淡、细腻、真实的叙述策略对村民传宗接代的生育文化心理进行了细致传神的描摹。但民间传说、求神拜佛等充满神秘魔幻色彩的元素的介入,再次刺破真实的幻觉,使读者意识到这是虚构的小说,并在真实与虚构的张力中恢复思考的能力。读者会用主体理性来体味中国式生育文化的痛处,思索生育文化的成因、流转和衍变,甚而拷问自身是否为这一文化痼疾所宰制,在反思之中探索更为健全的人性化的生育观念。
文本叙述形式上的虚实张力还有许多。如蛙作为一个意象的运用,蛙不仅在寓意上指涉娃,勾连娲,推及生育,还衍生为姑姑害怕青蛙的一个魔幻心象。文本中一系列关于蛙的描述为书信体的平实叙述插上了超现实主义的翅膀;第五部话剧中关于魔幻铺排的叙述更是数目颇多:二十一世纪的公安派出所所长说出状子本官接了一定会转交包大人的台词,电视剧《高梦九》的摄制组竟然假戏真做地开堂审案,未曾生养过孩子绝了经的五十多岁的小狮子竟然分泌出旺盛的乳汁等等。总之,这些文本形式层面的虚实叙述在阻断读者拟真感受、引发本体性思考的同时,还为文本内容层面的虚实叙述层面编织了美丽诱人的外衣。
三、小说叙述与正史记载间的虚实互现
《蛙》是一部小说,就文本体式而言具有虚构性。然而,叙述人却用了几近真实自传的书信来讲述故事,刻画人物,展示乡村计划生育史。故而,文本中那些人那些事构筑的高密东北乡六十年生育史便被涂抹上了真实的色彩,这与正史记载的新中国计划生育史,天然地产生了相互比照勾连的一面,在文本深层蕴指的肌理层形成了一个虚实相生的结构系统。以陈寅恪先生文史互证的治学方法为切口对这两种同谈计划生育史,而文体迥异的文本进行考量,也许可以洞察出别样的历史和个体。
文本用大量的细节叙写了高密东北乡六十年的生育史,可简略勾勒如下:
1953年至1957年由于国家处于生产发展、经济繁荣的好时期,高密东北乡新生儿数量激增。
1961年春至1962年秋,因为饥饿,全公社没有一个孩子出生。
1962年秋,高密东北乡地瓜大丰收,几近三年的饥饿一去不返,生理机能恢复正常的人们又开始了旺盛的生育。至1963年初冬时,高密东北乡降生了2868名婴儿,此地建国后的第一个生育高潮来临。
1965年底,人口急剧增长,中央意识到人口膨胀的压力,计划生育政策提上日程。政府不但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而且采用多种方式宣传普及计划生育知识,批判重男轻女思想,还给育龄妇女免费发放避孕套和避孕药。新中国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掀开了大幕。
1970年夏天,姑姑率领小狮子和黄秋雅乘坐着由秦河驾驶的铁皮机动船到民风彪悍的东风村动员严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张拳老婆到公社流产。蝌蚪亲眼目睹了河上追逮张拳老婆的全过程,最后的结局是耿秀莲死亡,一尸两命。此事例可证明文革时期,基层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力度并未放松。
1979年,在蝌蚪与王仁美结婚之日,姑姑讲的一段义正言辞的话语充分表明高密东北乡的计划生育运动依然如火如荼。全国上下贯彻落实一对夫妻一个孩的生育原则,计划生育政策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
1983或1984年时,忠实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姑姑,率领计划生育工作组追捕违规怀孕的王仁美和王胆。最后的结果依然悲惨,王仁美一尸两命,王胆则在产下不足月的女儿陈眉后死亡。这两个悲惨的事例足以证明80年代中期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时的严苛和血腥。
政策执行的力度虽然很大,但秉持生男孩传宗接代观念的广大民众偷生超生的行为并未被杜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黑孩子”的数量肯定相当的惊人。这批“黑孩子”的户口问题,在1990年第四次普查人口时终于得到了解决,有“黑孩子”的家庭为此支付了巨额的超生罚款,但这些钱到底有几成进了国库,却是无人能算清楚的糊涂账。最近十几年来,又有多少这样的“黑孩子”出生,估计又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现在的罚款是二十几年前的十几倍。由此可窥见整个九十年代高密东北乡的计划生育政策依然存在,但似乎已不很严苛,其主要靠重罚来节制超生。
2008年左右的生育现状则是:有钱的罚着生,没钱的偷着生,当官的让二奶生,计划生育政策仅作为罚款的依据而存在。[2]
现存史书对于新中国计划生育史的描述是何模样,它与小说的历史叙述有何异同?历史的原初到底是何模样?带着探究这些疑问的执着,笔者特意查阅了《当代中国的计划生育事业》和《新中国人口五十年》两书。它们关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提出衍变、执行力度手段及效用的记载基本相同,无任何实质性的差异。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颁布、贯彻执行的时序记载与小说文本中的叙述基本一致,从某一层面上来看,这也凸显出小说文本关于计划生育史叙述的真实性。但小说与史书对于政策执行过程和效绩的叙述则大不相同。
小说文本中铺排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过程可谓惊心动魄,三个追捕画面的细致描摹,把计划生育执行过程中的冷血和残酷展现得淋漓尽致。东风村动员张拳老婆去卫生院引产时,工作组与张拳的武力冲突,致使姑姑头部受伤,姑姑威胁张拳坐牢的言论迫使其妻耿秀莲现身,后河面搜捕以耿秀莲的一尸两命而告终;在搜捕王仁美时实行的株连四邻政策使得肖上唇对王家发出了恶毒的咒骂,其后来举报王胆藏匿在王家地窖的告密行为与这次被殃及铲掉风水树的场景息息相关。而四邻对王家大门的拳打脚踢甚至威胁放火烧门之举,则凸显出群众暴力的可怕,善良淳朴的民众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而又有所谓领导的支持时,人性中阴暗的恶魔暴力因子伺机而出;追捕王胆时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者们不仅再次运用发动群众的招数,而且关了陈鼻和他女儿陈耳的禁闭,甚至无视法规,私自动用公民的私有财产去做寻人补助之资。河面追捕的历史再次重演,王胆当场死亡,产下一不足月女婴陈眉。结果的些许不同依然无法掩盖政策执行时的浓厚血腥味。然而,史书对于新中国计划生育过程的记载压缩到了两百多字,仅对政策衍变进行了简短的叙述。对执行过程中的阴暗面只字未提,仅用走过了一条曲折而又光辉的道路来概括。史书对真实的无情筛选和简化记载有效地抹去了事件发生时的鲜活、残酷和血腥。两相对照,历史的虚幻与真实,吊诡地融为一体。
计划生育政策在高密东北乡的实施结果不仅仅是有效地控制住了人口暴增的局面,更为重要的是其还导致了不少农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四处流浪。政策实施的负面效果并不限于此,还应包括:乡村干群间的紧张关系、邻居之间的猜疑告密、恐怖的民众暴力、冷漠的看客等民间的阴暗质素的滋生蔓延。最为严重的则是其对正常人性的扭曲,由此给弱势善良的民众套上了沉重的心灵枷锁,使得他们在罪责的挣扎中卑微而又无奈的活着。
史书中关于计划生育政策取得成就的综述,一样经不起小说文本的质疑。姑姑作为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实施的执行者晚年不断的反省自己的罪责,供奉泥娃娃,帮助违反政策的人们生育,承认陈眉代孕之子为小狮子所产等行为完全看不到姑姑的生育观有何变更,小狮子关于孩子的言论和行动再次对这一说法形成了强烈的反讽。蝌蚪、袁腮、李手、金修、父亲等等,小说中的人们没有一个人的生育观和婚姻观得到了改变,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世界性好评一样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说法,西方人对于此政策的批评一直就没消停过;计划生育政策在现今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在小说文本中该是一个更大的嘲讽。
过程与效绩叙述两相比照充分显示出史书对历史事件的化约化、窄化处理质地,在具体的编码过程中又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宰制,故其记载的历史事件干枯而又充满了政治修饰语。正如小说文本中蝌蚪写给杉谷义人的信中所说:“但那是历史,历史是只看结果而忽略手段的,就像人们只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等许多伟大建筑,而看不到这些建筑下面的累累白骨。”[2](P145)但小说文本就不一样,它不仅写结果更写手段,其对历史事件的叙述细致、完整、鲜活。因此要真正了解历史的本真时,只看官方史书是远远不够的,对小说文本的适度研读可为真相的揭示提供有效的资料。
陈寅恪先生“文史互证”的治学方法,本意是用史家的眼光考量诗文,为史寻找新材料,以期把握更加全面真实鲜活的历史。笔者拿史书中的计划生育书写与小说勾勒的生育史比照用意却不在与此,亦不在于批评历史文本的失真和冰冷,而在于用新的眼光去阅读小说和历史、用学识和睿智去阐释文本、思考人生。笔者认为与其说是文史互证不如说是文史互现,在鲜明的比照中,挖掘史书与小说两种文体关于虚实的张力性描述,真切地感悟作为文学的小说在建构历史时的人道主义立场,关注历史场景中的各色人等如何地生活,体察人在外界环境形塑过程中如何的顺从与抗拒。小说的历史叙述用虚构的形式讲述真实鲜活的历史,用丰富的细节彰显人性在历史进程中的原初延展,但历史事件的真实展示不是小说家的职责所在,其对复杂人性的描摹刻写、剖析拷问才是文学存在的真义,小说文本存在的理由亦源于此,小说的历史叙述与现实史书记载的正史间的互现性虚实的意义同样在此。
[1]张鹤.虚构的真迹——书信体小说叙述特征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莫言.蛙[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
文娟(1981-),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200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