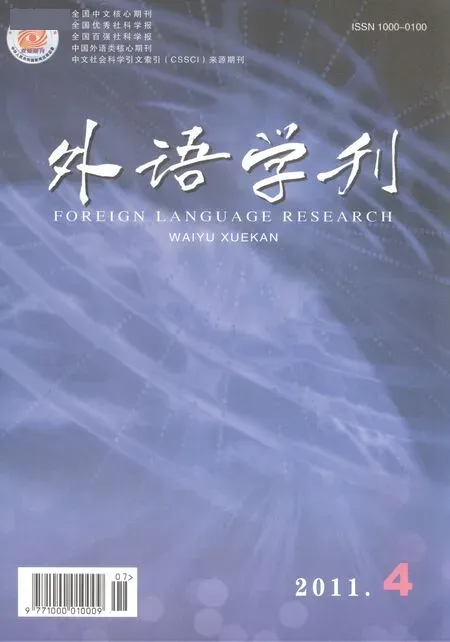俄国小说的起源*
白文昌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150080)
1 问题的提出
19世纪20-30年代,俄罗斯文学如沉睡几百年的火山一般突然爆发,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辉。无论从作家队伍还是从作品数量讲,俄罗斯文学在这一时期取得的成就大都发生在小说领域。正如别林斯基所说,“今天,整个我们的文学都变成了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打倒了一切,吞没了一切……什么书最被人们爱读和争购?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什么书使文学家在旦夕间致富,获得房屋和田产?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什么书记述着人类生活、道德规律和哲学体系,总而言之,所有一切学问在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别林斯基1996:120)。然而,俄罗斯文学史还有一个事实让人感到奇怪,那就是俄罗斯在19世纪以前没有一部像样的小说作品。关于这点他们自己也直言不讳。
“当时的文学主要是从法国文学翻译过来或者加以改作,至于取材于俄国生活的独特的创作,就差不多没有了。”(高尔基1979:5)俄国文学的这种状况使别林斯基发出感叹:“俄国文学不是土产的而是移植过来的植物……我们的中篇小说开始的不久,真是不久,即从本世纪的20年代起。在这之前,它是由于奇想和时髦而从海洋彼方搬来,强制地移植在本国土壤上的异邦植物。玛尔林斯基君是……它的首创者。”(别林斯基1996:134)如果别林斯基把玛尔林斯基称为俄国中篇小说的首创者,还不完全是从文学体裁发展角度出发所作的严格学术阐述,那么弗里德林德尔(Фридлендер)在其主编《俄国长篇小说史》中说,“俄国文学中的长篇小说在18世纪中期出现……第一个长篇小说作家是艾明(Эмин1735-1770)”(Фридлендер 1962:47)。这是一个文学史家和文艺理论家在苏联科学院出版的权威著作中的论述,是严格从文学体裁发展的角度做出的学术定论,他们认为在18世纪中期以前俄国没有小说。那么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
2 小说概念与分类
在溯源俄国小说之前,有必要先就“小说”概念统一认识,因为对“小说”这个文学中的后起之秀,不同阶层、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人们的认识都不同。
“小说是一种文学体裁。通过一定的故事情节、典型环境的描写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来概括地反映社会生活,揭示社会本质。按其篇幅和内容的广狭,可分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小小说等。”(董大年1988:877)这一定义在我国已经取得比较一致的认可。例如在最通用的汉语工具书《新华字典》、《辞海》、《文学词典》(1983)和《文学原理新释》(顾祖钊2000)等中都有相似解释。可是当我们用俄语表达“小说”概念时,却遇到困难:在俄语中找不到与汉语“小说”概念等值的甚至相近的词汇。俄语中表示小说的词有 роман(长篇小说)、повесть(中篇小说)和 рассказ(短篇小说),它们都与汉语的“小说”不对等。俄罗斯通常用的проза(散文作品)也与汉语“小说”并不完全吻合,因为:(1)中国与俄国区分文学作品类别的方法不同。俄国采用西方流行的三分法——根据反映社会生活时塑造艺术形象的不同方式和特点,把文学分为3大类:叙事文学、抒情文学和戏剧文学。而中国习惯采用四分法——根据作品结构、体制和语言运用等特点,把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4种体裁。(4)中国按照“以对人物、情节和环境的具体描绘去反映社会生活”这一小说创作的根本特征抽象出“小说”这个较大的类概念,“根据作品篇幅长短、容量大小、情节繁简、人物多寡”分出了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等几个从属类。俄国“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同游记(путешествие)、政论(публицистика)等一样,都是从属于叙事文学的几个平行体裁”(Волков 1994:130)。
中国人研究小说时求同存异,强调作品在结构、体制和语言运用方面的相同点,把不同仅归于篇幅、容量、繁简等形式因素。俄国人不同,他们从三分法角度出发,强调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不同。例如,利哈乔夫(Д.С.Лихачев)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读长篇小说,读者主要是在对小说主人公命运的思考中自己得出结论;而读中篇小说,读者的思路大都由作者引导……所以,中篇小说往往比长篇小说篇幅短、人物少、目的明,对人物命运的叙述较少、情节紧凑激烈”(Кузьмин 1984:3)。库兹明(А.И.Кузьмин)就此问题发表论述:“短篇小说一般只讲一件事,这是它的中心,情节比较集中、紧凑,让人阅读和理解起来有一气呵成之感;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一般围绕一个人讲述几件相关的事情;长篇小说一般反映一个时代或人的一生,中篇小说却往往局限于几件个别的、有时非常重要的事件、情节,由它们构成人物生活的某个时段;长篇小说描绘几个人的生活,而中篇小说常常只描写一个人物以及他周围人物的生活;长篇小说中复杂而紧张的情节交织在一起,事件的展开气势磅礴、紧张激烈;而在中篇小说里,情节的发展往往平淡、和缓;尽管不能根据作品的篇幅划分它属于哪种体裁,但中篇小说的篇幅往往比长篇小说短。篇幅决定情节安排和材料使用,中篇小说的重心往往不在情节发展,而在对人物内心的刻画,对自然景物等的描写”(Кузьмин 1984:5)。
两位俄国学者在论述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的不同时使用大量感性、模糊、量化的概念。比如利哈乔夫使用“大都”、“往往”、“较”等;而库兹明多次使用“一般”、“往往”、“常常”等。这些词语本身表达的概念模棱两可,缺乏科学研究需要的严格和清晰,不适合学术概念的区分和界定。很难根据这些标准判定某个作品是长篇还是中篇:(1)有些作品无论从篇幅、人物,还是情节上看,本身的“体裁”特征十分模糊。比如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我们既可以把它看成格里尼奥夫个人生活中的“几件个别的、……非常重要的事件、情节,由它们构成人物生活的时段”(中篇特征),也可以看成“反映一个时代或人的一生(普加乔夫和他的时代)”的作品(长篇特征),作品的篇幅也很难说是大还是小。在确定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的体裁时也会遇到相似问题。(2)即便考察那些在体裁归属问题没有任何争议的作品,上面提到的那些标准也不具备多大的操作性。例如,为什么不能说《静静的顿河》不是围绕一个人物描写他生活的某个时段?因为整部作品围绕哥萨克青年葛利高里展开,而其他人物都是主人公周围的人;况且作品的确只写了葛利高里生活的一个或者几个片段,因为当故事结束时,主人公只不过是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相反,从拉斯普京(В.Г.Распутин)的中篇小说《活着,可要记住》我们到是读到了安德列和纳斯焦娜可悲而短暂的一生……
所以,俄国学界对于把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作为3种独立的文学体裁这种分法并不十分严格,值得商榷。对此,他们自己也有坦率的论述。库兹明就说过,“文艺理论对于把中篇小说作为一种体裁,对于它和长篇小说的区别没有明确的界定”(Кузьмин 1984:6)。”……显然,现在使用的这套术语需要重新考虑,进一步明确”(Вавилов 1975:368)。俄国学界关于小说的这种认识与我们的观点何其相似!
以往,俄国学者一般都把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作为独立文学体裁研究,比如《俄国长篇小说史》(1962)、库兹明的《现代俄国中篇小说》(1975)、辛年科(Синенко)的《当代中篇小说》(1971)和别林斯基的《论俄国的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等。这种研究自有其价值,不必赘言。但它没有把小说作为一个整体纳入其分析视野,忽略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整体特征、演变过程、发展规律等许多层面的考察,难免失之偏颇。既然无法在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之间划出一条明确、定性的分界线,不妨换一个角度,把它当作一个整体考察,相关研究也许会更全面、更客观一些,会看到一些处于俄国人视角盲区的东西。本文把一个相对“中国式”小说概念引入俄国文学研究,考察俄国小说如何丛萌芽走向成熟。
3 溯源与考证
如果文艺复兴运动标志着欧洲诸国近代文学繁荣的开始,那么俄国文学直到17世纪末才结束中世纪时期。17世纪,俄国发生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表明俄国社会生活开始从中世纪向新时期过渡。第一,在人们意识中,君权神授的观念开始动摇。自1598年留里克王室中断以后,皇位不断更迭,甚至三番五次出现自称为王者。“这种‘称王游戏’反映出人们思想意识中一个原则性的进步:人们不再相信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沙皇,他体现上帝的意志”(Лихачев 1980:335)。1598 -1613 年在俄国历史上被称为“混乱时期”。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忙于争夺王位的政治斗争,无暇顾及思想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放松对人民的精神控制,出现一个无“书刊检查”的时代,作家的意志不受文学外其它因素影响,直接体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作家开始自由安排作品中人物的行动,摈弃中世纪传统“要么是圣人,要么是罪人”的模式,从而发掘出人物性格中丰富、复杂、矛盾的特点。第二,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与奴役日益加剧,广大农民的反抗情绪更加激烈。17世纪在俄国历史上叫做暴乱年代,1606-1607年爆发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波洛特尼科夫农民起义;1649年沙皇阿列克谢·罗曼诺夫颁布《法典》,农民被附着在地主的土地上,农奴制度在法律上完全形成;1667-1677年爆发更为壮阔的斯捷潘·拉辛领导的农民起义,农民首次作为重大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阶级斗争历来是影响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与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相适应,17世纪的文化也一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具有很强的反叛意识。50年代尼康的宗教改革给俄国单调的社会文化生活以沉重打击,结果是正教罗斯分裂,大约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人保持旧的礼仪习惯。第三,在俄国的经济生活中手工业和商品生产显著增长,出现标志资本主义萌芽的工场手工业,商业活动密切各地间的联系并逐渐形成全俄统一市场。第四,近代民族国家逐渐形成。列宁说,“在中世纪的莫斯科皇朝时代,国家不是建立在民族的联合上,而是建在地域的联合上,国家分成为一些领地或公国,仅仅在俄国历史的近代(大约自17世纪起),这一切区域、领地和公国才真正在事实上融合成一个整体”(曹靖华1992:18)。第五,由于民族国家形成,文化迅速发展起来:在莫斯科开办最初的学校,大量西方的世俗性文学作品翻译过来,俄罗斯文学中首次出现经过加工的西方骑士小说,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促进俄国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更新。对传统文学体裁重新思考促使一种全新的、结构复杂的作品出现,如带有浮士德式主题的《萨瓦·格鲁德岑的故事》。俄国出现了第一座剧院,文学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新现象。
与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相适应,17世纪文学也处在一个过渡阶段。它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中世纪文学束缚,但已经出现一些新倾向:
(1)内容上出现世俗化、个性化和民主化倾向。例如这时期最富有时代生活气息之一的《弗罗尔·斯科别耶夫的故事》。这篇故事的主人公不是什么虔信、有德行的圣人,而是机智甚至滑头和善于争取个人幸福的普通人。指导人物行为准则的不再是神的旨意和基督教的善恶观念,而是人对此世幸福的追求;个人从中世纪被视为群体部分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人物不再千人一面,表现出自己的个性。文学第一次把人描写成矛盾复杂的社会产物,把人的性格看成“善”和“恶”特性的结合。所有这一切都体现新时代对中世纪思想的背叛。
(2)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带有鲜明民主色彩的讽刺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谢米亚卡法庭的故事》。故事的上篇以滑稽喜剧的口吻讲述一个穷苦农民在遭遇一系列不幸时闯的“祸”;下篇讲述该农民被告上法庭后,如何机智地向法官谢米亚卡展示一块用布包着的石头,法官误以为这是向他行贿的暗示,作出有利于该农民的判决以及原告们为避免执行判决而向农民交付赎金的故事。另一篇有典型意义的作品是《棘鲈的故事》。它以童话形式,通过鱼类的拟人化行为,揭露大贵族巧取豪夺农民土地而逍遥法外的社会现实。这类作品能够批判社会贫富不均,揭露官场腐败黑暗,嘲笑封建制度“公正”。它们虽然无作者姓名,但可想而知,由小公务员、小市民等下层知识分子创作。这表明社会中民主阶层力量的壮大和民众社会意识的觉醒。
(3)出现虚构的人物和情节。在诗体故事《戈列·兹洛恰斯基》中,主人公没有名字,称为年轻人,用来概括当时整个青年一代。“这是俄国古代文学中第一个虚构的概括形象”(曹靖华 1992:21),表明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从一般实用体裁(历史、布道、书信、传记等)中分离出来了。
(4)文学作品中出现口语化和作品形式平民化倾向。受译介的西欧骑士小说和冒险小说的影响,文学作品中虚构的、引人入胜的情节大大增加。文学形式更加自由,内容更加适合消遣。这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十分流行的“故事”文学形式中。当时,“故事”指“不刻意追求强烈表现力的讲述或平实而扩展的叙述,它同另一种重要体裁‘记’(слово)的区别是:‘故事’注重客观叙述,而‘记’注重抒发主观的情绪和感受”(Кузьмин 1984:9 -10)。《萨瓦·格鲁德岑的故事》就是这样一部典型作品。它写于17世纪60年代,讲述俄国商人的儿子萨瓦·格鲁德岑为了享受尘世的欢娱而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故事:萨瓦被父亲派往外地处理商务,受到一名有夫之妇的诱惑。淫荡女人先挑起他的激情,又抛弃了他。萨瓦痛苦万分,为了夺回她而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怆害灵魂。此念一闪,魔鬼便出现了。萨瓦背叛基督,同魔鬼签订了出卖灵魂的契约,女人回到萨瓦的身边。后来,萨瓦与魔鬼周游欧洲、参军、从莫斯科去斯摩棱斯克。在魔鬼帮助下,他连续战胜3个巨人,显示奇特的勇敢,凯旋莫斯科,成为英雄。但是,算总帐的时候到了:萨瓦得了致命的病,才召来神甫做忏悔。这时,那恶魔现出“兽性”真形,折磨他,使萨瓦饱受非人之苦。他很后悔,祈求圣母保佑,圣母显灵,那张卖身契落到教堂地面上,萨瓦从病榻上一跃而起,精神百倍。他康复后把财产分给穷人,自己削发出家。这个故事里的恶魔是萨瓦个人欲念的化身,恶魔出现之日,恰是萨瓦心生占人妻女邪念之时。故事情节已不再靠史事铺排,而是由主人公的个人品质、意志和欲念、幸运或失败推动。故事文体也有变化:它初次尝试在广阔历史事件的背景上、在生活现实环境里描写个人生活。故事时间的跨度很大,约占17世纪最初的30年。此外,突破爱情和情欲的描写禁区。这部作品虽然没有完全摆脱宗教神学的说教,但有着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简单平实的叙述风格,使用较多的口语词汇。难怪尤里·洛特曼把这部作品称为“俄国的第一部长篇小说”(Лотман 2001:30)。
考察这些作品,可以看出“俄国散文体系在17世纪经历了根本的转变和革新……出现了散文的小说化”(Лихачев 1980:173)。那么,17 世纪出现的文学形式“故事”是否就是现代小说在俄国的最初萌芽?回答之前,须要先弄清什么是小说,它有哪些特征。
关于小说,佛斯特在被誉为20世纪分析小说艺术的经典之作《小说面面观》中采用一个十分通俗简单的说法:“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某种长度的故事”(佛斯特1981年:3)。佛斯特的观点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比如马振方给小说下的定义:“小说是以散文体摹写虚拟人生的自足的文字语言艺术”(马振方1999:6)。这个定义实际上包含小说成为小说的4个基本规定性:叙事性、虚构性、散文性和文字自足性。17世纪出现在俄国的“故事”这种文学形式具有比较简单的、容易为大众接受的叙述形式(指大部分故事用散文体写成。即使用诗体写成,也十分通俗易懂);有了虚构人物、情节和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环境,人物表现出一定个性,具有一定概括性等特点,具备小说这种体裁的基本要素。这些特点使人们有理由把《萨瓦·格鲁德岑的故事》称为“俄国长篇小说的萌芽”(Фридлендер 1962:39),虽然它用诗歌体裁写成;而曹靖华认为《谢米亚卡法庭的故事》和《棘鲈的故事》“可以说是后来现实主义小说的萌芽”(曹靖华1992:23)。
4 结束语
俄国小说17世纪末已经开始萌芽。它的直接来源是中世纪的宗教故事、古代民间创作、译介的西欧骑士小说和俄国现实社会中的新生事物。所以,俄国小说绝非仅仅是18世纪从海外“移植过来的植物”,否则它在19世纪的繁荣景象倒真的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
别林斯基.文学的幻想[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
曹靖华.俄苏文学史[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
高尔基.俄国文学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董大年.现代汉语分类辞典[Z].北京:汉语大词到出版社,1998.
顾祖钊.文学原理新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普希金.普希金小说集[Z].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许贤绪.当代苏联小说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
Вавилов С.И.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Z].Москва:Прсвещение,1975.
Волков И.Ф.Те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M].Москва:Просвещение,1995.
Кузьмин А.И.Повесть как жанр литературы[M].Москва:Знание,1984.
Кузьмин А.И.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повесть[M].Ленинград:Наука,1975.
Лихачёв Д.С.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Ⅹ - Ⅻ веков[M].Москва:Просвещение,1980.
Лотман Ю.Учебник п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M].Москва: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2001 .
Синеко А.Современная повесть[M].Москва:Просвещение,1971.
Фридлендер Г.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го романа[M].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АН СССР,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