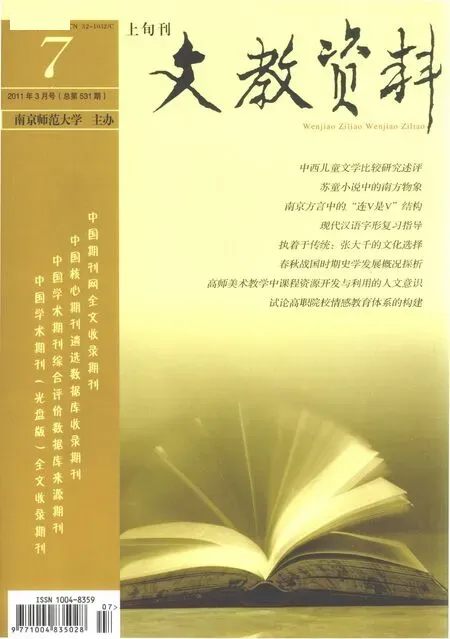执着于传统:张大千的文化选择
徐涛
(内江师范学院 政法与历史学院,四川 内江 641112)
一、时代之变局与画家身份之转变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涌入,中国艺术的发展在受到传统文化影响的同时,还受到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西方文化的强势挑战构成近代影响中国绘画发展的两大要素,左右了中国绘画在近代以来的发展路向。
中国传统所谓的“画家”,是文人而兼习画艺者,从身份上来看,隶属古代的士。文人学道之余以画为寄、自写心胸,宋元之后的文人绘画领域,董其昌式的“寄画于乐”成为一种主要的潮流。及至明清时期,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政治体制及社会思潮发生变化,文化生态的急剧转折,明清之际的文人更多关注生计问题,反映在绘画上就是文人画家开始职业化。这种状况,及至二十世纪的上海,更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上海是近代以来开埠最早的城市之一,开埠之后因其进出口贸易和商业、金融业空前发达,由一个普通县城一跃而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受近代上海商业化的影响而逐步萌芽并发展形成的海派文化,是以市民大众为主要对象,将文化变成一种特殊的商品引入市民的消费领域,以迎合市民的需要为主旨的消费型文化。寓居上海职业化的文人自写心胸的创作传统与职业化、商业化的创作相乖谬,“为我”的创作传统如何与“为他”的创作要求避免冲突,就成为其时诸多画家难以绕过的现实问题。
1840年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同时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伴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势涌入,画家也承受着传统艺术从原则到技术都面临被彻底否定的沉重压力。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其时的画家亦秉承了传统士人“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观,紧随时代潮流,融入到破与立的时代洪流中,勇于担负起了救亡图存、薪火相传的历史使命,而近代文化冲突所产生的多元性选择及变化着的文化环境也为中国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多重的路向取舍。于是,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主流画坛,出现了以下几种选择:西化派,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坚持传统,以京派为代表;内部的革新与中西融合,以岭南画派和海派为代表。西化论和中西融合论注重绘画的时代性,强调绘画的工具理性,将绘画当作一种救亡图存、提升国民素质的手段,或向内求,或向外索,努力实现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化。传统派注重文化的民族性,强调文化的地域差异,认为中画、西画不是量的差别而是质的差别,中国文化的出路应是内求而不是外索。
1919年,从海外学成归国的张大千,寓居当时亚洲最现代化,同时也是海派文化发源地的商业都市——上海,拜师曾熙学习书法,后以卖画谋生。彼时中外冲突所引起的震撼已不像列强初入之时那样让人痛彻心扉,让张大千感受至深而难以回避的是:新兴的现代市民,对传统画坛公认的艺术审美标准并不认同,对传统文人画清冷孤寂的格凋和单调晦暗的画面丝毫不感兴趣。是回归、坚持传统还是走上西化的道路,就成为摆在张大千面前一个不得不选择的问题。身份的割离、价值的迥异、追求的殊途、多变的文化环境,使得张大千在选择的路径上具有多重自由度,从而塑造出张大千独特的人生形式和艺术经历。
二、破与立的时代激流中对传统的整合与重构
张大千的成长经历、文化背景似乎从开始就注定了他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作为一个世俗画家,张大千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画家,他是一个政治权力上的超越者,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和强烈的参与意识,同时他还是一个自由职业者,缺乏古代士人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更不像徐悲鸿、林风眠那样在青年时代就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在艺术形式上,他既不像林风眠那样以西方美术的形与质来表现中国艺术的韵律感,又不像徐悲鸿那样用近代西方美术的“科学法则”来改革传统绘画的造型法则。张大千的文化思路不是离析与破坏,亦不是融汇与建构,而是更倾向于传统内的整合与重构,试图在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的前提下重构与更新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事实上早在张大千之前,在上海卖画的任伯年、吴昌硕等海派画家,为了适应市民的欣赏趣味,已经开始将传统文人画灰暗清冷的格凋改变为鲜明热烈了。张大千承继了海派画家这一变革,画风转入工整秀丽,色彩热烈明快,造型肯定而爽健,在当时画坛大都还沿袭明清文人画传统或者偶尔作些修补的情况之下,他的改变的确具有极大的开创性。
在张大千因时而动的背后,是他对传统绘画艺术生命力的高度肯定和认可。一个画家能承前启后、功成名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深厚的传统功底。张大千的传统功力,诚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张大千曾花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临摹古人名作,他从清代石涛起笔,到八大山人、陈洪绶、徐渭等,进而广涉明清诸大家,再到宋元。他把历代有代表性的画家的作品一一挑出,冥思神合、心摹手追,跨越时空广泛与古人进行对话。然而张大千并不局限于此,1925年,张大千加入了以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寒之友画会”,二十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兴起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美术上直接引发了版画利用民间艺术的创作实践,也直接促成了油画民族化问题的提出。及至抗战全面爆发,出于抗战的需要,作为民族传统绘画形式的中国画,在民族文化讨论的热烈氛围中,更加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独立的民族性,坚持、维护民族性、回归传统成为其时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张大千亦勇于负起了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四十年代初,张大千远赴敦煌面壁三年,改向民间艺术学习。单以敦煌壁画时间跨度而论,张大千临摹的古人画作历经北魏、西魏、隋、唐、五代等朝代。张大千在师法古人方面的成就,的确足以令后人瞠目结舌、汗颜无地。
面壁敦煌,使得张大千在正统的传统绘画体系外,找到了开拓中国画新境界的突破口。文人画占据主流后,民间艺术并不为人重视,但只要追溯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唐以前,民间传统是艺术的主流。到了宋以后,文人传统才开始兴盛。民间美术是中华审美心理结构的主要支架,是中华艺术发展的源泉。张大千对民间艺术的汲取是主动的、自觉的,他认为,创造敦煌壁画的那些民间画匠,并不比其时的宫廷画家阎立本、吴道子逊色。所以,他敢以惊人的毅力,面壁敦煌,独辟蹊径,追根溯源,直追唐宋。国学大师陈寅恪在观看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后撰文评价:“张大千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吾民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张大千更清醒地看到传统艺术的根源,勇于担负起重振民族艺术的使命,把自己从传统延续型的画家转变为融合性的画家。“这种融合不是中体西用的延续,而是传统艺术结构内层的调和,也可以说是一位现代艺术家对于他所理解的传统在现代的重新诠释。”[1]大千先生在敦煌艺术中找到了中国绘画久已失去的色彩生命,这是他泼墨泼彩画风的精神内核,可以说,是敦煌之行,奠定了张大千作为一代大师的基础。
三、互生共存时代背景下对传统的创新与超越
自鸦片战争后,传统中国文化(艺术)在近代始终面临着如何实现由地域文化向国际文化或言传统文化如何向现代化文化转变的问题,张大千的后半生,可以说就是这一历史使命的践行者。1949年后,张大千“长年湖海”,成了“行走的画帝”。1949年,张大千赴印度展出书画,此后便旅居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地,并在世界各地频频举办个人画展。张大千在去国远游几十年间,曾在二三十个国家巡回举办画展,足迹遍及欧美、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着实地宣扬了中国文化。1956年张大千与西画大师毕加索会晤,被西方报纸誉为“历史性的会见”、“中西绘画大师首次会晤”。从此画界便有“东张西毕”的美传。1958年,在美国纽约举行的世界现代美术博览会上,张大千以一幅中国画《秋海棠》荣膺国际艺术学会颁发的金牌奖,并被该学会公选为“当代世界第一大画家”。这是中国人在美术方面第一次获得如此高的荣誉。
张大千的贡献在于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扩大了中国画在世界上的影响,而且在全面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开拓创新。他在泼墨与没骨画法的基础上,吸取了西方的现代艺术法则,创造了泼彩法,从而一变他平生所致力的工细、奔逸的画风,形成了墨彩交辉的半抽象的境界与情调,开拓出一种雄奇壮丽的新风貌。
张大千感应时代包容摭取独创的泼墨泼彩画风,将传统中国画风作了新的现代诠释,使现代经由传统提升至一新的境地。“这显示出张大千最重要的时代意义:他将中国绘画由古典带入了现代,使传统中国艺术精神做了成功的现代转化;也使世人对传统与现代的互动发展关系,有了更深一层的体认与省思。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艺术)创作内涵,是中国知识分子近百年来不断挣扎努力、所期望达成的目标与理想,也是反传统主义之激进立场对传统中国文化最大的质疑。”[2]
张大千的泼墨泼彩法固然含有西方艺术的元素,但其可贵之处是在创造出一种半抽象墨彩交辉的意境的同时,技法的变化始终能保持中国画的传统特色。因此,张大千的泼墨画风与传统中国画学具有生命内涵的连系衔接,是对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张大千的艺术成就证明了传统中国艺术能够在现代世界中作积极的沟通与转化,他这种在当时与世界 “对话”的大气而新颖的艺术操作方式,不仅实现了全球化艺术视野的重大超越,为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路向与艺术范式,而且从新的思维与新的方法上开启了现代艺术研究、创作的一代新风。
四、结语
通过张大千的艺术经历可以看出,他的文化主张不是离析与破坏,亦不是融汇与建构,而是更倾向于传统内的整合与重构,试图在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借助西方文化的某些元素重构与更新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张大千这种天生的保守性及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认同成为其文化性格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现代与传统、全球化与本土化,一直是困扰现代中国人的难题,张大千的文化心态和策略或许会带给人们诸多有益的启示。
[1]魏学峰.论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的时代意义敦煌研究[J],2006,1.
[2]巴东.张大千于传统中国绘画在现代转化的特殊意义.张大千研究[M].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1996: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