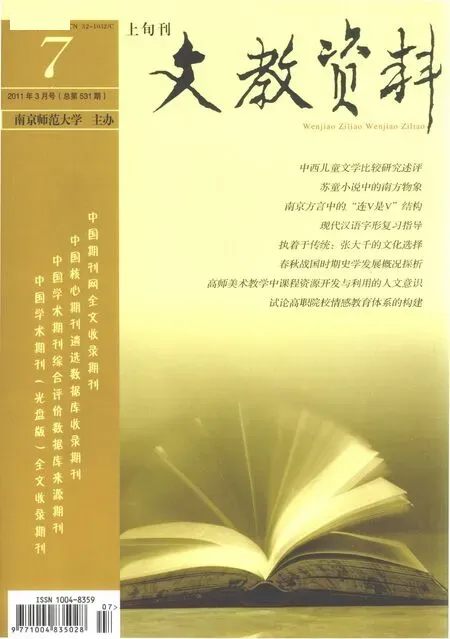朱天文文学道路探析
王艺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朱天文在内地读者中的知名度,并非来自她的小说创作,或是“胡兰成私淑弟子”、“张派传人”这类小资或伪小资膜拜的标签,抑或是“侯孝贤御用编剧”这一文艺青年们热爱的面孔。当真正读朱天文的小说时,会发现它并不那么易读,也许她不仅仅具备以上所提及的那些身份,且有着自己已然建立的独特的、值得玩味的坐标。朱天文是谁?
朱天文,1956年生,作家朱西宁与日本文学翻译家刘慕沙之女,祖籍山东临沂,生于台北。出生于书香世家的朱天文,很早就开始发表作品,曾主编三三集刊、三三杂志,并曾任三三书坊发行人,由其为代表的“三三体”文学,曾在年轻学子中风靡一时。1983年起参与电影编剧,自此便与电影结下不解之缘,掀起80年代台湾新电影浪潮。1994年以小说《荒人手记》获得首届时报文学百万小说奖。2008年出版小说《巫言》。
朱天文自小受张爱玲书香蕴泽,又因缘际遇、爱屋及乌地师承胡兰成的礼乐文化,充任了二人文风的联系者。朱天文既从胡兰成处汲取丰厚的文学滋养,又吸收了张爱玲的特立独行。因此,评论家王德威才将张胡二人称为朱天文创作上的“祖师奶奶”、“祖师爷爷”。
一、“张派传人”的叛逃
尽管朱天文一再声言:“读张爱玲长大的我们,结果,她可能成了我们头上的乌云,遮得地上只长弱草。”但张爱玲依然是探讨朱天文创作历程中不可回避的话题。人性的主题、苍凉的基调、参差的结构、繁复的意象等,这些基本元素的不完全吸纳就足以构成“张爱玲体”。在出离之前,承续是一个必要的步骤。
张爱玲提供了一种关照世界的方式,标识了一种创作路数,即不靠逻辑,不靠学识,理直气壮地写所看所想的,以一种自然生成的态度从事创作,归结起来亦可说是张爱玲的个人主义:见人所不见,忘记所以的出于自我之中。朱天文在散文集《花忆前身》里,坦承她心仪张爱玲这种“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在朱天文的作品里,天大地大,都由她一己视角出之,自身的所历所思悉数化作故事下的潜流,凭一己之意驰骋性灵。
张爱玲小说热衷于对日常凡俗的捕捉,发现平淡人生的传奇。朱天文亦是如此,她对物质世界充满着好奇和咏叹,对一切实指发出赞美。朱天文从张爱玲处学得了俾睨世情的清高孤傲,却学不来张爱玲看透世情的冰凉。张爱玲以生活中平常的事实和经验中的利害得失作价值标准,她的温情背后裹紧了世故。而朱天文虽然外表淡然,不露声色,却依然存有过于正经、清贞决绝的一脉天真,她以文笔的铺张抵抗世事的颓靡。
张爱玲最吸引朱天文的是她作品中的苍凉感。无论是《世纪末的华丽》《荒人手记》,还是《巫言》,都萦绕着一种颓靡、苍凉的情绪,这一点受张爱玲的影响可谓甚深。苍凉感作为张爱玲作品世界里特殊而完整的审美意境,从某种程度讲也是作家心灵深处人性意识的一个鲜明折射。就苍凉感的自身意蕴而言,它是张爱玲在人生终极意义上痛苦徘徊后的悲哀发现,而她作品里表现出来的淡淡的漠然折射出的是对人类把握自身命运之能力与前景的清醒的怀疑。不幸的童年、没落的家族、动荡的现实处境使张爱玲成为一个失落者,从而造成了她精神上的悲观气质,这种沉落直接演化成苍凉的基调。而朱天文毕竟生长环境优渥,历事不多,她在作品中的咏叹末世、赞赏颓废更多是出自对现实保持距离的审视批判,她怀有更多的是天真、含蓄与内敛。正如王德威所言:“朱学不来张爱玲的狎昵与讥诮。她的荒人在最绝望的时分,依旧透露庄重而夸张的姿态。……一种习惯成自然的造作。”[1]P2
朱天文的才华并不妨碍她拥有对人性普遍的同情,而这却有可能使她仅仅止于这种智慧式的慈悲。读者不禁为她极端靡丽的文字所吸引而心生赞叹,为她的敏锐和细致入微的品察而自叹弗如,甚至为她些许的幽默笔致而会心微笑,却难以由此而得到某种慰藉乃至共鸣,毕竟,才女之书有一种不自觉的高高在上。
《荒人手记》“差不多把三四十岁以前作了一次盘整,它是一次盘整的结晶”。[2]朱天文自言此书完成,她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走出张爱玲的阴影和对胡兰成的悲愿。朱天文从未掩饰她对张爱玲作品中苍凉意味的由衷喜爱,尽管她自己希望与张爱玲拉开距离,以至于想要“叛逃”,但这种叛逃应该是吸纳之后的升华,而不仅仅是单纯的背离。
二、倒映和重叠——所谓兰师
在《巫言·巫界》中有诗引自胡兰成《乙巳游大洗矶边》:浪打千年心事违,还向早春惜春衣;我与始皇同望海,海中仙人笑是非。朱天文于其下写道:“总总,事与愿违,书字人的一生啊寥寥数言道尽。镜境的倒映和重叠,我于其上写字。”
在散文集《花忆前身》里,朱天文回顾了与胡兰成的交集。与胡密切交往的几年,正值朱天文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正是朱天文自谓的“前身”,她自言后来的写作生涯,整个其实都在咀嚼、吞吐,反复涂写和利用这个前身。由此可见,胡兰成对朱天文的影响可以说是延绵终身的。
朱天文毫不讳言她对胡兰成的尊敬和崇拜,“我于其上写字”正是对她信仰的宣扬。无论在精神气质还是审美理想上,朱天文都可谓做到了对恩师的“倒映和重叠”。深受胡兰成美学濡染且深以他的文章为中文之本色的朱天文,以情感的本然真诚为本质的价值观,正是源于胡兰成。
知识对胡兰成而言,无非只是感性的材料。他引导他的徒弟们吟哦诗礼中国,想象日月江山,实际上是以他的美学理论为基础,大兴土木,并于其上构筑礼乐乌托邦。这一种对待知识的态度,在表征上是高度文人化的,但其实也是非常中产阶级、非常“雅痞”也非常“士大夫”的一种城市(或都会)小知识分子的文化品位哲学。就如朱天文所言:“办三三,都说要做‘士’,要研究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学问,切莫以文人终身,遑论小说家不过一艺而以。”这种高度文人化的观念在朱天文的《荒人手记》《巫言》中更是获得了惊人的展现。
不论是《荒人手记》里接近色彩元素周期表的红绿二色命名、樱花祭、符号城市、天照大神、神女之舞,还是《巫言》中“冷知识”的遍地开花:牛仔裤设计史、一级方程式赛车、电子舞曲、凯蒂猫、细胞转型、釉下蓝、伏特加、综艺岛生态,朱天文对现实的热情,对物的高度重视,每每流露出一种物的情迷。因着人的目光的注视和纪念,物不再是冰冷的对象而有了生命和神性,朱天文实在是万物有灵论的。尽管看起来眼花缭乱的知识堆砌,令人阅读之时产生难以消化的“食伤”之感,但朱天文这样庞杂的物语实乃传达着她本人对世事的审美观照,万物有灵,每样事物有它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位置,尽管这可能被无意忽略或有意离弃。就像朱天文一意要为乃师正名的种种举措:办三三以发表胡文,写长文以纪念兰师,甚至宣称她最重要的代表作《世纪末的华丽》《荒人手记》《巫言》都是为了续完胡兰成的未竟之作《女人论》……这些举动无非意在为兰师归档,使这一充满非议与争议的人物在被放逐良久之后有所归依。
始终在胡兰成的人文体系中安身立命的朱天文,一直都恪守着胡兰成强调的“礼仪之美”而“不逾矩”。她说:“一个文明若已发展到都不要繁殖后代了,色情升华到色情本身即是目的,于是生殖的驱力全部抛掷在色情的消费上,追逐一切感官的强度,以及精致敏锐的细节,色授魂与,终致大废不起。”[1]P2这可以看作是朱天文对自身书写特征的准确描述。《荒人手记》曾拟名《航向色情乌托邦》,貌似是朱天文反写了兰师遗教,由礼逾色,但她所描述的情欲否定了生殖目的而升华为本身即是目的,而她又否定了情欲中的肉欲成分,透过她的书写,透过建筑那些转瞬即逝的感官殿堂,肉欲转化为情欲,再被化为一幕幕唯美的色境。实际上,朱天文营造了一个属于她的既衍生于社会又游离于社会的色情乌托邦,以让应时的酷儿们有所依归。
《巫言》里,帽子小姐为坚定分手而去印度瞎拼回来的物品,在决心瓦解之后再看,“一件一件,她陌生不识,又依稀记得”,“宝变为石,那是帽子小姐当过一段时间白痴和野兽的唯一物证”。[3]P61“去圣愈渺,宝变为石”是朱天文在《巫言》里一再强调的箴言,帽子小姐无法克制情欲,再次奔投欲海,于是曾经可珍贵的自我救赎变成了虚妄和幻境,也许这就是宝变为石吧。
朱天文将兰师遗教奉若圣经,并将之衍生扩充,折冲于最细密的现实关怀和最迂阔的生死忧虑间,朱天文与胡兰成,他们之间的授与受,造就了当代文学的一段华丽缘。
三、结语
曾经,朱天文为张爱玲的华丽文采所俘获,为胡兰成的谦谦气度所吸引,是张爱玲和胡兰成给了朱天文最纯粹的文化滋养和最直接的文学理念,无论是苍凉意蕴还是礼乐之美,都在朱天文的作品中得到了深切的反映。但是,一个真正具有独立个性和野心的作家是绝不会满足于成为某种标签的附庸的,朱天文在不断地颠覆和反叛中明晰着属于自己的独特坐标。她的文字敏感、细腻、奢靡而绚烂,她用精致的才情、迷离的意象,把物质精微繁复和精神的矛盾纠结都一一呈现,摹写出都市怪兽浮光掠影的本质。她自信而笃定地,走着蜿蜒而坚定的属于自己的路,朱天文在路上。
[1]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2]废墟里的新天使——1999.4.为《荒人手记》英译本出版的新书发布会而作.在美国纽约中华文化中心举行,夏志清主持,王德威即席口译.
[3]朱天文.巫言[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朱天文.荒人手记[M].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5]朱天文.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M].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