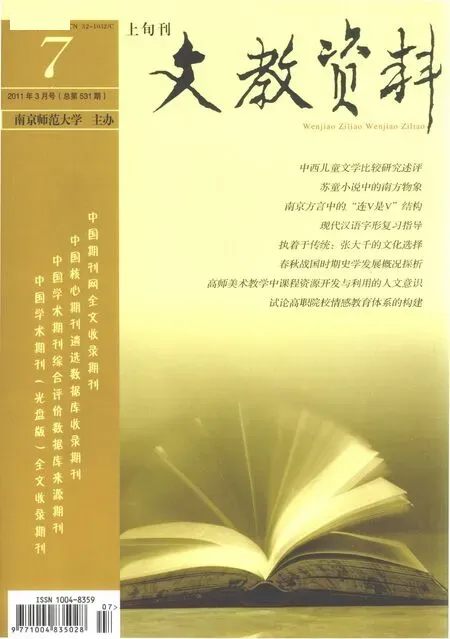苏童小说中的南方物象
刘小玲
(中国矿业大学 文学与法政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0)
一、动植物意象
在苏童小说中,最常出现的动物就是猫。《罂粟之家》是这样介绍刘素子的:“我看见旧日的枫杨树美人身着黑白格子旗袍,怀抱黄猫坐在一张竹榻上,她的眉宇间有一种洞穿人世的散淡之情,其眼神和微笑略含死亡气息。”[1]这样看来,美人刘素子极爱猫,再联系文中这只猫的命运,似乎让我们感受到黄猫就是刘素子,刘素子就是黄猫。《舒家兄弟》中的舒农一开始对猫的认知只限于猫轻捷的姿态和自由的人生,但是后来舒农在楼顶上看到了父亲的秘密后,对猫的认识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舒农觉得身边的世界变了样,他发现自己真的像一只猫,被黑暗中又腥又涩的气息所迷幻,他咪呜咪呜叫着,寻觅自己的一份食物”。[2]后来的舒农,真就像只猫一样,跟踪哥哥舒工约会,偷窥父亲和丘玉美偷情,最后就像猫一样从房顶跳下,坠楼身亡,还发出了咪呜咪呜的叫声。从开始羡慕猫的自由,到最后像猫般跳楼,猫贯穿了舒农十四岁后的人生,他如猫,猫也如他。
由于猫的眼睛是绿色的,总带有阴寒的气息;由于猫轻捷的身形,总给人神秘感。猫在发情期,夜里的声声惨叫,都让人毛骨悚然。这样看来,猫总与阴暗、神秘、自由、性欲有着极大的关系。从刘素子到舒农,他们的形态、神态、命运都与猫息息相关。猫在苏童的笔下象征着性欲,一旦被猫诱惑,结局必然是死亡的深渊。
与动物相对应的植物,在苏童笔下也融入了这个南方世界。植物本身就是一个地方的特有标志,因此在南方世界环境的构造中举足轻重。在枫杨树村,罂粟是乡村的标志之一。罂粟加工后即是鸦片,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在中国大地就成了邪恶的象征。然而负载着中国人屈辱的植物却在枫杨树村生机勃勃的生长着。如《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中的描述:“直到五十年代初,我的老家枫杨树一带还铺满了南方少见的罂粟花地。春天的时候,河两岸的原野被猩红色大肆入侵,层层叠叠、气韵非凡,如一片莽莽苍苍的红拨浪鼓荡着偏僻的乡村,鼓荡着我的乡亲们生生死死呼出的血腥气息。”[3]猩红色的罂粟鼓荡着血腥的气息,象征着无限扩大的欲望,象征着人性的冷酷、邪恶。刘老侠就是一颗生长旺盛、具有勃勃生机的罂粟。刘老信活着的时候,刘老侠就与他争土地,而在刘老信死的那一刻,刘老侠也要让弟弟在地契书上按下指纹,不忘让死人给他作出最后的贡献。苏童将扭曲的人性放大,叫人看清人自身的面目。
苏童笔下的这些动植物对其中的人物都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但被它们吸引后,死亡成了必然结果。这些不受人力控制,生长在南方的动物、植物的客观存在就赋予了阴郁、残酷、绝望的本能,那么南方世界更是散发出了来自母体的腐败与堕落的气息。
二、风物意象
小桥、流水、人家是典型的南方组合,它们在大多数人眼里会是一幅很惬意的江南水墨画,但在香椿树街上,河水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桥洞里住着流浪的人儿,和尚桥却是为梅氏的祖奶奶和一个和尚偷情而建。
即使到了百年之后,人们仍然怀念横贯南方城市的河流。我们的房子傍河建立,黑黝黝地密布河的两岸。河床很窄,岸坝上的石头长满了青苔和藤状植物。我记得后来的河水不复清澄,它乌黑发臭,仿佛城市的天然下水道,水面上漂浮着烂菜叶、死猫、死鼠、工业油污和一只又一只避孕套。
正是雀背驮着夕阳的黄昏,和尚桥古老而优美地卧于河上,状如玉虾,每块青石都放射出一种神奇的暖色,而桥壁缝里长出的小扫帚树,绿色的,在风中轻轻摇曳。[4]
这样看来,“我”的祖先逃向的香椿树街并不是一个好去处。在南方闷热、潮湿的环境里,细菌在空气中随处飞荡,腐烂、恶臭的东西随处可见,恶臭的河水里绿绿的植物疯狂生长,人却不得不忍受这些腥臭压抑的活着,当压抑的情绪无处释放时,市井小人就采取了畸形的排解方式——欲望纾解,祖奶奶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水在《诗经》中有表达男女爱慕之情的说法,水本身也有女性的象征;桥在民俗中也有两性关系的象征,牛郎织女鹊桥相会,许仙和白娘子在桥上结缘都印证了这一点。因此当小桥、流水在腥臭、肮脏、糜烂的香椿树街结合时,它们便不再是一幅乡村水墨画,这里象征了欲望和情爱。
除了这些自然风物外,苏童笔下的建筑物也承载着深刻的内涵,比如梅家茶馆。“到了一九七九年,茶馆的外形早已失去了昔日雍容华贵的风采,门窗上的朱漆剥落殆尽,廊檐上的龙头凤尾也模糊不辨,三面落地门上的彩色玻璃已与劣质毛玻璃鱼目混珠。仰望楼上,那排锯齿形的楠木护壁呈现出肮脏晦涩的风格”。[5]昔日雍容华贵的风采为什么呈现出肮脏晦涩的风格?原因就在于易主了。现在的主人姚碧珍,她仪态之骚情、谈吐之放肆是香椿树街闻名的。光顾茶楼的客人基本都是男人,而一群闲来无事的男人又能在这里谈多文明、多高雅的事儿?加之风情万种的老板娘,茶楼无疑是个乌烟瘴气、肮脏晦涩的地方。后据《香椿野史》记载,梅家茶馆在历史上发生过轰动一时的杀人案。由此,梅家茶馆便成了凶杀、私通、纵欲的象征。
河水、和尚桥、梅家茶馆,它们都承载了黑暗的意义,苏童不惜将故乡以这样的姿态呈现出来,他也说这样看来自己像是故乡的不孝子孙,但是他就是厌恶这样的南方,因为在他印象中的南方并不会以他的意志为转移。
三、颜色意象
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深受大众的喜欢,大多数人对红色的喜爱来自于它代表了吉祥和喜庆,却没有看到红色其实是一个对立统一的颜色。它是吉祥与灾难、喜庆与悲痛、青春与死亡、战争与和平、神圣与亵渎、热情和疯狂等的对立统一。在西方文化中,红色却意味着鬼魅出动的危险时刻,更多地侧重于残酷、危险、狂热、激进、血腥、暴力等负面意义。
《罂粟之家》中,罂粟红始终贯穿其中。沉草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看到一路山猩红的罂粟花盛开着,他面对红色罂粟的表情是迷惘的;当刘老侠看到刘老信的地里长出了猩红夺目的花时,他的眼睛就亮了,他听见了那些鬼花花的歌唱;刘素子死后躺在大竹榻上,黑发里插着一朵鲜红的罂粟;庐方在罂粟缸里击毙沉草后,“他感觉到罂粟在缸里爆炸了,那真是世界上最强劲的植物气味,它像猛兽疯狂地向你扑来,那气味附在你头上身上手上,你无处躲避……”。[6]罂粟红本身就会让人产生晕眩、悲戚的感觉,加之它挥之不去的气味更使得一切都被笼罩在这里,无处可逃。红色罂粟象征了欲望、死亡和不可自拔的压抑。
再来说说被张艺谋拍成电影的 《大红灯笼高高挂》,它改编自《妻妾成群》。虽然在文本中苏童没有设置红色意象,但是出自对作品内心的需要和对艺术的追求,大红灯笼成了影片中尤为重要、尤为突出的意象,而大红灯笼的选择也正暗合了苏童的审美趣味。大红灯笼在影片中既是陈家的照明,又是决定哪位姨太太可以陪房的工具。影片中有一幕,下人雁儿总期盼着有一天她也成为这座宅子的女主人之一,因此她在房间里做了很多红灯笼,当这些被颂莲发现的时候,全部被烧了。由此可见,这里的红色象征着地位、争夺和欲望。
红色在苏童的小说里没有传统上喜庆、吉祥之意,大多都是阴暗的,甚至是死亡的象征。除了红色之外,黑色、白色也是苏童钟爱的颜色。陈佐千的大宅是一座黑色大宅,里面住着他和四位姨太太;陈文治有一座黑砖楼,那里是他用来窥视祖母蒋氏的地方。黑色象征了神秘、偷窥、无尽的欲望。白色出现在《米》中,大米的颜色是白色的,五龙一生对米都有一种执着而又变态的爱恋。米对于五龙来说是一种食欲和性欲,因此白色也就成了欲望、变态、罪恶的象征。
苏童的意象世界里,自然景物、社会风物都被他利用,就连颜色也逃不出他的世界,研读他的作品犹如沉浸在意象的河流里,我们随着这条无尽头的河流沉沉浮浮……
四、结语
在苏童小说的南方世界中,小桥、流水、茶馆、罂粟、红色等,凡是在他视野范围中的都能变成他笔下寓意丰富的意象。意象作为艺术视觉和知觉的空间,苏童将零碎和闪烁不定的意象变为叙事化的意象,构成其小说的叙事性,同时叙事的意象被故事化后又具有了所指和能指的功能。可以说苏童创造了一种小说话语,这就是意象化的白描,或白描的意象化……苏童大胆地把意象的审美机制引入白描操作之中,白描艺术便改变了原先较为单调的方式,出现了现代小说具有的弹性和张力。
[1]苏童.苏童中篇小说选.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23.
[2]苏童.香椿树街故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48.
[3]孔范今,施战军.苏童研究资料.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339.
[4]苏童.香椿树街故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83.
[5]苏童.香椿树街故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84.
[6]苏童.苏童中篇小说选.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