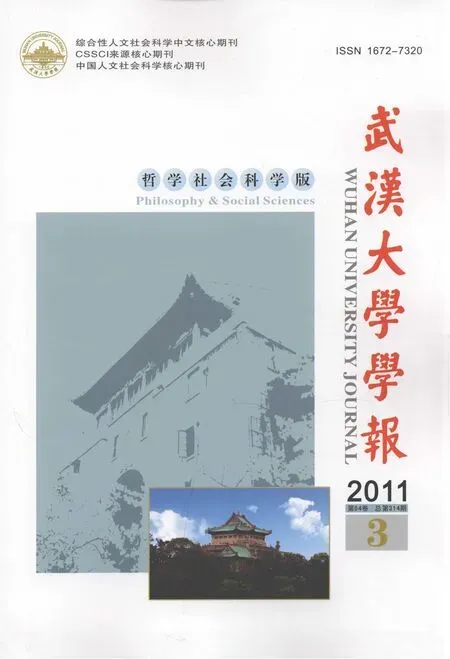当代西方学术思潮的全景图谱——《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的左与右》评介
袁银传 康 丹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是当代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新左派理论家和政治评论家,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左翼核心刊物《新左翼评论》的编辑和灵魂人物,被恃才傲物的文化批评家泰勒·伊格尔顿(Eagleton)称为“不列颠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佩里·安德森的许多作品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后现代性的起源》、《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等,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重新评价自己的政治战略和理论遗产做出了多方面的理论贡献。2007年,安德森推出了自己的又一部著作《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Spectrum:From Right to Left in the World of Ideas),该书一经问世就赢得学界的高度评价,《泰晤士文学增刊》把这本书评论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政治、历史和哲学论集”,《大西洋月刊》认为这是“当下知识最渊博、思想最深刻的评论家的力作”,《共和》认为“安德森仍然不失为激动人心的典范”。该书的中文版历时三年的翻译,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0年10月出版,并且被《光明日报》图书出版部推荐为2010年度十部最有影响的图书之一。
正如作者安德森在前言中所写:“本书是一部有关当代思潮史的著作。可以把它看做一份对于特殊知识景观的全景指南。”①佩里·安德森:《思想的谱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页。以下除非特别标出,全部引自该书,简便记,统统只标注页码。从主体部分看,《思想的谱系》是一本书评汇编,其中大部分文章写成于1992年到2005年并发表在《伦敦书评》杂志,有部分更新。回顾曾经发表的书评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二次创作活动,而且将它们按照主题和文体一致性来分类并非易事。但对于这位博学多才、文字考究的作者而言,他巧妙地将这些文章归为不同章节,分别涵盖政治学、哲学和历史学,并以两篇颇有个人风格的文章作为结尾,其构思之精准令人折服。该书针对西方当代思想领域的各种变化极富信息量的叙述和评论既丝丝入扣、逻辑严密,同时呈现出一种行云流水般的美感。
“本书的展开遵循了时间的顺序,从冷战结束开始。”(第4页)该书第一部分考察了来自右翼的四位思想家迈克尔·奥克肖特、卡尔·施密特、列奥·施特劳斯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还有同一阵营的两位学者:费迪南德·芒特和蒂莫西·加顿·阿什;第二部分考察了世纪之交的属于中间派的三位领军性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尤尔根·哈贝马斯和诺贝尔托·博比奥;第三部分转移到了六位左翼历史学家、思想家和小说家:爱德华·汤普森、罗伯特·布伦纳、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赛巴斯蒂亚诺·廷帕纳罗、戈兰·瑟伯恩和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后一章作为附录包括两篇文章,其中一个是评价著名刊物《伦敦书评》的;另一个则记录了佩里·安德森的父亲詹姆士·安德森在中国的一生,对于了解民国时期的中国(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和外交),颇具史料价值。
从全球范围来看,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以来,右翼的观点赢得了更广阔的空间,中间派逐渐迎合他们,而左派则仍然处于大撤退之中。安德森指出:本书写作的目的之一也就是“要抵制这种退步”(第4页)。而左派若要有力回击右派的进攻,就必须拥有一种直面理论对手的交流、对话和交锋的能力。在《纪念:爱德华·汤普森》中,安德森写到:“辩论是冲突的对话,其实际效果取决于在真理的渴求与愤怒的爆发、辩论的天职与激情的燃烧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第215页)可见,安德森是把自己作为一个辩论者,回顾和呈现出这本具有较大时空跨度的人文知识分子论文集的。而且,佩里·安德森深厚的学养、娴熟的文字技巧、非凡的语言掌控能力以及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丰富阅历,使其在政治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等领域游刃有余。
该书第一部分政治学,分为三章。第一章《顽固的右翼》用比较研究的视角考察了奥克肖特、施特劳斯、施米特和哈耶克的异同。虽然“四人专业各不相同,哈耶克是经济学,施米特是法律,施特劳斯是哲学,奥克肖特是历史,但政治学把他们的关切都引到了同一个领域”(第5页)。“对于这四位思想家各自学术观点的形成具有关键影响的共同经历是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欧洲出现的种种社会危机。”(第5页)安德森批判了施米特的在政治层面的非此即彼的赤裸裸的“抉择论式”观点。而奥克肖特的抉择论始终只是在道德层面上的。安德森还讽刺了施特劳斯所阐发的系统的政治学理论并由此培育出了一个特色独具、见解独到的美国保守主义学派。接着,安德森“把哈耶克和奥克肖特之间的关系作为切入点”(第18页),并通过对比深入剖析了他们的思想,即无论用什么形式表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都在抨击、歪曲和抵制民主、议会、协商等一些起积极作用的和平要素。安德森在第二章《宪政舞台》将批判的目光转向了“一位精明的唐宁街政治顾问”费迪南德·芒特。认为他“试图用一系列公正而又温和的、有助于适应英国之外的‘未来潮流’的变革来重新唤醒英国宪政的‘旧精神’”(第38页)。芒特的代表作《英国今日宪政》对于英国的构架以及修复这种架构所需要的东西的文字功夫和才能无人质疑,但是在政党问题的淡出是一个惊人的倒退。但安德森认为这当然不是芒特的疏忽,之所以“他对宪政的分析之所以漏掉了政党,是因为对政党进行思考将会引发一些致命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他一开始就想刻意压下去的”(第48-49页)。另外,通过将芒特的代表作《英国今日宪政》与罗德尼·布雷热的《宪政改革》的比较,安德森明确指出芒特在方法上存在局限性。最后安德森揭示了芒特并不是极右翼阵营里的异端分子,其“《英国今日宪政》不是设法扩大民主,而是为了维护旧式自由而限制民主”(第60页)。在附记当中,安德森注意到了芒特十年间的令人震惊的变化,认为芒特的新书《关注差距》“不是对英国宪政遗产的慢条斯理的改进,而是对英国社会两极分化的滔滔不绝的控诉”(第61页),全书充斥着对不平等的麻木不仁和当代英国核心地位的自鸣得意。第三章《中欧之梦》转到讽刺英国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欧洲研究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教授蒂莫西·加顿·阿什。作为研究欧洲问题的学者,加顿·阿什始终明白他的中欧观“不过是一个自编自导的神话而已”。这种意识形态“被无耻地炮制出来就是为了把‘PCH三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装进西方的外交套子”(第90页)。安德森毫不客气地说:“历史事实是,一味讨好‘PCH三国’的战略不仅在道德上令人反感,而且就政治而言也是盲目的”(第92页),并且指出加顿·阿什的视野过于局限。在附记当中,安德森提出加顿·阿什的新书《自由世界》的视野扩大了,但是其整个架构“就是一个巨大的高悬在上的暴力之笼”(第121页)。整本书透露出更大的无知和对美国的谄媚。
贯穿第二部分哲学的一个主题就是对“共识”和那些竭力鼓吹“共识”的哲学家的反感,由霸权政治控制的“共识”被安德森的严密逻辑给戳破。这一部分明确针对当代西方三位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美国的约翰·罗尔斯、德国的尤尔根·哈贝马斯和意大利的诺贝尔托·博比奥。在这三位哲学家中,约翰·罗尔斯受到安德森的批评最多。针对罗尔斯的评论《设计共识》,顾名思义,在安德森看来,这里所指的共识是被人为设计出来的。通过对比分析罗尔斯的《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这两本政治哲学著作,安德森质疑了罗尔斯的原初理论的两个基本的正义原则以及由此构建出来的宏大思想体系,并且毫不客气地指出,按照罗尔斯的逻辑应该可以给他的《正义论》写本题为《非正义论》的续篇。在评价哈贝马斯的《规范事实》中,安德森认为哈贝马斯的第一本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方法与论点方面是相互矛盾的”(第144页),忽略社会不平等的事实,而去幻想达成某种必需的共识只能是天方夜谭。安德森认为,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表达的政治立场“与民主形同陌路”(第149页),因为一再地回避现实的真实性,其所宣称的理论只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过时又过时的哲学”(第160页)。在《谋求价值》中,安德森评论了博比奥风靡意大利的最具时事性和个人风格的作品《左翼和右翼》,认为该书不那么令人信服。博比奥本该说明却并没有解释天生的平等和不平等之间的事实上的平衡以及社会不平等的可变性和不可变性等问题上取得的共识,同时安德森认为在没有与经验的社会世界密切相关的情况下构建一种政治价值论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安德森客观评价博比奥在哲学上超越了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因为“后两人曾试图抹杀存在和应在之间的区别,在理想化现存世界还是超越现存世界之间不断摇摆,而博比奥则死死固守法律实证主义和培养他的政治现实主义原则:价值和事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不容混淆的范畴”(第171页)。在这一部分的最后,安德森花费了较大篇幅在《武器与权利:可调整的中心》中探讨了罗尔斯、哈贝马斯和博比奥这三位政治哲学家在冷战之后的十年中对国际秩序和正义问题的论述,对他们试图继承康德的“永久和平”理想而重建当代国际秩序及其理论学说做出了尖锐的批评。通过分析他们各自的成长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他们世界观形成的影响,安德森认为他们的理论建构工作不仅无法实现永久和平与国际正义秩序的理想,他们对帝国战争的军事干预的一致认同,反而掩盖了美国以及其他国际强权对地域冲突的非正义的干涉,还可能沦为国际霸权的理论工具,因为“真正的世界主义秩序需要法律的力量,而不只是外交上的认同”(第174页)。
该书第三部分历史学转移到了左翼的领域,左翼学者在安德森笔下的待遇要好许多,不乏溢美之词,即使是批评也相对委婉。在回忆自己的同事、“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首创者、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时,安德森赞扬他的文字“闪耀着激情和智慧”(第219页),但是对他沉溺书斋的责备也毫不遮掩。对意大利语言学家赛巴斯蒂亚诺·廷帕纳罗,安德森毫不吝惜地在标题中使用了“杰出”这个词表达了自己对这位“二十世纪下半叶最纯粹、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第227页)的肯定:“在浩瀚如海的结构主义的(或有关结构主义的)文献中,没有人能够在西方语言学比较历史的把握上与他并驾齐驱。”(第232页)同时安德森充满着对廷帕纳罗的遭遇巨大精神压力的同情,一个是不敢在公共场合讲话,另一个是严重的广场恐惧症。安德森对剑桥著名社会学家戈兰·瑟伯恩的赞扬也溢于言表,称赞他的著作《性与权力之间》通过强有力的理论结构、有趣的数据支撑、一系列宏大的叙事,第一次为读者提供了真正的全球历史著作范本,“是历史学知识和想象力的伟大作品,是各种天赋极为罕见地融合在一起的结果。”(第268页)在评论经济学家罗伯特·布伦纳时,安德森指出布伦纳的著作的特点是将英国革命的时间跨度定位于长期的动荡的背景之下,大加表扬他的新著《商人与革命》“改变了英国革命的历史面貌,虽然从未提到马克思的名字,但马克思的精神却无处不在”(第283页)。但是,安德森也委婉地指出布伦纳忽略了“君主作为贵族秩序的拱心石在支撑起整个等级制度的拱形结构上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作用”(第300页)。让《思想的谱系》变得格外有趣的是,安德森在这个部分里放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哥伦比亚著名小说家加西亚·马尔克斯。马尔克斯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也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安德森称赞他“对他的祖国的即使是最糟糕的描述,也都充满了诗意般的温暖,一种永恒不变的爱”(第259页),马尔克斯从整个拉丁美洲的地缘政治学的立场出发反思整个拉丁美洲,他的著作《为小说而生》是“一座宏伟的、精致的文学想象力的大厦”(第257页)。但对于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安德森的批判、讥讽之意则浸透了字里行间。尽管承认霍布斯鲍姆有着“优美含蓄、凝练率直的文笔”(第329页),但也不客气直接地指出了霍布斯鲍姆“缺乏近距离政治讨论”、“缺乏对欧洲共产主义问题的真正的学术研究”、“缺乏宽容”(第340页)而导致不应该的错误一再发生。
第四部分由两篇附录组成。一篇是对《伦敦书评》从1979年创刊到1996年这一时间段的同情性的评价。另一篇文章是关于安德森的父亲,一位英裔爱尔兰人和他当时工作过的中国海关。从最后这篇关于安德森父亲的文章,我们可以对其家庭历史窥见一斑。
回顾全书,《思想的谱系》对当代西方社会思潮进行了一次全景扫描。就其范围来说,该书的论题涵盖政治学、哲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经济学、法学、国际关系等不同的学科领域,话题涉及各种各样的理论,如宪政理论、国家理论、民主理论、正义理论、家庭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古代和20世纪的教训的理论、关于记忆和死亡的理论等等,论域极为广泛,足以说明作者的博学。就其体裁来说,因为大都是曾在《伦敦书评》上发表过的文章,如何给这些“书评”再写书评,难度可想而知,若非安德森善于组织二手材料,是一个文字高手,实难完成。开阔的学术视野,渗透着哲学的深邃、历史学的广博以及文学评论家的激情和洞察力,使这本著作具有了一种超越单纯政治论著的独特魅力。作者的文字叙述行云流水,读者更在本书中可以寻找和体会其中的理性洞察力、率真品质与道德激情。所以,尽管佩里·安德森与爱德华·汤普森长期相互抨击,但是当这位左翼前辈晚年托人转告“奥克肖特是个无赖。告诉安德森清掉他的流毒”(第226页)时,安德森也的确将奥克肖特列为《思想的谱系》开篇批判的头号人物。同样出于这种热情,他可以一边毫不留情地挑出霍布斯鲍姆的种种失败,一边又饱含温情地责怪“伟大人物总有一些可以理解的瑕疵,包括有时看不到自己的伟大之处,或者什么东西会损害自己的声誉”(第339页)。就其写作方法来说,安德森没有简单地就事论事对人物进行单独评说,而是从比较视域将思想人物放在“思想的谱系”大视野之中,通过对比得出中肯的结论。全书逻辑十分严密,简洁而不乏充实。同时作者毫不隐藏自己对笔下各类人物的褒贬之情,褒则不吝溢美之词,贬则辛辣而一针见血。此外,让这本书独具魅力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前言中安德森说“研究某人为什么会如此坚持己见,这样的冲动不仅是十分适当的,而且会富有收获”,而安德森本人也正好可以成为这样的研究范本,他一直骄傲地保持着他的独立。
诚然,安德森所言并非全部真理,但单就书评而言,作者批评性的赞赏态度、刨根问底的执著精神、多层面的深刻分析,以及深入浅出的评论、优美生动的叙事、形象诙谐的语言,这些研究问题的方法和写作风格都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研究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