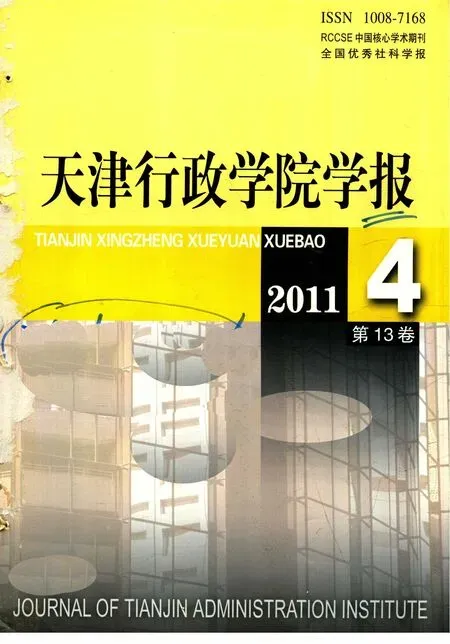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宗教与政治冲突
钟龙彪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 300191)
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宗教与政治冲突
钟龙彪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 300191)
原生主义和工具主义争论的焦点在于:具有宗教背景的政治冲突的本源何在?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双方各执一端,互相对立。如果运用建构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宗教和政治冲突的关系,就会发现在政治冲突中,对宗教信仰和物质利益的追求两者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建构关系。“宗教因素”体现者能成功地利用宗教实现它们自身的目的,客观条件是存在现实的社会危机,某个特定社会的财富和权利分配高度不平等;主观条件是“宗教因素”体现者根据宗教传统对现实问题的有说服力的解释。根据建构主义对宗教信仰和物质利益关系的理解,对宗教促动政治冲突的机制的分析,减少宗教性的政治冲突,必须“三管齐下”,综合运用威慑和压制性否决、发展社会经济和民主化以及对话这三种治理策略。
建构主义;宗教;政治冲突;机制;治理
作为人类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宗教一直是影响世界各国内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和睦以及国家间关系、地区稳定、世界安全的重要因素。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9·11”事件以来,宗教问题正因其在国内、国际冲突中扮演的似乎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引起人们的关注。目前,学界分析宗教与政治冲突关系的主流范式是原生主义(Primoridialist)和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t)。原生主义者认为,国内、国际政治冲突的本源是宗教信仰。工具主义者认为,国内、国际政治冲突的本源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政治、经济利益,宗教只是一件外衣、一种工具。原生主义和工具主义争论的焦点在于:政治冲突的本源何在?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本文在运用建构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宗教和政治冲突的关系后,认为这两种范式是可兼容的。根据建构主义对宗教和政治冲突关系的理解,本文认为对宗教背景下的政治冲突应秉持综合治理的策略。
一、原生主义和工具主义对宗教在政治冲突中的角色的争论
原生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宗教是政治冲突的促动力。因为,宗教、宗教文化以及因宗教影响而形成的民族文化传统,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影响。不同信仰的民族之间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习俗风尚、礼仪禁忌、心理情感、价值观念、伦理规范,以至于语言文化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其中任何一种差异都会成为他们之间产生矛盾和冲突的原因。如果它还涉及政治问题并与之结合起来,就会使问题更趋复杂。特别是对事物、对问题作价值判断、决定价值取向时,总是受着判断者的宗教信仰、所受的传统文化教育、民族的状况如何的制约。民族之间关系如此,国家之间关系同样如此[1](pp.8-9)。比如,在原生主义看来,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矛盾就是因为宗教导致的。他们原本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但长期以来,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矛盾尖锐,在宗教信仰上,穆斯林把牛肉作为主要的肉食来源,而印度教徒则视牛为神,对其顶礼膜拜。因此在伊斯兰教的宰牲节时经常出现教派冲突,甚至发生流血事件。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差异还体现在社会生活上,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不能通婚,不能共同进餐,居住区也彼此明显分开。由于教派矛盾的不可调和,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后不得不实行印巴分治。印巴分治后,两国又因宗教问题至今冲突不断。
工具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是经济政治利益,而不是宗教的差异。表面上,宗教冲突、教派纷争是信仰、意识形态的冲突,但在实质上,这类冲突和纷争仍然是民族的,甚而是同一民族内部因政治经济利益的差异所导致的。就是说,宗教冲突、教派纷争只是表象,甚而是假象,在这类冲突和纷争的背后,则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经济因素。尽管宗教冲突、教派纷争有信仰和生活方式上的对立,但其基本原因仍在于政治经济利益的差异产生的矛盾。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根源于政治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或战争,有的与宗教无关。然而,确有一些根源于政治经济利益的矛盾、冲突或战争,不是具有宗教的色彩,就是得到宗教外衣的掩盖或庇护,甚至表现为赤裸裸的不同宗教(或同一宗教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这里,宗教被作为政治工具而被人们所利用。所谓宗教工具,指的是宗教不是作为信仰对象,而是用来达到一定社会政治目的的手段[2](p.19)。比如,在工具主义看来,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的主张并非宗教教义,而是政治主张,目标是反对美国人及其同盟者。它的活动并非宗教活动,而是政治活动,只是利用伊斯兰教名义、以伊斯兰教为幌子、在伊斯兰教掩盖下从事恐怖主义活动。
冷战结束以来,原生主义和工具主义的辩论主要围绕“文明冲突论”展开。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可谓是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原生主义者。他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政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后冷战时代,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对立或经济摩擦,人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和冲突的根源是文化,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事务中最主要的行为体,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具有不同文明的国家和国家集团中。文明的冲突将支配全球政治[3](p.22)。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于世界上的伟大宗教;那些具有共同的种族和语言,但在宗教上相异的人们可能相互屠杀[4](p.25)。
亨廷顿认为,未来文明认同将越来越重要,主要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之间的互动将塑造世界。未来最重要的冲突将发生在区分这些文明的断层线上[3](p.25)。在微观层面上,最强烈的断层线是在伊斯兰国家与其东正教、印度、非洲和西方基督教邻国之间。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在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冲突[4](p.199)。
为什么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最为严重呢?一些西方人认为西方只是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暴力分子之间存在问题,而不是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存在问题。但是,亨廷顿认为,1400年历史却提出了相反的证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不论是东正教,还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经常充满风暴,彼此将对方视为外人。在亨廷顿看来,造成这两大文明持久冲突的原因,不在于诸如12世纪的基督教狂热和20世纪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这些暂时的现象,而在于这两种宗教的本性和基于其上的文明。一方面,冲突是差异的产物,特别是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观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超越并结合了宗教和政治,而西方基督教则持有政教分离的观念。另一方面,冲突也产生于它们的相似性。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他们都是富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还持有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与其他文明普遍持有的轮转或静态观完全不同[4](pp.230-232)。
亨廷顿甚至认为,只要伊斯兰仍是伊斯兰,西方仍是西方,这两个伟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在未来将继续决定它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像在过去的一千四百年中一直决定着那样[4](p.234)。所以,他强调,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扩展到全世界。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4](p.241)。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范式受到了工具主义者的强烈批评。例如,福勒认为,“因权力、财富、影响分配不公以及大国不尊重小国引起的世界性冲突大大超过基督教、儒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文化是表达冲突的载体,而非原因”。麦哲认为,“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社会经济,而不是文明。虽然文明差异确实助长、促成了许多讨厌的冲突,但它们与一些冲突并无必然的关联,而只是作为诸多因素中的一个起作用,或许在有些情况下,文明的差异甚至有助于避免战争”[4]。中国学者也对文明冲突论持批判态度。例如,刘靖华认为,“本质上,文明是不冲突的,真正冲突的导因在于经济利益和权力平衡关系遭到破坏而导致的。意识形态冲突实则是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一个国家是以民族国家利益而不是以文明背景因素来确定自己的政策”;“冷战后的世界仍旧是一个多极经济利益和权力关系动态平衡的世界。当这一关系失衡乃至严重崩坏,社会就会产生冲突乃至战争。道义、宗教甚或文明都将退为经济利益及权力平衡关系这一巨大现实力量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5]。
针对批判,亨廷顿回应道:“对于人来说,归根结底最重要的,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或者经济利益。人们认同之所在,人们为之而战斗、而牺牲的,是信仰和家庭,血统和理念。这就是为何文明冲突正在取代冷战,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现象,为何文明范式提供了比其它范式都更为有益的出发点,有助于理解和应对世界正在经历的变化。”[6](p.161)
可见,原生主义和工具主义这两种分析范式的对立源于其在世界观上的分歧。在世界观上,原生主义坚持理念主义,认为观念、信仰、价值、规范是影响人、团体、民族、国家行为的重要因素;工具主义坚持物质主义,认为物质利益是影响人、团体、民族、国家行为的重要因素。
二、建构主义视野下的宗教与政治冲突
其实,把政治冲突分解为单纯的信仰冲突和纯粹的利益冲突,并不符合现实。对信仰的追求,对物质利益的争夺,都是政治的动力。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向来都是难解难分的连环套。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说,“将‘利益’和‘价值’区别开来是一个谬误。一种利益只有在被认为有价值时才成其为利益。……在这里,真正应探讨的不是价值和利益之间的区别,而是像领土、贸易机会这样的普世性价值-利益同特殊的价值-利益之间的区别,后者是某些国家根据其‘文化’所特有而其他国家所没有的”[7](p.54)。也就是说,价值和利益并不是没关系的,更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呢?
在建构主义看来,价值和利益是建构关系。建构主义是理念主义,但并不认为权力和利益是不重要的因素,只是认为权力和利益的意义和作用依赖于行为体的观念[8](p.23)。国际政治中权力分配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分配建构的,利益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观念建构的。不是说观念比权力和利益重要,也不是说观念独立于权力和利益。权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它们实际上所具有的作用,是因为造就权力和利益的观念起了作用[8](p.131)。行为体怎样看待世界对于解释其行为是重要的。行为体的观念不能不受到它所处文化环境的塑造。文化现象像权力和利益一样是客观的、具有制约作用的、真实的。建构主义所指的“文化”,即社会共有知识,有许多具体形式,包括规范、规则、意识形态、组织、威胁体系等,可以是合作性质的,也可以是冲突性质的[8](p.141)。
如果运用建构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宗教和政治冲突的关系,就会发现在政治冲突中,对宗教信仰和物质利益的追求两者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建构关系。正如一个学者指出的:“所谓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只能是国家、民族内部各种利益的交织,也只能是领袖和精英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框架认识到的利益。利益冲突经过文明或意识形态透镜折射后,可以扩大许多倍。在两大意识形态的对立已经不大突出的今天,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实际利益矛盾同文明或文化价值观的矛盾容易重合。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所产生出来的冲突可能比单纯的利益矛盾更为尖锐。如果这样看待利益与价值观的关系,那么从利益角度和从精神信仰角度解释国际冲突是可以兼容的,国际政治的文明范式不必排斥其它范式,其它范式也不必排斥文明范式。”[7](p.54)
宗教之间之所以发生冲突,一个重要因素是宗教认同的相互排斥。宗教认同是宗教存在的基础和获得力量的源泉。任何宗教都以自身特有的信仰和礼仪而与其他宗教相区别,在同一宗教内部才有所认同。宗教认同是宗教得以存在的基础。如果宗教没有认同,而与其他宗教混同,它就会失去自身宗教的特色、失去自身的信徒。有的教徒在认识问题、处理问题时之所以以信仰划线,完全是宗教认同的观念在起作用。宗教虽然都宣讲它的普世和宽容,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同宗教之间甚至开展了对话,可是,宗教的普世和宽容并不能替代宗教在教义、教理之间的分歧和差异,宗教对话只能缓和它们之间在非信仰领域内的矛盾和对立,无法解决宗教之间的认同。因为宗教认同是宗教获得凝聚力或内聚力的源泉。应该看到,宗教认同获得凝聚力的同时,也就具有了排斥力。宗教认同是排他性的,凝聚力越强,排斥力也会成正比例地增加。比如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有着种种原因制约着它无法顺利解决,其中,宗教认同显然是个重要的原因[1](p.9)。
进一步分析,宗教认同的相互排斥又是因为受到不同宗教文化的影响。可以说,以宗教意识形态为核心、灵魂的宗教文化,较之宗教自身有着更宽泛、更深刻的社会感染力。宗教文化对社会各不同领域的影响,对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习俗风尚、礼仪禁忌、心理情感、价值观念的影响,都在无形中启迪、熏陶、束缚、控制它的信众。在宗教国家,或有宗教信仰氛围的国家和地区中,宗教、宗教文化对教徒的影响是与生俱来的。人们通常看到的是,由宗教文化影响而衍生的那种情感、心理、习俗、观念,与宗教的情感、心理、习俗、观念常常是合一的,无法截然分开。宗教信仰可以通过个人的自觉选择而抛弃它,但宗教文化的影响、氛围或所处的生活环境,则是信仰者个人无法选择的,也是人们无法抛弃的;或者说,宗教文化的影响、氛围和环境,它的潜移默化及其形成的传统,较之宗教本身更为顽强、固执和持久。即便有某些人,不再信仰宗教,但这些人很难完全摆脱所接受的传统文化的影响[1](p.8)。
犹太教文化对犹太人的深刻影响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犹太人在历史上经过三次大流亡,最后一次是在公元135年。犹太人散居世界各地,已无共同地域可言。他们或与当地民族融合,或被同化,语言因地而异,生活入乡随俗,甚至宗教礼仪也有差别。但是,共同的宗教信仰——犹太教,成为维系民族意识和民族凝聚力的精神纽带。可以说,没有犹太教,犹太民族早就不存在了,也没有今天的以色列。犹太教中的“应许之地观”(即巴勒斯坦早就是上帝应允赐给犹太民族永远居住的一块乐土),既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泉,也是支撑犹太人虽历经磨难、却百折不挠重返故土、重建家园的精神支柱。正如以色列《独立宣言》所说:“被驱逐出以色列的故土后,流散到各国的犹太人对故土始终忠心耿耿,始终不渝地希望返回故土和获得自由,从没有为此停止过祈祷。”[9](p.129)千百年来,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无论是在宗教祈祷,还是在日常婚丧嫁娶仪式上,都念念不忘讲述返乡复国的主题。每当祈祷和其他仪式结束时,他们都高呼“明年相会在耶路撒冷”。直到今天,这句话仍在以色列犹太人中广为流传。正是基于这种根深蒂固的故土观念,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者们视巴勒斯坦为“犹太人记忆中永存的历史家园”,并最终将其作为复国地点的唯一选择。1948年,以色列最终建国。
以色列重新建国以来,国际上对其支持最大的国家是美国。其原因除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外,居住在美国的600万犹太人(其中信奉犹太教的约370万,其余为世俗犹太人),特别是美国政治势力中的犹太集团对美国政府决策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而犹太教则是美国犹太人认同以色列的思想根源。长期以来,由于宗教原因,美国犹太人与异族通婚的现象比其他主要族裔要少,也不大接受异族皈依者。这就使美国犹太文化中保持着固有的宗教传统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犹太教徒,还是世俗犹太人,大多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有着不同程度的认同感,在阿以冲突中支持以色列。美国犹太人,尤其是世俗犹太人,虽大多已“美国化”,却依然保持了“犹太气质”。这种气质及民族认同感均来源于犹太人的宗教情结。与以色列的世俗犹太人一样,一些美国犹太人虽自称不信仰宗教,但也会去犹太教会堂参加礼拜,按民族传统过逾越节等宗教节日,婚丧嫁娶均遵循犹太教习俗。因此,他们往往不可避免地受到犹太教潜移默化的影响。另外,美国人常常把犹太人与犹太教徒完全等同起来。因为不少犹太人也许平时极少进犹太教会堂,但等他们退休后往往又会重返会堂,开始关心犹太教信仰[10](p.45)。
可以设想,假如没有犹太教这个强大的精神纽带,犹太人要维系民族意识,要实现复国是非常难以想象的,美国的犹太人也不会如此坚定地支持以色列。犹太教文化对犹太人的利益认知和行为选择的影响真是太深刻了。所以,理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行为,自然不能离开其利益,但离开其宗教文化背景,也难以解释利益认知和行为选择。
对国际政治冲突的分析,也不能仅看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还要分析宗教文化的影响。比如,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并不仅是领土争端,还涉及宗教信仰。在犹太人看来,巴勒斯坦是《圣经》中所描绘的“留着蜜和奶的地方”,是“祖先的家园”,是“神授的”。对穆斯林而言,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长期居住之地,是穆斯林的第三大圣地,任何异教徒企图控制耶路撒冷的图谋都是不可容忍的。所以,巴以冲突不仅涉及巴勒斯坦人,还涉及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不仅涉及以色列人,还涉及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多次阿以战争中,散居世界各地的一千多万犹太人不仅出钱出枪,而且还有数万犹太人组成志愿部队前往以色列参战。许多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也将支援巴勒斯坦人看做是自己神圣的宗教义务,其中既有政府行为,也有民间行为。许多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组织还视支持巴勒斯坦人恢复民族权利为其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事实上,巴勒斯坦的宗教特殊性已使巴以争端向全球犹太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矛盾方向转变,导致巴以冲突成为以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为一方,以全球犹太人为另一方的国际化冲突。可见,中东地区深厚的宗教文化背景是导致巴以问题扩大化、国际化和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宗教促动政治冲突的机制及治理策略
宗教是如何促动政治冲突的呢?它需要两个条件。第一,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在世界多数地区,宗教传统的复兴以及新宗教运动的涌现都伴随着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如果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社会平等,宗教团体的生活通常就是和平的。第二,“宗教因素”体现者的活动。如果没有“宗教因素”体现者的活动,任何“宗教因素”都不可能产生影响、发挥作用,形成现实的活力,特别是它的政治活力。“宗教因素”体现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宗教信仰者中的教界人士(教职人员)得以体现。他们在教民中的声威,使他们可能成为普通教民的代言人和宗教利益的维护者,他们中的某些人,则可能是某一地区或某个国家的宗教领袖。一般情况下,他们会引导教民遵纪守法、与社会其他成员和睦相处,不会与社会相抗衡,是社会的稳定因素;在特殊情况下则又当别论,可能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另一类是那些并不具有教职的非教界人士。他们是这一或那一宗教的信仰者,往往以宗教为工具,骗取一部分教民的信任,使之成为他们的追随者。这些人通常是一些国家的政治反对派,或某些从激进到极端的小集团、小组织的头目和骨干[2](p.19)。
因此,“宗教因素”体现者能成功地利用宗教实现它们自身的目的,客观条件是存在现实的社会危机,某个特定社会的财富和权利分配高度不平等;主观条件是“宗教因素”体现者根据宗教传统对现实问题的有说服力的解释。因为,国内和国家间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是客观事实,也是主观评价,是取决于主体间对于共同经验的共同解释的。国内和国家间可以觉察的权利、财富分配以及与这种分配相应的合法性话语这两者之间是一种静态均衡关系,而不是永远不变的。这就是说,国内和国家间的历史统治格局往往伴随着意识形态的、宗教的或者道德合法性之支持的格局。但是,当国内和国家间的权力和财富的集中大大超出主体间可接受的不平等限度时,当富人和穷人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大时,当穷人的数量增加并且不断被边缘化时,现有的、对物质和非物质利益的任何不平等分配的合法性解释就会面临压力。这个时候,新的观念往往会及时涌现、旧的传统通常会被重新解释。而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危机之中,政客们可能会求助于宗教来扩张他们的野心,甚至动员他们的成员进行暴力活动[11](pp.175-177)。
如何控制、减少宗教信仰在政治冲突中对暴力的激化作用?有三种策略:第一,威慑和压制性否决策略;第二,发展社会经济和民主化策略;第三,对话策略[11](pp.177-187)。
威慑和压制性否决策略。它的思想传统是现实主义政治,又称权力政治。这种政治传统关注的冲突处理方式是通过压制变革要求来维持政治现状。不管其动机如何,都要使这个对手意识到在可接受的成本内使其不可能在对抗中成功。在这里,它意味着要用强力的冰水扑灭宗教憎恨的火焰。对乞灵于宗教的政治冲突要运用武力的压迫予以平息。要使追求权力的政客以及修正主义的民族意识到,或者他们不能成功,或者将为成功付出高昂的代价。同样的,对那些普通成员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环境的威慑要能使高度动员起来的激进分子和支持者也不再指望用武力完成他们的目标,从而最终放弃使用武力。这一策略的目标在于压倒对方精英求助于宗教所形成的潜在动员效果以及由宗教激发的牺牲意愿,建立压迫的优势,从而保证对社会的心理控制。这样,公开的反抗就成为绝望的行为并要承担极高的风险。
发展社会经济和民主化策略。当前宗教在政治上的复兴是世界经济危机和发展危机的结果。既然这样,那么,降低宗教团体对绝望的人们的吸引力并控制他们升级冲突的潜力的最好办法是克服潜在的社会经济危机。这样,宗教信念被利用来动员普通成员的可能性就会消失。对现状满意的人将会增加,而武装团体就会失去支持。大多数人们就会反对把暴力作为一种政治冲突的合法手段,转而支持温和的宗教领袖和政治领导人。简言之,随着社会中分配不公平现象的减少,暴力形式的抗议就基本失去了它们的吸引力。从这个观点来看,追求和平的国内外政策制定者应该促进经济发展并公平分配,从而改善那些容易受社会经济萧条甚至崩溃影响的社会弱势群体的经济、社会条件。经济社会发展将减少宗教信仰的政治特性,信仰问题将转入私人领域,宗教分歧就不会转变为政治分歧。
对话策略。这种策略试图提高人们参加,或者支持,武装斗争的内部阻力。与前两种策略相比,威慑和压制性否决策略与发展社会经济和民主化策略主要对行动的外部动机进行操纵,而对话策略则依靠有说服力的论证内在地改变人们的心思。他们必须出于原则性的理由放弃使用暴力,把暴力看成是不正当的、不正义的。这种策略的根据在于,世界各大宗教都包含了大量的源头和传统。这些源头和传统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格局中兴起并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的。一般的宗教团体和特定的宗教权威都面临如何用源头和传统来解读当前的社会经济政治现实的挑战的问题。极端主义者可以利用对宗教经文和教义的片面解读来合法化其暴力行为,号召人们为战争作出牺牲,谴责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温和主义者也可从经文和教义中解读为教导信仰与暴力的不相容、号召人们为了和平作出牺牲并尊重不同信仰的人。关键是什么样的宗教权威,从什么角度去解读经文和教义。一句话,宗教引导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建构主义对宗教信仰和物质利益关系的理解,对宗教促动政治冲突的机制的分析,减少宗教性的政治冲突,必须“三管齐下”,综合运用这三种治理策略。特别是针对当前的宗教恐怖主义,既要用武力打击恐怖势力,同时要积极发展经济,改革政治,改善民生,铲除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土壤,还要积极引导宗教与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正确地解读宗教的经文和教义。
我国新疆反对“三股势力”(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的斗争经验就充分证明了综合治理策略的重要性和正确性。
长期以来,“东突”势力不断制造分裂活动。中国政府一直依法打击“东突”势力的破坏活动。但“东突”势力依然有活动能量,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新疆同我国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仍然较大。新疆同全国一样,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2]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散布歪理邪说,如“虔诚的穆斯林不应该服从异教徒的政府”,“在政府的清真寺礼拜是哈拉目”,“跟领政府津贴的伊玛目礼拜无效”,鼓吹所谓的“圣战”,宣扬“杀死一个异教徒等于七次朝觐”,等等。目的是在穆斯林群众的信仰上引起混乱,煽动群众与政府对抗,为分裂活动创造群众基础[13](p.138)。他们通过地下经文学校向青少年灌输泛伊斯兰主义和分裂思想。在地下经文学校,反动宗教分子讲经布道,大肆宣传泛伊斯兰主义的言论。地下经文学校培养的一些学生已成为在新疆从事分裂活动的骨干力量。1990年4月的巴仁乡暴乱,参加者中青少年占80%;“伊宁2·5事件”的骨干分子基本上都是地下经文学校的学生[1](p.93)。
针对这两个主要原因,一方面,中国政府从国家发展战略和各族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高度重视新疆的发展和建设,始终把帮助边疆地区发展经济、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一项基本政策,适时做出一系列推动和促进新疆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另一方面,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了教务指导委员会,组织力量编写《新编卧尔兹演讲集》,对伊斯兰教教义做出符合社会进步要求的阐释,从伊斯兰教教义教规的角度,有针对性地对在新疆地区流传的歪理邪说进行批驳,旗帜鲜明地反对三股势力。这项工作叫做“解经”工作[13](p.138)。实践证明,这项工作对维护新疆稳定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据了解,在乌鲁木齐“7·5”事件中,新疆没有一座宗教活动场所和一名宗教人士参与打砸抢烧,各族宗教人士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14]。
四、结论
原生主义和工具主义争论的焦点在于:具有宗教背景的政治冲突的本源何在?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双方各执一端,互相对立。如果运用建构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宗教和政治冲突的关系,就会发现在政治冲突中,对宗教信仰和物质利益的追求两者并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建构关系。
“宗教因素”体现者能成功地利用宗教实现它们自身的目的,客观条件是存在现实的社会危机,某个特定社会的财富和权利分配高度不平等;主观条件是“宗教因素”体现者根据宗教传统对现实问题的有说服力的解释。根据建构主义对宗教信仰和物质利益关系的理解,对宗教促动政治冲突的机制的分析,减少宗教性的政治冲突,必须“三管齐下”,综合运用威慑和压制性否决、发展社会经济和民主化和对话这三种治理策略。
[1]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
[2]金宜久.国际政治中的“宗教因素”[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9).
[3]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J].Foreign Affairs,1993,(3).
[4]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等.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5]刘靖华.霸权的兴衰[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
[6]Samuel P.Huntington.If Not Civilization,What?[J].Foreign Affairs,1993,(5).
[7]王缉思.国际政治的理性思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9]徐新,凌继尧.犹太百科全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0]段琦.美国宗教嬗变论[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4.
[11]F·佩蒂多,P·哈兹波罗.国际关系中的宗教[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
[12]新疆工作座谈会召开,胡锦涛温家宝发表重要讲话[EB/OL].http://www.xinhuanet.com/chinanew s/2010-05/21/content_19849101_1.htm.
[13]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新时期阿訇实用手册[Z].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14]不许玷污清真寺[N].人民日报,2009-07-27.
D8
A
1008-7168(2011)04-0036-06
10.3969/j.issn.1008-7168.2011.04.006
2011-03-16
钟龙彪(1969-),男,江西全南人,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段志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