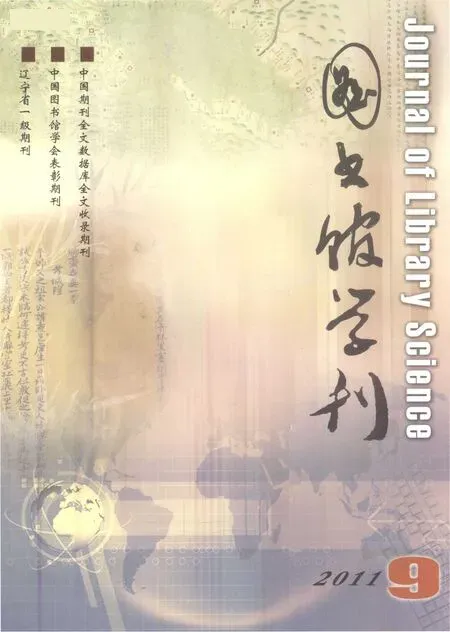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机构的文化贡献
施 静 朱月婵
(炮兵学院图书馆,安徽 合肥 230031)
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机构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统一性和继承性的重要保障,其机构的设置、制度的建设、纂修的成果等对推动和繁荣时代文化、历史文化和档案文化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1 对推动和繁荣时代文化的意义
1.1 资政参考,推进政治文化的发展
历代王朝的档案文献编纂机构馆藏内容丰富且重要,汇集了前朝的各项典章政令、史书图籍等,不仅可为统治者提供借鉴参考的管理经验,而且可直接作为剥削压榨农民阶级的依据。任何一个朝代,都是把维护本阶级的政治利益作为重大任务摆在档案文献编纂机构选题的首位。如历朝历代的诏令、奏书、法典的编纂,就是为了吸收统治经验、便于参考借鉴,常常是统治阶级编纂选题的主要方面。
以这类题材为选题的编纂汇编卷帙浩繁,如诏书是封建社会以皇帝名义发布、传达其指令的一种重要文书,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诏书的汇编范围包括该时期各项重大事件的发生情况、各项重要政策的颁布和实施、各项重大人事任免升迁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广泛的内容,是反映当时阶级斗争、社会制度变革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统治阶级编纂《宝训》的直接目的,主要是宣扬最高统治者的功德,积累统治经验,便于施政时参考借鉴,以巩固封建帝王的万世基业。关于奏书的目的,元朝陈旅在《国朝文类·序》称:“编者取材的原则是经世致用”,“然所取者,必其有系于政治,有补于世教,或取其雅致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弗取也。”[1]其资政经世的目的可见一斑。如汉初的各项政治制度,大多是参照前代(特别是秦代)的典章而制订的,叔孙通定朝仪就是依据古礼与秦仪,萧何定汉律也是依据秦法。统治者在政务活动中查用档案文献编纂的事例屡见不鲜,说明了统治者设置编纂机构积极收藏、修撰史书典籍的政治目的。
1.2 宣传教化,推进正统思想的传扬
统治阶级加强、巩固集权统治,借助中国传统封建儒家文化的熏陶,对臣民进行政治教化的管理,宣传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逐步麻痹臣民的思想意识,使其忠君为国的思想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从根本上说,以编纂档案文献的方式宣扬其统治思想与管理理念。如唐宪宗时礼部尚书权德舆编纂的《陆宣公奏议》,该书的编纂目的主要就是宣扬以陆贽为封建朝臣的楷模,标榜他的为臣事君之道,作为巩固封建统治的龟鉴。又如明太祖朱元璋主持编纂的《御制大诰》,是明代初期的法典、案例文件汇编。朱元璋在为该汇编撰写的序言中规定,无论官员还是百姓,每户必须“有此一本”,若犯答、杖、徒、流罪名,因为“有此一本”则可以罪减一等;否则,罪加一等,并要求臣民“熟视为戒”。[2]编纂此书的主要功能在于统治与规范民众的思想与行为,最终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服务,其政治目的性显而易见。可见,封建帝王把编纂活动作为宣扬教化臣民忠君不二、奴役臣民思想的教本。
1.3 延续文明,促进科学文化的传播
为了适应当时政治斗争和文化学术发展的需要,档案文献编纂机构不断发展完善,利用保藏的档案文献资料进行编史著述,大量的档案史籍典经得以广泛流传、利用,对我国古代科学文化的传播交流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然,推动社会文化进步的根本动力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然而作为历史记录的档案文献编纂,对于集中、有针对性地促进文化学术发展无疑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这表明我国古代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和当时文化学术的传播发展密切相关。
我国著名的古代史书《左传》和《国语》,相传为鲁国太史左丘明所编纂,从书的内容上可以看出这两部书无疑是根据大量档案史料编纂而成的,特别是《国语》,完全是一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史官记录的汇编。此外,史官所保存的天文历法记录也有编成专书的,如战国时魏国史官石申,编著《天文》8卷,齐国史官甘德根据观测记录编著《天文星占》8卷。[3]这些著作,作为记载科学文化的知识载体,促进了当时文化的交流传播和传承。就档案文献编纂活动所取得的成就上看,档案编纂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创造活动,其编纂成果己经成为社会文化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编纂成果所包含的史实、知识、智慧、教训、经验等,作为人类共有的文化信息特征越来越得到大家的认同。
2 对传承历史文化的贡献
2.1 史馆制度与史学发展交相辉映
自唐代实行史馆制度,其纂修成果无一不是在广泛利用档案史料的基础上修撰而成。唐史馆大量征集保藏档案文献资料,并大规模利用档案修史,不仅是史馆工作的繁荣进步,而且也是史学的飞速发展。“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和《北史》都成书于唐朝的史馆。[3]这表明,我国古代的档案文献编纂与史学发展紧密相连,档案文献编纂是史学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是史书之源,修史必须以档案为前提和基础。两者“相须而成”的关系刘知己曾作过精辟的阐述:“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4]
我国从古至今,许多重要的历史著作,如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班固写《汉书》以及历朝历代帝王的起居注、实录、方志和谱牒等,都是利用档案写成或直接由档案编纂而成的。著名清史学家戴逸先生所言,是档案熔铸了史学;史学的大厦,正是建筑在档案的基石之上的。春秋战国以来史学著述的盛行,推动了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在封建社会的发展。档案编纂与史学工作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联系,如同韦庆远教授所言,我国最早的史官,同时也是负责保管档案的工作人员,最早的史籍,在某种意义上说,只能算是一些公布档案的汇编。古代历史工作和档案工作,不论就其内容以及负责这些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基本上都是同一的。如西汉时太史比较集中掌管史书编纂之事,司马氏世代为周室太史,至汉武帝时,司马迁父子相继纂其职,乃“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微,论考之行事,略三代,录秦汉”,[5]上记黄帝,下至于汉武,纂《太史公书》130篇,即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2.2 维系历史文化的一脉相承
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档案文献的原始载体难以永久保存。但由于我国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档案文献的积累和编纂,如最早的档案汇编《尚书》中保存了中国古代一部分重要的档案文献和珍贵的历史记载,成为研究我国上古历史有文字可考的稀有宝贵史料。历朝历代利用原始档案材料编纂起居注,它虽然不是原始文件的汇编,但其中保留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起居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实录,不仅成为封建王朝的一个传统,是具有档案汇编性质的编年体史书,更为编史修志保留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古代的档案原件流传至今的件数虽然寥寥,但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的信息内容却有相当部分流传至今,使我国成为世界文化典籍资源十分丰富的文明国度之一,其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历史上有着相当发达的档案编纂工作。
发源于史官文化的传统文化,养育了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官员;编纂官员则创造、推进和发展了传统历史文化。他们通过对文书的撰写和档案文化典籍的保存、整理、著述,实现知识的传播、流动和延伸,促进了文化的累进与增值,构成了新的文化。新的文化又对档案编纂官员产生新的影响,这种影响又反馈到其工作中,构成新一轮的循环。这种互动关系,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创新和发展。档案编纂的存史功能,对于维系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可谓是功不可没。
3 对形成和繁荣档案文化的贡献
档案文献编纂机构的产生和发展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档案编纂活动的兴盛在强化传统历史文化的统一性、整体性、延续性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构成中国传统历史文化核心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儒家学说,以及各朝各代的档案编纂和国史方志无一不是历代档案文献编纂官员在充分利用档案史料的基础上,集结了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化成果整合而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代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具有强烈的历史性、遗传性,使得档案编纂的传统历代相因,连绵不断,为维系中国传统文化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功能。所以说,编纂机构本身就构成了我国档案文化的重要部分,兰台、东观、史馆、翰林院等编纂机构的设置是我国古代博大的档案物质文化的代表,伴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其文化“古董”的意义便可体现。而编纂制度的建设、编纂成果的流传、编纂职官的文化素质要求、编纂思想的积淀也是我国档案文化资源一道独特的风景。
对我国古代编纂职官而言,在编史修志的同时,进行档案文献编纂理论学术研究活动,是档案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形成了文化自觉的主体意识。文化自觉即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6]在此过程中,相伴而生的是我国古代繁荣的档案文化和社会文化。如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对一系列编纂活动进行了理论上的归纳和总结后,提出了“比次之书”、“比次之法”、“比次之道”、“比次之业”等概念。所谓“比次”,即“整齐故事”,对档案内容加以梳理,形成体系,以便利用。“天下有比次之书,有独断之学,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而“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比次之书”的关系,就如同“旨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所以,“比次之书”、“比次之业”“不可轻议也”。同时,他还指出了“比次之道”与其他学术研究在方法上的不同,他认为:“独断之学、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书欲其愚……不名家学,不立识解,以之整齐故事,以待后人之裁定,是则比次欲愚之效也。”[7]章学诚的编纂思想,是对历代档案文化成果整合、归纳后形成的,他将档案文献编纂作为一门具有独立研究领域、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专门之学,其对档案文献编纂理论的研究和总结,为建国后档案文献编纂学的正式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借鉴,是我国古代档案文化理论传承和总结的突出表现形式。
[1] 元陈旅.国朝文类·序[M].
[2] 大诰初编·颁行大诰[M].
[3] 邹家炜,董俭,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简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4] 刘知几.史通外篇·史官建置第一[M].
[5] 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 丁华生.论档案专业文化的自觉与建设[J].档案学通讯,2009(2):4-7.
[7] 刘耿生.档案开发与利用教程[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377-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