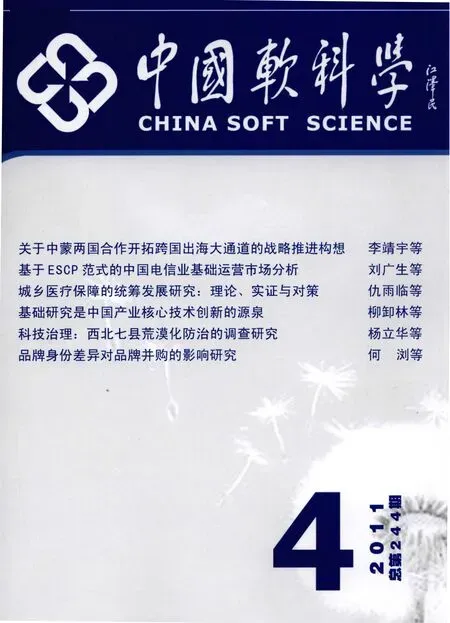确立清洁能源国际科技合作国家战略的思考与建议
郑方能,封 颖
(1.科技部高新司能源与交通处,北京 100862;2.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38)
确立清洁能源国际科技合作国家战略的思考与建议
郑方能1,封 颖2
(1.科技部高新司能源与交通处,北京 100862;2.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38)
文章从清洁能源国际科技合作面临的新形势入手,论述能源领域国际科技合作的战略重心发生了转型,探讨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对清洁能源问题的认识的主要差异。随后,着重提出制定清洁能源国际科技合作国家战略的构想,从顶层设计和具体设想两个层面阐述了加强清洁能源国际科技合作的若干建议。
清洁能源;国际科技合作;国家战略;中国
近年来,全球能源结构正在进行重大调整,许多国家将发展清洁能源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关乎一国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2009年 1月 27日,奥巴马在其首份国情咨文中强调“清洁能源经济的领先国家必将也是全球经济的领导者,那么美国必须扮演这样的角色”[1]。2009年 4月 27日奥巴马在对美国科学院讲话中指出“能够领导 21世纪全球清洁能源的国家将能够领导 21世纪的全球经济”[2]。
一、清洁能源国际科技合作面临的新形势
清洁能源已将成为我国政治、经济、外交和科技面临的重大议题之一。能源与政治是双面胶,特别是在视能源为国家安全根本保证的全球背景下,能源无疑是政治交往与谈判中的筹码,一旦掌握了能源问题的主动权,也就自然可以获得解决众多国际问题的主动权。更为急迫的是,作为世界上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我国面临着全球压力,我国应对清洁能源的方式必然具有全球意义。
清洁能源问题有大量的科学技术内涵,清洁能源合作已然跃升为国际科技合作中的热点问题。中国开展清洁能源国际科技合作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70年代末期,已经形成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合作体系,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以中美清洁能源合作为例,自 1978年以来,美国能源部一直与中国开展科技合作。1997年双方发起了中美环境和发展论坛,促使双方高层对能源、环境、科技、贸易和发展问题的一体化予以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它看成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SED)的前身。2006年以来,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议程将能源、环境和技术创新问题包括进去,这就表明科技对两国的重要性日益提升,科技关系自身走向成熟。2009年中美两国首脑会谈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双方开展清洁能源合作的重要性,双方同意成立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承诺在未来的 5年中共同投入1.5亿美元用于联合研究。2010年 7月,包括中国、美国在内的 22个国家能源 (科技)部长在华盛顿召开会议,共同探讨发展清洁能源。
然而,当前我国外交界、科技界对清洁能源国际科技合作重要性的认识和实践尚存不足。首先,在思想上,常常把清洁能源国际科技合作的作用局限于获得更多的国外资金或实物援助;其次,在制度上,常常把清洁能源国际科技合作等同于普通外事活动;再次,在全球层面的能源科技合作中,中国目前还是个“小伙伴”,在主要能源组织中缺乏足够的发言权,更谈不上主导权。这种局面将影响国家长远发展的需求。因此,拓展清洁能源国际科技合作的空间和领域,制定清洁能源国际科技合作国家战略,对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从国家的长远发展考虑,我国政府应在清洁能源国际科技合作方面有一个综合性的考虑,从战略层面开展更长远的谋划,不仅为了更好地促进我国能源科技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而且也是从更高的层次、更广阔的领域为国家发展服务。
二、能源领域国际科技合作的战略重心发生了转型
能源的国际合作,一般来说主要涉及 3个领域:传统/化石能源的跨国开采和贸易、清洁能源和新能源的技术研发和市场培育、能源资本市场国际化经营。以往,国际社会在能源领域对我国的关注重点是:我国是工业化的后来者,能源企业在世界各地获取能源资源而闯入了老牌殖民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他们由此制造出“中国能源威胁论”,并通过各种方式为我国获取国外的能源设置障碍。如 2005年中海油竞购尤尼科案造成就中美能源摩擦,进而影响了双边关系。
如果说以前国际能源问题的关注焦点在于到处找油找气,考虑怎样拿过来;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上对能源问题的关注焦点逐步发生了重大转型:发达国家纷纷转向清洁能源 (包括传统能源的清洁化以及可再生能源)、能效和节能、智能电网等对相关产业具有巨大带动作用的领域,并开始探讨相关公共财政如何合理支持以及大企业下一轮的投资方向。正是基于这些形势和结构的新变化,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购买、投资海外油田、气田已没有金融危机前那么敏感了,而对中国发展清洁能源给予了高度关注。
美国政治精英们非常担心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落后。2009年 9月 27日《纽约时报》一篇题为《新的人造卫星》文章指出,“过去 18个月里发生的最重大事件是中国决定成为环保国家”,“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中国已悄悄踏上利用清洁能源发电的创新之路,而其现实意义不亚于苏联当时发射首颗人造卫星。危险的是,我们至今对此置若罔闻”。2009年 1月德国推动建立了一个有98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国际可再生能源组织(IRENA),该机构作为可再生能源的“新代言人”旨是在全世界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扩大使用新能源。2009年 10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战略性能源技术计划》,宣布未来 10年将投 730亿美元研发新能源。2010年 5月 12日美国参议院公布了《国家能源法案》(又名“气候与能源法案”)的草案版本,一是开放了近海油气资源开发权,二是支持建设新的核电站并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新一代(第四代)核电站技术的战略计划。法案的核心思想便是美国能源供应要实现自给化,实现最大程度上的“自给自足”。奥巴马政府能源政策实施的目标可总结为:在基本稳定油气需求总量的前提下,用增加本国油气产量来抵消减少的进口量;未来依靠不断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来满足能源需求增长;通过各种节能措施降低能源总需求,进而达到逐步降低化石能消费比例的目标,并显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尽量避免通过在发电、钢铁、化工等领域使用低效、成本高的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实现减排目标。这些国际动向都充分说明了,发达国家正在促进一个新的全球节能减排和清洁能源投资市场的形成,利用它来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为本国占据一个未来世界中的能源领域制高点。
三、我国与发达国家对清洁能源国际科技合作认识的主要差异
我国与发达国家对清洁能源问题的认识及对彼此的预期,存在以下 4点主要差异和分歧,由此造成了一些长期存在的误解和摩擦。
第一,在对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的认识上存在诸多差异,特别是对国际气候变化合作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理解上存在明显分歧。以美国为例。美国采取的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全球策略,提倡“祖父原则”:即维持现状,当前有多少排放,是今后排放量的基础。而我国则强调发展需求,谋求合作共赢。此外,在国际合作方式上两国也存在着差别:我国希望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多边的协商谈判来解决全球的能源环境问题,美国往往从单边的大国角度,谋求通过联合国框架之外的机制下来解决,如“G8+5”机制就是这种安排。
第二,在合作的概念上存在分歧。我国较多地强调合作中的相互交换、互惠的一面,发达国家则更多地强调两国对第三方或两国共同面临的问题采取相似的、协调一致的立场。例如在中美海外能源合作问题上,中国希望更多加强双方在油气勘探开发、技术转让等领域的互惠合作;美国则强调中方应与美国一道对某些反对美国的能源富国采取与西方一致的遏制政策或至少不加强与其能源合作,突出的是与美国的配合、协作。
第三,在清洁能源核心技术转让、资金援助上意见不一。在技术转让方面,中国主张将技术转让作为优先之一,发达国家应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以优惠的条件转让新技术。发达国家则极力推动技术转让的完全商业化,强调技术为私营企业所有,政府无权干涉,而美国政府在为美国企业推销产品的游说工作却不遗余力。
第四,发达国家向我国征收“碳关税”的可能性极大。2009年 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其中包括所谓的“碳关税”条款,即从 2020年起,对不接受污染物减排标准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具体的措施将表现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研究表明,如果征收碳关税,中国产品出口的总体税负将在 20%左右。按目前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 (45美元 /吨 CO2)对我国产品征收碳关税,将使得我国企业每年增加约 550亿美元额外负担,我国进入欧美市场的产品关税将从目前3%~4%的水平上提高约 14个百分点。目前,机电、建材、化工、钢铁等高碳产业占据了中国出口市场一半以上的比重,如果开征“碳关税”,短期内必然会对上述行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并且,按照技术互换协议条款规定,如果想在清洁能源领域获得美国的技术支持与援助,就必须接受美国的减排标准,这就相当于同意美国针对中国进口企业征收碳关税。我们应谨记欧盟 REACH指令(全称为《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法案》)带来的教训,在“碳关税”问题上应及早分析其可能对我国的影响,并提前采取适当应对措施。
四、制订清洁能源国际科技合作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
近两年来,诸多重大国内外论坛、高层会议等传递出多方面的信息:金融风暴引发的西方对价值观的反思将影响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干预主义的新左派思潮逐渐占据上风;环保主义者的运动升级为环保主义,并出现环保霸权主义倾向;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这些思潮将深刻影响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国必须对此认真研判,在新一轮全球化中找准位置。
中国对于清洁能源国际科技合作的基本原则和态度包括以下五点。一是中国开展国际清洁能源科技合作的基本态度应当是立足现有的国际清洁能源格局,不挑战、不试图打破既有的能源利益分配。二是中国的清洁能源国际科技合作应当是全方位的。从中国自身来说,应当考虑政府与企业两个层面的合作。既要参加有关国际组织的协调、对话机制,也要鼓励能源科技企业走出去。三是中国应当加深与全球层面国际清洁能源组织的合作程度,拓展与区域层面国际组织的科技合作,特别是在中国作为重要成员或主要成员的国际组织中推动创建国际清洁能源科技合作的政治框架。四是要加强与主要能源消费国的协调,特别要注意避免清洁能源竞争关系的政治化,要注意避免直接冲突。因为从国际清洁能源科技合作的发展历史看,双边合作的紧密程度直接决定了在面临突发事件时一国抵御风险的能力。五是作为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和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应当参与、甚至主导国际清洁能源合作的重要议题,全面参与协调型或对话型组织的同时,积极争取在同盟型和协作型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
清洁能源国际科技合作的主要领域应包括如下几大领域。通过国际合作能够最快和最有效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领域要优先予以考虑。一是采用低碳技术,我国能源结构将长期主要依赖煤炭,这使得我国有必要加大对碳捕获与封存新技术的研究、示范和推广的支持。二是提高能源效率和节能措施,这方面我国有极大的潜力,改善能源利用效率和节能措施,在气候和能源安全方面都能取得近期效益。三是发展智能电网,建立高效的输电系统和采用智能电网技术。四是推广可再生能源,依靠不断发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来满足能源需求增长。五是量化碳排放量,为低碳技术融资,包括对碳排放量进行准确的量化和预测,以及为低碳技术的开发和推广进行融资。
五、制订清洁能源国际科技合作国家战略的具体设想
当前,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积极与西方发达国家开展清洁能源技术合作,特别要与能源消费结构相似的美国加强沟通与协调。在清洁能源国际科技合作国家战略构想的基本框架内,现重点就中国与发达国家清洁能源合作问题提出 5点建议。
一是尽最大努力优化国内能源结构,推行节能减排。能源是国民经济的血液,能源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一旦清洁化,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速度将随之改变,不同人群的收益和不同公司的经营状况也将随之改变,财富的分配和政府工作的方式都会发生变化,这么多的变化显然将会触及到社会发展的核心。对中国来说,我们是不顾一切地要更多的、便宜的能源,还是尽最大的努力要清洁的能源?在这方面,国家层面的政策导向要清晰,要有一种无论宏观经济、国际政治环境如何变化都不为所动的坚持。法国从上世纪 60年代起就坚定不移地发展核能的实例启示中国,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清洁能源的发展,以参与相关国际合作来反推本国的发展,提高清洁新能源与传统化石能源的竞争力。节能减排已然成为了一种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一种普世价值观,一种通货。就像知识产权一样,不按照知识产权规则办事,就是在发不义之财。同理,不开发清洁能源、不推行节能减排,就是在置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不顾,出口产品因此会受到抵制。
二是逐步构建新的全球清洁能源合作框架,扩大我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国际主导权。马丁·沃夫等国外学者称中国是一个“早产的超级大国”,也就是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全世界对中国的责任期待更大了,中国有权且应该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同时也必须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和义务。随着中国的崛起,这将是中国未来国际合作面临的大战略、大挑战,也是大机遇,但是机遇不等于我们会把握好。国际能源合作政策如何适应在这一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如何运用话语权来参与、甚至是主导对我国有利的国际能源秩序、能源生产消费格局的形成和制定?这方面,我们现有的人才储备、政策准备、制度设计、能力建设显然还相当薄弱。总体来说,中国要在内政、外交、贸易、科技等各个层面构建全球清洁能源合作框架,扩大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国际主导权。具体措施主要包括:建立碳排放市场,广泛推行清洁发展机制;促进清洁能源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保障稳定的清洁能源供需,保持清洁能源价格的稳定;降低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实现全球能源利用的转型。
三是做好应对碳关税的相应准备。中国应对碳关税国际贸易纠纷比较稳妥的政策选择,是未雨绸缪,做好节能减排的宣传交流工作,让国际社会广泛认同这样一个看法:中国还没有达到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和环保水平,但是在努力,而且努力的效果是越来越好。这样,中国在应对碳关税国际纠纷方面就会较容易找到道德意义上的制高点。同时,中国要开展相应政策研究,寻求相关学理支持。如法学在内的多学科的系统研究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构建国际科技合作法律机制、引进内涵能源 (embedded energy,指产品 /产业上游加工、制造、运输等全过程所消耗的总能源,相对于直接能源消耗而言,隐含能源从另一个视角揭示了经济活动的能源消耗状况和环境影响)等理论作为政策工具。
四是加强能源科技界与外交政策界的联系,提高国际谈判能力。具体目标有 4点:一是鼓励中国能源科学家参与国际研究项目;二是提高中国为清洁能源领域的国际问题决策提供建议的能力;三是提高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整体科技能力;四是提高中国的国际声望、吸引国际社会对中国清洁能源发展进行投资,并充分利用能源国际舞台来展示中国的实力,实现国际研发资金、智力资源、人力资源流入中国的战略意图。通过支持那些政府和社会行为体 (包括科技界)之间互动的论坛,全球问题的治理可能会取得更大的突破。必须建立和培育能源科技界和外交政策界之间的联系,让科学家和决策者以相似的方式了解情况:前者了解决策的现实;后者了解能源科技在政策中的作用和局限。必须提高国际谈判参与官员对能源科技的把握能力,这对于提高中国能源和气候政策国际谈判方面的能力显得尤其重要。
五是多种形式加强清洁能源国际科技合作。可资利用的国际合作的形式至少有以下 6种:一是能源科技合作协定,包括双边、多边的正式协定;二是吸引国际相关能源科技机构和组织落户我国,政府要始终对这些国际组织给予基本稳定的支持,包括合作发展所需的经费支持,利用这些国际机构的影响力、辐射力、创造力推动我国利用国际人才和国际舞台;三是创设以我国为主导的国际能源机构、组织或者联盟。如二战后成立的欧洲核能研究中心 (CERN),该中心帮助德国和以色列之间实现了战后的首轮接触,并在冷战期间与苏俄及其它东方阵营国家保持着开放的科技关系;四是设立能源教育的国际奖学金,培养和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能源管理、能源金融、能源贸易人才来华、为华工作。如,英国的牛顿国际奖学金计划是为了从世界各地挑选最佳的处于博士后早期阶段的研究学者,给他们提供长期的支持,由此成功维持了其与英国研究机构的关系;五是能源“二轨外交”,即官方、正式外交之外的外交形式。可以用来让处于官方谈判和协调程序之外的具有公信力和影响力的科学家和学者参与进来。如,冷战时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科学院之间举行的会议都会向各自的政治领导人汇报;六是举办国际、国内能源科技节和能源科技展览,尤其是与能源科技史相关的活动,可以成为强调科学之普世性和共同文化利益的有效平台。
[1]Obama’s inaugural address[EB/OL].[2009-01-27].
[2]Obama’s remarks at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annualmeeting[EB/OL][2009-04-27].
[3]万钢 .把握全球产业调整机遇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J].求是,2010(1).
[4]万钢 .科技支撑 科学发展——在 2009中国国际节能减排与新能源科技高层论坛上的讲话[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3).
[5]李学勇 .加快推进自主创新着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J].求是,2010(3).
[6]杜占元 .加强产学研合作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J].中国科技产业,2009(5).
[7]查道炯 .拓展中国能源安全研究的课题基础[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7).
[8]马建英 .浅析中美清洁能源合作 [J].现代国际关系,2009(12).
(本文责编:海 洋)
Considerations and Suggestions on Establishing National Strategy on International Science&Technology Cooperation in Clean Energy
ZHENG Fang-neng1,FENG Ying2
(1.D ivision of Energy and Transportation,Department of High and New Technology Developm 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M 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Beijing100862,China;2.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ical Info rm ation of China,Beijing100038,China)
Starts from current international science&technology cooperation framework on clean energy,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technology cooperation in energy fields and talks about four main differences of clean energy issue between China and developed nations.Then it puts up policy-suggestions on making a national strategy and how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science&technology cooperation framework on clean energy in the years ahead.
clean energy;international science&technology cooperation;national strategy;China
G321.5
A
1002-9753(2011)04-0125-05
2010-12-15
2011-04-19
国家软科学课题(2010GXSIK087)
郑方能(1963-),浙江舟山人,科技部高新司能源与交通处处长,主要研究方向:能源与交通管理与政策。
————不可再生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