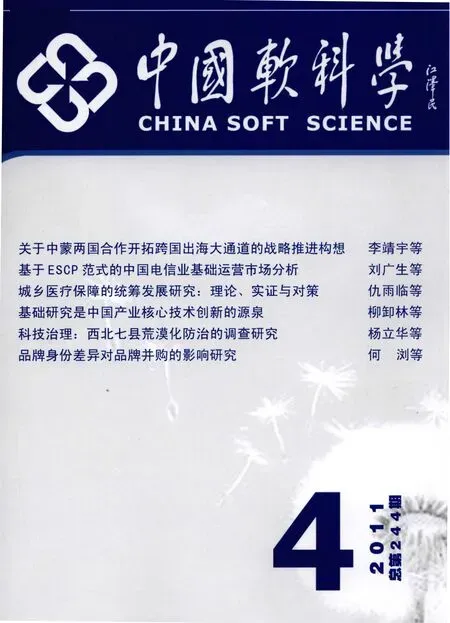创新型国家目标下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的变革与发展
张义芳,翟立新
(1.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38;2.科学技术部政策法规司,北京 100862)
创新型国家目标下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的变革与发展
张义芳1,翟立新2
(1.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38;2.科学技术部政策法规司,北京 100862)
本文以创新型国家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的共性变革趋势为基础,通过对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历史回顾,揭示了现阶段我国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中仍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指出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下,我国的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必须做出适应性调整和完善,包括:以创新体系的要求再造公共科研组织体系,多举措做强企业技术研发支撑组织,以及以组织和制度创新引领跨部门跨组织合作,推动合作研发的深度发展。
创新型国家;政府研发组织体系;科技体制改革
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是一个国家的政府为实现其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履行其公共科技职能而支持建立的制度化和组织化的研发机构体系。根据政府科技研发机构内涵的宽窄不同,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特指政府所有并由政府运作管理的研发机构 (政府直属研发机构)所构成的体系,广义的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则泛指由政府提供全部或部分资助、面向国家或政府需求开展研发活动的组织所形成的体系,其范围不仅包括政府直属研发机构,也包括按照一定的框架协议受政府资助和间接管理的半公立研发组织,以及由政府支持创立的各种形式的公私合作研发组织。尽管狭义的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是过去二十多年来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但鉴于新时期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新要求,本文选择以广义组织体系的视角,分析探讨创新型国家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的共性演进趋势,并对我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之下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提出一些认识和思考。
一、创新型国家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的发展演变
科技进步的加快和国际科技经济军事竞争的加剧牵引着各国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的深刻变革。对创新型国家科技发展历程的研究表明,过去数十年来,美欧日等先进国家基于提高本国的科技、经济、军事竞争力的需要,充分运用法规、政策、计划支持等工具,以寻求最佳的公共科技研发组织形式、保障最优化的公共科技研发组织结构、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紧密结合为目标,推动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实现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在变革的过程中,政府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进行了大量的制度尝试,有许多的组织创新,主要归纳为以下三点:
1.从传统的分工到多样化的分工合作,强化跨部门整合与协同
众所周知,各国的科技研发运行体系传统上呈现一种线性递进结构,产、学、研基本上是分立运转的孤立系统,彼此之间缺乏有机的互动性,军民部门亦是如此。然而,当代科技日益交叉融合和相互渗透的趋势,使得部门间的关联度和交互效应大大提高,客观上要求相关部门和机构在各个层次上加强研发协作和融合。而国际产业技术竞争的加剧,也迫使各国政府较之以往更多地介入产业竞争前技术研发活动。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些国家率先对本国的政府研发组织体系进行调整,从研发组织模式和资源配置上强化公私部门以及军民部门等的广泛合作,从而把国家科技活动带入全新的合作创新模式[1-3]。早在二战期间,美国政府为吸引最优秀的科学家参与原子弹研制,开创了寓军于民的军事科技组织模式,由此演化出的军民一体化军事科技体制不仅保障了美国强大的军事科技优势,也有力提升了其国防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欧洲,军民科技研发亦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德国 FhG、荷兰 TNO等国家应用研究机构集民用产业科技和国防科技研究于一身,彼此“交互肥沃、共同进化”,既保障了国防技术力量,也支持了对中小企业的技术服务[4-5]。20世纪 70年代,美国认识到新科技革命下产学合作的重要性,乃突破传统窠臼,率先资助大学建立产学合作研究中心,创造了有别于 PI课题组的全新的大学科技研发组织模式,不仅为大学创造了新的科研发展空间,更加速了新科技创意向市场的转化。也是在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产业技术竞争,运用政企合作的“研究组合”,成功地抓住了新技术产业革命的战略机遇,成为各国建立官产学研产业技术研发联盟的典范。及至 1990年代,区域创新受到重视。作为激励区域创新的策略安排,各国加强以合作为特点的区域创新网络建设,德国的“生物区竞赛”计划、“纳米区竞赛”计划、法国的竞争力园区计划,均代表了两国以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为目标的创新集群发展新策略,展现出政府不同的科技研发组织策略思考。这些不断涌现的合作涉及政企合作、产学研合作、军民合作、中央地方合作,是各国政府面对全球科技、经济、军事日益加剧的竞争所采取的科技研发组织模式变革,不仅打破了传统的部门界限和层级阻隔,克服了分割管理模式中分散化、功能分割、各自为政的缺陷,也推动了以提升产业、区域和军事竞争力为目标的多样化合作研发组织的勃兴。
范围广泛、内容丰富的跨部门跨组织研发合作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现已成为创新型国家组织国家重大科技研发活动的主导模式。然而,在保持部门和组织分工的前提下实现跨部门跨组织合作是存在相当难度的,必须加强国家层面集中决策,国家层面统筹设计以及强力的独立监管,才能有效克服部门自我中心主义和组织合作障碍,推动合作的顺畅实现 (美国国会在军民科技融合上发挥了强力的监管促进作用)。近年来,创新型国家围绕科技研发合作体制建设,均加强了由国家首脑领衔或对国家首脑负责的跨部门科技决策、协调或咨询体系建设。这种宏观统筹管理为实现跨部门跨组织合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体制保障,体现了深刻的创新系统思想。
2.以精简、高效、优化为核心,再造政府科研机构体系
为国家创新体系奠定坚实的公共科技基础是创新型国家政府科技施政的主要目标。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 1990年代的十年,是主要国家重构其政府科研机构体系的重要时期。新公共管理运动促发的公共部门改革、新科技革命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科研优先领域变化、大学科研力量的崛起,加上政府科研机构本身因体制机制弊端而导致的机构臃肿、使命不清、效率不高、科研与经济脱节等问题,促使一些国家的政府下决心对本国的政府科研组织体系进行调整和改革,探索有助于提高公共科研生产力的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以提升政府研发科研体系的效率、适应性以及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各国政府科研机构改革的重心是改变长期形成的官僚式科研体制,提高效率。改革在一些国家采取的是非连续性渐进模式,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则较为激进,涉及科研机构组织形态、管理方式甚至所有权等重大变革。这场变革打破了长期单一僵化的政府科研组织形态,产生了作为政府执行机构的科研机构 (英国)、独立行政法人科研机构 (日本)、国有商业化公司 (新西兰)、政府参控股公司 (瑞典)、政府资助的独立非营利科研机构等新型的组织形态。新组织形态突破了政府科研机构僵化的官僚体制,引入了私营部门先进的组织管理经验 (如法人治理结构、竞争机制、灵活的人事薪酬和绩效管理制度等),扩大了科研机构的自主权,激发了科研机构的生机和活力,提高了科研效率。而与科研机构组织形态变革相适应,政府对公立科研机构的治理也从传统的“控制导向型”向“保持距离和关系型”(arm’s length)转变,由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 (比如部分科研机构采用研究委员会等中间型治理组织管理)。一种以委托—代理关系为基本框架、以契约制为治理机制、以提高公共科研使命性和效率性为主要目标的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初步形成[6-8]。
精简机构,明晰政府支持的科研机构的范围、重点和力度,也是一些国家政府科研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鉴于科学研究的无限性、国家财政的有限性以及政府科研机构本身的一些体制机制局限,各国严格界定国家科研事业的职能范围,不仅从严控制政府科研机构设置规模和数量,减少不必要的重复设置,而且把因情势发展可以脱离政府职能范围的科研机构或已可以社会化运作的科研机构,通过民营化、市场化、企业化或合并进入大学等方式剥离,以集中国家的有限财力,办好国家科研职能范围内的公共科研事业。在精简的同时,优化结构,扩大新兴高科技领域的科研组织设置。对确定为享受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则按照国家科技优先领域和战略规划,明确使命和功能定位 (一些科研机构存在使命模糊和功能异化问题),并根据机构的具体性质和特点,采取差异化的资助制度,比如英国作为执行机构的科研机构,按机构性质又细分为全额财政拨款机构、财政补助机构、净支出财政拨款机构和营运基金类机构四种类型,给予不同的资助安排,并形成规范的约束制度,以实现政府科技投入价值的最大化。
3.加强技术基础设施和企业研发服务组织的建设
至少在上世纪 80年代以前,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的政府对研发活动的支持仅限于基础科学和与政府使命相关的研究,认为基础科学才是“公共物品”,其供给是政府的责任,而技术作为经济活动的资产是纯粹的私人物品,政府不必干预或支持。然而,冷战后全球产业技术竞争日益加剧的现实,改变了政府固守的这一职能分界。事实上,技术经济学家早就提出,技术具有公有私有两面性,而技术基础设施则被当代学者广泛认为属于公共或准公共物品的范畴,这就为各国政府制定技术政策、干预技术研发活动提供了理由。
近十年,各国政府科技研发组织和计划中促进产业部门技术创新的成分明显增加,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加大对产业技术基础设施的投资。基础技术、共性关键技术等作为重要的“技术基础设施”,是企业开发与应用新技术的基础,而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也急需国家增加新兴技术基础设施供给。近年来,美国政府实施的竞争力计划和国会通过的竞争法案,均将主要从事标准与基础技术研究的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 IST)列为少数重点支持的机构,反映了政府对作为产业技术创新平台的技术基础设施的高度重视,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则启动了相关计划,如以色列的“共性研究与发展和技术基础设施 (Magnet)计划”和韩国的“产业技术基础设施计划”[9]。二是从弥补市场供给不足的角度,支持服务于企业的应用研究组织的发展。在欧洲,不仅有大体量的国家型综合性应用研究机构,如德国弗朗恩霍夫学会(FhG)、芬兰国家技术中心 (VTT)和荷兰应用科学研究院 (TNO),政府还支持大学建立各种应用研究中心,同时支持形形色色的行业研究协会的发展。这些应用研究机构面向企业需求,帮助企业提升技术和商业流程,对促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活络国家创新体系贡献良多①例如在德国,弗朗恩霍夫学会(FhG)、工业研究协会联合会 (AiF)以及附属于大学的应用研究中心均提供面向企业的研发服务。FhG中来自中小企业的研发合同已占到其产业研发合同的 60%,而AiF基本上完全面向中小企业,通过促成中小企业的合作研发来提升德国中小企业的技术竞争力。在英国,新任首相卡梅伦2010年10月宣布启动技术与创新中心网络计划,政府将在未来4年内投资2亿英镑,创建一系列技术创新中心,以促进英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三是制定相关法律和制度,利用政府部门的研发资源支援民间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将创新型小企业纳入到政府科技研发组织工作中,这方面美国堪称典范。按照相关法律,美国主要的政府部门和机构必须以研发采购的方式招募小企业参与其SB IR计划补助的研发课题 (知识产权归小企业所有),同时,政府部门和机构在履行自身使命的工作中也充分利用和推动小企业的创新。比如国防部的国防预研项目,特别重视吸收小企业参加,将小企业作为美国未来的国防预研创新竞争能力来培育;国家科学基金会支持的工程研究中心(ERC),专门吸收创新型小企业参与转换型研究活动,以利用小企业创新能动性强的优势,促进 ERC研究成果的商业化 。
创新型国家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的上述演化和发展,是这些国家选择创新型国家发展道路的必然结果。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近年来陆续推出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以提升国家经济竞争力为目标发展政府科技组织体系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继创新型国家之后,追赶型国家的政府也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目标,调整和完善本国政府的科技研发组织体系。然而,尽管各国在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发展方向上具有上述的一致性,但在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大国和小国、市场经济国家和转型国家,因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不同,变革的环境和条件不同,变革的进程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二、我国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的变革进程
我国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的变革是在整个国家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环境中进行的,是随着整个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而逐步推进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效法前苏联的国家管理模式,将国家科技研发组织和活动纳入高度集中的行政体系,由此形成了与计划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以国家统一计划为特征的行政管理计划型科技体制。这种高度集中的科技体制,在科技资源少、活动规模小、国力有限和国际封锁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巨大的制度优势,为我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防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固有弊端却日益显现,主要表现在:条块分割,科研机构体系庞大臃肿、效率不高;科研组织大一统,科研院所作为行政附属物,被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科技和经济严重脱节,科技成果不能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科技体制改革成为历史的必然,而科技体制改革首先从改革旧体制下的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开始。
1985年中央颁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在经历了 1978年以来的酝酿和探索之后,进入到有领导的全面展开阶段。从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的角度,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985-1994年:这一阶段,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是“面向、依靠”,政策走向最重要的是“稳住一头、放开一片”,分流科技人才,盘活科研结构,引导科技工作面向经济主战场。主要措施包括改革科研机构的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扩大科研机构自主权以及改革科研人员管理制度等,目的是将市场手段和竞争机制引入政府科技组织工作中。
1995-1998年:按照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要求,出台了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提出了“调整结构、分流人才、转换机制、制度创新”四项改革内容。鉴于“调整、分流”涉及的问题较为复杂和困难,决定先进行试点,包括基础研究“五所二校”试点和四个产业部门研究所结构调整试点,为下一阶段全面改革探索方案、积累经验。
1999-2005年:在前期试点基础上,调整和分流的对象从个别院所和少量部门作为操作单元,转向对科研院所的布局结构进行系统调整。1999年中央提出全面推动应用开发类科研机构和设计单位向企业化转制,对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实行分类改革。此次改革之后,全国共有 1200多家技术开发类院所转为或进入企业,从体制上解决了大批应用开发类院所长期游离于企业之外的问题。公益类科研机构也按分类转型、保留精干队伍、加大政府支持力度的路线进行了全面调整。与科研机构改革相伴,科技中介服务组织获得加速发展。也是在这一时期,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引入中国,政府开始用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框架重新思考中国的科技体制问题。
2006年以后,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的总体部署,将全面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确立为新时期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开始从分类推进向系统推进转变,改革重点也从体系结构调整与微观运行机制改革,进入到以明确创新主体功能定位、强化创新主体能力、促进创新要素联系互动,从而提高创新系统整体效率为重点的宏观和微观结合层面,以形成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国防科技创新、区域创新、科技中介服务等相互促进、充满活力的国家创新体系[10]。
总之,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在 2006年以前基本上是围绕调整科技研发组织体系结构和完善微观运行机制渐进展开的,逐步完成了大规模、大范围的结构调整任务。这个改革过程是艰难的、曲折的,成效也是巨大的。通过改革,我国公立科研院所数量大幅度减少,从改革前的 5000多家,减少到目前的 3000多家,科研机构的学科和人才结构得到显著优化,组织形式趋于多样化,“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运行机制得到普及和加强。2006年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新体改目标确立之后,改革的重心从“自下而上”突破旧体制障碍,向更加注重“上下互动”推进系统整合和制度创新转变,以提高系统整体创新效率。按照创新体系的新目标审视我国的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目前尚需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一是我国的公立科研机构无论是在数量结构、组织形式、使命功能定位、制度机制以及科研质量效率等方面还没有达到创新体系的要求。在一些领域,规模过剩与布局分散的顽疾依然存在。我们明确了公共研发服务应采取直接组织、间接组织及出资购买并举的方式,但它们之间的分界原则还不明晰,相关的组织形式或制度安排有待建立;而对政府直接举办的科研机构,至今没有建立起法律制度保障下的有效力的监管、评估和问责制度,造成一些科研机构偏离自身的使命或功能定位,科研活动随意性较大;与此同时,科研院所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行政主导资源配置、以简单的行政评价代替同行评价等不合理的制度机制在一些院所仍然存在。
二是公私部门间缺乏有效的互动,上中下游有机联系的完整创新链发育不健全,未能形成资源集成、有效协作的良好组织制度环境。例如,产学研结合一直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重点难点问题,然而时至今日仍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从体制上看,缺乏顶层设计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产学研结合涉及科技、教育、产业、财政等不同行政部门之间在政策和资源上的协调与整合,没有国家最高层的统领以及强力的监管促进,产学研结合很难实现自上而下的质的突破。此外,高效的科技桥梁组织稀缺也是制约我国产学研结合的一大瓶颈。我国没有类似德国弗朗恩霍夫学会这样的国家型非营利性应用研究机构,通过转换型研究,将大学 (上游基础研究)和产业界(下游技术开发)有机结合在一起;也缺乏像美国半导体研究公司 (SRC)的第四极媒合组织,缺乏能直接接手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并将其迅速商业化的创投公司和创业型企业。
三是我国科技研发组织体系中,尚缺乏向社会开放、系统配套的公共技术平台和综合性企业研发服务组织。在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基础技术和共性技术支持,而共性技术、基础技术服务薄弱一直是影响我国企业技术创新的障碍。近几年全国各地兴建了一批公共技术平台,但真正能促进企业创新发展的却不多。公共技术平台该如何建设、如何运作以及以怎样的方式来促进产业技术创新,成为政府目前十分关注的问题。另外,在行业和区域集中度低、中小企业密集的某些行业,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中小企业技术研发服务组织网络。
三、创新型国家目标下我国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的发展方向
创新型国家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的演进以及我国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存在的与国家创新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加快推进以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为目标的科技体制改革,在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的发展上实现四大根本性转变——目标提升、功能扩展、组织模式演进和管理创新。具体而言,目标上应从聚焦国家科技发展提升到全面关注国家整体的创新能力和贡献;功能上从解决“市场失灵”为核心扩展到兼顾“系统失灵”的体系功能,以系统性的方法对研发创新相关组织流程和环节做全面优化。与之相适应的是,传统的以支持大学和科研院所为特征的公共科研组织模式,也应逐渐扩展到包含公私合作组织模式。在科研管理上,则必须按照现代科研院所的要求,完善政府治理模式,提高科研院所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性与治理机制的有效性。只有经过这样的全面转型,才能最终在我国建立起适应国家创新发展需要的、完善高效的政府科技研发组织体系。
(一)从结构 -制度 -机制三维入手,以创新体系的要求再造公共科研组织体系
公共科研组织体系的再造,涉及公共科研组织的新建和某些科研组织的转型和功能调整,重点是要解决公共科研领域的重大结构、制度和机制问题。一是进一步优化公共科研组织的体系结构,在通过多元转型和结构重组实现科研院所体系精干化的基础上,细分科研机构类型,给予不同的资助安排,并形成差异化的管理制度,同时着力加强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二是从公共科研服务需求的具体性质入手,灵活选择公共科研服务提供与生产的多样化方式,如由政府直接组织 (政府直属科研机构)、间接组织 (政府给予特别资助的科研机构)或政府出资购买 (向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研发机构购买研发服务)。三是完善政府直属科研机构的治理模式,从传统的“控制导向型”向“适距控制型”转变,形成以委托代理关系为基本框架,以契约制为治理机制,以提高公共科研使命、效率和质量为主要目标的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四是以改革科研机构内部行政化管理模式为重点,推进科研院所和大学建立现代科研管理制度,提高公共科研管理的品质和效率。五是推进国际评价,对国家级科研机构的创新能力和科研质量实行国际标准评价,促使其以“产出”影响为导向提高科研效率,以逐步增加世界级研究基地的数量。
(二)多举措做强企业技术研发支撑组织体系,助力企业技术创新
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是现阶段我国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着力点和突破口,需要政府在科技研发组织策略上做出相应的调整,包括:(1)加强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组织的共性技术研发与扩散功能,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共性技术的支持,多形式多层次培育共性技术研发主体。(2)从国家层次支持发展若干综合性公共技术创新平台,特别是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先进制造系统的研发以及优秀中试基地的建设。(3)加强面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研发服务组织网络建设。借鉴德国和英国的经验,将分散在一些行业和地方的技术开发机构按行业或区域归并,并最终形成伞形的全国产业技术研发协作组织,以此为基础搭建中小企业技术服务的区域、行业和国家平台,更有效地为企业服务。(4)实施创新集群和区域技术中心促进计划。以竞争性资助方式支持集群创新网络的发展,促进传统集群向创新集群的转型,同时支持各区域依托大学等创办工业技术研究组织或产学研研发联合体,为区域特色产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科技基础。
(三)以组织和制度引领合作,推动跨部门跨组织合作研发体制的深度发展
组织和制度是促进研发合作体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在部门分立、条块分割的现实体制之下,军民合作、产学研合作等的深入发展有赖国家自上而下做出强有力的组织和制度安排。在宏观管理层面,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国家顶层科技统筹协调体制和机制,变革分割管理模式,推进“跨部门协作”,在微观组织层面,要消除影响合作研发的各种组织制度缺陷。以产学研结合而言,一方面,要广泛借鉴国际最佳组织实践,加强公共部门产学研合作研究组织建设,完善其功能定位、组织形态、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并高度重视独立非营利应用研究机构和行业研究协会等科技桥梁组织的培育,发挥其独特的媒合功能。另一方面,要着力整合官产学研资源,促进重大技术研发联盟和创新网络的形成和发展。自 2007年起,科技部已着手推动重点产业组建产学研合作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目前开局良好,示范作用已经显现。然而,要实现产学研创新联盟的良性健康发展,还需要政府在跨部门统筹协调、政策法规、计划支持以及联盟组织等方面提供更为有力的保障。当前,应以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契机,在国家战略性产业发展的相关技术领域,推动建立上游的探索性基础研究、中游的应用研究直至下游的技术或产品开发的完整的创新组织链条,增强共性、关键和前沿技术突破能力,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升我国的产业核心竞争力。
[1]Industrial Research Institute.A Report on Enhancing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ve Research Agreements[R].University Relations Committee,Washington DC,1995.
[2]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R].STIReview No.23,OECD,1999.
[3]R Lambert-HM Treasury.Lambert review of businessuniversity collaboration[R].HMSO December,2003-hmtreasury.gov.uk.
[4]www.fraunhofer.de/[EB].
[5]www.tno.nl/[EB].
[6]Michael Crow,Barry Bozeman.美国国家创新体系中的研究与开发实验室 [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
[7]OECD.公共研究的治理——走向更好的实践[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6.
[8]OECD.The Changing Role of Government Research Laboratories[M].Paris:OECD Bookshop,1989.
[9]吴建南,李怀祖 .技术基础设施研究进展[J].科研管理 ,1999,(1):61-68.
[10]万钢主编 .中国科技改革开放 30年[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本文责编:润 泽)
Changes i n Governmental R&D Organizations and I nstitutions Towards an I nnovative Country
ZHANG Yi-fang1,ZHA ILi-xin2
(1.Institute of Scientific&Technical Info rm ation of China,Beijing100038,China;2.M 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Dept.of Policy and Regulation,Beijing100862,China)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common evolutionary trends of governmental R&D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n innovative countries.On the base of brief review of China’s S&T system refor ms,the unresolved issu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Chinese Government in R&D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are explored.Finally,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suggestions for Chinese government to improve its R&D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towards an innovative country.These suggestions include:restructuring public sector research institutions,enha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R&D service organizations to provide supports to enterprises’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facilitating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e cooperation by 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novative countries;governmental R&D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S&T system reforms
G311
A
1002-9753(2011)04-0118-07
2010-11-08
2011-02-21
张义芳 (1964-),女,天津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科技管理、科技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