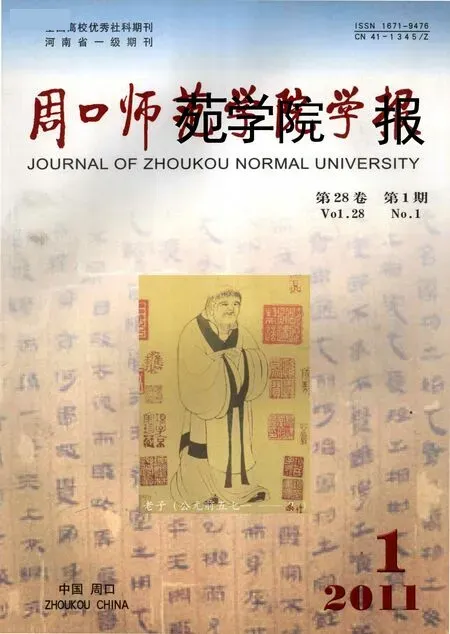论韩愈庄骚并举之意义
李生龙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论韩愈庄骚并举之意义
李生龙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韩愈“庄骚”并举的意义有四:在儒学语境下,“庄骚”并举,且置“庄骚”于儒家经典之后,提升了“庄骚”的地位;启发了后世对庄骚共性的思考,促使人们对庄骚的思想内蕴、艺术精神作深入探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庄骚浪漫、谲怪特色形成的原因,并使之得到比较符合儒家理性的解释;激发了后世学者对庄骚接受史的探讨,使庄骚在文学史上的传承线索渐趋明朗。
韩愈;庄骚;并举
韩愈《进学解》提出的“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诘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既是韩氏自己的古文攻习范围,也是古文运动成员的古文攻习范围。其中“庄骚”并举,其意义如何,学者多习焉不察,似无人深入考察。本文就此发表一点看法,向同行请教。
一、在儒学语境下,“庄骚”并举,且置“庄骚”于儒家经典之后,提升了“庄骚”的地位
楚辞与庄子虽可能产生于相近的文化土壤,艺术上又有许多共通之处,但在先秦时代,它们基本上各行其道,互不相干。汉代以后,庄与骚事实上逐渐有了关联。韩愈之前,许多作家如贾谊、扬雄、张衡、赵壹、阮籍、嵇康、郭璞、张九龄、李白等在具体创作中都已融汇庄骚,这一点,笔者在《论庄、骚的融通与影响》[1]一文中已有所论及。
然而,汉代的文化主流是儒学及史学,儒者、史家都讲究“无征不信”“不语怪力乱神”,秉持儒者或史家崇有尚实的理性精神,对庄骚的浪漫、虚幻成分并不认可。庄、骚的文辞虽然也颇受儒者或史家称赏,其地位却不仅不能同儒、史并列,甚至难以附儒、史骥尾;如果有人想提高庄骚的地位,就不得不将之牵强地比附于儒家经典。
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评论庄子说:“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孟子荀卿列传》甚至称庄子为“滑稽乱俗”的“小儒”。司马迁看重的是庄子善于属书离辞,指事类情,而对其寓言“空语无事实”颇有微词。对楚辞,司马迁《贾生屈原列传》所取的是推崇楚辞的刘向的评价,对楚辞中同样存在的“空语无事实”的内容未予涉及。可到了东汉,班固作《离骚序》,就开始从儒学角度批评楚辞“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认为楚辞中的昆仑、宓妃之类的虚荒诞幻内容不符合儒家理性。班氏是儒者,又是史家,他的态度代表了儒家与史家的基本立场。
屈原和楚辞的推崇者王逸,力图把楚辞与儒家经典联系起来,并证明楚辞符合儒家经典,以便把楚辞提升到与儒家经典并列的地位。他称《离骚》为“经”,说楚辞也是运用比兴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以便借儒经权威来解决楚辞中存在的“虚无之语”与“非法度之政”之类的问题:“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帝高阳之苗裔’,则《诗》‘厥初生民,时维姜嫄’也……‘驷玉虬而乘鹥’,则《易》‘时乘六龙以御天’也;‘就重华而陈词’,则《尚书》‘咎繇之谋谟’也;‘登昆仑而涉流沙’,则《禹贡》之敷土也。”[2]
王逸的解释虽牵强,却提升了楚辞的地位,故后来为颇有儒家情结,并且非常注重提升楚辞地位的刘勰所部分采纳。刘勰对前人的楚辞评论有所折衷,他承认楚辞同儒家经典既相合又不相合。《文心雕龙·辨骚》说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等四事乃“比兴之义”,是维护王逸的意见;说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等四事乃“诡异之辞”,不符合儒家经典,意见跟班固一致。这种折衷,可谓用心良苦。显然,刘勰也没有解决楚辞中的浪漫、虚幻成分是否合理的问题,更没有解决《庄子》“空语无事实”的问题。
魏晋南北朝至初唐绝大多数人都把屈原当文人看待,只是一般论者都认为屈原的品格、地位高于宋玉、景差、唐勒等一般文人。但到盛唐,屈原的地位反而下降到同宋玉并称“(屈宋”),完全被视为“词人”了[3]。魏晋玄学家以《易》《老》《庄》为“三玄”,且多研究《论语》,隐含着将《庄子》与儒家经典并列的意思,但因庄子有明确的否定名教、否定儒学的矛盾倾向,故儒家情结较深的士人多攻击老庄。唐代崇道,尊庄子为“南华真人”,科举设有“道举”《,庄子》为士人所普遍修习,这可能为韩愈将《庄子》附于儒家经典之后创造了条件;但庄子变成了道教神仙,又同攘斥异端的儒家有对立的一面,因而一般儒者也不便公然把庄子拉到儒家门下。
总的说来,在韩愈之前,除王逸、刘勰等极少数人力图用楚辞攀附儒家经典外,玄学家将《庄子》同儒经《周易》并列外,庄与骚同列于儒经之后的现象从未有过。庄、骚大致各行其道,虽然创作界有融通庄、骚之实,理论界却没有人把庄、骚并举。
韩愈把庄、骚相提并论的理由是什么,韩氏自己并没有直接说出。宋代魏仲举所编《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二《伤春四首》其二“屈原《离骚》二十五,不肯啜糟与醨。惜哉此子巧言语,不到圣处宁非痴。幸逢尧舜明四目,条理品汇皆得宜”数句下注云“:韩(醇)曰:先儒云:公以(屈)原词介于庄周、司马迁之间,其《感春诗》云云,盖与屈原之惩于风谏,而伤其违圣之达节也。”《(四库全书》)这里说韩愈认为屈原的作品介于《庄子》与《史记》之间,肯定屈原的惩于讽谏,却为屈原有违圣人之通达节概而伤感,其实也是根据《进学解》所作的推测。
这里我们姑且不深究韩愈内心到底怎么想,只是从情理上作一些推测:韩愈虽以复兴儒学自命,想建立起儒家的“道统”,却因为他只是文人,更多的是思考如何建立儒家的“文统”。就儒家“文统”而言,他在《答李翊书》中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读”,学习范围定在“三代两汉”之间,而庄、骚正在此一范围之内。他虽辟佛老,但在唐代普遍崇道的文化背景下,批佛是主,老只是连类而及。且庄子虽被称为南华真人《,庄子》虽被称为《南华真经》,并非为道教所专有,唐代士大夫不读《庄子》者很少,所以《庄子》似不是他所辟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前代文人创作,特别是韩愈本人的创作,实际上都未能绕开庄、骚。
与韩愈志同道合的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也开列了一个古文学习书目:“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柳氏对这个书目交待得比韩愈清楚一点,他之所以把儒家经典列在前面 ,是因为那是“取道之原”;取《庄》《老》,是为了“肆其端”,即从一个侧面拓展文学创作的源头;取《离骚》,是为了“致其幽”,即为了使创作更加深沉幽眇。柳氏的这个书目虽与韩愈相近,并在说明理由方面胜于韩愈,却因为把庄、骚隔离开来,反而不及韩愈把“庄骚”连在一起那样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李翱作为古文运动的一员,也曾在《答朱载言书》中说:“六经之词也,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也。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4]李氏把庄、骚并列,且称读了庄、骚就好像“未尝有六经”,从庄、骚“创意造言”的独创性角度认定它们堪与儒家经典比肩,其观点本于韩愈又跨越了儒经独尊的底线。他的提法可能有些过头,没有引起后世儒士的广泛回应。
韩愈把庄、骚并举,且让它们紧附于儒家经典之后,看上去是一件平常事,却极大地提高了庄、骚的地位。因为在儒学作为主流话语的时代,韩愈是大儒,被后世推为文宗,他的评价当然极有分量。故韩愈之后,一般儒者多认同他的提法。宋人胡仔说:“学者欲博读异书。余谓退之《进学解》云:‘上窥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丘》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若只读此足矣,何必多嗜异书?”[5]明人刘绘说:“韩子曰:‘易奇而法,诗正而葩,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正道气与辞也。天地之理,中焉已矣。其气深厚和平,其辞大雅宏畅,则圣人之文也,六经是已。孔子删述,自谓‘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善学孔氏者,唯孟轲一人,其后诸子理不足而任于气,故其辞醇疵相杂。荀卿以下庄、骚、太史、董仲舒、贾谊、刘向、扬雄诸人,穷理尽性,虽不能如圣人,而纂辞摹像,则标准六经,故旨趣各随所见,而篇章音欵莫有踰焉。”[6]清人蔡世远记其伯父习孚先生云:“士不读庄骚班马,一木偶人耳。六经之外,唯此最要,而后渐及于诸子百家,汝其识之。”[7]清人乔亿说:“诗学根本《六经》,指义四始,放浪于《庄》、《骚》,错综于《左》、《史》,岂易言哉 !”[8]1069又说:“诗不缘于《楚骚》,无以穷《风》、《雅》比兴之变,犹夫文不参之《庄子》,虽昌明博大,终乏神奇也。”[8]1116
当然,后世也有儒者不同意韩愈的意见。比如宋儒王炎批评韩愈以文章为道,故言“下逮庄骚”[9],明人受理学浸润较深的顾璘批评当时文人学习儒术未烛大义,就负其高明,“驰意于荒忽诡诞之技,取庄骚、扬雄氏之言而影响刻画,艰文奇字,读者不能句,朋徒相誉,号之曰‘才’”[10]。但从总体上说,韩、柳所开的书目为后世学古诗文者所继承,庄骚并列的格局也从总体上得到确定。
二、庄骚并举,启发了后世对庄骚共性的思考,促使人们对庄骚的思想内蕴、艺术精神作深入探究
庄与骚有何共同特点?韩愈之前,尽管已有不少人在创作中融通庄、骚,却未能从理论上加以分析、概括。就是韩愈、柳宗元、李翱等,对庄、骚共性的认识、表述也是模糊的、语焉不详的。但是到宋代,人们的认识便逐渐清晰起来。例如曾巩《祭欧阳少师文》称赞欧阳修:“唯公学为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发,醇深炳蔚,体备韩马,思兼庄屈,垂光简编,焯若星日。”[11]把“思兼庄屈”看做欧阳修文章的一大特色。宋人诗歌中则每每有对庄骚共性的概括:
韩维:法书传隶古,才笔拟庄骚[12]。
苏辙:微言精老易,奇韵喜庄骚[13]。
陆游:安得人间掣鲸手,共提笔阵法庄骚[14]。(自注:韩文公以《骚》配《庄》,古人论文所未尝及也。)
陆游:遗文诵史汉,奇思探庄骚[15]。
陈造:虚孰高名擅顾陆,仅识妙思陵庄骚[16]。
程公许:崛奇庄骚语,雅淡商周颂[17]。
仇远:搜奇薄庄骚,稽古极羲昊[18]。
韩维称庄骚为有“才笔”,苏辙谓庄骚有“奇韵”,陆游谓庄骚乃“掣鲸手”,探之可得“奇思”,陈造谓庄骚有“妙思”,程公许谓庄骚之语“崛奇”,仇远也说庄骚有“奇”的特点。这些概括,都指出了庄骚在构思、造境、语言等诸多方面的共同审美特征。
宋人已开始注意将庄、骚加以比较。据林希逸《南华真经口义·外篇·骈拇》注,塘东刘叔平曾作过《庄骚同工异曲论》,林氏对之加以发挥说:“塘东刘叔平向作《庄骚同工异曲论》曰:庄周,愤悱之雄也。乐轩先生甚取此语。看来庄子亦是愤世疾邪而后著此书,其见既高,其笔又奇,所以有过当处。”[19]刘叔平之《庄骚同工异曲论》今不可见,林希逸在他的基础上发挥,认为庄子也跟屈原一样,是一位愤世嫉俗的人,识见高,下笔奇。林希逸还对庄骚的特点有所概括。其《次云方先生诗集序》云:“得遗风于风雅,寄逸思于庄骚。”[20]指出庄骚的共同特点是有“逸思”,即想象力强、情致高远。林氏还有一首《读黄(庭坚)诗》,称赞黄庭坚作诗深得庄骚遗意:“我生所敬涪江翁,知翁不独俄诗工。逍遥颇学漆园吏,下笔纵横法略同。自言锦机织锦手,与寄每有《离骚》风。内篇外篇手分别,冥搜所到真奇绝。颉颃韩柳近庄骚,笔意尤工是晚节。……”[21]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了解林氏对庄骚精神的理解是多方面的。
宋人方澄孙有《庄骚太史所录》。该文是对韩愈“下逮庄骚,太史所录”观点的解读,故先从儒家宗经的立场、文章发展正变的角度来谈《庄》《骚》《史记》的地位和影响,说:“盖自《六经》而下,唯《庄》《骚》《太史》为最工,有志于文者,类喜言之。虽然,《庄》者,理义之变也;《骚》者,《风》《雅》之变也;太史所录,乃《尚书》《春秋》之变也,不变则不工矣。”从正变说入手肯定六经不可动摇的地位和《庄》《骚》《史记》的价值,符合韩愈“下逮庄骚,太史所录”之本意。接着作者针对当时某些人否定庄子、屈原、司马迁的言论加以批驳:“然而世之议三家者,曰漆园之文伟,其失也诞;灵均之文深,其失也怨;司马父子之文浩博闳肆,其失也豪。噫,亦孰知其不诞则不伟,不怨则不深,而不豪则不足以发其浩博闳肆也哉!夫大羹玄酒,味之正也;《云门》《咸》《韶》,音之正也。三家者,负其诡异杰特之才,不安乎正而必出乎变,力扫世俗之尘腐,而为千古言语文字之宗祖,其用志亦良苦,而自成一家 ,亦良可喜矣。”肯定了《庄》《骚》《史记》“力扫世俗之陈腐”的美学价值。
方澄孙不仅站在儒家立场推崇六经而肯定《庄》《骚》《史记》的美学价值,还从文章艺术的角度对儒家六经的缺陷和《庄》《骚》《史记》的艺术魅力加以比较,以见出由正而变之出于不得已。文章以似抑实扬的手法指出,圣贤之正论会流于淡薄无味,《风》《雅》之正声会流于简朴无华,《尚书》《春秋》之正例会流于谨严太过、绳尺甚苛;而《庄子》之文广譬博喻,使人心旷神怡;屈原之文凄切感惋,使人志消意沮;司马迁之文雄浑雅健,更使人气疏才涌。因而《庄》《骚》《史记》之文虽属变体,未能完全符合儒家之道,却为工于文者所喜。文章结尾勉励学者努力修习、接近儒家之道,劝诫他们不要流于秦汉以后之文风,且似对韩愈略有微词:“噫,学至韩愈,文至《庄》《骚》《太史》,而终不足以近道,则有志圣贤之事者,安得不重有感于斯!”[22]然细按文意可知,这种批评是不痛不痒的,实际上作者仍是在解读、维护韩愈的观点。文章对《庄》《骚》《史记》特点、价值揭示得非常具体细致,有比较,有概括,客观上有助于学者理解韩愈“下逮庄骚,太史所录”的用意,体现了宋人对庄骚思想艺术价值的深刻理解。
元人刘壎认为玩味、取法庄骚是诗文涤去尘俗、不断出新的源头活水:“语意不尘,诗文之一妙也。韩文公曰:‘唯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或曰:是不难。熟覆庄骚,即不尘矣。夫《南华经》与《楚辞》二书,经千有余年,然一展读,则焕然如新。学文者能取庄骚玩味之,又取《世说新语》佐之,则尘腐之疾去矣。”[23]
明代作家对庄骚共同特点的理解比前代更为具体、深入。何良俊从庄骚各自的特点及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角度说:
春秋以后,文章之妙,至庄周、屈原,可谓无以加矣。盖庄之汪洋自恣,屈之缠绵凄婉,庄是《道德》之别传,屈乃《风》《雅》之流亚,然各极其至。若屈原之《骚》,同时如宋玉、景差,汉之贾谊、司马相如,犹能仿佛其一二。庄之《南华经》,后人遂不能道其一字矣。至如庄子所谓嗜欲深者天机浅,屈子所谓一气孔神于中夜存,又能窥测理性,盖庶几闻道者。盖古人自有卓然之见,开口便是立言,不若后人但做文字[24]。
归有光从地域的角度说:“荆楚自昔多文人,左氏之传,荀卿之论,屈子之骚,庄周之篇,皆楚人也。试读之 ,未有不《史记》若也。”[25]说左氏、荀子、屈原、庄周皆楚人,其文皆如《史记》,颇有自己的体会,可惜未说出理据。
陈继儒对庄骚的行文特点及诠释方式也有很独到的剖析与见解:
古今文章无首尾者独《庄》《骚》两家,盖屈原、庄周,皆哀乐过人者也。哀者毗于阴,故《离骚》孤沉而深往;乐者毗于阳,故《南华》奔放而飘飞。哀乐之极,笑啼无端,笑啼之极,语言无端。乃注者定以首尾求之,李北海所谓似我者拙,学我者死也。大抵注书之法,妙在隐隐跃跃,若明若昧之间,如詹尹之卜,取意不取象。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辞。龙不挂钩,龟不食墨。悬解幽微,何常之与有?而况庄子哉![26]
谭元春著《遇庄》33篇,在序言中介绍自己读《庄子》的方法说:“阅《庄》有法:藏去故我,化身庄子。坐而抱想,默而把笔,泛然而游,昧昧然涉,我尽庄现。循视内外,其有不合者,听于其际与其数。如咒咒物,物利咒止,又如物获咒益,不晰咒故,因而遇之,芒昧何极?……”这显然是一种体验读书法。有意思的是,他认为读《庄》要“庄骚同思”,通过体验楚辞来进一步体悟《庄子》:“文理潦倒,《庄》《骚》同思。我爱《天问》,灌灌如诉,薄暮雷电,即记其事,前丝后丝,总不相连。兹谈羊蚁,胡乃及鱼?见鱼书鱼,想亦如是,因而遇之,以破吾拘。至巧者化工,人敢椎拙,仰而思天,宁不怪绝!瞻彼小草,叶叶染采;小虫跂跂,其壳青黄。天地大文,亦既工此,海入其塘,岳入其牖。无小无大,爱玩终日,因而遇之,字句我师。”[27]通过感悟来体认庄骚的共同美感,把文学之思与哲理之思打成一片,这种欣赏庄骚的方法,确实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陈子龙的《庄周论》说庄周也是怨愤而著书:“庄周者,其言恣怪迂侈,所非呵者,皆当世神圣贤人。以我观之,无甚诞僻,其所怨亦犹夫人之情而已。”“庄子乱世之民也,而能文章,故其言传耳。夫乱世之民,情懑怨毒,无所聊赖,其怨既深,则于当世,反若无所见者。”[28]152-153这一观点颇与宋人刘叔平、林希逸相近而表达得更加深切著明。陈氏的另一名文《谭子〈庄骚二学〉序》指出庄骚有截然相反的一面,庄子出世而屈原不忘情:“战国时,楚有庄子、屈子,皆贤人也,而迹其所为,绝相反。庄子游天地之表,却诸侯之聘,自托于不鸣之禽、不材之木,此无意当世者也。而屈子则自以宗臣受知遇,伤王之不明而国之削弱,悲伤郁陶,沈渊以没,斯甚不能忘情者也。”然而,庄骚又有相同、相通的一面,那就是:“夫庄子勤勤焉,欲返天下于骊连、赫胥之间,岂得为忘情之士?而屈子思谒虞帝而从彭咸,盖于当世之人不数数然也。予尝谓二子皆才高而善怨者,或至于死,或遁于无乎有之乡,随其所遇而成耳。故二子所著之书,用心恢奇,逞辞荒怪,其宕逸变幻,亦有相类。”[28]76-77这是说,庄子向往上古骊连氏、赫胥氏之世,屈原追慕虞舜、彭咸等人,他们都既有用世之心,又有超越现实之意;用心相同,故表达之虚荒幻诞、高逸变幻也自然相同。
陈氏生当乾坤板荡、舆图换稿之际,故于庄骚有自己独到的感悟与理解。此后明清易代,许多士人怀着孤臣孽子忧危之心,不肯屈仕新朝,也都从庄骚中找寻自己安身立命的精神天地。庄子之轻视富贵,不臣诸侯,屈原之不忘宗国,秉持清高,在他们看来真是殊途同归,完全可以合而为一。桐城人方以智抗清被捕,以大义凛然感动清将被释,此后易服为僧。曾作《药地炮庄》,又仿屈原《九歌》而作《九将赋》,康熙十年(1671年)竟死于惶恐滩头[29]。吾湘王夫之作诗哭之,其一曰:“长夜悠悠二十年,流萤死焰烛高天。春浮梦里迷归鹤,败叶云中哭杜鹃。一线不留夕照影,孤鸿应绕点苍烟。何人抱器归张楚,余有南华内七篇。”其二曰:“三年怀袖尺书深,文水东流隔楚浔。半岭斜阳双雪鬓,五湖烟水一霜林。远游留作他生赋,土室聊安后死心。恰恐相逢难下口,灵旗不杳寄空音。”[30]都是以庄骚况拟方氏。
方以智的桐城老乡钱澄之抗清失败后则闭门著书。钱氏作有《庄屈合诂》,认为庄骚皆经学之支流,故《庄》继《易》而《骚》继《诗》。他这样回答有关“庄屈不同道,庄子之言,往往放肆于规矩绳墨之外,而皆为屈子所法守者”的质疑:“庄子述仲尼之语曰:‘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夫庄子岂徒言其言者哉!一旦而有臣子之事,其以义命自处也审矣;屈子徘徊恋国,至死不能自疏,观其《远游》所称,类多道家者说。……而太史公称其蝉脱于浊秽之中,以浮游于尘垢之外,亦诚有见于屈子之死非犹夫区区激愤而捐躯者也。是故非天下至性之人不可以悟道,非见道之人亦不可以死节也。吾谓《易》因乎时,《诗》本乎性情。凡庄子屈子之所为一处其潜,一处其亢,皆时为之也。庄子之性情于君父之间,非不深至,特无所感发耳。诗也者,感之为也。若屈子则感之至极者矣。合诂之使学者知庄屈无二道,则益知吾《易》学、《诗》学无二义也。”[3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推测钱氏合屈、庄为一的意图说:“盖澄之丁明末造,发愤著书,以《离骚》寓其幽忧,而以《庄子》寓其解脱,不欲明言,托于翼经焉耳。”[32]但唐甄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庄、屈有可以互补的一面,屈原可以济庄子之放浪:“第若庄子之遗世绝物,以卿相为污我,于心安乎?是故当以屈子之志济之,则达而不至于荡。”而庄子则可以抵消屈原之愚忠:“为屈子计,当怀王入秦时,以死争之不得,则从王行,如蔺相如以颈血溅秦王事,若不济,得死所矣。不然,弃其室家,从渔父于沧浪,孰得而非之!乃呜咽悲泣,自捐其躯,吾嫌其近于妇人也。是故当以庄子之意济之,则忠而不至于愚。”[33]唐氏认为庄子的“遗世绝物”可以抵消屈原的愚忠,显然从庄子中找到了某种符合近代民主意识的东西。到晚清,庄骚中所蕴涵的桀敖不驯还在许多志士仁人身上有所体现。龚自珍“名理孕异梦,秀句镌春心。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古来不可兼,方寸我何任。所以志为道,澹宕生微吟。一箫与一笛,化作太古琴”[34]就集中表达了这种情况。
三、庄骚并举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庄骚浪漫、谲怪特色形成的原因,并使之得到比较符合儒家理性的解释
庄骚都有浪漫、谲怪、虚幻的特色,这一点,今人大都借用西方的浪漫主义、文艺心理学、神话学、符号学诸种理论加以解释,似乎已无探讨余地。然而在韩愈之前,人们用以解释的理论就是寓言和比兴。庄子所用者是寓言,楚辞所用者是比兴,两者有何关系,没有人加以深究。寓言也好,比兴也好,为什么要用那些虚荒诞幻之物,在秉持无征不信、不语怪力乱神的人们心中也是一大疑问。儒士兼史学家的班固对楚辞的“不经”提出质疑,王逸勉强牵附儒家经典加以回应,而儒家情结深厚的刘勰仍同意班氏之说,可见这个问题颇难圆满解决。问题难解决是一回事,文学创作中照写又是另一回事。理论上的不圆通并不妨碍创作实践的照常进行。特别是六朝以来各种志怪、神话小说大行其道,根本就把儒家的不语怪力乱神、无征不信的信条抛到了一边。当然,理论界还是很希望解决这一问题的。早期人们常用“禀气说”解释虚幻怪诞,认为一切都出于“自然”[35]。佛教盛行以后,人们又从中找到了一种叫“幻化”的理论,想借此一揽子解决各种虚荒诞幻、牛鬼蛇神之事何以产生的问题。例如明人李长庚在《〈太平广记〉钞序》中说:
始知吾之常见常闻者,皆桎梏也;所创见创闻者,亦刍狗也。平时所执以是者,眼中之屑也;所排以非者,空中之华也。疑之则形影尺凫也,印之则千江一月也,如是而吾之性灵始出。即学者载籍考信六经矣,《易》言牛掣天劓,载鬼张弧,近于怪也;《诗》言芍药舒脱,近于戏也;《春秋》之石言鹢退,蛇斗豕啼,近于诬也;《礼》言吾与尔三焉,近乎诞也。何莫非圣贤旁引曲说,以极人之情变,以断人之疑根?故《易》言穷理尽性者,以理非穷则不能尽也;《孟》言尽心知性也,以心非尽则不能知也;《老》言有欲以观其徼者,徼即其穷且尽焉之处也。人之见闻穷尽于徼,则根尘两脱,真性现前。信手拈花,随场说法,饮食门户,可以证道;墙壁矢溺,可为悟门;微言谑语,可以释纷;术解方伎,可以利用;嬉笑怒骂,可成文章。奇形幻影,咸海藏之浮沤;异迹灵踪,总化身之示现。善才童子五十三参,备历种种变相,差别智尽,方归根本。三教圣人,其设喻广譬,引度世人,作此方便津筏耳[36]。
李长庚不仅用佛教之幻化说解释文学创作中各种幻相产生的原因,还指出儒家经典中同样也存在着近于怪、戏、诬、诞的现象,向儒家经典和不语怪力乱神的理念提出了挑战。这样一来,问题已经不限于庄骚了。
针对连儒家经典都有怪、戏、诬、诞的问题,儒士不得不起而思考、应对。当然,儒士是不愿用佛教理论来回应这样的问题的,必须另辟蹊径才行。到清代,儒家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易教下》中具体地回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儒家经典中的象、兴、例、官 ,莫不源于《易》之“象”,与《易》“象”属同一类别。“象”的构设,无非是为了体现“道”而已:“《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万事万物,当其自静而动,形迹未彰而象见矣。故道不可见,人求道而恍若有见者,皆其象也。”也就是说,一切“象”皆是“道”之外化。“象”无所不在,表现形形色色、林林总总,归结起来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天地自然之象”,一种是“人心营构之象”。天地自然之象是实象,如《说卦传》讲的天为圜;人心营构之象是虚象,如《易经》讲的睽车之载鬼、翰音之登天。人心是虚灵之物,故“意之所至,无不可也”。但“人累于天地之间,不能不受阴阳之消息,心之营构,则情之变易为之也;情之变易,感于世之接构,而乘于阴阳倚伏为之也”,所以“人心营构之象,亦出于天地自然之象也”。也就是说,人本于天地自然,而且要同社会接触,所以不管怎么心虚用灵,人心都要受人这一自然体和社会现实的制约。这颇有点今天我们所说的浪漫主义乃植根于现实主义的味道。这样的解释,确实既符合儒家理性,也符合现代哲学、心理学之常理。
有了这么一个理论前提,儒经、庄骚、诸子中的种种虚象就可以一揽子解决了。章氏认为,《易》虽包六艺,但与《诗》之比兴尤为表里。先秦诸子百家,深于比兴,皆《诗》之流别:“然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庄》、《列》之寓言也,则触蛮可以立国,蕉鹿可以听讼;《离骚》之抒愤也,则帝阙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纵横驰说之士,飞箝捭阖之流,徙蛇引虎之营谋,桃梗土偶之问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议。然而指迷从道,固有其功;饰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营构之象,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范天下也。”读者应该看到了,章氏讲的“《庄》、《列》之寓言也,则触蛮可以立国,蕉鹿可以听讼;《离骚》之抒愤也,则帝阙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已回答了庄、骚中为什么多有虚象的问题。
作为儒者,章氏把一切文学均归于《易》教,把一切文学浪漫、奇谲现象均归于《易》象之变种,目的就是为了否定佛教之幻相说。他甚至想把佛教也纳入《易》教之内:“至于佛氏之学,来自西域,毋论彼非世官典守之遗,且亦生于中国,言语不通,没于中国,文字未达也。然其所言与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较诸子百家为尤盛。反覆审之,而知其本原出于《易》教也。”[37]可是他又认为,佛教起初虽符合圣人之教,但发展下去,就同圣人背道而驰了。由此他说,儒者对佛氏也不要那么不共戴天,只要佛氏能改弦更张,回到儒家人伦日用的轨道上来,也依旧可以符合圣人之道的。
如前所云,汉代至六朝,班固、刘勰等就对楚辞中不符合儒家理性精神的内容提出质疑,这种质疑甚至影响了对楚辞的评价。韩愈“庄骚”并提之后,这个问题实际上仍长期未能解决,儒门中认为“原之为书,其辞旨虽或流于跌宕怪神、怨怼激发而不可以为训”[38]者仍大有人在。《庄子》“空语无事实”的问题则更加突出。明人都穆曾指出:“六经如《诗》《书》《春》《秋》《礼》《记》,所载无非实事。自骚赋之作兴,托为渔父、卜者及无是公、乌有先生之类,而文词始多漫语,其源出于《庄子》。《庄子》一书,大抵皆寓言也。”[39]所以解决好庄骚与儒经矛盾的问题,牵涉到韩愈让庄骚附儒经骥尾是否能成立的大问题。章氏的解释,正可以释儒者之疑,虽然在我们看来章氏把屈原、庄子、诸子百家及佛教统统纳入《易》教明显存在着儒门偏见。
所以说,韩愈的“庄骚”并提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人们进一步思考庄骚浪漫、谲怪特色形成的原因,并使之得到比较符合儒家理性的解释。
四、庄骚并举,激发了后世学者对庄骚接受史的探讨,使庄骚在文学史上的传承线索渐趋明朗
前面已经说过,庄、骚的接受始于创作界,早在汉代就开始了。但在韩愈之前,却很少有人探索作家在具体创作中接受庄骚的情况。到宋以后,这种探讨便逐渐多了起来。例如谢枋得《文章轨范》卷7评苏轼《前赤壁赋》:
此赋学庄骚文法,无一句与庄骚相似,非超然之才,绝伦之识,不能为也。潇洒神奇,出尘绝俗,如乘云自卑御风而立乎九霄之上,俯视六合,何物茫茫,非唯不挂之齿牙,亦不足入其灵台丹府也。
前引林希逸《竹溪十一稿诗选·读黄(庭坚)诗》:
我生所敬涪江翁,知翁不独俄诗工。逍遥颇学漆园吏,下笔纵横法略同。自言锦机织锦手,与寄每有《离骚》风。内篇外篇手分别,冥搜所到真奇绝。颉颃韩柳近庄骚,笔意尤工是晚节。……
元人祝尧评李白《大鹏赋》,虽然肯定楚辞而贬低庄子,却并没有否定庄骚对李白的共同影响:
赋而比也。太白盖以鹏自比而以希有鸟比司马子微。赋家宏衍巨丽之体,自楚骚《远游》等作已然。司马、班、扬尤尚此。此显出庄子寓言本自宏阔,而太白又以豪气雄文发之,事与辞称,俊迈飘逸,去骚颇近,然但得骚人赋中一体尔。若论骚人所赋,固当以优柔婉曲者为有味,岂专为宏衍巨丽之体哉!后人以庄比骚,实以庄骚皆是寓言,同一比义。岂知骚中比兼风兴,岂庄所及。庄文是异端荒唐缪悠之说,骚文乃有先王盛时发乎情止乎礼义之遗风。学者果学庄乎,学骚乎?[40]
明清以后,论及前代文人创作中接受、融汇庄骚的更多。这里略举数例,以见人们对庄骚共同影响的关注:
陆子放翁诗万卷,后来老练更疏狂。须知深得庄骚意,莫与唐人较短长[41]。
楼敬思云:稼轩驱使庄骚经史,无一点斧凿痕,笔力甚峭[42]。
杜子美原本经史,诗体专是赋,故多切实之语。李太白枕藉《庄》、《骚》,长于比兴,故多惝恍之词[8]1087。
诗本贵洁,亦贵拉杂;能洁难,能拉杂更难。近代诗人,吾见有能洁者矣,未见有能拉杂者也。能洁而不能拉杂,不失为高手;不能洁而遽言拉杂,难乎为诗矣。夫所谓拉杂者,形体则然,其意义未尝不洁,若《庄子》、《离骚》皆是也,独诗也哉![8]1097
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本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其斯以为白之真原也已[43]。
太白诗以《庄》、《骚》为大源,而于嗣宗之渊放,景纯之俊上,明远之驱迈,玄晖之奇秀,亦各有所取,无遗美焉[44]57。
诗以出于《骚》者为正,以出于《庄》者为变。少陵纯乎《骚》,太白在《庄》、《骚》间,东坡则出于《庄》者十之八九[44]67。
曹子建、王仲宣之诗出于《骚》,阮步兵出于《庄》,陶渊明大要出于《论语》[44]54。
曲江之《感遇》出于《骚》,射洪之《感遇》出于《庄》,缠绵超旷,各有独至[44]57。
从上面的引文我们可以看出,时代越晚,人们对庄骚影响的追溯就越前,由苏轼、黄庭坚、陆游、辛弃疾而张九龄、陈子昂、李白、阮籍、曹植、王粲,等等,无不一一梳理。这种梳理对我们今天思考后世对庄骚的接受自然不无裨益。现当代各种文学史都或多或少论述过这一问题。近年来单篇论文也不少,如缪钺的《灵谿词说——论苏、辛词与〈庄〉、〈骚〉》(《四川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陆永品的《论〈庄〉〈骚〉并称的文化现象》(《河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刘项、王延双的《论早期天人观对〈庄〉〈骚〉浪漫特色的影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北方神话对〈庄〉〈骚〉浪漫特色的影响》(《北方论丛》1997年第6期),刘项的《齐文化对庄骚浪漫特色的影响》(《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吴淑玲的《论庄骚结构的趋同及其艺术价值》(《郑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蔡觉敏的《论神话思维对庄骚的影响》(《贵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论庄子、屈原人生境界的同异及对后代士人之影响》(《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8年第 4期),焦雪梅的《〈庄〉〈骚〉浪漫主义之比较》(《菏泽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吴思增的《陈子龙和明清之际“庄骚”合称》(《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等等,探讨的广度与深度都显然超过前贤,使庄骚共性的研究及其接受线索越来越清晰。如果从学术渊源的角度说,所有的这些研究其实都导源于韩愈。
[1]李生龙.论庄、骚的融通与影响[J].中国文学研究,2004(2):23-26;31.
[2]洪兴祖.楚辞补注[J].北京:中华书局,1983:49.
[3]李生龙.历史上屈原诠释之视角解读[J].中国文学研究,2009(3):46-51;56.
[4]董浩.全唐文:卷635[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6411.
[5]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10[M].廖德明,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75.
[6]刘绘.与王翰林槐野论文书[M]//黄宗羲.明文海:卷252.四库全书.
[7]蔡世远.哭伯父习孚先生文[M]//二希堂文集:卷10.四库全书.
[8]乔亿.剑溪说诗:卷上[M]//郭绍虞.清诗话续编.富寿荪,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9]王炎.见张南轩[M]//双溪类稿:卷19.四库全书.
[10]顾璘.读书图说[M]//息园存稿文:卷7.四库全书.
[11]曾巩.曾巩集[M].陈杏珍,晁继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526.
[12]韩维.王侍读挽词二首:其一[M]//傅璇琮,倪其心,孙钦善,等.全宋诗:第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262.
[13]苏辙.和张安道读杜集〔用其韵。〕[M]//苏辙集.陈宏天,高秀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54.
[14]陆游.雨霰作雪不成大风散云月色皎然[M]//剑南诗稿校注:卷49.钱仲联,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942.
[15]陆游.散怀[M]//剑南诗稿校注:卷57.钱仲联,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4296.
[16]陈造.次韵解禹玉[M]//全宋诗:第45册.四库全书:28076.
[17]程公许.赠修水黄君子行[M]//全宋诗:第57册.四库全书:35503.
[18]仇远.和蒋全愚韵[M]//全宋诗:第70册.四库全书本:44159.
[19]林希逸.南华真经口义[M].陈红映,点校.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140.
[20]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12[M].四库全书本.
[21]宋陈思.竹溪十一稿诗选[M]//两宋名贤小集:卷320.陈世隆,补.四库全书.
[22]魏天应.论学绳尺:卷7[M]//方澄孙.庄骚太史所录.四库全书.
[23]刘壎.诗文取新[M]//隐居通议:卷18.四库全书.
[24]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23[M]//元明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59:202.
[25]归有光.五岳山人前集序[M]//震川先生集:上册.周本淳,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7.
[26]陈继儒.狂夫之言:卷4[M]//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43.
[27]谭元春.遇庄序[M]//谭元春集:卷33.陈杏珍,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902-903.
[28]上海文献丛书编委会.陈子龙文集:卷3[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29]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有公司,1986.
[30]闻极丸翁凶问不禁狂哭痛定辄吟二章[M]//王船山诗文集·六十自定稿·七言近体.北京:中华书局,1962:215.
[31]钱澄之.《庄屈合诂》自序[M]//续修四库全书:子部16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002:604.
[32]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34[M].北京:中华书局,1987:1139.
[33]唐甄.《庄屈合诂》序[M]//续修四库全书:子部 16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002:603.
[34]龚自珍.自春徂秋偶有所触拉杂书之漫不诠次得十五首[M]//龚自珍全集:第 9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485-486.
[35]李生龙.“天人感应”与神话、志怪[M]//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长沙:岳麓书社,2009.
[36]李长庚:太平广记钞序[M]//冯梦龙.冯梦龙诗文初编.橘君,辑注.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59-60.
[37]章学诚.内篇一·易教下[M]//文史通义:卷1.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38]朱熹.楚辞集注[M].蒋立甫,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
[39]都穆.南濠诗话[M]//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91:17.
[40]祝尧.古赋辨体:卷7[M].四库全书.
[41]魏裔介.读陆放翁诗[M]//兼济堂文集:卷17.四库全书.
[42]张宗橚.词林纪事:卷11[M].复印本.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2:310.
[43]龚自珍.最录李白集[M]//龚自珍全集:第3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255.
[44]刘熙载.诗概[M]//艺概: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The significance of HAN Yu’s enumerating Zhuangzi and Chuci simultaneously
LI Shengl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The significance of HAN Yu’s enumerating Zhuangzi and Chuci simultaneously has four aspects.First,under the context of Confucianism,enumerating Zhuangzi and Chuci simultaneously,and putting it after the Confucian classics,has promoted the position of them.Second,It has inspired successors’thinking to the similarity of Zhuangzi and Chuci,and promoted deep research to the thoughts,connotations and art spirit of them.Third,it has promoted people to explore the reasons why zhuangzi and Chuci formed characteristic as romantic and fantastic to some extent,and get explan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fucian sense largely.Finally,it has stimulated later scholars’probing to the reception history of Zhuangzi and Chuci,and made the transmission clue of Zhuangzi and Chuci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coming gradually clear.
HAN Yu;Zhuangzi and Chuci;enumerate simultaneously
I206
A
1671-9476(2011)01-0021-08
2010-09-02
李生龙(1954-),男,湖南祁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