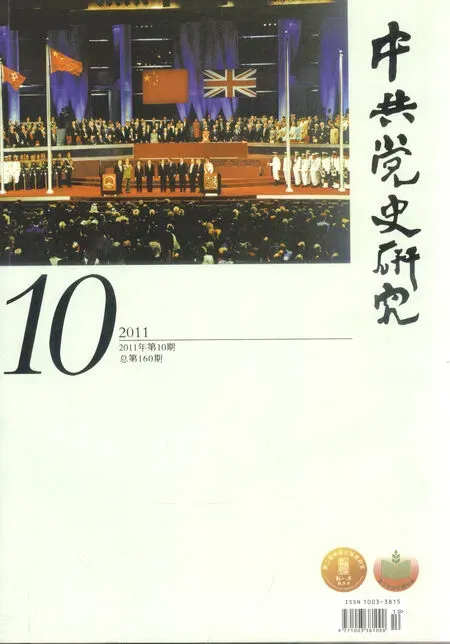美国对华核战略与一九六九年中苏边界冲突*
詹 欣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无论对中苏关系还是中美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关这段历史,近些年国内外学术界已有相当多的论著,它们主要集中在冲突的起源、进程以及对中苏、中美关系影响的讨论上①William Burr:Sino-American Relations,1969:Sino-Soviet Border Conflict and Step Towards Rapprochement,Cold War History,2001,Vol.1,No.3,pp.73—112;William Burr,ed.:The Sino-Soviet Border Conflict,1969:U.S.Reactions and Diplomatic Maneuvers,A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Goldstein,Lyle J.:Return to Zhenbao Island:Who Started Shooting and Why it Matters,China Quarterly,December 2001,Issue 168;苏联方面的著作,可见Viktor M.Gobarev: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1949—1969,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12/4(1999),pp.43—47;关于德国档案,可见 Christian Ostermann,ed.:East German Documents on the Border Conflict,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6—7(1995/96),186—193;中国方面的论著,有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徐焰:《外来核威胁迫使中国发展核武器》,《文史参考》2010年第8期;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与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杨奎松:《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对美缓和》,《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12期;何慧:《美国对1969年中苏冲突的反应》,《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陈东林:《核按钮一触即发:1964年和1969年美国、苏联对中国的核袭击计划》,《党史博览》2004年第3期;王成至:《美国决策层对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判断与对策》,《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张曙光:《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大多数学者认为,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对中美关系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问题是,如果中苏边界冲突仅仅维持在常规武器的对峙上,这种影响还会有这么大吗?当中国在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之前,美国决策层多次探讨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军事打击,苏联并不积极,为什么仅仅过了5年,当苏联转而试探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核打击时,美国决策层反而开始反对?美苏中都是有核国家,那么核因素在三者之间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是本文试图寻找的答案。
一、尼克松政府初期继续强调中国的核威胁
尽管尼克松上台伊始,便指示其国家安全顾问重新审查对华政策问题,①NSSM 14:U.S.China Policy,February 5,196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69—1972,Vol.XVII:China 1969—1972.p.8.但其步骤是谨慎的,在核战略方面更是沿袭了约翰逊政府的对华政策。1969年2月6日,尼克松要求国防部副部长戴维·帕卡德对饱受争议的“哨兵”反弹道导弹系统进行联席复查,中国核威胁论仍然是“哨兵”系统存废的主要争论之一。支持者认为,到70年代初估计中国将拥有约10枚洲际弹道导弹,如果没有“哨兵”系统的保护,美国在中国使用10枚洲际弹道导弹的第一次军事打击下将会导致高达700万人口的伤亡;而反对者则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在战略进攻力量方面对于中国将具备有效的威慑,推迟部署并不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②Paper Prepar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Undated.FRUS,1969—1972,Vol.XXXII:SALT 1969—1972.p.7.
与此同时,情报部门也对中国战略武器计划进行评估,为高层决策提供参考。这份文件是尼克松政府关于中国战略武器计划的第一份评估报告,所以在总则方面对中国战略武器计划进行了回顾。文件的基调仍然强调中国核威胁论,认为:(1)战略武器系统的开发在中国一直被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尽管在过去的十年里遇到了经济与政治危机,但是该计划仍然得以继续进行,中国已经进行了许多适当的研究与开发,并建立许多必备的生产设施来支持正在进行中的重要战略武器计划。(2)中国已具备了地区性核打击能力,其现在拥有几枚可由两架喷气式中型轰炸机运载的热核武器。(3)随着中国生产喷气式中型轰炸机并开发战略导弹及其相配的热核弹头,在未来几年这种有限的能力将得以适当的增长。中国可能将于1969年或1970年开始部署中程弹道导弹,到70年代中期将能达到80至100枚的水平。(4)关于洲际弹道导弹,如果中国最早在1972年末达到初始作战能力的话,其数量到1975年可能在10至25枚之间。(5)中国可能近期将使用经改造过的中程弹道导弹作为发射工具发射卫星。
不过与约翰逊政府时期的评估相比,该文件还用较多的笔墨分析了中国战略武器计划所面临的问题。他们认为:(1)未来中国战略武器计划的速度、规模和范围仍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中国在开发和制造现代武器系统上所花费的时间要比几年前预测的长。因为中国缺少在复杂的现代武器系统上取得快速进步所必需的广泛的技术和经济基础。这种局势还会由于国内政治局势骚乱、困惑和不确定而加剧,甚至一定程度地被延长。(2)由于中国领导人难以取得尖端武器计划的生产与部署和发展工农业关系二者之间的平衡,因此中国设计者可能认识到,他们不可能与超级大国的核打击能力相抗衡。这将导致中国放弃初期导弹系统的大规模部署,而希望从拥有相对较少的导弹和飞机上获得重要的威慑作用和政治影响。(3)由于中国核战略部队相对较弱,中国肯定会认识到对邻国和超级大国使用核武器必将冒中国遭受毁灭性打击的风险。整体而言这份文件在分析中国战略核武器计划的有限性同时,继续强调了中国核威胁论。③NIE 13-8-69:Communist China’s Strategic Weapons Program,February 27,1969.http://www.foia.gov/nic_china_collection.asp.
2月底戴维·帕卡德完成了报告,建议尼克松继续进行反弹道导弹计划,但需要略加修改。对此,基辛格表示赞同。尽管他认为部署的主要原因是“用我们愿意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来换取苏联愿意限制进攻性武器”,但他也承认完全否定一次偶然袭击的可能性或将有更多国家掌握核能力的前景,在他看来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中国只是第一个可能成为这样的国家;别的国家还会跟上来。如果没有任何防御,一次偶发的发射就可以造成巨大的损害,甚至一个核小国也能够讹诈美国。①参见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261—262页。3月5日,国防部对约翰逊时期的“哨兵”计划提出了一个改进的版本,即“卫兵”计划。其目标表面上是:(1)提供针对苏联和中国的地区防御;(2)为国家指挥机构提供针对苏联进攻的防御;(3)保护陆基进攻性武器“民兵”导弹,以确保遭受第一次打击后的报复能力。②Henry Kissinger to Richard Nixon,“Issues Concerning ABM Deployment”,5 March 1969,National Archives,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Project,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iles,Box 843,ABM Memoranda.但实际上美国两届政府在部署反弹道导弹的理由上仍然是一样的,“即看来取得某种保护以防较小的核国家的意外袭击或蓄意进攻是明智的,而不要企图建立一个防御苏联的庞大民防体系,因为这将会引起武器控制问题和预算问题”。3月14日尼克松批准了这项计划,并声明“中国对我国人民的威胁以及一次意外进攻的危险是不能忽视的。批准这一计划,就会使得在70年代发生中国的进攻时,或者来自其他任何方面的意外进攻时,把美国遭受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更为严重的是,尼克松进而暗示美国和苏联在遏制中国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苏联像我们一样,不愿意使他们的国家暴露在潜在的中国共产党的威胁之下。因此我认为,哪一国也不会赞同放弃这整个计划,特别是在中国人的威胁存在期间”。③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册,第216页。
为了进一步有效地防范中国的核威胁,7月14日,尼克松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就美国在亚洲的核战略问题进行跨部门研究(NSSM 69)。该指令要求在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研究:(1)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核能力。即列出在哪种可能的情况下美国将会对中国实施核打击,包括对中国可能的目标体系和美国打击这些目标所需的核力量进行研究,还涉及美国的战略力量配置、行动计划、所要求的指挥和控制系统、运作程序以及有关战略的定性问题等。(2)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术核能力。要求对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术核能力角色,包括可能的中国袭击和对盟国与非盟国以其他形式的袭击进行威慑和防御等情况进行审查。(3)核保护问题。这项研究主要分析美国面对中国的核威胁,对盟国和非盟国所要承担义务的政治情况。(4)核不扩散问题。这项研究要求对上述三个领域中所产生可能核扩散的效应和对扩大“核不扩散条约”执行面的潜在影响进行分析。④NSSM 69:U.S.Nuclear Policy in Asia,July 14,1969.FRUS,1969—1972,Vol.XVII.p.48.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在强调美国对中国核威胁关心的同时,也进一步关注中国的核计划与核不扩散二者之间的关系。
有学者披露,尼克松和基辛格曾考虑默许苏联对中国西北地区的核基地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彻底解除中国不负责任地动用核武器的担忧,其根据就是这份研究报告指令。甚至说基辛格的下属(未透露姓名)在冷战结束后承认当时美国政府考虑了所有方案,包括默许苏联或与其合作攻打中国核设施的方案。以此说明当时尼克松政府更加倾向于“联苏抑中”,而并非众所周知的“拉中抑苏”的基本路线。⑤转引自王成至:《美国决策层对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判断与对策》,《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确实,直到1969年上半年,尼克松政府与约翰逊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并无本质的区别,仍然在各种场合强调中国核威胁论。但仅从一份研究指令就推断出美苏联手或默许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打击未免过于草率。这项指令原计划要求在9月30日之前提交报告,但基础研究直到1970年7月才完成,而提交到高级评估小组进行讨论已经是1971年3月的事情了。⑥Memorandum for Record of the Senior Review Group Meeting,March 12,1971.FRUS,1969—1972,Vol.XVII.pp.269—271.至于为什么拖了这么久,除了官僚机构互相推诿以外,也一定与中苏边界冲突有关。
二、核阴影笼罩下的中苏边界冲突与美国的对策
(一)中苏边界冲突的爆发与美国的最初反应
1969年3月,苏联挑起中苏边界武装冲突。美国情报部门最初认为这场冲突是由中苏双方长期以来角逐对珍宝岛的控制权所致,并且判断是由中方引发了最初的冲突,但预测近期内不会发展为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①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Directorate of Intelligence,“Weekly Review,”21 March 1969,CIA Freedom of Information release to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也坦言,在当时“我们仍然主要关心越南问题,而不能对我们不了解其根源、而且其意义要经过好几个星期才能看清楚的事态发展做出反应……然而尼克松和我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更富侵略性的共产党国家,我们认为,更可能是北京挑起了战斗”②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册,第218页。。至于中国之所以进行“挑衅”,情报部门推测主要出于以下几个目的:(1)让苏联在国际共产党代表大会上难堪;(2)向苏联表明中国人无所畏惧;(3)吸引世界舆论并试探苏联的战略意图;(4)通过强化外部威胁来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分裂和权力结构的混乱。③U.S.State Department,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Intelligence Note,“Peking’s Tactics and Intentions Along the Sino-Soviet Border,”13 June 1969,National Archives,SN 67-69,Pol 32-1 Chicom-USSR.这一时期美国基本处于观望状态,并认定中国是冲突的挑起者。
但随着中苏边界冲突的加剧,美国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在地域方面,中苏边界冲突的扩大促使美国政府改变原来的“中国是挑衅者”这一判断。5月2日与6月10日在新疆中苏边界地区开始爆发武装冲突,中苏之间的边界冲突似有升级之势。基辛格说:“在新疆发生的敌对行动打翻了我心中对谁是可能的进攻者的天平”。当他看了一份详细的地图时,“发现新疆事件发生的地点离苏联的铁路终点只有几英里,而离中国的任何一个铁路终点却有几百英里。这使我认识到,中国军事领导人不会选择在这样不利的地点发动进攻。此后我对问题的看法就不同了”。④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册,第222页。但问题是,如果苏联是挑衅者并对中国进行全面入侵,显然,一个完全被削弱的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可是如何利用当前中苏分歧,却是一个战略上的问题。7月3日尼克松指示基辛格,就当前美国如何从战略上利用中苏分歧进行分析(NSSM-63)。指令要求从美中苏三角关系的角度探讨中苏分歧的广泛意义,特别是一旦中苏发生军事冲突美国可能的对策进行分析,此外也要研究当前在中苏持续紧张的情况下美国可能的对策。⑤NSSM 63:U.S.Policy on Current Sino-Soviet Differences.July 3,1969.FRUS,1969—1972,Vol.XVII.p.42.
但是,烟草MES的后续开发还需要结合新技术的应用,例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在提高了企业信息化水平后,还应该考虑生产管理的智能化,这也是未来的主要发展方向。
其次,中苏边界冲突的核因素加速了中美缓和。早在中苏边界冲突刚刚爆发时,便出现了苏联打算攻击中国核设施的流言。3月末、4月初柯西金的女婿等人访美时试探说苏联将要摧毁中国的核设施;7月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接到来自于苏联的信件,询问如果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意共的立场是什么;此后苏联和美国的报界也开始有零星的报道。⑥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William Rogers,“The Possibility of a Soviet Strike Against Chinese Nuclear Facilities,”10 September 1969,National Archives,SN 67-69,Def 12 Chicom.针对这一时期的流言,8月12日情报部门完成了关于中苏关系的国家情报评估,特别对苏联企图进攻中国核设施和导弹设施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报告在开篇对3月以来中苏边界冲突进行了简单的描述,认为当前中苏关系改善的可能性极小,而未来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对于中国的核威胁,苏联可能认为即使少量的中国导弹也会改变战略形势,随着力量的增长,中国在使用地面部队上会更少受到约束。当前苏联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外交和军事措施,但是最具有吸引力的可能是先发制人地发动常规空袭,以摧毁中国的核设施和导弹设施。不过报告也认为中苏双方都会比较谨慎,中国不可能对苏联采取主动进攻,苏联也不希望与中国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冲突。①NIE 11-13/69:The USSR and China,August 12,1969.FRUS,1969—1972,Vol.XVII.pp.42.8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加州圣克利门蒂召开会议讨论中国问题,但并未做出任何决定。不过在这次会议上尼克松的革命性理论却使内阁成员大吃一惊,他说苏联是更具有侵略性的一方,如果听任中国在一场中苏战争中被摧毁,那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基辛格后来对此做出评论:“一个美国总统宣称一个共产党大国、一个我们与之没有任何联系的长期以来的敌人的生存,对我们具有战略利益,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件大事”②President Nixon’s Notes on a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undated.FRUS,1969—1972,Vol.XVII.pp.67;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册,第228—229页。。
按照尼克松7月3日的指令,除了组建以副国务卿理查森为首,包括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各部门代表在内的特委会来完成这份报告以外,基辛格也请求兰德公司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亚伦·怀廷提供对美国如何从战略上利用中苏分歧这一问题的看法。8月16日怀廷连夜赶写了一份题为《中苏敌对及其对美国政策的启示》的报告。虽然怀廷已不再是官方人员,也无法看到最新的国家情报评估,但其观点却与其极为相似。他认为当前苏联的军事部署和政治行为表明苏联对中国的核设施和导弹设施进行军事打击的可能性在增加,而对美国国家利益最大的威胁可能是双方要使用核武器。为此,他建议美国政府应该:第一,阻止苏联进攻中国;第二,阻止在中苏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第三,尽最大可能确保中国将苏联视为唯一的敌人。但是由于中美之间当时处于敌对状态,美国实现这些目标手段有限,于是他提出四点建议:(1)美国总统向中苏两国领导人致函,表达美国的立场和对中苏关系紧张的关切;(2)停止在华间谍活动;(3)如果苏联攻击中共,那么美国应该把中国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4)解除对华贸易制裁。怀廷的建议很符合基辛格的胃口,特别是把中苏边界冲突的核问题与美国的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从战略角度分析中美苏三角关系,正是近来尼克松和基辛格所考虑的问题。③Allen S.Whiting to Henry Kissinger,16 August 1969,enclosing report,“Sino-Soviet Hostilit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Policy”,National Archives,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Project,Box 839,China.
(二)苏联对华核威胁的加剧与美国的担忧
自3月以来有关苏联打算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的流言传播已有一段时间,但均是来自于第三方,美国从未在正式外交场合直接从苏联得到确切的相关信息,直到8月18日,在苏联驻美使馆的午餐会上,苏联驻美使馆二秘鲍里斯·达维多夫突然询问美国国务院负责北越问题的特别助理威廉·斯蒂尔曼,如果苏联进攻中国并摧毁中国的核设施,美国将做如何反应?如果中国在其核设施遭到苏联打击下寻求美国的帮助,那么美国的态度是什么?是否会利用此坐收渔翁之利?④U.S.State Department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US Reaction to Soviet Destruction of CPR Nuclear Capability”,18 August 1969,National Archives,SN 67-69,Def 12 Chicom.关于苏联试图军事打击中国核设施,他还提出了5项理由:(1)中国的核能力在不远的将来会对苏联构成威胁,因而必须在数十年内消除这种能力;(2)对中国的打击将削弱毛泽东的统治,使中国持不同政见的高级官员和党的干部得以升迁;(3)中国因为担心苏联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而不大可能进行反击,此外毛的地位被削弱会阻止他卷入与苏联的战争;(4)苏联的行为不会影响美国,事实上消除了中国的威胁反而使其从中受益;(5)如果苏联不采取行动,中国将会悄悄地发展核力量而不引起外界的警觉。这是苏联官员首次试探美国官员对苏联军事打击中国核设施的态度。由于达维多夫已在美工作多年,是个美国通,且同美国务院及其相关机构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在以往与美国官员交往时,他经常提出一些想法和假设来试探美国的反应。因此在美国看来,很难说他提出军事打击中国核设施是个人行为,但是否完全依照指令行事也不能确定。⑤State Department cable 141208 to U.S.Consulate Hong Kong etc.,21 August 1969,National Archives,SN 67-69,Pol Chicom-USSR.
关于苏联是否真正计划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学界争论较大。当前尚无苏联官方档案得以证实,我们只能从美国档案进行间接的推断,在苏联官方存在着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的讨论,至于这种讨论是否真正升级为军事计划,未来还需要苏联档案的佐证。不过大多数学者都引用1978年叛逃到美国的联合国副秘书长阿·舍甫琴柯的回忆录,谈到当时在政治局多次研究了这一问题。①参见杨奎松:《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对美缓和》,《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12期;陈东林:《核按钮一触即发:1964年和1969年美国、苏联对中国的核袭击计划》,《党史博览》2004年第3期。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积极主张无限制地使用核武器“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而另外一种则主张用有限数量的核武器进行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攻击”,摧毁其核设施。其实这两种主张并无本质区别,都赞成对华使用核武器,不同处仅仅是使用核武器的数量而已。不过赞成这两种手段的人并不多,即使后一种手段,国防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也表示反对,他认为太过冒险,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丰富的游击战知识和经验,一两颗原子弹难以奏效,反而会使苏联陷入一场如美国在越南那样的没完没了的战争。因此在轰炸中国问题上,苏联政治局分歧严重并陷入了僵局,有好几个月不能就此做出决定。由于格列奇科的主张是以美国不会积极地反对苏联的惩罚性行动而会把它“吞下去”为前提的,于是苏联外交部、克格勃和军事情报局开始探听华盛顿对一场核打击可能做出的反应。苏联驻华盛顿使馆奉命非正式地向美国中级官员进行了了解。②参见〔苏〕阿·舍甫琴柯著、王观声等译:《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194—195页。如果舍甫琴柯的回忆录可靠的话,那么这就是8月18日达维多夫向斯蒂尔曼进行试探,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依照指令的最有利证明。但是一些俄罗斯学者对舍甫琴柯的回忆录有所怀疑,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研究员乌索夫认为,苏联在当时并没有真正的核打击中国的计划,只是想逼迫中国回到谈判桌前,核打击的消息是苏联有意散布出去的。③参见陈东林:《核按钮一触即发:1964年和1969年美国、苏联对中国的核袭击计划》,《党史博览》2004年第3期。而远东研究所原所长基塔连科甚至认为根本不存在此事,是舍甫琴柯根据中央情报局需求编造的④参见徐焰:《外来核威胁迫使中国发展核武器》,《文史参考》2010年第8期。。中国的一些学者也支持俄罗斯学者的看法,认为“中苏两国领导人当时对于战争可能性的判断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双方都是为了应付对方的进攻而备战,迄今还没有任何档案材料证明,双方任何一方制订过进攻对方的计划”⑤李凤林:《亲历中苏(俄)边界谈判》,《百年潮》2008年第7期。。还有中国学者认为,“苏联自试验成功核弹和洲际导弹后,遇到国际危机时便经常炫耀其威力”,“1969年6月以来,美国媒体和官员讲话中一再传出苏联可能对华实施核打击,甚至说苏方官员对美做过试探。此时正值尼克松刚担任总统,决心从越南乃至亚太地区采取军事收缩,并考虑实施联华抗苏的战略,在此背景下放出这类消息,自然含有恫吓中国以促其对美国接近的目的”。⑥徐焰:《外来核威胁迫使中国发展核武器》,《文史参考》2010年第8期。
无论是否真正存在苏联军事打击中国核设施的计划,中苏关系紧张加剧却是不争的事实。8月25日,基辛格在圣克利门蒂召开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即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计划和危机处理小组委员会的会议,要求他们制订一个在中苏爆发战争的情况下美国政府的应急计划⑦参见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册,第229页。。8月2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威廉·海兰德向基辛格提交了一份文件,对美国立场进行分析。他提出当前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不偏不倚的政策,另一种是偏向中国,他认为这两种选择均不可取。如果美国对苏联打击中国核设施保持中立,并继续与苏联进行一系列的谈判,如有关中东问题的双边和四国谈判、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谈判(SALT)、海床条约谈判等,那么势必会被中国认为是美国对苏联军事行动的默许,这与尼克松政府试图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愿望背道而驰;而偏向中国,则会导致苏联极大的敌意,使苏美关系长期受到伤害。①Memorandum From William Hyland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August 28,1969.FRUS,1969—1972,Vol.XVII.pp.71—74.其实这里面还暗藏一个涉及军控的观点,即超级大国在实施预防性核打击方面的合作先例将使得任何形式的国际核军控体制难以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②参见张曙光:《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第264页。。
专家们的分析进一步加深了基辛格的担忧。9月4日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继续在圣克利门蒂召开会议,讨论美国政府的应急计划。在这次会议上,基辛格明确指出如果听任苏联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势必造成这样一种惹人厌烦的情形,即确立了一个大国可以使用核武器解决争端的原则。如果这个原则被确立,那么对美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计量的。因此基辛格认为当前对于美国人来讲,仅仅研究核武器对健康和安全因素的影响是根本不够的,还必须考虑到美国在欧洲核政策等因素。那么美国政府当务之急是应向苏联人清楚地表明美国的担忧,并劝阻他们不要贸然行事。④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of the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 Meeting,September 4,1969.FRUS,1969—1972,Vol.XVII.pp.76—77.但并非每一个人都同意基辛格的观点。国务卿罗杰斯并没有把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可能性看得那么严重,他认为近期苏联的各种试探,是一种好奇而不是信号。显然苏联受到中国问题的困扰并正在进行艰难的抉择,尽管不能排除苏联进攻的可能性,但是他不相信这种状况会发生。因为如果苏联一旦进攻中国,它将不得不冒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危险。罗杰斯认为中苏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不超过50%。⑤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William Rogers,“The Possibility of a Soviet Strike Against Chinese Nuclear Facilities,”10 September 1969,National Archives,SN 67-69,Def 12 Chicom.
虽然罗杰斯向尼克松阐述了国务院的观点,但显然并没有得到认同。基辛格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苏联人(达维多夫)不会如此随便地提出那样的问题。9月1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和约翰·霍尔德里奇在递交给基辛格的备忘录中,进一步支持了基辛格的观点。认为如果美国不对苏联图谋进攻中国核设施的行为做出明确的反应,将会被认为是美国默许了苏联的进攻计划。为避免给人这种印象,应该制定一个统一的原则,即美国反对苏联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⑥Memorandum from John Holdridge and Helmut Sonnenfeldt,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to Henry Kissinger,“The US Role in Soviet Maneuvering Against Peking,”12 September 1969,National Archives,Nixon Presidential Materials Project,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Files,Box 710,USSR Vol.V 10/69.关于基辛格不赞成罗杰斯的分析,见该文件空白处基辛格手书的评语。
在基辛格眼里,苏联通过各种渠道试探美国的反应,根本不是好奇,而是一种明确的信号,虽然不能说这就意味着苏联要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但它加深了美国政府对这一问题的担忧,特别是在使用核武器方面。美国正在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以摆脱在越南的困境,而默许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势必给缓和中美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但此时中美之间并无正常官方沟通渠道,除了在媒体上明确自己的态度以外,似乎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就在基辛格一筹莫展之时,中苏关系出现了改善的迹象。
三、中苏边界冲突的缓和与美国把中国纳入核军控体制的战略启动
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率队参加胡志明葬礼回国途中,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针对近来关于苏联试图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核打击的传言,周恩来说,“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最清楚。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①转引自杨奎松:《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对美缓和》,《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12期。。最后双方一致同意,首先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协议,并进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②参见《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20—321页。。9月18日,周恩来致信柯西金,建议双方承担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武装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③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462—464页。。9月26日,柯西金复函周恩来,苏方已采取了实际措施使边境局势正常化,并任命以库兹涅佐夫为首的代表团准备与中方进行谈判④参见《周恩来年谱》,第323页。。显然中苏双方已从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中退却了下来。
关于周恩来与柯西金的会谈,对于美国人来说非常突然,尼克松是从报纸中才得知这个消息的,并召见基辛格询问他的看法。因为无法掌握更多的信息,基辛格只能从会见的联合声明进行分析。他认为声明中并没有使用过去描述这种会谈的标准形容词“兄弟般的”,表明双方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至于尼克松询问双方的会谈是否表明中苏之间的缓和,基辛格并不同意,他认为这是双方严阵以待,以准备下一回合的斗争。9月16日《伦敦新闻晚报》刊登了一名与苏联官方有着密切联系的记者的文章,似乎进一步验证了基辛格的观点,该记者在文章中谈到了苏联对设在新疆罗布泊的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空中袭击的可能性,并指出“过去一年的事态发展证明了苏联恪守这样一个理论,即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利益,有权干涉彼此的事务”⑤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册,第231—232页。。为了应对中苏之间可能爆发的战争,9月17日在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上,小组成员对涉及美国国家利益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例如如何增强美国侦察飞机对中苏边界的侦察?如果苏联对中国沿海和香港港口进行封锁,美国将如何应对?一旦中苏爆发战争,美国在北越问题上的战略对策是什么?等等。⑥Minutes of the 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 Meeting,September 17,1969,FRUS,1969—1972,Vol.XVII.pp.82—85.
虽说中苏之间的争吵自9月11日以来开始降温,但在基辛格看来这也许是大举入侵的前奏。9月29日他在给尼克松的备忘录中,回顾了近一段时间苏联的活动,并指出他非常关心美国对这些试探的反应。他认为“苏联对他们的对华政策可能还不确定,而我们的反应可能影响他们的打算……苏联可能利用我们在中国和世界上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我们正在秘密协商,而且很可能对他们的军事行动处之泰然”。因此他认为美国应该清楚地表明没有玩弄这些策略⑦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Kissinger)to President Nixon,September 29,1969.FRUS,1969—1972,Vol.XVII.pp.101—103.。然而在尼克松还没有来得及就这些建议采取具体行动的时候,10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准备与苏联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10月20日中苏两国边界谈判在北京复会,中苏敌对态势得以进一步缓和。不过对于基辛格来说,他仍持怀疑态度,认为程序性的协议改变不了渊源深远的紧张关系。
11月10日,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最终完成了关于中苏发生重大武装冲突美国对策的报告。报告共提出了14点应急措施,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关于美国如何阻止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报告建议美国“应该公开强调其公正、不卷入的立场,敦促中苏双方不要使用核武器,通过谈判恢复和平,并采取步骤避免任何挑衅行动。如果敌对行动由苏联挑起,那么美国应该表达强烈的关注;如果使用核武器,那么美国应该强烈谴责这种行为。这些观点应该私下地告之苏联人与中国人。如果中苏之间发生常规武装冲突,美国不会显著地改变对苏联的双边谈判立场。但是如果苏联使用核武器,那么美国至少将延期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这份报告制定于中苏战争一触即发之时,但完成时中苏之间已开始进行外交谈判和后撤边界军事人员。与同一时期关于美国从战略上利用中苏分歧进行分析的NSSM-63报告相比,该报告主要针对的是在中苏之间爆发核战争的情况下美国的对策,因此具有应急的特点。①Washington Special Actions Group Report,November 10,1969.FRUS,1969—1972,Vol.XVII.pp.118—121.
虽然由于中苏边界局势的相对缓和,这些措施已失去了实施的意义,但是此次危机还是使得美国决策者着实紧张了一阵。事实上除了反对苏联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以外,尼克松政府也害怕苏联此番核讹诈会逼迫中国反应过度,促使其加入核军备竞赛,那样美国将面临更复杂的环境,而此时美国情报部门完成的一份对中国战略武器计划的评估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该报告在论调上与2月27日的国家情报评估并没有什么不同,仍然在强调中国威胁论的同时指出所面临的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是在分析中国在发展战略武器方面所遇到的诸多技术、资源和国内等因素以外,特别详细分析了苏联对中国核设施进行核威胁给中国战略武器计划带来的影响。报告认为“苏联军队的大规模集结和近来边界尖锐的冲突,已经增大了北京对苏联可能对中国采取一些重大军事行动的担心”。对于苏联的威胁,报告认为中国可能选择有三:一是中国的恐惧可能刺激他们采取紧急行动以尽快部署;二是推迟部署,至少是推迟那些对苏联构成明显威胁的武器,否则会增加苏联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三是改善其地面部队的机动性和火力,在尽可能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在常规武器水平上与苏联发生冲突。报告并没有对中国将做哪种选择做出明确的判断,但认为中苏对抗将可能继续成为影响中国战略武器计划的重要因素。②NIE 13-8/1-69:Communist China’s Strategic Weapons Program,October 30,1969.FRUS,1969—1972,Vol.XVII.pp.114—117.
此后,随着中苏边界冲突的缓和,美国对华核战略逐渐开始考虑把中国纳入核军控机制上来。
总之,尼克松上台伊始,虽说有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意愿,但在具体行动操作上极其谨慎,其对华核战略与前任约翰逊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仍然在强调中国核威胁的情况下继续对其进行遏制,这一时期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方法似乎并不多。中苏边界冲突确实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一个机会,然而最初美国并没有意识到,美国还理所当然地把中国作为冲突的挑衅者,并不想更多地卷入中苏之间的冲突。不过随着中苏矛盾的激化,特别是有关苏联打算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流言逐渐增多,甚至在官方渠道苏联外交官员开始对美国进行试探,这时美国政府才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美苏中三角关系初露端倪。如果中苏边界冲突仅仅维持在常规武器的对峙上,尼克松政府不会如此严重关注,毕竟中苏关系恶化已有十年,中苏边界纠纷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但是美苏中都是有核国家,核因素的存在使得中苏边界冲突变得与以往不一样了。如果听任苏联对中国进行核打击,那么完全被削弱的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时会被中国视为美苏勾结,对中美关系的改善带来负面影响。如果苏联仅仅是以试探来逼迫中国重回谈判桌前,那么这种核讹诈也可能会使得中国加入到核军备竞赛,为正在准备与苏联进行裁减军备谈判的美国带来极其复杂的局面。因此中苏边界冲突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一个机遇,但是核因素却是加速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