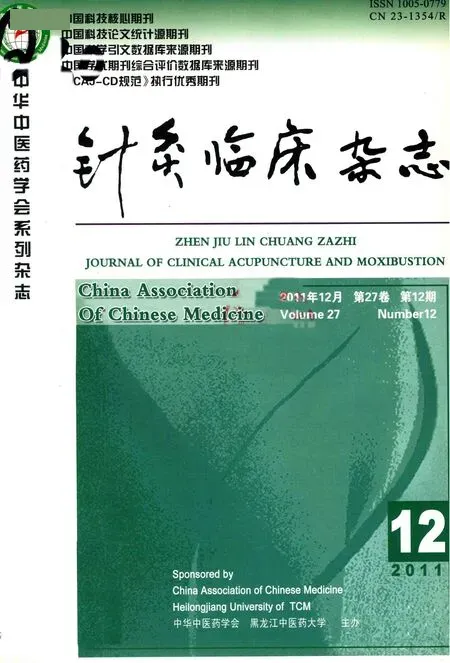《针灸问对》灸法特点浅析*
齐丽珍,马晓芃
(上海市针灸经络研究所,上海200030)
《针灸问对》[1]成书于嘉靖庚寅 (1530年),是汪机针灸学术思想的代表作。全书共分3卷,上、中卷论述了针灸基本理论和针法,下卷涉及灸法和经络腧穴。全书用问对的形式阐明了针灸的学术观点,有独到的见解,是一部难得的针灸专著,几百年来一直为后世医家所推崇。兹就汪机的灸法特色与学术见解探讨如下。
1 注重辨证察形
汪机非常重视辨证察形,认为它是针灸治疗的依据,提出“切脉观色,医之大要”。书中有“奈何世之专针科者,既不识脉,又不察形,但问何病,便针何穴,以致误针成痼疾者有矣。间有获效,亦偶中耳,因而夸其针之神妙,宁不为识者笑耶?”又曰:“……察脉盛衰,以知病在何经,乃可随病以施针刺也。苟不诊视,则经脉之虚实,补泻之多寡,病症之死生,懵然皆无所知矣。于此而妄施针灸,宁免粗工之诮哉!故集见于此,俾后之针士,必先以诊视为务也。”可见十分强调辨证的重要性。辨证是中医学的精髓所在,辨证即是认证识证的过程,它运用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所得,全面了解患者的具体症候,再通过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辨证分析,得出病机之所在,抓住疾病的本质。证是对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病理反映的概括,包括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反映这一阶段病理变化的本质。然后根据辨证的结果,确立施治的原则和方法,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中医学的辨证论治不是以消除原始致病因素及逆转病理变化为特长,而是运用针灸、药物等治疗手段,从整体上予以调节,消除病理产物的复合刺激,纠正功能失调,调动机体抗病能力和调节平衡能力,从而起到综合的作用。此外,诊法对针灸补泻的选择具有指导意义。如书中记载:“脉实而疾,则深刺以泻;脉虚而徐,则浅刺以补。邪气脉来紧而疾;谷气脉来徐而和。学者于此而察识之,则临病施针,庶免妄治之失矣。”由于病起的部位不同,治法亦当因之而异。“夫病变无穷,灸刺之法亦无穷,或在上,下取之;或在下,上取之;或正取之;或直取之。审经与络,分血与气,病随经所在,穴随经而取,庶得随机应变之理,岂可执以某穴主某病哉!……苟不知通变,徒执孔穴,所谓按图索骥,安能尽其法哉?”汪机认为针灸时应辨别病在气分还是血分,根据气分病、血分病的不同采用不同的取穴方法。病在气分,可以远道取穴、交叉取穴,因为针灸可以调气、行气,使气至病所。病在血分,宜在痛处或病变所在部位取穴治疗,以便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强调针灸要根据辨证,随机应变。汪机还提出,针灸当明经络,知脏腑气血之多少,注意经病、络病的不同,分清病在气或在血。“病随经所在,穴随经而取”,方得随机应变之理,不可执中无权,拘于某穴主某病之说。告诫要注意四时气候对人体的影响,凡病要辨别邪正内外虚实,才可施针补泻,庶不致误。针灸要深浅适宜,远近得当,他指出:“工之用针,当知气之邪正,病之死生也。初则浅之,以候皮肤之气,次则深之,以候肌肉之气,又次则深之,以候筋骨之气。若邪虽内舍,而神犹附属者,则渊澄而可见,切而按之,则劲急而可辨,用针之际,岂可不谨候乎”。临证时须根据辨证辨别阴阳虚实,实者泻之,虚者补之,陷下或寒证须灸之。由此看出汪机这种因证制宜,灵活施治的学术观点对后世针灸临床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针灸临床辨证论治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从整体而言,针灸临床辨证论治的思路是在中医学理论整体指导下进行的。尤其应强调在辨证论治中要重点突出针灸施治方法的自我特点,在经络理论的指导下,注重辨证选经、辨证选穴和辨证选法(针灸方法和针灸手法)。
2 针灸宜忌
对于灸法的适应证,书中记载:“大抵不可刺者,宜灸之。一则沉寒痼冷;二则无脉,知阳绝也;三则腹皮急而阳陷也”。即灸法的主要作用是温经散寒、舒筋活络、温阳补虚、回阳固脱、补中益气、升阳举陷,对于风寒湿痹、素体阳虚易感冒、阳气下陷内脏下垂或阳气欲绝诸虚百损等症候,均可用灸法治疗。汪机还根据《素问》和《难经》典籍所云,认为“阳气陷下者、脉沉迟也、脉证俱见寒……并宜灸之”,而“设脉浮者,阳气散于肌表者,皆不宜灸”。在灸法具体运用上,书中也有多处阐述,如对于头目之疾宜少灸,“纵使应灸,亦不过三壮、五壮,以泻热气而已”;痈疽用灸,头部宜小而少,“若身上痛则灸至不痛,不痛须灸至痛”;咳嗽不宜多灸,“纵灸肺俞、风门,不过三壮、五壮,泻其热气而已,固不宜多灸,三伏之中更不宜灸也”。这对临床灸法的应用具有指导意义。然也不必全盘接受,现今三伏灸在临床上已广泛运用于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并已取得了较显著的疗效。陈铭等[2]对107例支气管哮喘患者,采用三伏灸(传统三伏日)和秋季灸(秋分前10天、秋分、秋分后10天)进行治疗,对比治疗后IgE、肺功能的变化。结果表明,夏季组疗效明显好于秋季组,提示三伏灸治疗支气管哮喘的疗效与季节有关。
3 灸量及补泻
汪机指出:“病变无穷,灸刺之法亦无穷。”医者临证时应根据疾病的病因病机、传变规律,随机应变,灵活选用穴位,确定灸量及补泻方法。灸量即灸法的刺激强度,主要体现在艾炷的大小、壮数的多少、艾灸时间的长短等方面,至于某穴宜灸几壮,汪机认为:“惟当视其穴俞、肉之厚薄、病之轻重,而为灸之多少大小则可耳,不必守其成规”。如头为诸阳所聚,艾炷宜小而少;若身上痛则灸至不痛,不痛须灸至痛。灸量与病种和患者具体情况密切相关,在临床中注意针对不同患者制定出灸法的量学方案可明显提高疗效。书中对灸法的补泻也引经作了概括,“以火补者,无吹其火,须自灭也;以火泻者,疾吹其火,传其艾,须其火灭也”。并对灸法治疗虚证、实证、寒证、热证的治疗机理作了总结,“虚者灸之,使火气以助元气;实者灸之,使实邪随火气而发散也;寒者灸之,使其气复温也;热者灸之,引郁热之气外发,火就燥之义也”。此外,对灸之不发的原因作了分析,“大抵血气空虚不能作脓,失其所养故也”。后世医家结合自己的经验,一直援引这一补泻方法来治疗各种疾病。当然,灸法的补泻作用还与穴位功能、临床证候、灸疗刺激量的大小(包括灸治的方法、艾炷的大小、壮数的多少、距离的远近、灸疗时间的长短)、病变的部位及患者的体质等密切相关[3]。灸法既能补虚,又能泻实,临床运用灸法,应遵循辨证施灸的原则,灵活运用,以便获得最佳的治疗效果。
4 反对无病而灸
汪机对“若要安,膏盲、三里不要干”之世俗通论,提出了非议。认为“人之有病,如国之有盗,须用兵诛,其兵出于不得已也。针灸治病,亦不得已而用之”,“夫一穴受灸,则一处肌肉为之坚硬,果如船之有钉,血气到此则涩滞不能行矣”。并举实例加以说明,“昔有病跛者,邪在足少阳分,自踝以上,循经灸者数穴。一医为针临泣,将欲接气过其病所,才至灸瘢,止而不行,始知灸火之坏人经络也”。认为“邪客经络,为其所苦,灸之不得已也。无病而灸,何益于事?”汪机对于灸法的防病保健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其所云也只是针对瘢痕灸而言。大量的临床实践证明,灸法具有温经散寒、通络止痛、扶正祛邪、祛风解表、消瘀散结、补益中气、升阳固脱、回阳救逆等作用。现代临床和实验研究也表明,灸法对免疫低下者巨噬细胞吞噬功能有显著增强作用,能提高白细胞减少者白细胞数,促进单核-巨噬细胞的吞噬作用[4~5];灸法对高脂血症具有调节和治疗作用[6],调整老年人的脂质代谢,对异常全血黏度有调节、降低作用,可防治由此诱发的心脑血管病[7~9];灸法能激活脏腑功能,调节代谢,明显改善机体的失衡状态,增强机体抗病能力;灸法对应激状态下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有良好的调整作用[10],能调节神经内分泌功能,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对免疫功能具有整体性与双向性的调节功能[11~13]。因此,经常用灸法灸治,达到了早期预防和治疗的目的,提高人们的生活及生存质量,取得增强体质、祛病延年之效果,减轻疾病给家庭和社会带来的沉重负担。灸法不仅广泛应用于疾病的治疗,而且对防病保健具有重要的意义。
[1]明·汪机.针灸问对[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2]陈铭,蔡宗敏,卢希玲.夏秋季节治疗哮喘的疗效比较观察[J].福建中医学院学报,1999,9(2):20 -22
[3]刘冠军.中医灸疗集要[M].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446
[4]朱文莲,刘仁权.艾灸大椎穴对免疫低下小鼠巨噬细胞吞噬功能的影响[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5,28(1):89 -90
[5]蔡晓刚.针灸试治白细胞减少症[J].家庭中医药,2008,15(3):32-33
[6]万文俊,张唐法,张红星,等.针灸调脂作用的临床研究[J].湖北中医学院学报,2006,8(4):59 -60
[7]邓柏颖,罗敏然.化脓灸对临床血脂影响的初步观察[J].山西中医,2002,18(4):38 -39
[8]吴中朝,王玲玲.艾灸降血脂作用研究[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12(5):41 -42
[9]粟胜勇,邓柏颖,李扬帆,等.针灸对中风后偏瘫肩痛及其全血黏度的近期影响[J].上海针灸杂志,2004,23(12):10 -12
[10]徐朝霞,张宏.针灸抗应激性损伤作用的神经内分泌机制[J].上海针灸杂志,2007,26(1):45 -47
[11]吴美倩,高镇五.灸法调节免疫功能概况[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91,15(6):51 -53
[12]施征,吴焕淦.不同针灸疗法对大鼠实验性溃疡性结肠炎免疫功能的调整作用[J].针灸临床杂志,1996,12(12):23 -25
[13]于颖梅,裴建,吴焕淦,等.针灸调节免疫抑制的研究进展[J].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03,15(3):37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