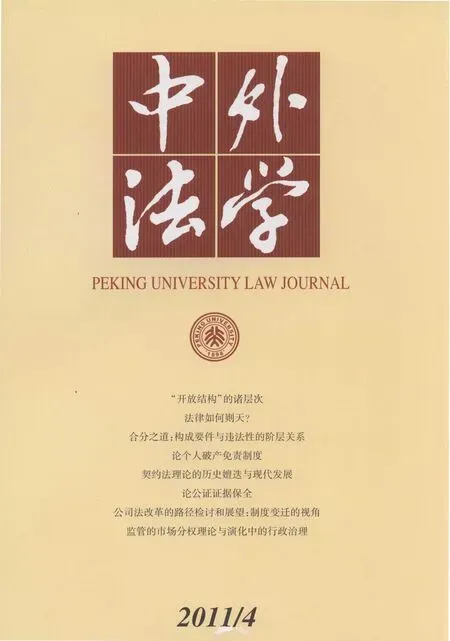公司法变迁中的商人角色
曾宏伟
“还存在一种危险,这就是把法律总是作为社会经济变化的一种结果,而不是这种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在这种意义上的原因。”
——伯尔曼〔1〕(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出版,页409。
我国公司法自1993年颁布至今,对它的争议和诟病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尽管经历了2005年的重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接连对其适用作出了数个司法解释,各项制度在不断完善之中,然而学术界要求对其进行结构性改革、从根本上变换立法思路等呼声依然此起彼伏。特别是公司法一些强制性规范被规避的现象大量发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公司法被“架空”的不争事实(虽然难有精确的数量统计),加之理论解释的主流方法受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约,从而引发了大家对公司法改革路径的思考,比如:强制性变迁还是诱致性变迁?移植抑或内生?如果进一步聚合焦点,则问题的核心是法律应当适应投资者,还是投资者应当遵守法律?进而,这一问题也和下述理论相关:公司的属性为何?公司法的属性又为何?如何正确认知和对待商人〔2〕因本文主要涉及公司法,而非一般的商事制度,因此文中的“商人”限指公司投资者。在公司法变迁中的角色?回答应然的问题,必须从实然的状态出发,如果离开基本的现实,则逻辑的演绎可能发生方向性的错误。对于商人在公司法变迁中的角色的回答,不仅要探寻其历史演变的逻辑,而且必须回到公司法如何定位、公司法立法博弈的格局如何等等原始的起点上来,在其中探寻商人角色演化的必然性;必须回到我国公司法创制和改革的路径约束上来,在其中寻找正确的方向。
一、商人角色演化的历史轨迹
回顾西方公司法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发现,作为传统商法的一部分,它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商人主导到国家主导的不断转变的过程。从欧洲中世纪到自由资本主义再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商人的经济、社会、政治力量不断壮大,地位不断提高,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通过民主立法程序参与到公司法立法中来,商人在公司法发展中的角色呈现出逐渐“弱化”的特点。当然,这种“弱化”也许只是表面的现象,公司法变迁中的商人角色也许由于某种原因发生了转移或者隐藏,而不是真正的弱化。
从中世纪到资产阶级革命前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是公司和公司法萌芽和发展的初期,商人无疑一直是最主要的推动者。伯尔曼曾经说过:“商法最初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虽不是全部——是由商人自身完成。”〔3〕伯尔曼,见前注〔1〕,页141。甚至可以说,公司和公司法早期的发展是商人与强权势力斗争和妥协的结果。比如由于中世纪的欧洲大陆仍然处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4〕商法起源于中世纪的商人法,欧洲古代法中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独立的商法或与之相类似的完整制度。(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页73。为了联合起来发展贸易和保护商人自身利益,商人们建立了自己的行会组织,比如在意大利最早出现的商人行会组织——商人基尔特。商人行业组织逐渐开始制定、编纂规约或习惯规则,这些行业规则、规约、商人惯例几百年间被商人行会因袭沿用,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商人习惯法(law merchant)。中世纪的商人阶层从封建主和教会那里争取到了对商人间贸易纠纷和争议进行处理的独立管辖权,普遍建立了包括市场法院、集市法院、商人行会法院和城市法院在内的各种商事法院,并逐渐形成了商事判例汇编,后来成为中世纪商人法的重要渊源之一,其中包括一些公司法规范。〔5〕比如根据伯尔曼先生的归纳,中世纪的商人法用比较集体主义的合伙概念取代了比较个人主义的希腊-罗马的合伙概念,而且产生了类似于一种股份公司的联营,每一个投资者的责任限于它投资的数额。又如16世纪到18世纪西欧出现的大量特许贸易公司,也都是靠政府(或皇家)的政治权力特许建立的,用向政府(或皇家)提供贷款或承担其他义务换取贸易垄断权,拥有特许贸易公司的股票也被看作一种特权。〔6〕参见张仁德、段文斌:“公司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分析与现实结论”,《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4期,页18-25。
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公司立法主要体现为政府——商人的博弈,商人依然是推动公司法发展的主要力量。比如在特许状的约束下,英国的商人们开始了自己的突围。18世纪初叶,商人们发现在没有取得皇家“特许状”的情况下,也可以模仿特许贸易公司的组织形式,通过发行股票来吸引投资者,组建公司——合股公司。它没有皇家的特许状,而且股票可以自由转让,股东只负有限责任,股票持有者并不像合伙制企业中的合伙人那样有权代表其他合伙人签署对所有合伙人都有约束力的合约,而是由被股东集体授权的经理人员来经营。〔7〕参见(美)罗森堡、小伯泽尔:《西方致富之路》,刘赛力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页225-226。事实上,商人通过从规制公司(regulated company)处取得类似子公司的合股公司(joint stock company)资格。1720年,英国发生了一场由一家特许贸易公司──“南海公司”掀起的股票投资狂潮,史称“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大量未经皇家特许的合股公司股票的发行使南海泡沫的继续膨胀受到威胁,〔8〕仅1719年9月至1720年8月这一年就新成立195家公司。在南海公司的游说下,英国议会1720年通过了“取缔投机行为和诈骗团体法”,即“泡沫法”(Bubble Act),禁止没有特许状的企业发行股票,直接导致许多合股公司倒闭,也导致英国公司的发展自此停滞了近一个世纪。〔9〕参见(英)罗纳德·拉尔夫·费尔摩里:《现代公司法之历史渊源》,虞政平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页2。但即使这样,也没有阻止英国商人创办公司的热情。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迫切需要创立大型企业组织,商人们很快想出了绕过法律障碍的办法,这就是将两种早已存在的合法组织形式──合伙和信托结合在一起,通过指定合伙人中的某些人作为其他合伙人的财产(股本)托管人,授予他们与其他个人或团体订立合同的权力,将经营权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而使合股公司得以继续发展。直到英国议会首先在1825年废除了“泡沫法”,不再禁止创办民间合股公司;1844年通过了公司法,对公司实行注册登记制度;1856年,英国议会正式确认了注册公司所有股东对债务只负有限的赔偿责任,从而建立了公司法基本框架。〔10〕张仁德、段文斌,见前注〔6〕,页18-25。由此可见,在现代公司法形成的过程中,商人的努力和创造始终是动力的源泉。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在现代公司法进一步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公司法立法中商人主导的模式却日渐式微,在立法机关主导下、各种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民主立法的模式日益发展。现代公司法的发展是立法者、法官、利益集团以及公司投资者共同推动的结果,商人的角色呈现出“淡化”的特点。美国学者威尔斯的实证研究对此提供了有力佐证。他以美国闭锁公司法的发展历程为例,论证了美国现代公司法制的发展是立法者、法官、利益集团以及公司投资者共同推动的结果,但是由于公司投资者遵循的是制度诱致性变迁路径,其作用不如其他主体显著,因此一直很少得到理论研究的关注。〔11〕See Harwell Wells,The Rise of the Close Corpo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Corporation Law,Berkeley Business Law Journal,Vol.5,2008,pp.263-316.See also Harwell Wells,The Modernization of Corporation Law,1920-1940,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Business Law,Vol.11,2009,pp.573-629.
法律常常是政治和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而对这一进程的解释中,我们常常会忽略了法律规则的变迁受制于社会整体力量的制约,而夸大了某一部分群体的作用。“虽然在经济学领域,亚当·斯密等人的观点已得到普遍认同,但是他们的主张在传统法学领域却几乎没有得到重视。”〔12〕See F.A.Hayek,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 and Economic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pp.101.这就告诉我们,公司法立法早已不再是简单的商人——政府博弈,而是以公司法立法为舞台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
二、商人角色演化的必然性
公司法变迁中商人角色的演化,特别是现代公司法立法中商人角色的“淡化”和博弈格局的变化,也许被理论研究者忽视了,但这并不因为“忽视”而增加了偶然性,相反这种变化有着深刻的必然性。其中最主要的,也许就是公司时代的来临和公司法性质的根本改变,使商人的主导已经在客观上成为不可能和不必要,立法机关主导成为客观要求。与此同时,由于政府对经济进行规制调控的加强和深入,政治文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使经济、社会、政治等宏观因素对公司法发展的推动更加直接和明显,商人对公司法立法的直接推动相对弱化了。而公司法的复杂化和立法技术的复杂化也使法学精英参与立法成为不可或缺。
(一)公司和公司法的深刻变革
公司起源于中世纪商人自发的联合,公司法在很长时间内无疑也是商人自治的规则。整个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公司法,即使国家对商人和公司进行了一些法律的规制,其基本性质也是“简单地在个人利益公共利益中采用自由放任—规制禁止的简单方式”,〔13〕邓峰:《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页29。邓峰在该书中对此公司时代的描述非常充分,这里不一一引述。公司关系总体上始终是私的范畴。但当世界进入公司时代,公司法就注定要摆脱商人自治法的标签。近代以来,公司的出现和迅猛发展,对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已经成为世界的第三极,“正如19世纪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世纪,20世纪将会是一个公司主义的世纪”。〔14〕Quoted from Philippe C.Schmitter,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36,1974,pp.85-131.公司构成了我们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一极,和1855年之前的世界——主要是一个国家和个人,政治和市场,政府与社会,公法和私法对立的时代不同,这是一个国家——组织——个人的时代。〔15〕同上注,页2。在公司时代,不仅公司自身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而且普遍意义上的公司的发展和对公司的规制,已经不再只是商人的家务事。
首先是公司自身特性的变化。与公司关联的债权人、政府、社区、劳动者的各自利益日益独立,公司的外部效应不断扩大,社会性、公共性不断增强。公司法日益成为一个组织载体,不仅仅适用于商人,包括慈善组织、国有企业、合作社乃至于工会等多种目标都可能借助于公司的形式来实现。公司越来越从仅仅被视为股东财产的集合趋向于作为独立的实体,公司、控股股东、小股东、董事和高管人员之间的个体利益分化越来越严重,这就会导致某项决策的合理性必然成为法律要考虑的问题。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利益相关者理论开始兴起,从而提出了对股东至上理论的修正,为认识公司本质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利益相关者的理论最早起源于多德(Dodd)与伯利(Berle)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论战,而在1963年由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对一个公司来说,存在利益团体,若没有他们,公司就无法生存,这些利益团体就是所谓的利益相关者(stakerholders)。〔16〕See R.E.Freeman,Strategic Management:A Stakeholder Approach,Pitman Press,1984.
随之是公司法本身特性的变化,公司法也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商人自治法。在量的维度上,公司法大量扩张,不仅各国纷纷出现了各种公司法的单行法,而且现代公司法的众多规则,以及和公司制度相关的法律规范非常广泛地分布在证券法、票据法、商业银行法、海商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市场结构法、国有企业法、合伙法、国有投资法、产业结构调整法、土地法、税法等等边缘法律部门之中。在质的维度上,公司法发生了更为重要和根本的深刻变化,
纵观整个20世纪到21世纪的公司法律制度的进化,可以看出以下几个趋势:首先,作为主体的公司和作为客体的公司交织在一起,公司治理、融资和并购三个主题共同构成了公司法进化的主题,将公司仅仅看做一种企业组织,已经远远不足以理解现代法律体系了;其次,就治理、融资和并购三个主题而言,有一个从分化到整合的过程,而三者共同围绕着资本市场而展开。第三,公司主体制度上不断放松,但行为制度上不断公共化和规制化。〔17〕同上注,页13、32。
资本市场和并购的发展,导致了传统上将公司看成是单纯股东利益的法律规则,越来越受到更多其他利益相关者考量的冲击。〔18〕See Ronald Daniels,Stakeholders and Takeovers:Can Contractarianism be Compassionate?,University of Toronto Law Journal,Vol.43,1993,p.315.公司法不仅要对公司内部关系作出调整,而且必须对公司的庞杂的外部关系予以关注,公司法的公法化倾向十分突出。〔19〕See Lawrence E.Mitchell,The Fairness Rights of Corporate Bondholders,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65,1990,p.1165.1983年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率先修改公司法,引入“利益相关者条款”,允许经营者对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负责,而不再只对股东一方负责。到1990年在公司法中制订“利益相关者条款”的州总计25个,目前数量迅猛增加到40个州,其都以不同形式制定了类似条款。
公司法在近代以来的不断扩张和进化,已经使之成为商法不能承受之重。〔20〕但比部门法划分“领地”之争更为重要的,是对公司法现代属性的客观认知。因为公司法属于哪个部门法或者哪个学科,至少在现阶段还只具有学术上的意义。而公司法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对其现代属性应该如何认识,究竟是商人自治法还是其他,则具有决定公司法立法取向和思路的实践意义。譬如当公司法已不再是传统的商人自治法,而我们仍然沿用商人自治的思维,或者将公司法仅仅视为调整商事主体关系的商部门法,则必然难以对管制——自治、管制——规避等范畴作出正确的分析。正如日本著名法学家酒卷俊雄所言:商法的条文是怎么也装不下偌大的公司法的,终究还是要将公司法部分从商法中独立出来,使其成为包括有限公司法在内的独立的公司法。〔21〕(日)酒卷俊雄:“日本公司法的沿革及立法课题”,《中外法学》1993年第1期,页65。1998年成立的英国公司法改革指导委员会则赋予了公司法更神圣的使命,它指出:公司法的最终目标应是在原则上成为追寻普遍繁荣和福利的最佳载体。〔22〕See Modern Company Law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The Strategic Framework:A Consultation Document from the Company Law Review Steering Group,February 1999,London:DTI,p.9.由于公司和公司法性质的根本转变,不仅商人,而且债权人、政府、社区、劳动者等利益相关者都参与到公司法的变革中来,促使作为民主舞台的立法机关不可避免地成为公司法变革的主导。
(二)推动公司法变迁的宏观动力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对商人角色演变的必然性的解释,也许还要从公司法变迁的宏观动力的角度作出合理分析,这也是对立法机关主导公司法变迁的动机的合理解释。这包括:
1.经济政策
公司法与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的关系极为密切,推动公司法改革的重要经济政策动因包括反垄断、经济安全等等。以二战后的日本为例,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日本对公司法进行了频繁的修改,达到十余次,平均每五年即修改一次,每次都是与经济政策的调整相适应的。比如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代,为了限制垄断,日本曾于1947年颁布《禁止垄断法》,严格禁止金融机构、事业单位、企业法人持有公司股份。但是,为使公司的股份不轻易流入外国投资者手中,防止本国企业被外国企业兼并,日本又先后于1949年、1953年对这一法律作了一定修改,放宽了对金融机构、事业单位购买公司股票的限制。由于法人相互持股容易形成垄断,随着法人持股的不断上升,其不足与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1981年日本修改商法时开始又对法人持股作了一些必要的限制。再如关于公司最低资本金的规定,也是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不断做出调整的。〔23〕参见杨丽英:“日本公司立法的历史考察”,《现代法学》1998年第5期,页125-129。
2.公司法竞争
在投资和贸易全球化的时代,出于吸引投资者等考虑,国家之间或者一国之内不同法域之间都在开展公司法竞争,成为推动公司法变迁的重要动力和走向趋同的重要原因。这也许是公司法现象中最具特色的一种,William Cary将其称为“向下的竞赛”。〔24〕See William Cary,Federalism and Corporate Law:Reflections upon Delaware,Yale Law Journal,Vol.83,1974,p.663.Romano教授提出,公司法必定对本地和国际经济活动施加影响,所以公司法的制定者应该促进公司法的系统建设,使本国的公司法在市场上成为更具吸引力的产品,吸引本地和国际企业家像消费者一样乐于使用它。〔25〕See Roberta Romano,The Need for Competition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Regulation,Theoretical Inquiry of Law,Vol.2,2001,p.387.在公司法竞争肇始的美国,特拉华州的公司法已经成为一种产品甚至一个产业,因为它的公司法,纽约证券交易所百分之四十的上市公司在特拉华州注册设立,特拉华州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来源于公司注册费,甚至是否是在特拉华州注册也会明显地影响一个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26〕See Ralph K.Winter,Jr.,State Law,Shareholder Protection,and the Theory of the Corporation,Journal of Legal Studies,Vol.6,1977,p.251.在欧盟,随着企业设立的自由化,美国式的公司法竞争也初露端倪,2000年欧盟法院在一个案件中裁决丹麦政府以对封闭式公司的最低资本额限制拒绝公司注册的行为违反了《欧共体条约》第48条规定的企业设立自由的原则而无效。欧洲的法学家分析,该判例将导致奥地利、丹麦和德国等设置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额的国家失去更多的投资。一种强大的竞争压力笼罩着欧盟各国的公司立法。〔27〕See Klaus Heine and Wolfgang Kerber,European Corporate Laws,Regulatory Competition and Path Dependence,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13,2002,pp.47-71.竞争意味着优胜劣汰,当一种公司法制度显现出明显的优势后,其他国家就会跟进效仿。公司法竞争现象的客观存在,有利于解释中国公司法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对制度移植的路径依赖。
3.社会力量
社会力量对公司法发展的推动是多维度的。在反垄断领域,公司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对大公司的愤怒和恐惧从19世纪下半叶就开始了。于是以利益集团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在公司法变迁中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这直接推动了对大公司和其垄断行为的打击,一些针对公司垄断行为的公司法规范开始出现,并广泛分布在证券法、反垄断法等新的法律制度中。在劳动者福利领域,一些国家社会力量的参与还产生了特色的公司法制度,比如日本的职工持股制度。职工持股制度,就是在股份公司内部设立本企业职工持股会,由职工个人出资,公司给予少量补贴,帮助职工个人积累资金,陆续购买本企业股票的一种制度。日本上市公司的股票一般以1000股为买卖的基本单位,1000股以下是不能购买的,每一股的票面为50日元,每一单位的股票的面额合计就是5万日元。但股票交易是按市价计算的,市价一般为票面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这样要购买一个单位的股票需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资金,这对职工个人来说绝非易事。而建立职工持股制度就可以由持股会组织职工每月从工资中扣除少量资金,集中起来以持股会的名义统一购买本企业的股票。股票由持股会持有,但按每个人的出资数分别列账,从而使职工零星出资购买股票成为可能。〔28〕杨丽英,见前注〔23〕。再如在美国,70年代以后,以养老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资金规模迅速增长,它们开始扮演稳定型的投资者角色,并由此争取政治和经济利益。比如1985年美国第二大养老基金——加州公共雇员养老基金(CalPERS)发起了股东权利运动,创立了机构投资者委员会(CII),它们奉行公司治理导向投资理念,积极介入目标公司的公司治理,因此推动了一些公司治理法案的产生,比如要求目标公司提供信息、全面披露经理层薪酬等等。
(三)公司法的复杂化和法学家的独特作用
如前所述,发展至今,公司法已经成为一个庞杂的体系,公司法立法技术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复杂化。而且,公司法处在经济法律体系的核心地位,公司法居于整个经济生活的法律调整的核心。与公司法相关的法律部门,诸如证券法、银行法、反垄断法、税法、会计法、公共经济规制、公共商事行为、破产法、保险法、海商法、合同法、财产法等,都以公司法上对组织结构、行为的法律调整为基础展开。〔29〕参见邓峰,见前注〔13〕,页41-42。因此,对公司法的修改牵一发而动全身,其立法技术的复杂性可想而知,这是商人们所难以承担的。《美国标准公司法》是法律精英团体直接制定的不具备法律效力的示范法律,但是在它公布后已经陆续被美国各州所采纳,以转换为各州公司法规范的形式间接具有了法律效力。它最早于1928年由美国统一州法委员会发布,定名为《统一商事公司法》,1943年由全美律师协会主持起草期间更名为《标准公司法》,于1950年公布。《标准公司法》于公布之后不断地修订革新,在57年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对美国各州公司法的现代化起着引领作用,同时在世界范围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30〕参见沈四宝编译:《最新美国标准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页250,第二编。随着公司法竞争的发展,还促使公司法的比较研究成为公司法立法不可或缺的支撑,公司法学者在这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彰显。在我国,专家主笔的立法模式一直是我国主要的立法模式,每次公司法立法和修订都成立了专家小组,负责立法咨询和执笔。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公司已不再是商人的工具,在整体上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和社会的支柱,公司法调整的范围于是远远超出商人间的投资、治理等社会关系。尤其在国际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公司法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国际竞争的手段和经济、社会政策的载体。在推动公司法发展的诸多因素中,发展经济和制度竞争往往是最直接、最主要的动因。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这种倾向更加突出。
虽然本文反复强调了商人在公司法立法中角色的“淡化”,但如果从政治的角度分析,这也许只是一个表面的现象。不仅商人依据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政治体系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由经理群体形成的“商业精英”及其与“政治精英”的转化、联合,还形成了公司对政治和权力的渗透。〔31〕同上注,页13。因此,商人虽然“淡出”了立法,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控制着立法机关。因此,商人改革公司法的需求可通过商人在立法机关的代言人得以表达,立法的回应也就不可能是经济制度演变那样的诱致性的路径,而且在回应的速度上也发生了变化。这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伯尔曼的疑问。
三、中国公司法改革中的商人角色
从1993年公司法首次颁布实施后的20年来,中国的公司法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完善,公司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弱小走向强大,包括立法机关在内的政府始终担当了培育者的角色,这个时期的公司法变迁本质上是一场政府主导下的追赶式立法。同时,借鉴和移植发达国家公司法始终是我们依赖的途径之一。当代中国公司法变迁的轨迹十分独特,公司法的始创和改革走的基本上是一条强制性变迁的道路,商人在其中的作用很小。问题是,为什么政府主导?为什么移植?为什么强制?
回答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中国公司法始创和改革的特殊历史背景。它是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大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根本特点即是统一步调、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革,因此公司法的变迁不可避免地要顺应这一潮流,发挥其工具性价值。如果说西方公司法的始创和变迁主要是法律和制度创新,而中国公司法始创和变迁在本质上主要是经济创新,甚至在1993年的版本中是服务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对公司法的发展也许贡献不大,但在移植公司制度推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上却是功莫大焉。公司法的工具性价值也许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阐释:
1.国企改革的法律工具
1993年《公司法》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主要是为国企改革提供法律支持,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发育。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里,扩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租赁、转换经营机制、股份制改制等等各种改革轮番登场,但国有企业效率低下、腐败丛生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虽然198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明确提出走联合之路,1986年国务院又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若干问题的规定》,推动了公司导向的国有企业改革,但在1993年以前真正采用规范的公司形式管理的国有企业几乎没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国有企业都真正采用规范的公司形式管理)。1993年11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指出“现代企业按照财产构成可以有多种组织形式。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益探索”。直至十七大的文件中,依然在强调要“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32〕《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4/content_6938568.htm,最后访问日期:2011年6月14日。
PDCA循环理论认为管理中的任何工作都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计划阶段(P),实施阶段(D),检查阶段(C)和总结处理阶段(A),这四个阶段紧密衔接,缺一不可,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PDCA循环模式之所以能够应用于创建高校的优良学风,关键在于它的长效性、持续性、循环性和可改进性等优点。
2.公司法创造的商人和公司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陆续颁布了一些公司立法,比如1988年6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企业可以采用独资企业、合作企业和有限公司三种形式,明确“有限责任公司是指投资者以其出资额对公司负责,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企业”;1992年5月15日,国家体改委正式发布了《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1992年深圳、上海等地颁布了各自的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但在1993年《公司法》出台以前,除依据1979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6年《外资企业法》和1988年《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设立的外资有限责任公司外,中国社会资本和规范的私人公司的数量都是非常少的。当时私人投资主要是个体工商户,或者挂靠国有企业和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因此,虽然一般认为,1993年《公司法》出台的背景之一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了公司热,形形色色的“公司”需要予以清理、整顿、规范,但这不意味着当时的公司法制度产生于这些公司实践,或者这些公司或其投资者在当时的公司法立法中发挥了作用。相反,很多“公司”都是在公司法出台后才逐步完善而名副其实的。更重要的是,在1993年《公司法》出台以后,私人企业方才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而2005年对《公司法》进行修订后,由于设立公司的门槛大大降低,注册公司的数量更是猛增。因此,如果说在西方国家是商人发明了公司、创造了公司法,则在当代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公司法创造了商人和公司。
时至今日,中国的GDP已经位居世界第二,尤其是私人企业控制的财富达到了惊人的规模,私人企业创造的GDP已经占到全国GDP的60%以上,甚至有数据称中小企业数量已经占全国企业数量的99%。那么,时过境迁,公司法强制性变迁和追赶式立法路径是否具备改变的条件了呢?是否可以采用或者更多地采用商人主导的诱致性变迁的模式呢?答案是否定的,我国仍然必须走强制性变迁的道路。其原因除现代公司法变迁的一般规律外,还有中国的特殊原因:
1.特殊的利益协调需求
近年来,我国各类公司扩展迅猛,在公司就业的人员大量增加,公司的债权人、劳动者等各种利益相关者的数量激增。这些利益相关者与公司特别是公司控股股东的矛盾纠纷也大量增加,民事案件“执行难”、农民工工资拖欠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难题。首先,其中有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数量不少的问题,与公司法的立法和实施中存在的缺陷密切相关。比如许多民事案件“执行难”问题,就与公司法的强行性规范在实施中落空,造成大量公司管理不规范特别是财务制度不健全,或者“刺破公司面纱”等制度不完善有关。其次,立法活动在很大程度属于政治的范畴,是利益平衡协调和妥协的过程,公司法立法也不例外。由于劳动者等利益相关者与公司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贫富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因此另外一些问题虽非都与公司法改革和公司法实施中存在的缺陷有着直接关系,但由于事关重大,因此是修改完善公司法所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此外,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大量的公司利益相关者缺乏足够的利益表达渠道,如果没有政府的主导和关切,他们的利益关切很难得到重视。因此出于利益平衡协调的需要,政府在公司法立法中的主导作用不是应当削弱,而是应当加强。
2.追赶和竞争
虽然公司法竞争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即使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大量的公司法移植现象,因此不能把公司法的移植一概视为从经济发达国家向经济落后国家的单向移植。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即使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公司法移植,也主要是从经济活力或者说经济创新能力更强的国家流向相对较弱的国家。特别是经济领先国家对世界范围内的公司法变迁的引领作用是十分明显的,1933年美国证券法就让强制信息披露成为各国对上市公司的一般规范。经济领先国家率先爆发的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司法规则,也会引领各国的公司法走向。比如在安然公司事件等系列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制定了Sarbanes-Oxley法案。受此影响,欧洲各国公司法的改革方案,其很多内容均与美国Sarbanes-Oxley法案近似,比如要求加强独立董事的作用和规范外部董事的独立性,强调年度报告和其他报告对公司治理等重大内容作出披露,严格公司会计和审计制度,强化对小股东和相关人的保护等。对我国公司法来说,则是由于经济上落后,尤其是经济体制和创新力上的落后,所以政府主导、所以立法上追赶。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客观上仍将在一个长时期内落后于发达国家,同时我国的经济在WTO框架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融入全球经济,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公司法竞争,因此不可避免地要继续把发达国家公司法作为我们修法的主要参照。因此在当代中国公司法的变迁中,商人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担任主导的角色,变迁的路径也很难以诱致性变迁和制度内生为主。
四、展望:从管制走向善治
上个世纪90年代,治理理论在西方国家兴起。治理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而“善治”则是治理的最高境界,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33〕参见俞可平:《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善治的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参与性、回应性、有效性、稳定性、廉洁性以及公正性等。治理和善治理论打破了社会科学中长期存在的两分法传统思维方式,即市场与计划、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它把有效的管理看作是两者的合作过程。〔34〕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分析的比较优势”,《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9期,页15-17。
公司时代到来后,公司成为社会的第三极及其对两极社会的冲击,无疑是治理和善治理论产生的重要背景。而治理和善治理论则为我们分析当下中国公司法实施中存在的“架空”现象提供了较好的框架。从善治的观念来看,出现超出“正常值”的公司法规避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对公司关系的管理方式主要是管制,没有形成政府、商人、公司、中小投资者、债权人、劳动者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治理,管理的合法性、参与性、回应性、有效性较差,而公司法与环境的不适应性、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抗性较强,造成政府和市场协调的失败,〔35〕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市场的失效和国家的不足相关。市场的失效指的是仅运用市场的手段,无法达到经济学中的帕雷托最优。市场在限制垄断、提供公共品、约束个人的极端自私行为、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统计成本等方面存在着内在的局限,单纯的市场手段不可能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同样,仅仅依靠国家的计划和命令等手段,也无法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最终不能促进和保障公民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正是鉴于国家的不足和市场的失效,愈来愈多的人热衷于以治理机制对付市场和国家协调的失败。参见俞可平:“治理与善治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9年第5期。所以公司法的诸多规范被架空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从管制走向善治,是解决严重的公司法“架空”现象的出路所在。这里试举数例,以探讨如何从善治的框架出发来改造中国公司法。
1.公司法的合法性改造
善治视野中的合法性,即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从我们所关切的公司法能否被严格遵守的角度来说,公司法的合法性在于公司法所设计的与公司有关的秩序是否被投资者、公司、债权人、劳动者等利益相关者所自觉认可和服从。而公司法制度的合法性以及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法制度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道德习惯等外部环境的适应性,因为这些环境因素不同程度地、共同地决定了公司利益相关者自觉认可和服从公司法的程度。
由于制度移植是我国公司法始创和变迁的基本路径,因此移植的技术和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司法的适应性和合法性。而当前公司法“架空”现象亦与公司法移植在一定程度上的失败有直接关系。比如虽然公司法上的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确实为大量的投资者提供了制度支持,但由于中国的家庭普遍实行家庭财产共同所有,而且家庭成员甚至朋友之间的高度信赖关系,因此从形式上弄虚作假满足公司法所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条件是十分容易和十分常见的现象,许多有限责任公司从一开始就无异于一人公司。这种根本性的规避,不仅使股东出资比例、分红比例等强制性规范变得毫无意义,而且可以说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的股东人数、治理结构等等都变得毫无意义,有时甚至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纠纷。没有充分考虑社会结构条件而直接移植国外的有限责任公司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失败的。因此,对公司法的结构性改革,不应是仅仅允许设立一人公司,而且还应当充分考虑公司的公共性,对公共性较弱的公司,完全可以将现有的诸多强制性规范,比如股东人数、组织机构等等,转变为选择性规范。
事实上,问题不是当否移植,是移植当否。当代中国的公司法移植总体上是选择性的,并非全盘照抄,而是将西方公司法制度选择性地嫁接到原有的经济、社会、政治体系之中。但在移植的技术上,确实存在较大的问题。移植,不仅要移植制度,更要移植观念和理念。移植,必须要攻克现代公司制度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兼容性难题。〔36〕一些学者对西方公司法与我国国情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兼容性作了研究,比如:“甚至在1994年通过公司法之后,公司法中规定的‘股权决定投票权’的原则在部分私有化中也未能得到执行。政府股份享有更大的投票权。内部交易和腐败也非常猖獗。何所记录的政府控股公司的自发私有化的例子中很多都涉及资金向海外市场的转移。这种状况为内部盗窃国有资产提供了方便。”“但在现行的宪法制度下,法律,如1994年通过的公司法和1993年通过的反不公平竞争法,是不可能实施的。杨指出了公司法和宪法制度的矛盾,而米勒指出了国家垄断电讯业和反不公平竞争法之间的矛盾。”(美)杰夫雷·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与宪政转型”,《开放时代》2000年第7期,页4-25。
此外,尽可能地减少强制性规范调整的范围,扩大公司自治的范围;在追赶发达国家的同时,我们也应重视内生性制度的建设,不断总结提炼本土化的商业规则、商业习惯并上升为法律,等等,也是公司法合法性改造所必须努力的方向。
2.公司法的参与性改造
善治所称的参与性,是指公民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对公司法的参与性改造,应当包括扩大公司法立法的公民参与性和利益相关者对公司治理的参与两个方面。虽然政府主导、专家主笔的公司法立法模式在现在和可预见的将来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中国公司法的立法程序中商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同样十分重要。而现实是这种参与的程度严重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公司法的立法质量。在当前的政治安排下,政府是公司利益相关者的主要代言人,因此政府需要在公司法立法进程中尽量扩大公民参与的范围。这种公司法立法的参与性,事实上也支持了回应性要求,即要求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及时了解商人等公司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法立法需求,并及时作出回应。此外,公司也需要善治,由于我国的公司控制权普遍比较集中,商人和劳动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也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