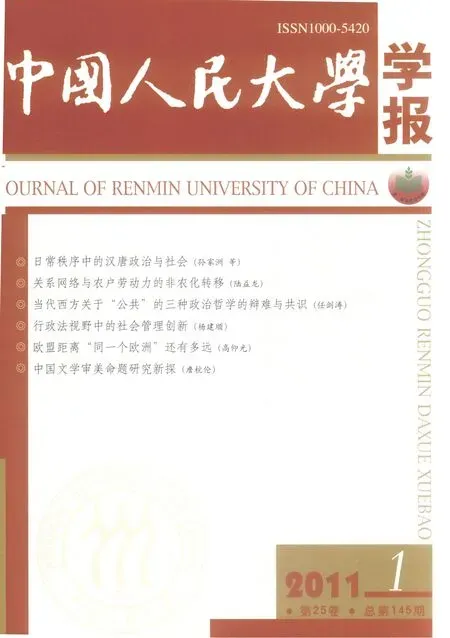洛克与现代民主理论*
霍伟岸
洛克与现代民主理论*
霍伟岸
洛克是否明确提出了一种现代民主理论,在西方学界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现代民主理论的五要素出发,依次考察洛克的人民主权观念、同意学说、代表观念、多数统治学说和反抗权理论。没有足够的文本证据支持认为洛克明确提出了一种现代民主理论的观点,但洛克对现代民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则毋庸置疑。
洛克;民主;同意;代表;多数统治
洛克与现代民主理论的关系一直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是从宪政传统来解读洛克,认为他基本上是一个前民主的思想家;20世纪50年代之后,关于洛克与现代政治民主理论关系的解说开始变成一个极度有争议的问题,学者们围绕着洛克学说的保守性与激进性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鉴于民主本身是个非常庞杂的概念,本文所说的民主仅限于现代民主、政治民主①政治民主是“主导的统领性民主”,“民主首先是个政治概念”。见萨托利:《民主新论》,12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也就是现代政治民主。所谓现代民主,概言之,主要是指现代民族国家普遍实行的代议制民主或间接民主,以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或直接民主相区别。现代民主理论一般包括五个方面的特征:(1)人民主权观念: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作为一个整体永远保留着不受任何限制的最高权力;(2)信托与代理:人民与政治统治者之间通过周期性选举体现了一种信托与代理的关系,当选者以人民代理人的身份来行使统治权;(3)政治平等:假定人民具有平等的政治人格和政治理性,拥有平等的投票权;(4)多数统治:假定多数人的意志可以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这不仅体现在选举中获得多数票的人可以当选,而且日常的政治决策也必须始终体现多数人的意志;(5)反抗权:当统治者违背人民的信托时,人民可以将其撤换,有时甚至可以通过革命推翻现有统治者,收回授权,再重新授予新的信托对象。
基于以上说明,本文的问题可以用下述方式提出:洛克的政治理论与现代民主理论的五要素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换言之,洛克是否明确提出了一个现代民主理论?我们该如何界定洛克在现代民主传统中的位置?
一、洛克是否有民主理论:西方学界研究综述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洛克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有政治权力,或政治服从的基础何在。他重点讨论的是人的自然权利 (自由)和政府权力的限度等问题,而不是政府的组织形式。换言之,民主问题在洛克那里还不是重要问题,他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民主理论。洛克虽然提及了多数统治,但通行的观点认为,他不可能真正信奉一种多数统治的民主学说,因为作为“个人主义者的君主”,他的诸多著名原理,如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理性的个人主义、不可让渡的自然权利和客观正义的自然法,是与多数统治学说不相容的。这个时期,只有肯德尔的观点与众不同。他在其著作《约翰·洛克与多数统治学说》中把洛克刻画成为一个极端的多数统治的民主主义者。[1]
20世纪50年代之后,关于洛克与现代政治民主理论关系的解说开始呈现出日益多样的面貌。洛克的政治平等学说首先成为学界辩论的焦点,核心问题是,洛克到底是在为谁的政治权利张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显然对于判断洛克与现代民主理论的关系有莫大影响。施特劳斯最早挑起这个话题,他怀疑洛克真的相信多数人能够给予个人权利以可靠的保障,他说:“洛克把多数人的权力视为对坏政府的制约,以及反对暴虐政府的最后凭借;他并不把它视为政府的替代物,或者就等同于政府。他认为,平等与公民社会是不能相容的。……最要紧的是,由于自我保全和幸福要以财产为前提,因而公民社会的目的就可以说是保护财产,保护社会中富有的成员免于贫困者的索要。”[2](P239)在这里,施特劳斯不仅明确否认洛克有一种多数统治的政治学说,而且指出洛克的政治学说本质上是为有产者服务的,只有富有者才享有政治权利,财产上的不平等可以合理地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人们进入政治社会的首要目的就是保护其财产。
麦克弗森扩展了这个话题,他认为洛克根本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指出,人们习惯于从洛克的政治思想中读出很多自由主义民主的假设,如基于同意的政府、多数统治,等等,但这些都是误读,因为这些假设都属于后来的时代,而不属于洛克所生活的17世纪的英国。在麦克弗森看来,理解洛克的关键是隐藏在其理论之下的社会假设,其中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劳资关系的有效性,以及劳动阶级缺乏理性思考能力因而也没有革命权。因此,麦克弗森认为,虽然洛克强调多数统治,而且他明确意识到当时的英国无产者占了人口多数,但由于他仅仅赋予那些有产者以政治社会的完全公民身份和完整的政治权利,所以所谓多数统治的实质是有产者的多数统治。就整个社会而言,处于统治地位的永远是有产的少数,而占人口多数的劳动阶级由于理性不完善而没有革命权,只能被迫接受永久被统治的命运。简言之,洛克是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家,其全部理论都是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张目。[3](P194-262)
然而,塔利与阿什克拉夫特等却提出了与施特劳斯和麦克弗森针锋相对的观点。[4][5][6]他们把洛克置于17世纪70—80年代激进辉格党与宫廷党和绝对君主之间围绕宗教宽容和王位继承而发生的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下来解读他的著作,认为他很可能会支持全体成年男子的选举权,因而是一个几乎与平等派立场一致的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这一派学者的语境主义解读中,洛克不再是一个大土地所有者或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也不再是正统辉格党的理论家,而是成为一个政治和宗教上的异见人士,他对经济和政治平等抱有更多的同情,他的政治学说被正统的辉格党人认为过于激进而拒绝接受。这样一个作为激进辉格党成员的洛克,被认为提出了一个至少在当时看来是非常激进的民主理论。
除了上述重要学者的解说之外,还有一种影响很大的意见是把洛克的政治理论冠之以“自由民主理论”的名目。例如,霍尔登把现代民主分为四种:新激进民主论、多元民主论、精英主义民主论和自由主义民主论,而其中的自由主义民主论——在霍尔登看来是唯一发展成熟的现代民主论——就被认为始于洛克。[7]尽管这种见解流传甚广,但有必要指出,持此论者更多的是从民主类型学或民主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待洛克的贡献或影响,而并不是从洛克自身思想的历史性和逻辑性的角度来考察他是否想要或者已经提出了一个民主理论。“洛克的民主理论”与“洛克对民主理论的影响”是两个迥然有别的概念。
那么,洛克到底有没有一种民主理论呢?我们主要依据洛克的文本,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的考察。
二、基于现代民主理论五要素的分析
关于洛克究竟有没有民主理论的问题,我们依据现代民主理论的五要素,逐次加以考察。
(一)人民主权观念
关于洛克是否有人民主权观念的问题,西方学界众说纷纭。反对派学者认为,洛克倡导的是一个有限权力的自由政府,不可能包容无限权力意义上的主权观念。例如,兰普雷希特指出,洛克“固然拒绝任何不依赖被统治者同意的政府;但他没有在任何地方支持一种人民主权学说”[8](P148)。拉斯基也认为:“洛克的国家也不是一个主权国家:‘主权’这个词在整篇论文中出现得不够引人注目。国家的权力仅限于维护自然法。当超越了那些界限之外,它的管辖就终止了。”[9](P43-44)而赞成派学者如肯德尔,则认为洛克的确提倡有限政府,但政府只是社会的代理人,其权力的有限性是基于其被授予的权力必须用于实现授权的目的;而社会 (或人民)作为委托者则拥有主权,它可以单方面确定与政府订立的契约的内容,并且永远保留着作为主权之体现的革命权。他还指出,洛克的政治社会的个体成员的权利只是社会主权的一个功能而不是对它的限制。[10](P90-111)拉斯莱特也认为,洛克的主权观念更接近今人而不是时人,我们必须把人民自己保留的“最终至高无上的至关重要的权力”称为“洛克关于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人民主权的观
念”。[11](P121)
回到洛克的文本,可以指出,主权 (sovereignty)这个词在《政府论》中出现的频率虽然不高,但的确在上篇和下篇中都有出现。①主权 (sovereignty)一词出现在《政府论》上篇第64、68、75、76、78、129、131、133节;下篇第4、61、83、108节。拉斯莱特所编辑的《政府论两篇》英文本关于sovereignty的索引不够准确。把这些相关文本综合起来看,其出现的语境几乎都是洛克对菲尔默父权论的驳斥。在这些讨论中,洛克所使用的“主权”概念是用来指称一种绝对的政治权力 (生杀之权),它具有至高无上性、无限制性、唯一性、不可分割性等特征。②现代主权观念通常认为主权是一种最高权力、终极权力,具有效力的普遍性和独立性,但“排除了对整体的、无限的、永恒的和不可分割的权力的主张”。在这个意义上,洛克的主权概念不够现代,更接近博丹和霍布斯等人的传统主权观念,即认为主权“集中在既定的中心”,“必须是绝对的、完整的、无限的和不可分的”。参见米勒、波格丹诺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725-726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但洛克的主权概念与博丹也有重要不同,他就不认为依照法律判人生死的权力以及宣战与媾和的权力是主权的特征,而这两点都被博丹归入主权的特征之列。参见博丹:《论主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洛克认为,主权的一个特征是制定有关生死的法律的权力,但根据这些法律来做出生死判罚则不是主权的特征,而是下级官员通常做的事。[12](P236)此外,洛克还否认宣战与媾和是主权的特征,因为即使没有公共权威的人 (如船长和私人种植园主)也可以做出这样的行为。[13](P238)
洛克关于制定有关生死的法律是主权特征之一的论述让我们自然想到了他在《政府论》中关于“政治权力”的著名定义:“政治权力就是为了管制和保存财产而制定带有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法律的权利,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害的权利;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公共利益。”[14](P268)但为什么洛克不把政治权力直截了当地称为主权?这似乎说明洛克认为主权与政治权力是两个有所区别的概念。在洛克看来,政治权力既包括立法权也包括执行权,既要维持内部秩序,又要维护外部安全;而主权似乎仅限于立法权 (因为他否认根据法律做出生死判决是主权的特征),而且不涉及与国家外部主体的关系 (因为他否认宣战与媾和是主权的特征)。此外,洛克认为政治权力的一个合理设置规则是分权,立法权与执行权由不同的人执掌;而主权则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分割性。
那么,主权是否可以等同于立法权?尽管洛克明确把立法权叫做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是“神圣而不可变更的”[15](P356),但它本质上是“得自人民的一种委托权力”[16](P362),有其行使的限度,不可以绝对专断地施及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必须以公共利益为目的,在形式上要以明示的经常有效的法律来体现,并且不能将此权力转让他人行使。任何被委托的权力都不可能是主权,因此立法权虽然可以说是主权的某种体现,但它本身并不能被完全等同于主权。
从《政府论》的文本来看,更为符合洛克所理解的主权特征的权力是人民的权力,抑或社会(共同体)的权力。第一,人民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也许有人会反对说,洛克认为个人的权利是更基本的,而且人民的权力也来自个人在自然状态中所拥有的自然法的执行权的让渡。但是人民权力至高无上与个人拥有天赋而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赋予人民至高无上的权力恰恰是为了使个人的基本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此外,自然状态中的个人一旦通过签署社会契约进入政治社会,那么除非社会解体 (亦即人民不复存在),否则都不能退出社会状态,恢复其自然状态中的权力,因此,只要人民存在一天,它就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第二,人民的权力也是无限制的。必须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无限制性,当然并非绝对意义上的无限制性,而是说它的行使只受人民自己意志的支配,不受其他任何人的意志和人定法的束缚。当然,这里不包括“上帝”的意志和自然法。人民的权力当然要为社会的存续和公共利益服务,这是神法和自然法的要求。第三,人民的权力也是唯一的和不可分割的。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社会中,人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权力必须统一行使。人民对其权力的行使,在洛克看来,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制宪权,亦即通过一个立法行为创建立法权,这也是一切政治社会的“最初的和基本的实定法”。[17](P355)人民全体依据多数同意原则,通过把立法权委托给某些人而确定政府形式。此后,人民作为一个权力主体便不再发挥作用,直到其发现政府违背了自己的授权信托并且一意孤行为止。这时,人民的权力就再度被激活,并以第二种形式来行使,那就是反抗权或革命权。
综上所述,如果说洛克有某种人民主权观念,那么在他的观念中,人民主权是由制宪权和反抗权组成的。制宪权随着立法权被确定归属和一个合法政府的诞生而告终结,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人民的制宪权此后就转化成为政府的政治权力,但人民自己永远保留反抗权。制宪权、政治权力和反抗权都是人民主权的不同面向,但它们各自并不能单独等同于或代替人民主权本身。更重要的是,政治权力与反抗权不能同时存在和发挥作用。当政治权力合法存在时,人民的反抗权就必须处于蛰伏状态,人民作为一个整体也就不能直接行使主权;而一旦反抗权成为现实的权力,则意味着政治权力不复存在,需要人民再度行使制宪权加以重建。由此可见,在洛克的理论中,人民的权力虽然至高无上,但其直接行使却是高度非连续性的,只有在政治社会的初创时刻和遭遇重大危机需要重建的时刻才会凸显出来;而且,当政治权力合法存在时,人民的主要身份不是主权者,而是对政府负有严格服从义务的被统治者。这或许是洛克在《政府论》中从未使用“人民主权”一词的一个原因。尽管我们很难否认洛克有一种人民主权观念,但从洛克对人民权力行使情境的谨慎界定可以看出,他的人民主权观念并未直接通向某种民主理论。
(二)信托与代理
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信托与代理关系主要体现为同意问题。毫无疑问,洛克认为在主权者人民和被授权的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信托与代理的关系,换言之,必须经过人民同意才能把至高无上的权力信托给政府,使其成为人民权力的代理者。任何没有获得人民同意的政府都是非法的。
我们接下来考察洛克的同意学说。首先需要指出,同意并不必然与民主相联系。霍布斯用人民同意一次性授权给主权者的学说来为绝对主义论证。[18](P128-142)当然,在另一个极端,平等派则倾向于把人民的同意与广泛的选举权联系起来。[19](P84-106)阿什克拉夫特等就倾向于认为洛克的立场接近于平等派;而持相反意见的学者则通常把洛克对明确同意与默示同意之间的区分当做他其实并不支持民主的重要论据,因为除了最初创建政治社会并签署原始契约的那些人对政府表达了明确同意之外,后来生活在某一政府统治下的公民大多只是表达了默示同意,而后者完全与选举权无关。[20](P663-671)本文倾向于同意后者的观点,但不同意其对洛克同意学说的解释。
洛克提出其同意学说为的是解决每个人对政府及其法律的政治服从义务的问题,而不是为公民的民主权利张目。洛克把同意区分为明确的同意和默示的同意。他说,没有人会怀疑,只有明确的同意,例如签署契约或公开宣誓,可以使一个人成为政治社会的完全成员。而且,一旦他明确同意加入某个国家,“他就永远地和绝对必要地有义务成为、并且始终不变地成为它的臣民,永远不能再回到自然状态的自由中去,除非他所属的政府遭受任何灾难而开始解体,或者某种公共行为使他不能再继续成为国家的一个成员”[21](P349)。明确的同意是自然状态中的个人放弃其自然自由而进入政治社会的充分条件,而且是唯一的充分条件。洛克从来没有说,仅仅身处一国的领土之上并享受到了该国政府所提供的安全和便利就可以使一个人成为该国的完全成员。同意遵守一国的法律仅仅是成为一国公民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只有明确的同意才具有这样的效力。
洛克还指出,当一个人加入一个国家而成为其完全成员时,他必然“也把已有的或将要取得的、且并非已经属于任何其他政府的所有物并入并隶属于这个共同体”[22](P348)。因为人之所以要脱离自然状态而进入政治社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他们的财产,那么这就可以推论出,人及其财产要同时进入政治权力的管辖范围之内,受政府制定的法律的调节。这里所说的财产主要是指土地财产。因此,当一个人进入政治社会后,就必然意味着他的土地财产同时成为该国领土的一部分,因而就给土地财产的占有附加了政治条件。“所以,任何人此后以继承、购买、许可或其他方法享用这样归并于那个国家并受其管辖的土地的任何部分,必须接受支配该土地的条件才能加以占有,也就是顺从对该土地有管辖权的那个国家的政府,如同它的任何臣民那样。”[23](P348)但是,这个附加条件只是遵守该国的法律和服从该国的政府,而不是成为该国的公民。这种政治义务与他对土地的享用共始终。“因此,当只对政府表示这种默示同意的土地所有者以赠与、出售或其他方法退出上述土地时,就可以随意加入其他任何国家或与其他人协议,在空的地方,在他们能够找到的空旷和尚未被占有的世界的任何部分,创建一个新的国家。”[24](P349)通常情况下,子女必须像父母一样成为一国的公民才能够继承他们的地产,通过地产的继承,父母的政治选择间接影响了子女的政治选择,从而保证了政治社会的稳定性。但这绝不等于父辈有权约束子女的政治选择,而只是表明子女为了获得特定的经济利益,需要以背负相应的政治义务作为代价。需要注意的是,子女要满足继承父母地产的附加政治条件,通常是通过明确的同意而成为一国的公民来实现的。但是,从原则上说,如果父母不要求子女一定要成为他们所选择的政府的臣民才可以继承他们的地产,那么子女也可以仅仅通过继承并享用父母的地产而对该土地上的政府表达一种默示的同意,但这种同意并不足以使子女成为该政府的臣民,而只是对之担负有限的服从义务。他们在本质上仍然是自由人,一旦通过转让或出售等方法使自己与其所继承的地产脱离联系之后,他们就可以自由选择加入别的政治社会或另外成立一个新的国家。
综上所述,洛克同意学说的重点在于阐明我们每个人的政治义务的合法来源。它把每个人自由的明确同意当做成为一国公民的唯一途径,强调每个人的政治义务都是自己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且我们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因为政治义务是不可自我解除的。因此,洛克的同意学说的确是一种高度个人主义的学说,但它是通过赋予每个人选择自己政府的权利来确定服从政府的义务,其着眼点在于服从的义务而不是选择的权利。可见,把洛克的同意学说与每个公民的选举权联系在一起乃是误解了洛克的本意。另外,对每个人而言,向某个政府表达明确的同意是一次性完成的行为,这种同意不需要连续性表达 (如周期性选举)就完全生效,并且在政府解体之前是不可撤销的。同意的内容,简言之,就是同意政府作为人民的代表行使权力,维护和平与安全,促进公共利益,并且同意服从政府为此目的而制定和执行的法律。
(三)政治平等
洛克政治平等学说的核心是代表问题。严格来说,代表与选举是没有逻辑关系的。一方面,代表不一定意味着选举,有些代表是不需要选举的。例如,英国有“王在议会中”的思想传统,王作为最高的立法者自然被视为人民的代表,但显然,国王不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另一方面,选举也不一定就意味着代表。罗马天主教皇是由枢密院的主教们选举产生的,但教皇并非主教们的代表,而是他们的绝对领袖。[25](P32-33)
就代表而言,一般可以区分出虚拟代表和实际代表两种概念。前者如“王在议会中”的英国国王或者一个由世袭贵族组成的会议,其代表人民的身份是在观念中虚拟形成的,不需要经过任何选举的程序;后者如现代代议制政府中的议员,其作为人民代表的身份是通过法定的选举程序确定的。显然,在洛克的论述中同时包含了这两种不同的代表观念。虚拟代表自然与民主无关,甚至通常是反民主的;而洛克的实际代表观念是否可以使他导向一种民主理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必须考虑洛克的政治平等学说的现实含义,也就是洛克是否主张普遍选举权。当然,我们不是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洛克是否有普遍选举权的主张。显然,洛克不可能为妇女和奴隶(他认可某种奴隶制)要求选举权。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这里所谓的普遍选举权是指全体成年男子选举权或者与之相近的选举权,至少比当时通行的政治实践门槛更低,从而可以赋予更多从前的非选民以选举权。
尽管洛克认为人在根本意义上是平等的,而且人人都有平等的自然权利,但这绝不意味着洛克也主张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人人都应该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特别是平等的选举权。
施特劳斯和麦克弗森都认为洛克的政治理论是为有产者的政治权利辩护,而麦克弗森的观点影响尤大。他认为,洛克把劳动阶级看做一个政治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关心财产的保存 (因为他们没有财产),而且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过一种完全理性的生活,因此不是政治体的完全成员,亦即不享受完全的政治权利,特别是没有选举权。[26](P247-251)阿什克拉夫特则从17世纪70—80年代辉格、托利两党政治斗争的历史背景出发,从洛克的文本中解读出更多的民主含义。他认为洛克所谓的同意有一种制度化的形式,即自由选举;而且洛克主张应该根据人口数量和纳税多少来重新划分选区,使人民在立法机构中获得更为公平、公正的代表,这意味着洛克在为更广大的人民——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处于底层的社会阶级——要求选举权,而这种权利不以是否拥有财产为基础。[27]
从争辩双方的论证手段中可以看出,要回答洛克究竟认为哪些人应该享有选举权的问题,单纯依据《政府论》文本是不行的,还必须结合考虑文本之外的语境因素。就本文有限的目的而言,笔者仅从实际代表与公民选举权 (投票权)之间的关系出发,来探讨洛克是否主张普遍选举权的问题。
洛克曾明确提及,把立法权交给“人们的集合体”比由单个人独掌更让人感到“安全和安心”。[28](P329)就英国的情况而言,立法权实际上同属三个机构所有,分别是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其中,前两个部分都非经选举程序产生,属于对人民的虚拟代表;而下议院议员则经周期性选举产生,属于对人民的实际代表。这里的问题就变成了:洛克是否主张一种广泛的下院议员选举权?笔者认为,很难找到令人信服的文本证据给出肯定性回答。持肯定性答案的学者最有力的文本证据就是《政府论》下篇第158节的有关论述,特别是下述关键段落:
如果拥有召集立法机关的权力的执行机关,遵照代表分配的真正比例而不是遵照它的形式,根据真正的理性而不是根据旧的习惯来规定各地有权被选为议员的代表的数目,这种权利不以人民怎样结成选区就能主张,而是以其对公众的贡献为比例,那么这种做法就不能被认为是建立了一个新的立法机关,而只是恢复了原有的真正的立法机关,纠正了由于日久而不知不觉地和不可避免地引起的不正常情况。……人民的利益和本意……需要有公平和平等的代表制……建立新的选区并从而分配新的代表的权力是带有这样一个假定的,即分配代表的尺度迟早会发生变更,以前没有推选代表权利的那些地方可以享有推选代表的正当权利;基于同样的理由,以前享有推选代表权利的地方可以失去这种权利,变得如此无足轻重而不配再拥有这特权。……如果人民以公正的和真正平等的办法来选举他们的代表,适合于政
府的原初体制,那么这无疑地就是允许并要
他们这样做的社会的意志和行为。[29](P373-374)
结合《政府论》下篇第 157节的有关论述①“因此往往发生这样的事,在有些政府中,立法机关的一部分是由人民选出的代表组成的,日子久了之后,这种代表的分配变成很不平均,与当初分配代表的理由很不相称。当我们看到有些地方仅有城市的名称,所遗留的只是废墟,在那里最多只能找到个别的羊栏和个别的牧羊人,而它们还同人口稠密和财富丰裕的郡那样,选出相同数目的代表出席庞大的立法者议会,我们就明白,沿袭业已失去存在理由的习惯会造成怎样大的谬误了。”见洛克:《政府论两篇》,372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可以看出,洛克主张依据人口的数量以及对公众的贡献来重新划分选区和重新分配“各地有权被选为议员的代表的数目”,从而实现对人民的“公平和平等”的代表。所谓对公众的贡献显然是指纳税。洛克在别处也提到:“凡享受[政府]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 (estate)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30](P362)estate在洛克的用法中通常指不动产,尤指地产。由于在洛克的时代,英国的圈地运动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无地农民,这样看来,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通过纳税来维持政府的运转。不过我们姑且不论洛克是否给选举权施加了财产权的限制②这是一个极富争议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对纳税的看法。认为纳税纳的是直接税的学者强调占人口大多数的穷人都不纳税,因此没有选举权;而认为纳税也包括间接税的学者认定绝大多数穷人实际上也在纳税,因而应有选举权。,单看他在第158节的主要意图。应该说,此处论述的重点乃是依据人口和纳税的标准更公平地划分选区和分配代表数目,换言之,他更关心的是选区的选举权分配是否公平,而不是个人是否应该拥有平等的选举权。洛克的实际代表观念主要是指全国人口的每个部分 (选区) ——而不是每个公民个体——都有权通过投票而被明确代表。
如果说洛克并没有主张普遍选举权,那么在他的代表观念中,虚拟代表显然比实际代表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根据虚拟代表的观念,公民个人,特别是穷人,即使没有投票权,依然可以在议会中被代表。这种观念背后的假设是“地主与穷人在一个单一的共同体中合为一体”[31](P676)。
(四)多数统治
肯德尔正确地指出,洛克是第一个提出单纯以数量为标准的多数统治原则的思想家。[32](P39-40)正是从洛克之后,今天意义上的多数决标准才开始为我们所熟知。这种观念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现在很多人把多数决原则与民主简单等同起来。但肯德尔提示我们,多数决原则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含义:(1)有组织的机构通过多数票来做决定的规则;(2)主张政治权力应该属于人民中的大多数人的一种理论;(3)拥护前述理论的人希望政府采取的、体现多数人掌握权力的组织形式。[33](P24-25)
这种区分对于本文的问题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
第一种含义是一种组织方法,甚至与政治都没有必然关系,更遑论民主。例如,美国最高法院现在有九名大法官,当他们意见不一致时,也会采用多数票决定的规则,但这绝不意味着最高法院是一个民主机构,恰恰相反,它乃是美国政治制度中最反民主的分支。
第二种含义是一种抽象的政治理论,它是在认可人民全体一致同意原则的前提下对于这一原则的进一步应用所作的让步。但这种理论仍然停留在观念层次上的多数人统治,而并没有落实在具体的政府制度上,因此它可以与各种不同的政府组织形式相容,而不仅限于民主制度。
第三种含义是指具体的政府组织形式,即经常性地诉诸多数人民的意志来进行决策的政治制度,只有在这个层次上,多数统治原则才可以与民主画上等号。
接下来我们看看洛克是在哪种含义上谈论多数统治的。根据前面对洛克同意学说的讨论,我们知道,个人在脱离自然状态进入政治社会时需要签署一个原始契约,这个契约秉承的是一致同意原则,也就是每个人都必须表示明确的同意,凡未同意者皆不受其束缚。这种一致同意原则与洛克赋予每个人的天赋自由是完全相符的。但洛克意识到,一旦由若干个人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集体行动与个人同意之间立刻就会发生冲突。因此,若要政治社会真正像一个共同体一样行动,就必须放弃一致同意原则转而接受多数同意原则。洛克由于看到一致同意原则的不可行,因而感到有必要把多数同意原则写进最初的社会契约中。也就是说,当人们签署了这个契约,就不仅仅意味着同意把个人在自然状态中拥有的权力转移给社会,而且意味着同意从此以后由社会的多数人代行这一权力,同意即使自己属于少数,也要认同多数人的决定并跟随其行动。笔者认为,写进原始社会契约中的多数统治原则乃是上述第二种含义下的原则,换言之,这主要是主张多数人应该掌握权力的一种抽象政治理论,而不是在具体的政府组织形式的层次上讨论问题。当然,应用这种多数原则的第一个重大场合就是决定政府的形式。
洛克在《政府论》下篇第十章讨论了“国家的形式”,亦即政府组织形式。他指出,基于原始社会契约规定的多数统治原则,签署这一契约而进入政治社会的多数人就可以行使“社会的全部权力”来确定政府的具体形式,也就是说,确定把立法权——政治社会中的最高权力——托付给谁。洛克沿用亚里士多德的分类,讨论了四种不同的政体,即民主制、寡头制、君主制和混合政体。这是洛克在《政府论》下篇中第一次提及“民主”一词,他对完全民主制 (perfect democracy)的界定是:“多数人……运用那所有的权力 [社会的全部权力]不时地为社会立法,并且通过他们自己任命的官员来执行这些法律。”[34](P354)洛克在这一段讨论中没有对四种政体的优劣进行评价,易言之,他并没有对民主制表示偏爱。可见,洛克认为多数统治原则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甚或信仰是可以与不同的政府形式相容的,该原则本身并不一定指向民主制度。为什么多数统治原则可以与寡头制乃至君主制相容,其要害就在于虚拟代表观念,经由这一观念,君主或少数贵族都可以成为人民的代表,只要他们的统治符合原始社会契约的基本目的。
但洛克有时对多数原则的讨论似乎不限于对立法机关的选择,而且涉及日常政治决策,如征税,他说:“诚然,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但是这仍须得到他自己的同意,即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35](P362)其实,洛克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征税的决策一定要通过民主制度来决定。当然,如果一个国家在最初选择了民主的政府形式,这里所谓“他们自己或他们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可以被认为是指全民公决或一个民主议会的多数决投票;但如果其政府形式是寡头制或君主制,则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贵族寡头会议的大多数或国王单独作为人民的代表而表示的同意;当然,洛克自己最倾心的是英国那样的混合政体,在这种政府形式下,人民代表的大多数则是指议会下院、上院全体议员,再加上在议会中的国王之总和的大多数。不过由于征税一般都是国王的提议,所以这里的大多数尤指议会两院全体成员的大多数。
综上所述,第二种含义的多数统治一旦确定了政府形式之后,就会面临两种情况:其一,如果大多数人民选择了民主政府,那么多数原则就将展现出第三种含义;其二,如果大多数人民选择了民主以外的政府形式,那么多数原则就将长期停留在抽象理论的层次,直到政府解体,人民的大多数再度面临选择政府形式的问题为止。从我们对洛克所偏爱的政府形式的了解来看,不能说洛克的多数统治学说具有直接的民主内涵。
(五)反抗权
当统治者违背人民的信托并拒绝通过法定程序予以更换时,人民就可以起来反抗,运用暴力推翻其非法统治,这是现代民主理论的应有之义。在这里,反抗权的主体应是人民自己,而不仅仅是人民的代表。任何拒绝人民亲自行使反抗权的理论都不能说是一种一以贯之的民主理论。
富兰克林指出:“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标准的宪政主义理论中,人民废黜实施暴政的国王及改变其官职权力的终极权利通常被等同于作为人民代表而被建立起来的宪制机构的权利。”[36](Pix)这种反君主主义传统,一方面反对君主滥用职权,实施暴政,另一方面同样担心民主革命。因此他们只敢把反抗权赋予人民的代表,如等级会议、王国的高级官员和贵族,但坚决反对普通臣民或全体民众起而反抗,后者被视为反社会和无政府主义行为。[37](P1-4)而洛克的反抗权理论则突破了这一限制。洛克所谓人民的反抗权,其实施主体既可以是人民的代表 (如议会,特别是议会下院),也可以是社会公众,乃至每个公民个人。[38](P379)如前所述,反抗权是人民主权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因此,它虽然一直是宪政主义传统中的一个核心主题,但也应当是现代民主理论的必要组成部分。
肯德尔还看到洛克的反抗权理论与现代民主理论的另一种重要关联,那就是前者可以被视为“使法律和政府持续性地对多数人意志负责”[39](P127)的一种办法。不过,肯德尔认为这种办法对于实现其目的来说是很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应该努力创造制度性条件来帮助形成多数人的意志。洛克忽视制度建设而单纯依靠人民的反抗权,这被认为是其理论的致命伤。[40](P127-129)笔者认同肯德尔关于洛克的反抗权理论与现代民主理论之关联的评价,但反对他对洛克的批评,因为这种批评的前提——即洛克的目的是要建构一种多数统治的民主理论——是不存在的。
洛克的确提出了一种完全意义上的人民反抗权概念作为其人民主权观念的合理推论,而且,这一概念也的确有督促统治者对人民负责的重要意图,但是仅凭这两点,不能合乎逻辑地推出洛克倾心于政治民主的结论。
三、洛克对现代民主理论传统的影响
笔者认为,洛克虽然有一种比较明确的人民主权观念,并且主张了一种比较彻底的反抗权理论,但是他的同意学说主要在于阐明每个人对政府和法律的服从义务的来源而不是指向民主权利,他的代表观念中虚拟代表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而实际代表则凸显的是选区的选举权而不是个人的选举权,他的多数同意学说主要是一种信奉多数人应该拥有权力的抽象政治理论,而没有落实在政府组织形式的层面上,因此,不能说洛克提出了一种现代民主理论。那些错误地认为洛克有民主理论的人要么没有看清洛克同意学说的意图,要么忽视了虚拟代表和实际代表的概念区分,要么误把作为抽象权力理论的多数统治学说混同于政府形式学说。
但这绝不是说洛克与民主理论毫无瓜葛,洛克在现代民主思想传统中没有位置。我们还是从上述五个方面进行简要剖析。
第一,中世纪结束之前的人民主权观念都有浓厚的宗教背景,人民权力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上帝”的授予,而且人民是个集体主义概念,而不是个人主义意义上的集合体。到了霍布斯那里,“上帝”隐退了,个人主义概念下的人民成了权力的终极来源,但霍布斯的人民主权观念主要是为了绝对主义王权出场作铺垫,人民拥有主权是为了把主权永久性地让渡出去。只有到了洛克那里,人民主权观念才第一次同时具有世俗起源、个人主义基础和仅可有条件且有限度让渡的含义,几乎可以说具备了现代民主理论所要求的那种人民主权观念的基本面貌。
第二,洛克的社会契约论,特别是他关于任何政府都必须基于人民同意的学说,论证了国家作为人造物的合法性来源,挑战了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君权神授说,在形式上非常接近民主政体的理想,并为日后的民主政治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①沃林认为,洛克成功地把政府改造成为社会的代理人,这为后来的激进民主主义乃至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奠定了基础。参见沃林:《政治与构想:西方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创新》(扩充版),322-331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
第三,虽然我们强调洛克的代表观念中有虚拟代表和实际代表之分,但这种区分是隐含的;随着公民权的不断扩大和普及,随着个人选举权日益取代选区选举权成为关注的焦点,随着虚拟代表概念越来越不符合民主的通俗理解,人们更容易从洛克有关代表的论述中读出充满代议民主联想的实际代表的含义。
第四,洛克的多数统治学说在政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单纯数量的标准当做政治决策的原则。由于民主发展潮流的平等化趋势愈益强调民主就是“数人头”,由洛克所开创的多数统治学说尽管最初只是一种抽象的政治权力理论,但很快就落实到政府形式的层次,并且带着咄咄逼人的势头不断闯进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今天,多数统治原则在很大程度上被等同于民主本身。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关联,让我们今天一看到洛克关于多数原则的论述,就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他在阐释一种民主理论。
第五,洛克革命性地把反抗权赋予社会公众乃至每个公民,这不仅是他的人民主权观念的自然推论,而且越来越赋予革命以民主色彩。受洛克反抗权理论的影响,现代民主革命理论至少具有两方面重要含义:民主革命不仅仅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政府的革命,而且是由人民亲自 (而不仅仅是人民代表)发起并推动的革命。
[1][10][29][32][33][39][40] Willmoore Kendall.John Locke and the Doctrine of Majority-rule.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5.
[2] 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3] [26] C.B.Macpherson. The Political Theory ofPossessive Individu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4] James Tully.A Discourse on Property:J ohn Locke and His A dversar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5] Richard Ashcraft.Revolutionary Politics&Locke's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
[6][27] Richard Ashcraft.Locke's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London:Allen&Unwin,1987.
[7] B.Holden.The N ature of Democracy.New York:Harper&Row,1974.
[8] S.P.Lamprecht.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ofJohn Lock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18.
[9] Harold J.Laski.Political Thought in England:From Locke to Bentham.New York&London:Henry Holt and Company,1920.
[11][12][13][14][15][16][17][21][22][23][24][28][29][30][34][35][38] 洛克:《政府论两篇》,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18] 霍布斯:《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19] 邓恩编:《民主的历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20][31] E.M.Wood.“Locke Against Democracy:Consent,Representation and Suffrage in theTwo Treatises”.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vol.XIII,No.4,Winter 1992.
[25] 萨托利:《民主新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36][37] Julian H.Franklin.John Locke and the Theory of Sovereign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责任编辑 林 间)
John Locke and Modern Theory of Democracy
HUO Wei-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Beijing 100029)
Whether John Locke had self-consciously put forward a modern theory of democracy is a contentious issue in the western academic circle.Based on analysis on Locke's idea of popular sovereignty,doctrine of consent,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doctrine of majority-rule and theory of resistance,we cannot find solid textual evidences to support the claim that Locke had some sort of modern theory of democracy.But it is of no doubt that Locke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democratic theories.
Locke;democracy;consent;representation;majority-rule
霍伟岸:法学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北京100029)
* 本文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科研项目“自然法传统中的洛克”(7500010327)的成果之一。论文初稿曾在2010年8月天津师范大学承办的“庆祝中国政治学科恢复与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三十周年”思想史论坛上宣读。论文修改时参考了与会学者的评论和提出的问题,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