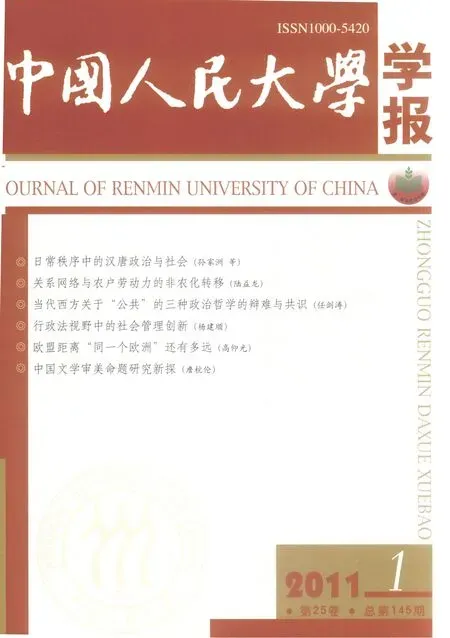从政治哲学视角看自然权利的力量*
王 利
从政治哲学视角看自然权利的力量*
王 利
作为近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自然权利具有能动性的建构力量。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自然权利的实现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主题,由不同的理论主体担纲。第一个阶段解决的主要是暴力问题,通过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等人的努力,将自然权利论证为抽象普遍性的法权。第二个阶段解决的主要是经济与社会问题,通过斯密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工作,自然权利转变为被启蒙的个体利益。第三个阶段解决的主要是平等和自由、同质与异质的矛盾,通过卢梭与康德的论证,自然权利转变为主体有尊严的自我立法。
自然权利;力量;抽象普遍的法权;被启蒙的个体利益;有尊严的立法主体
人们一般将自然权利学说看做近代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往往从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角度将其视为论证个体自由的学说,强调自由的被动或消极面相,多少忽视了自然权利本身所具有的能动性力量。与古希腊的自然正当与基督教世界的神义正当不同,自然权利不仅提供了崭新的正当性类型,还切实参与了公共秩序的建构。在近代政治哲人的笔下,自然权利学说很少软弱、消极和抱怨,而是充满了力量和激情,饱含着为新政治形态立法奠基的雄心抱负。有趣的是,自然权利学说大都有着新教背景,典型者如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等。他们有着直接的政治对手和理论对手,前者如西班牙天主教帝国体系和罗马教廷,后者如西班牙萨拉曼卡学派,包括维多利亚、苏亚雷兹、阿亚拉等人。①在思考近代西方思想史时,西班牙帝国及萨拉曼卡学派值得重视,由此才能彰显西欧新教诸国的现实目标。参见塔克:《战争与和平的权利》,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Philip Bobbitt. The Shield of Achilles:War,Peace,and the Course ofHistory.New York:Knopf,2002.
自然权利学说滥觞于16世纪,兴盛于17世纪,繁荣于18世纪,衰落于19世纪。从整体上来说,自然权利学说洋溢着乐观向上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具有鲜活的原发性力量。这与西方近代早期的历史使命密不可分,必须建立新的政治架构,以凝聚内部力量,应对外部战争。自然权利即是能动的建构性力量,自然权利学说在本质上即是新的权力哲学。它正确处理了力量与审慎之间的关系,找到了积聚力量的方式,为政治社会奠定了个体同意的普遍基础。它为如何从最为基本的单元——个体之上吸纳力量以建设新秩序提供了一套有效的制度设计,充分调动各种思想资源,为新制度提供了合理论证。这是一次具有高度共谋意识的行动,哲学家和政治家朝着同一方向齐头并进。结果是,自然权利以其自身作为正当性的标准和尺度,并以全新的创造性为近代政治提供了巨大的能量。
自然权利的能动性的建构能力体现为一个逐渐实现的过程,这也是自然权利不断自我确证、否定和扬弃的过程。依据逻辑次序与时间次序的统一,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主题,由不同的理论主体担纲。第一个阶段解决的主要是暴力问题,通过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等人的努力,将自然权利论证为抽象普遍性的法权。第二个阶段解决的主要是经济与社会问题,通过斯密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工作,自然权利转变为被启蒙的个体利益。第三个阶段解决的主要是平等和自由、同质与异质的矛盾,通过卢梭与康德的论证,自然权利转变为主体有尊严的自我立法。
一、自然权利:抽象普遍性的法权
依托于自然状态的自然权利拥有赤裸裸的力量,对于自我保存来说,先发制人是合理的。自然权利就是自然状态下战争的权利。最极端的是霍布斯的构想: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1](P131)洛克的自然状态貌似平和,却也有暗流涌动。他在《政府论》下篇曾两次坦言,要陈述一种“奇怪的学说”①“9.我并不怀疑这对于某些人似乎是一种很怪的学说”;“13.对于这一奇怪的学说——即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人都拥有执行自然法的权力——我相信总会有人提出反对”。参见洛克:《政府论》(下篇),6-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碰到盗贼将之杀死是合理的,因为盗贼要威胁人们的人身及财产权。斯宾诺莎更为直接,将自然权利直接等同于权力。他的例子是大鱼吃小鱼,大鱼的权利在于拥有更大的力量。[2](P10-11)因此,自然权利的出场是血淋淋的,它以自我保存为期许,却允诺人们能够为了这个不甚高明的目的不择手段。马基雅维利的逻辑被运用到自然状态中:人们能够为了一个正确的目的释放所有的能量,因为这个正确的目的遵从着自然必然性。实际上,自然权利是作为一种“内在化”的解放力量出场的。所谓“内在化”,是指经过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人,尤其是个体本身承载了价值意义。近代政治哲人极尽所能地将自然权利所具有的全部力量呈现出来,意在表明这是一个摆脱了古代和基督教传统束缚的新生事物,它是正当而强大的,必能创造新天地。但是,自然权利仅仅作为革命性的解放力量,无法营造一个和平安定的政治环境;它仅仅拥有锋利的杀伤能力,很有可能在共同生活中互相伤害,甚至自我摧毁。
霍布斯的工作就是以自然权利和主权国家为两端,构造具有绝对性的公共秩序。以共同的自我保存亦即和平为目的,自然权利要在同意的基础上限制肆意行动的自由,将“杀人”的意志、理性和力量委托给主权者。霍布斯认为,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同意在效果上是一致的。自然权利对于限制自身权力并委托于他者的同意就是公共秩序的合法性起点。为了强化国家主权在公共秩序中对个体权利的超越性,霍布斯以主权者不参与立约为由,特别论证了主权者逾越于法律体系之上,因为法律不过是主权者的意志。国家主权一定是超越自然权利的权威性存在,具有生杀予夺的惩罚性权力,而且这种权力就是主权者的权利。对比“自然权利”与“主权者的权利”两个概念,可以发现,二者具有相当程度的同构性。自然权利是缩小的主权者权利,主权者权利是扩大的自然权利。霍布斯的逻辑是,自然权利和国家主权都是权利,二者是直接相通的同质性存在。只是在政治社会中,自然权利必须被委托,由拟制的主权人格代表。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主权者只能是唯一的,与之同构的任何实体性存在对于主权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自然权利必须转化为臣民,而不能继续保存能够任意使用暴力的自然权利。因为自然权利的出场和存在就意味着自然状态,意味着冲突和战争。自然权利坚硬的暴力内核必须经受文明的洗礼。政治就是一场文明化行为。从自然状态向政治社会的转变,是对自然尤其是人的自然的降低,却是对作为驯化暴力的政治的肯定。自然权利必须经受实质转化,祛除暴力特征,摒弃战争权利,实现规训和服从,成为受到国家保护、获得法律承认的政治权利。
但是,霍布斯的转化工作完成得并不彻底。“保护与服从之间相互关系的理性原理”[3](P577)仅提供了驯化暴力的机制,仅设计了将自然权利的强大力量予以法律化的程序,但未能实现国家主权与自然权利在常态社会下的真正和解。这是因为,国家主权与公民权利的直接相关性比较脆弱,公民权利很容易受到国家主权的伤害和侵犯,二者的权力并不对等,公民相对于国家处于明显劣势。所以,还需要实现自然权利的宪政化,这是由洛克实现的。
自然权利的宪政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洛克遵循霍布斯的基本逻辑,着重改造其绝对性。但是他的靶子是以神学政治立基论证绝对性的费尔默,霍布斯反倒成为他克服费尔默的理论框架。①费尔默、霍布斯、洛克三者之间的思想关联是一个极为有趣的理论课题。参见纳坦·塔可夫:《为了自由:洛克的教育思想》,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政府论》上篇颇费心力地进行了神学政治批判,目的在于指出用《圣经》来论证君主权利的绝对性是不可靠的。打掉绝对权力的神圣起源,旨在为自然权利的出场提供世俗化的背景。霍布斯在保命意义上提出的自然权利过于血腥暴戾,洛克将其转化为财产权。相比于保命,财产权有三个特点:第一,保命是由危机状态产生的,财产权则能兼顾战争与和平状态,尤其适应于和平状态。保命的背景是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状态,财产权的背景则是两种自然状态,一种是常态的自然状态,较为温和平静,但也潜藏杀机;另一种则是战争状态,这是常态的激进化。第二,保命需直接诉诸武力,自然权利等同于先发制人的战争权利;财产权则诉诸人类劳动,系由劳动施诸自然所创造的价值。在洛克看来,征服性战争不属于劳动。第三,保命意义的自然权利在公民社会中转化为公民的服从与自由,二者集于一身,不可分离;财产权意义的自然权利在公民社会中转化为公民的财产权与反抗权,前者受政府保护,系公民服从;后者是以财产权自身为标准衡量政府行为,系公民不服从。
洛克的论述重点在于公民社会中政府与财产权的关系问题,他是以重新构造的自然状态和作为财产权的自然权利为基础的。洛克从两个方面着手将自然权利宪政化。一方面,公民在政治社会中拥有反抗权,这是当政府威胁到个体财产权时的“义举”。反抗权就是革命权,反抗权的成功实施意味着政府的解体。洛克强调,政府解体与社会解体并不是一回事。洛克采用将源于自然权利的反抗权上升为合法权利即公法宪政的方式,使财产权拥有高于政府的权利,为政府必须适当进行自我约束和节制设计了制度底线。另一方面,洛克提出了政府分权制衡的体制,即立法权、执行权与对外权的区分。实质在于立法权与执行权二权之间的区分,因为对外权从性质上属执行权。立法权就是常态状态下的主权,即对法律的制定;执行权是受立法权委托对法律的执行。与将反抗权上升到公法宪政层面相仿,洛克为执行权开辟了“特权”之路,即在特殊情况下拥有生杀予夺的“特权”。事实上,特权就是危机情况下对主权的运用。根源于财产权的反抗权的存在,使主权在常态下要保持自我警醒、约束和限制,以免侵犯财产权;根源于立法权的特权的存在,使主权在非常状态下能够临机决断,避免政府的解体。自然权利的宪政化与主权的宪政化是同一过程,目的也相同,都是为了调节国家主权与公民权利的直接对立,通过制度设计更有效地实现政治权力,保障个体权利,使主权之力与权利之力都能够节制审慎。
洛克致力于自然权利的宪政化,旨在改变公民个体在面对国家主权时的弱势地位。既要坚持霍布斯的逻辑,又要改造霍布斯的暴戾,这是宪政化的双重任务。斯宾诺莎则更为冷酷。他祛除了自然权利诉诸保命和财产权时关系到人的身体的种种遗迹,强调在现代社会中如何保存内在自由,认为这才是自然权利最为重要的使命。内在自由指的是良知、信仰和思想言论自由,关涉人的灵魂。与霍布斯着眼于以人为的超越论再造秩序以终结内在论、洛克以宪政论提供一套有关自然权利的审慎化方案不同,斯宾诺莎一以贯之地使用了内在论,试图通过为外在权利与内在自由划界来保证内在自由的实现。
内在论奉行的是否定性逻辑,实现的是不断革命。霍布斯等人找到了自然权利这个实体,试图终结内在论,并在个体之上重建秩序。斯宾诺莎的内在论以理性为主导,试图追求圆满的真理。对他来说,理性就是力量。为了保证真正的理论探究不受侵扰,斯宾诺莎借助于近代的自然权利学说,将其打造成一个徒具力量的形式化概念。自然权利等同于也仅仅等同于力量,仅是谋求共同生活、建立公共秩序的基础与开端,并不包含更多含义。在自然权利基础上建立的政体是以形式理性搭建的共同生活的平台,仅仅对人们的外在行为构成约束,而无法触及人们的内心。人们的外在行为要遵从国家法律,内心却可以另行一套。权利有外在内在之分,这是斯宾诺莎的创造。人们当然可以说,他苦心孤诣是为了在现代保存古代,在启蒙时代保持犹太性。但无论如何,斯宾诺莎以区分内在外在的方式撕开了利维坦的一道口子,开启了以内在之名反抗外在的行动,其精神气质是秉承典型的内在论,因为内在论旨在以否定性的逻辑实现不断革命。
斯宾诺莎崇尚自由与民主的合体,原因在于民主政体更能坚守内在外在的界限,能够更好地保护内在自由。这并非有意向现代政治献媚,他的政治偏好与政体形式无关,其核心关注在于要牢牢守住外在权利与内在自由之间的界限,《神学政治论》第十九卷暴露了他的真实意图。[4](P260-261)斯宾诺莎对于内在外在的区分会造成三个后果。首先,外在权利的形式化。虽然斯宾诺莎将马基雅维利的精神实质融入了霍布斯的理论框架,但他并不关心政体形式,而是更为关注现代政治是否具有理性基础。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建立在启示信仰亦即激情或意志之上的神权政体,斯宾诺莎以深挖神权政体根源的方式将其理论基础归于激情。在神学政治批判基础上建立的现代政体则试图以哲学即理性为基础。但是,斯宾诺莎清楚,现代政治需要的理性在于对大众的启蒙,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他诉诸形式化的理性,这就是将自然权利等同于力量的理由。以理驱利,所得者仅是力而已。其次,公共权力的中立化。在斯宾诺莎手中,自然权利转化为仅具形式理性的力量,由此建立的公共权力体现为绝对性的增加,亦即统治力量与被统治力量的相对权重。民主政体是人民自己统治自己,具有最高的绝对性。这种绝对性并非霍布斯意义上国家对于公民的超越性,而是统治者的实际力量。究其实质,斯宾诺莎的绝对性所描绘的是公共权力的中立化。公共权力对于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不因文化信仰和身份差异而有所不同,“绝对”能不偏不倚,一视同仁。权力的中立化是自然权利形式化的必然结果,斯宾诺莎就是要将政体的精神内核转化为形式理性,保持一个仅靠中立力量搭建和维系的外在政治框架。最后,在政治上,外在权力保护内在自由;在价值上,内在自由高于外在权利。斯宾诺莎在外在与内在之间划出界线的用意在于限制外在权力,这种限制与其说是制度设计,毋宁说是理论规定,他的《伦理学》是一整套具有几何学外观的规范化理论体系。一方面,将自然权利外在化,祛除价值,等价于单纯的力量,在此基础上建立公共生活;另一方面,将内在自由凌驾于外在权利之上,内在自由是目的,外在权利是手段。斯宾诺莎的信心在于内在自由旨在追求理性的圆满而更有力量,结果却提供了内在自由对外在权利的优越乃至否定,二者之间的矛盾要等到卢梭的共和思路予以解决。
总之,通过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的努力,自然权利在第一阶段成功转型,奠定了建构公共秩序的基础,祛除了暴力特征,成为公民社会的法权。这种法权是抽象的,从自然状态中以身体为依托的保命到通过劳动创造价值的财产权,再到内在自由,自然权利变成了一种抽象的权利,被外在化、形式化、中立化。同时,这种法权是普遍的,权利之自然不仅由于具有共同的人为标准,还因为权利可以诉诸每一个人,生死、劳动价值、内在外在都足以适用于各种人群,自然权利变成了普遍的权利,成为文明社会的标志。自然权利转化为抽象普遍的法权,成为抽象国家的基础。
二、自然权利:被启蒙的个体利益
自然权利在第一阶段的任务是进行国家政权建设,解决宗教与政治问题;在第二阶段的任务则是进行社会建设,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自然权利转化为抽象普遍的法权,暴力得以规训,政治得以法律化,但自然权利本身所蕴涵的能量并未消逝,而是转化到了经济与社会领域,致力于营建文明社会。作为权力哲学的自然权利学说披上了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的外衣,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辩护,为资本雇佣劳动提供了说明,为作为独立领域的社会提供了论证。伴随着资产阶级的壮大和社会关系的调整,一个能够与国家相抗衡的公共领域出现,个体利益在市场交换中可以像魔法一般产生公共利益,通过“需要的体系”能够实现社会整合,自然权利在经受商业社会洗礼后变成经济和社会权利。
第二阶段的理论源头可以上溯到洛克。洛克的理论贡献不在于对霍布斯的修修补补,而在于用财产权概念为自然权利找到了现实化的途径。洛克的财产权包括人身、财产及自由,通称为财产权。他为财产权赋予了三个崭新的特点。第一,将财产权从神学体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摒除了宗教的道德约束,使之成为人类本身的创造。在《政府论》上篇中,财产权甚至成为衡量亚当的后代是否拥有统治权的标准之一,直接参与了神学政治批判。[5](P62-68)不仅如此,在《政府论》下篇中,财产权被论证为道德上的善,成为政府的目的和立法的依据。第二,财产权源于人的劳动,由人类劳动施加于自然界,创造价值。人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构成财产权的内核。它有两种典型载体——土地与货币。洛克所关注的并非营利的商业活动,而是人类劳动创造价值本身,这是人类行动的自由的集中体现。在本质上,财产权的核心在于人类对价值的创造,这种创造就是自由,可以延续、反复、运动、增长。第三,财产权在所有权和使用权上能够分离。在自然状态中,二者是合一的。进入政治社会,公民将保护财产权的权利交付政府,由政府提供保护;但公民仍持有反抗权,反抗权的根源就是对财产权的拥有。政府保护财产权的力量就是对于财产权的使用的集中,而反抗权则证明公民个体仍是财产权的所有者。源自财产权的反抗权能够建构宪政,在根本上高于政府,属宪政主权层面。对于财产权的使用则一方面给予政府,使其拥有保护之力;另一方面仍为公民持有,以进行经济和社会活动。
洛克的财产权学说在将自然权利成功政治化以创设宪政政府的同时,也开辟了经济化与社会化的道路。商业社会的塑造及一系列规则的形成为自然权利政治化后的剩余能量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搭建了政治秩序的法权框架后,自然权利改头换面,以产权和社会权利的名义,投入文明社会的建设。亚当·斯密的理论对这一转化进行了卓越的论证。
第二阶段的核心即是亚当·斯密。他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感论》涉及经济与社会建设的基本问题,所以往往被人们视为论证商业社会合理性的作品。但回溯近代西方思想史的大传统,这两部作品却是其宏大的正义论体系构想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斯密是在17世纪政治哲学家以自然权利为起点打造的近代政治正当性基础上工作的。所不同的是,斯密将自然权利的政治化亦即政治秩序的建构当成了理论前提,他不必关心自我保存的暴戾,也无需为政治找到一个具有经济社会意义的基础,而是直接从经济社会命题入手,探讨“自然秩序”的构成。
18世纪经济社会诸命题中最核心的一个是:财富从何而来。重商主义与重农学派有不同的看法:重商主义认为财富来自对外贸易,重农学派认为来自土地上的农业劳作。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认为财富来自于生产而非流通领域;他也批判了重农学派,认为不仅土地,所有生产性领域都能产生财富,重要的是要通过劳动创造价值。斯密的样板是英国兴起的制针业。他以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为起点,勾勒了以财富增长为主线的自然秩序的生成过程。斯密的论述有三个要点:
第一,追求多余的财富是合理的。在古代与基督教传统中,经济属于家政的范畴,亦即满足自然需要的自然必然性。亚里士多德、阿奎那都反对超出自然需要牟取利润的商业行为,认为它既不自然也非神圣。近世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对财富来源的探究就在不断地突破根据自然必然性讨论财富的做法,因为自然必然性意味着财富是匮乏或短缺的,他们的意图在于确定财富增长的合理性。这既体现了现代国家在垄断暴力之后对财政税收的进一步需要,也表明自然权利原则在经济社会领域的普及。财富的增长意味着要超出自然必然性的限度,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体,追求扩大再生产获得“利润”成为一个可以不断复制的正当性目标。
第二,财富增长可以诉诸自然秩序。自然秩序就是市场机制。它的基础是每一个人的个体利益,或者说每个人的利己主义。斯密用生产领域的专业化分工作为论证的开端,分工基础上对剩余产品的交换则使个体利益获得实现。为了实现个体利益而开展的竞争最终竟然可以促进公共利益,这就是市场的奇妙作用,斯密称之为“看不见的手”:“由于他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它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6](P27)
自然秩序中的自然并不意味着事物的本质或本源,而是特指从追求个体利益出发最终促进公共利益这一过程是“自生自发的”,超脱于人们的控制和创造,有如神助,近于神迹。与其说自然秩序旨在论证市场机制的巧妙逻辑,不如说试图强调人们对个体利益的追求就其自生自发而言是正确的,这就需要对自然秩序的起点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自然秩序的起点在于“道德情感”,而不是谋利行为。
第三,个体利益是需要启蒙的。斯密为个体利益设计了不同的面相。对于单纯的经济活动来说,个体利益面临的就是一系列经济关系,所遵从的仅是自然秩序的规则,无需利润之外的动力。但是,对于社会领域来说,在个体利益的利己之心之外必须加上同情,这是营造道德情感的基石。同情预示着利他,即使就程度而言较为单薄。同情的目标是合宜,是对于单纯自利的约束,可类比于柏拉图的“意气”(thymos)概念。由自利导致公益,这是自然秩序;由同情产生道德,这是社会秩序。斯密要在转化了的自然权利基础之上构造新的经济与社会领域。《国富论》探讨了经济领域的自然秩序,《道德情感论》则论述了社会秩序的道德原则。
与斯密同时代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其他代表人物同样致力于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建构。以市场机制为内核,文明社会 (civil society)逐渐成形。苏格兰启蒙运动构筑的文明社会与17世纪政治哲人以自然状态为背景设想的政治社会(civil society)大不相同。名虽同,实已变。政治社会的“文明”之处在于驯化暴力,将自然权利政治化。文明社会的“文明”之处在于谋求发展,将自然权利经济社会化。文明社会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它是一个需要的体系。为了满足需要,文明社会要不断地创造财富,保持增长。同时,为了满足需要,还要不断地制造需要。需要成为一场无止境的运动。其二,它培育了社会生活所需要的道德、礼仪、风尚、习俗,孕育了懂礼貌、讲规矩的文明个体,特别是孕育了中产阶级。其三,它成为独立于国家的公共领域,具有自身的独特逻辑,遵从着在质上不同于国家和政府的合理性。而且,社会的分化进一步对政府的形式化、中立化提出了要求。
人们往往把休谟的质疑当成自然权利学说的衰落,其实不然,自然权利自身的转化和重构才是历史进程的内在动力。休谟只是以极端的怀疑论对经验论的归纳基础提出了疑问,认为理性遵循的因果关系或许只是因果性联想。功利主义与康德分别是对休谟质疑的两种回应,也是自然权利的两种替代形式。功利主义诉诸“功效”概念,以“相关事件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标准,强调利益算计之后的结果。[7]康德则诉诸先验图式,旨在论证能为自然立法的主体。前者倾向于社会领域,后者倾向于形而上领域,分别提供了一套普遍性学说。第二阶段还可以延伸到德国的国民经济学体系和社会理论,李斯特、马克思、韦伯、齐美尔、特罗尔奇等人仍在为探询文明社会的内在规律和动力而努力,只不过他们统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自然权利营建文明社会的力量在资本主义对世界市场的席卷中转化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转化为资本家与无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如何应对阶级分化和商业社会带来的不平等,如何解决平等与自由之间的冲突,但仍坚持自然权利,是卢梭与法国大革命的任务。
三、自然权利:有尊严的立法主体
卢梭看到了自然权利法权化与经济社会化之后的问题,他着手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公意,或普遍意志。基于被启蒙的个体利益之上如何达成公意,克服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在本质上的不睦,是《社会契约论》的重点。公意遵循近代自然权利学说的基本逻辑,以自然状态与政治社会的二分作为起始点,但卢梭诉诸“社会”契约,放弃了统治契约的暴戾之气。卢梭的社会契约将人们之间相互立约转变成个体自身的要求与行动。他延续了霍布斯论证自然权利与利维坦的同构性,只不过将同构性的基础替换成“意志”。个体意志通过社会契约实现公意的方式不再是签订外在的契约,而是自我立法。每一个人运用意志,自己为自己立法,“仿佛”每个人自己遵循的规则就是共同体的法律。“仿佛”是其中的关键,旨在将外在性的他律变成内在性的自律。公意就是人民主权。人民主权的核心是要建构一个统一的整体,它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方式就是通过“仿佛”的转变,使公意直接同质性地落实于每一个人的自我立法。这就将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统治转化成人们对自己的统治,将人们对一个由签订契约成立的政府的服从变成了自我服从。统治与服从之间的外在张力被解除了,个体成为能够自主运用意志进行立法的主体,这就是公民。
在卢梭看来,公意对公民的要求非常严格,这是因为公意常常受到众意的侵扰,公民必须与市民倾向作斗争。公意是普遍意志,众意是特殊意志。个体因为占有欲、虚荣心或其他激情的支配,会形成特殊意志。特殊意志描述了人性中“利己求私”的一面,这与财产及占有有关,不只是公民社会的状况,可以一直追溯到自然状态。特殊意志的典型存在领域是社会领域,是作为市民存在的个体结成的社会关系,但其形成可以一直追溯到自然状态,这也是社会不平等的起源。公意是对于特殊意志的克服,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公意在数量上的优势,而在于质量上的纯粹性。卢梭认为,真正统一性的构成一定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意志”。这就需要摒弃私利,消除外在与内在之间的界限,将不同的意志凝聚为一个整体,形成国族 (Nation)。
公意的产生系出于自然人的自我立法,这亦是自然人向公民的转变。卢梭认为,自我立法是自由的体现。卢梭的自由是“摆脱束缚”的自由与“积极行动”的自由的新的合题。17世纪自然权利学说的逻辑是将自然权利作为内在性的终结,在此基础上建构人为的超越性:国家主权。斯宾诺莎试图在内在自由与外在权利之间划定界限,以更好地保护内在性,但是,又不得不把自然权利形式化,内在外在的对峙仍难以消除。卢梭要使自然权利脱胎换骨,从抽象普遍的法权与被启蒙的个体利益发展成为自我立法的主体。他的自由概念有三个显著特点。首先,自由就是自主。无论是抽象普遍的法权还是被启蒙的个体利益,都有赖于转化,尤其是外力的转化,在卢梭看来,其中必定包含着强力和欺诈,这是自然权利仍受奴役的体现。外在与内在的区分表面上看是要确保内在自由的价值,实质却是对公民进行的人为撕裂。摆脱自然目的与神圣权利的束缚构成了自由的前提,但自由的精粹并不在于由此拥有了“积极行动”的全部可能性,而在于能够在摆脱束缚的权利基础上主动为自身设定规则义务:服从自我立法才能体现自由的层次和境界,也是人兽之分的根本。其次,自由是平等的自由。卢梭有名言曰:“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之中。”[8](P8)他将自由与枷锁相对立,强调不平等对于人性的败坏。《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就描述了由自然向文明的败坏过程。卢梭并不认为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社会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喜事,早在自然状态中,就发生了由于占有欲和财产权等不平等关系的引入对自然平等和自然自由的败坏。文明社会是对各种不平等的固化,而公意则是对于平等的自由的实现。恰恰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立法主体,每一个人遵从的法律与自我立法的结果相同,所以才能克服由于自然的败坏而导致的不平等的加剧。最后,自由即德性。由自然义务向自然权利的转折是近代政治正当性的实质变化,近代哲人都对体现自然义务的德性学说进行了改造。马基雅维利将德性改造为政治德性,霍布斯和洛克将德性改造为社会德性,德性成为自然权利得以实现的工具。卢梭认为,自由体现了在扫除一切障碍后人的自我约束,这是崇高的尊严。自由在个体内在层面实现了超越性,自由体现了巨大的力量,其本身就是德性,无需他求。
尽管卢梭认识到社会契约的脆弱,设计了立法者、公民宗教等措施予以补救,但他对自由的纯化和提升仍然显示出强大的信心。自然权利摒弃了保命意义的暴戾和个体利益意义的谋私,虽然仍立足于个体,但个体能够掌握和运用自由的力量,将自身建构成为能够自我立法的主体。通过自由,摆脱奴役;通过自由,成为主体;通过自由,实现德性。自然权利作为内在革命的终结点,在将个体转化为主体的过程中,以内在性为基础重构了超越性,而且并非诉诸外力,仅仅是依靠个体自身的力量。卢梭相信,个体完全能够拥有这种力量,因为就人之本性来说,人是会趋向于自然的目的。卢梭的信念源于他对人性看法的转变,即在自然权利降低人性的基础上为人性重置一个目标。他把古代传统中的“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y)概念重新引入,试图以此化解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对立。正如后世许多评论家共同批评的,卢梭试图以回复古典的方式解决现代性危机的做法只会进一步加剧现代性危机。①最典型的论述,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言:“感受到现代的历险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并返回古典思想中去寻求解救之道的,卢梭并非第一人。我们只需再提及斯威夫特的名字就够了。然而卢梭并非一个‘反动派’。他使自己沉浸于现代性中。有人禁不住要说,唯有这样接受了现代人的命运,他才能够返回到古代。无论如何,他之返回古代同时又是现代性的一个推进……他以古典的古代、同时又是以一种更加先进的现代性的名义,对现代性所作的激情洋溢而强劲有力的攻击,被尼采以毫不逊色的激情和力量再来了一次,尼采由此就预言了现代性的第二次危机:我们时代的危机。”参见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257-25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卢梭的理论与法国大革命的实践给予德国哲人以巨大的震撼。康德继承了卢梭自我立法的思路,用先验图式为主体奠定了普遍有效性的根基,使之具有“人为自然立法”的能力。卢梭沉浸于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对立,康德则在自然与自由之间展开论述,二元论范式一脉相承。康德的批判哲学意图论证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主体,以及沟通两种理性的判断力的主体。主体以普遍有效性为前提,以“人是目的”为绝对律令,以批判理性为限度,使自由凌驾于自然之上,自由同时拥有了统摄自然的能力。康德的自由主体将自然权利发展成为“人的权利”,人权堂而皇之地拥有了自主地位,不再需要诉诸“自然”的理由。如果说卢梭仍在自然权利的范畴内改造自然权利,比如说他仍将自然权利的根基界定为自我保存的欲望,同情对自爱的协调不足以保证自然人的占有欲和权力欲;比如说他仍认为理性的力量弱于意志,由个体利益转化为公共利益需要由个体意志向公意的集中,那么,康德则义正词严地为理性正名,在批判哲学的名义下为合理性上升到理性提供了严格的先验式证明,同时又高举绝对律令的旗帜为人们在道德上的自我服从确立了普遍有效的准则。因此,康德的理性批判并不是有关理性有限性的学说,而是有关理性能力与道德能力的学说,这些能力都要诉诸被重新塑造出来的能动性主体,这个主体具有运用理性的“先验”资格,这个主体在进行理论和实践的理性创造中获得“自由”的尊严。由卢梭的意志主体到康德的伦理主体,由卢梭的立法主体到康德的自由主体,由卢梭在自然与文明间的游离到康德以自由为内核对自然的先验优越,这无异于一场有关权利学说的“哥白尼式革命”。
从卢梭到康德,旨在高扬人的尊严的主体权利学说既是对自然权利学说的实质性改造,也是根本性扬弃。主权权利彰显的是主体的自由,是体现主体尊严的自由,是优先于自然并为自然赋予形式的自由。在某种意义上,主体权利亦是自然与权利之间斗争关系的解决:权利对自然的反动终于达致自我立法的程度。近代自然权利学说为权利找到的自然理由无法满足权利日益增长的自我确证的需要,机械自然观在抽空自然目的的同时,也将人性欲望化。欲望意义上的自然固然获得了解放与革命的力量,但亦将人之为人的意义降低,甚至打开了将人引向兽的通道,暴政在自然必然性的旗号下惶惶然登场,政治秩序也必须依靠外在强力建立。主体权利为个体重新拾回了自信,强调人类自由就是人的自我立法,这种能力是天然地属于人的。卢梭认为这是由文明向自然的回归,康德则认为这就是人类自由本身的卓越。自由不再仅仅是摆脱束缚和积极行动的合题,而是通过自我立法确定尊严的道德能力。尊严最集中地体现在摆脱了各种束缚之后能够自愿选择自我立法而不是虚无。尽管仍是自愿选择的结果,自由因为选择了重新服从某种义务的方式而值得尊敬:对于卢梭是公意,对于康德则是绝对律令。此时的义务及对义务的服从成为权利的派生物与对应物。先有权利后有义务,先有自由选择义务的权利再有服从义务的高尚。权利的论证不再需要诉诸自然,仅需诉诸人类自身:对义务的自由选择证明自由的尊严,主体完全有能力做到自律。
在第三阶段,自然权利通过自我立法的自由展示了人之为人所具备的尊严,意在使每一个人都成为主人,而非奴隶;成为目的,而非手段。自然权利能动性的建构能力在有尊严的立法主体中得到完全的实现,它不仅是公共秩序的来源和根据,也成为权利主体本身自我确证的价值标准。虽仍有二元论的嫌疑以及产生虚无主义的危险,但自然权利成功转变为作为价值的自由。个体成为主体,内在与外在相统一,自由为自然立法,权利获得尊严。
四、结语:自然权利的意义
在古今之变的大格局中,自然权利为近代政治提供了全新的正当性,集开端、价值、力量于一身,显示出巨大的能动性力量。
自然权利是新的开端。近代哲人为政治秩序奠定了一个较低但较为巩固的基础,这个基础与古代及基督教传统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自然正当的实质是理性占据统治地位,神义正当的实质是启示占据统治地位,二者皆为高调理想的虚幻想象,将人类事务的根据诉诸人类事务之外,缺乏务实精神。自然权利的现实性在于,要将政治真正奠基在人类本身所具有的能力上。因此,不但拒绝自然目的的指引,也否定上帝之城对于地上之城的优越性,而是坚信“正确理解的人性”就是公共秩序的开端。开端是对目的领域和神圣之物的排斥,是对人性本身尤其是自然激情与自然理性的肯定。开端意味着“基础”,这个基础是属人的。开端意味着“起点”,这个起点乃为人力所及。开端在将自然等同于必然性的同时,解放了人性,提供了自然状态,也同时找到了价值和力量。开端蕴涵着原则,自然权利既是政治与道德事务的开端,又为政治与道德事务确定原则。
自然权利是新的价值。这种价值由保命、财产权和自由始,在法国大革命中被引申为“自由、平等、博爱”,在罗尔斯的理论中被鲜明地表述为“权利优先于善”。平等的自由与经过理性选择的自主是论证自然权利之所以成为价值的两个显著论据,而在背后支撑的则是一种源初意义的“正义感”。这种正义感蕴藏于人性之中,属自然激情的内涵,却是为理性所辩护的正确而合理的激情,在近代早期通称为“自我保存的欲望”,在霍布斯的理论中最为典型。而霍布斯又是接纳了马基雅维利的前提,将自然等同于必然性,将僭政 (tyranny)等同于自由创造。因此,权利的价值本质上就是自我保存的价值,就是为了自我保存而自由创造的价值,也就是用僭政的方式来克服自然必然性的价值。这就意味着,自然权利在开启了合法的政治秩序的同时,也为各种形式的反抗甚至革命提供了理由:在理论上权利政治可以无限递推到各种原本不是权利的事物。如果权利就是正确的标准,那么权利可以诉诸人性,也可以诉诸非人性。①福柯等后现代作家即将权利与人性相对立,深挖人道主义的权力根源和现实机制,他们的论题就变成“人之死”。
自然权利是新的力量。它将原本受到自然目的和神圣权利桎梏的力量释放出来,以积极行动的人类自由创造性地建构秩序,拥有巨大的活力和能量。在建构公共秩序的过程中,自然权利得以转换为抽象普遍的法权、受启蒙的个体利益以及有尊严的立法主体,这也是自然权利本身经受驯化的过程。自然权利的力量就是自由的力量。自由不仅是消极地摆脱束缚,还能积极主动地行动,尤其是通过自我立法确立主体地位,体现人之为人的高贵尊严。自由体现了强大的建构能力,在向平等的自由的扩展中,演化成人民主权意义上的民主。民主是自由的普遍化,本质上旨在追求平等权利,由特定的人或特定阶层的自由推演到人民全体。法国大革命的实践及其理论表述如卢梭与康德的思想证明,以平等的自由为基础的共同体是作为主人的公民之间的联合,现代共和的前提是人人都能做主、人人都要负责。平等的自由成为人民统一性的基础,这是一项极具想象力的创造性思想。
总的来说,自然权利构成普遍性文明的内核。西方文明的普遍性曾与征服捆绑在一起,但都遭遇到了“命运”的阻碍。亚历山大的征服夭折于他的暴亡,其实说明了古希腊城邦政治本身的局限性;罗马的征服依靠于武力,却难以在言统上建立严整叙述,反倒在征服基督教的过程中被反向征服。只有在近代,西方文明奠基于自然权利之上,才与殖民贸易和海洋自由一起,打造了一种以平等的自由为内核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文明以普世著称,至今仍为非西方社会艳羡不已。
[1][3] 霍布斯:《利维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 斯宾诺莎:《政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5] 洛克:《政府论》(上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6] 亚当·斯密:《国富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7] 李强:《自由主义》,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8] 卢梭:《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责任编辑 林 间)
The Strength of Natural Right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WAN G Li
(School of Government,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Natural right,as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legitimacy,has active,constitutive strength.I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the realization of natural right has experienced three periods;each has its distinctive theme and bears its different theoretical subject.The first period mainly focuses on resolving the problem of violence:through the efforts of Hobbes,Locke,and Spinoza,natural right is justified as the right of abstract universality.The second period,rather,takes up socio-economic problems:with the work of Smith and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natural right is transformed into self-interest of the enlightened individual.The third and the last period tries to solve the tension between equality and freedom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homogeneity and heterogeneity:according to the arguments of Rousseau and Kant,natural right is transformed into the subject's self-legislation with dignity.
natural right;strength;right of abstract universality;self-interest of the enlightened individual;self-legislating subject with dignity
王利: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北京100871)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中西思想史中的政治正当性研究”(项目编号06JJD770011)的研究成果之一。感谢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刘晗博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康子兴博士、张笑宇硕士与笔者的讨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新刚博士协助校对注释,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