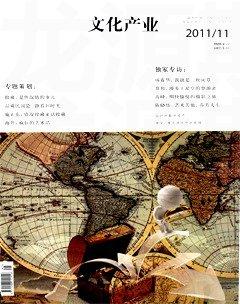育邦:漫步于星空的悠游者
梁雪波
“读书就是游荡。”育邦在介绍法国作家帕斯卡·基尼亚尔的小说时如此说道。对于育邦来说,阅读就像林中漫步,有一种“不寻求达到目的的等待”,在漫无目的的碎步中充满了探秘的冲动、未知的发现、相遇的喜悦,充满无限的可能性。
作为一个痴迷于阅读的“悠游卒”,育邦对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有着深入的考察与理解,加缪、贝克特、佩索阿、巴别尔……他沉溺其间,感受、思考、呼吸,书籍成为他进行自我观照的隐秘的镜像。从这个角度说,育邦是一个有着多重灵魂的人。
作为一位年轻的作家,育邦在诗和小说之间游走多年,他的小说写作“致力于中国小说的革新,致力于对阅读经验和生活经验的双重超越”。在最近完成的“虚构之诗”中,他通过对经典文本的模拟、仿写、戏谑性的混淆。表达自己对诗歌与世界的感受,以图达到以假乱真的写作“预谋”。
与育邦交谈,让人不由地产生“重新做一个读者”的冲动。他说自己喜欢那种无所事事的阅读时光,他认为文学在当代的功用之一,就是“能让我们意识到自身的匮乏,还有生活中那些已经削弱我们并正在让我们气喘吁吁的东西”。
《徒步者随录》的作者、文体考究的散文家钟鸣曾经有过这样的自我评价:“太少的人生经历和太多的幻想”。这句话用在70年代出生的人身上似乎更加契合。毕竟,50年代出生的钟鸣还当过兵、做过知青,经历过文革、
80年代的文化热潮等等。而对于“70后”,比如育邦来说,生活的轨道仿佛早早地就铺设好了,他不再是“迷惘的一代”,也不属于“垮掉的一代”,在政治喧嚣退潮后的转型社会,他与时代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在物质世界与内心真实之间游移往返。
1976年,育邦出生于位于苏北的灌云县,父亲在乡政府工作,一家人就居住在乡政府院子里,这里还有一座不大不小的文化站。小时候的育邦性格文静、内向、不爱说话,勤劳能干的母亲对他一直宠爱有加,家庭氛围和谐安宁,父母对他也没有严苛的管束。育邦还记得,当年乡文化站里有一个图书馆,因为都是熟人,他经常去玩,图书馆其实并不大,藏书也十分有限,但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那小小的屋子和花花绿绿的图书就包孕着整个世界,神秘而无穷。
“从小我就对未知的事物充满渴望,并且保持浓烈的兴趣。”育邦认为这种对知识异乎寻常的热情,是一种延续至今的惯性。让他记忆深刻的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万花筒,“这是我一生中最感兴趣的玩具。”他常常把它带在身边,甚至在上学的路上也要玩一玩,弄一弄。“我那好奇的眼睛一睹到万花筒的筒口时就会睁得更大,我的瞳孔一定也倒影出缤纷绚丽的色彩。那一刻,我——一个胆小的孩子,惊讶远远地超出了羞涩。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世界啊l我曾见到和未曾见到、我能想象的和不可想象的色彩旋转着,悸动着,跳跃着……一个立体的迷幻世界……”童年的乡村生活对育邦来说,是短暂的易逝的,犹如万花筒中的碎片。
三年级时,育邦就转到镇上的小学读书了。回望小学生活,他印象最深的是朱老师。朱老师博学优雅,为人刚正不阿。教他时已经快五十岁了,还只是个代课教师。“他依稀有一些白头发,整个头发都是根根直竖,很能让人想起鲁迅先生。”育邦喜欢上他的语文课,至今还能历历记得他讲的纪晓岚,徐文长的故事,那些充满智慧的古代文士给育邦以无限的憧憬,“他讲了很多古代文人墨客的故事,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一颗种子。今天说来,这颗种子就是对于文学和语言的尊敬,对于纯粹知识分子的尊敬和向往。”朱老师还写得一手好字,他常常用“温暖而宽大的手掌”握着育邦的小手,辅导他练习书法。对朱老师,育邦至今仍持有一份尊崇和感激之情,他说:“朱先生是那个贫乏时代里的乡村知识分子,贫困却清静。他的影响在贫瘠的乡村里代表着一种无形的道德力量。在我的生命维度里,他占据着与陶渊明,孟浩然,徐文长等这些古代杰出知识分子一样重要的位置,并且他的坐标确定着其他人的坐标。”
关于小学的读书生活,很多年之后,育邦在他的小说《身份证》里,有过一段“煽情”的描述——“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了,你那时就学会了早起,早晨五点半就起床了,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起床后锻炼身体,活动活动筋骨跑跑步,更主要的是读书。先是背诵语文课文,你能背下当时课本上所有的课文,你现在还能记得那些熟悉的课文的名字,《爬山虎的脚》、《故乡的杨梅》、《游击队之歌》,《神笔马良》,《凡卡》,《小抄写员》,《踢鬼的故事》,《最后一课》……多么动听悦耳的名字啊,就像山涧的甘泉滋润了一个因急速赶路而干涸疲惫的人。你甚至想再找来你当时读的小学语文课本,一个字一个字一幅插图一幅插图从头到尾慢慢地阅读品味,仿佛一个老酒鬼碰到五粮液或茅台,他不敢大口地喝,只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饮,留下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回味,品评。……”
小时候的育邦,懂事,乖巧,学习上基本不需要父母操心,因此也颇得老师的喜爱。他喜欢读课外书,这对他的作文产生着,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他记得,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写过一篇作文,这篇作文他没有按照通常的要求(记叙文要真人真事)来写,而用了一种虚构的方式,甚至还用了“象征主义”的手法,其中写到了“花”和“伞”这两个意象,寓意老师和同学的关系,写得很美。老师为此表扬了他,并用毛笔把这篇“美文”抄下来,贴在黑板上,当作范文。育邦说,其实当时自己也不懂什么意象啊象征啊,可能是课外书读得多,自然而然模仿出来的。后来上初中、上高中,他也写过许多所谓的优秀作文,但都没有留下印象,唯独这篇作文让他难以忘记。
在镇子上读完初中,然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县中,父亲工作调动伴随着母亲焦灼的呵护之心,于是一家人都搬到了县城。那段读書岁月,也许正如育邦笔下的文字:“时光与世事在这里迅即流过,带来无尽的惆怅和思考。”
1994年,育邦考上南京师范大学,一路风尘地来到了省城。南京属于亚热带温湿性气候,鱼米丰饶,历史悠久,文人墨客辈出。而20世纪90年代正是先锋小说异军突起之时,当年在南京活跃的年轻小说家就有苏童,叶兆言,韩东、朱文等一大批。在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也有两位小说家鲁羊、郭平,两位都是育邦的老师。受他们的影响,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育邦开始尝试写小说,因为他觉得自己和文学的关系更为密切,而当时认为成为一名作家的主要方式就是写小说。前期的写作,以仿作为多。育邦发现,其实法国文学中就有仿作的传统,很多好的作家在年轻的时候都有模仿前辈作家、优秀作家的经历,然后慢慢再形成自己的风格。“当时自己也读到了很多好的作品,但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赋予作品以生命,这个时候模仿是最好的手段。更多的意义上是一种练笔吧。”
大三的时候,有一次鲁羊在课上读了一段发表在《译林》杂志上的作品,那是葡萄牙大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的随笔集《惶然录》片段,当时该书还没有出版中译本。育邦听了之后非常喜欢,还把那期《译林》借来复印了,然后就期待着《惶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