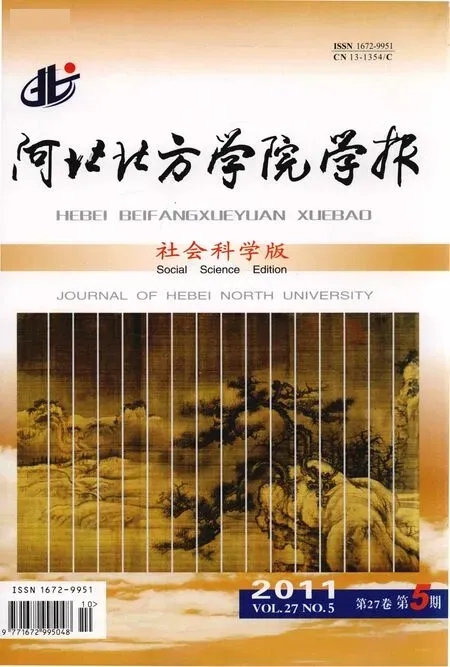白马人山、树和动物崇拜的文化人类解读
权新宇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政史系,甘肃 成县742500)
白马人①文化的核心是白马人的原生性宗教信仰,不研究白马人原生性宗教信仰的人,很难说是真正了解白马人的文化。白马人的原生性宗教信仰有两大主题: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白马人的山、树和动物崇拜隶属于自然崇拜,在白马人原生性宗教信仰中占有很大比重。对白马人山、树和动物崇拜体现、成因及崇拜表层背后所蕴含的生态意蕴的探讨是研究白马人原生性文化的重要内容。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做些探讨,一方面以促进对白马人原生性文化的了解,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对生态概念以另外一种后现代话语进行诠释。
一、白马人山、树和动物崇拜的表现形式
白马人崇拜山神、水神、火神、树神、天神、地神等,理论上天神最大,但实际上最崇拜的是山神。他们认为一切天灾人祸、人间祸福都与山神有关。因此一年中的节日活动多以敬山神为主要内容,各家各户的生老病死都要以各种形式向山神祈福、还愿。
(一)“叶西纳蒙”和“则叟毕丁”神山
白马人多居住在川甘交界的山区,山与白马民族有密切的联系,山是与人们生活、生产密不可分的自然物。人们靠山生产、靠山吃饭。大山崇拜成为白马少数民族自然崇拜最基本的形式。白马人认为有山的地方就有山神存在,因而在白马社区神山诸多。但最大的山神是“叶西纳蒙”,汉语称“白马老爷”。据民间传说,“叶西纳蒙”是文县的神仙,一次到峨眉山办事,途经平武县牙汝村时,忽然天降暴雨,河水陡涨,山崩地陷。据说神仙路经每站的时间是有规定的,白马老爷为了拯救当地的白马人,耽误了赶路的时间,错过了行期,便化作一座高山,成为保护白马人的山神。“纳蒙”就是“黑天神”之意。每年的四月十八、七月十五、十月十五是白马人祭祀“叶西纳蒙”的日子,正月初六的跳曹盖也要敬山神,每三年一次大祭祀。
除“白马老爷”山神之外,也有各寨山神。如文县铁楼藏族乡的入贡山、中岭山、立志山、麦贡山四村人都姓班,他们就崇拜山神“则叟毕丁”,即“三峰七兄弟”。相传白马班氏门中有兄弟7人,他们团结,尊老爱幼,惩恶扬善,深受村民们的喜爱。有一次七兄弟到山顶取木料,这时外村有个人也来此取木料。他看到兄弟七人团结,力大无比,砍倒的树不用任何工具就可划成一张张的木榻,于是他装出一副可怜相,让七兄弟帮助他,七兄弟答应了他的请求。当七兄弟正共同将一截圆木掰开时,那人起了坏心,使劲将圆木一推,七兄弟的手都夹在木头缝中,那人又将木头一推,七兄弟连同木头一齐滚下悬崖。与此同时,那人鬼使神差般地被木头挂了一下,也一同坠下悬崖。这时下起了瓢泼大雨。待雨过天晴后,在七兄弟坠下的地方长出了三座山峰。从此附近的老百姓特别是班氏人等,都来祭拜七兄弟变成的三座山峰。
(二)村寨附近的神树林
在白马人聚居区与山神崇拜相关联的是“神林”、“神树”崇拜。无论是平武、九寨沟,还是文县的白马人均认为乔木、灌木都有神灵,在其居住的每个寨子均有神树。在白马人看来,神林是神与鬼栖息之地,人们时时要向神树祈祷,感谢它对村寨和人畜的护佑,神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白马人也认为,祭祀这片神林,村寨就会安宁,就不会发生灾害,不会发生偷盗。村寨也因此会兴盛富裕。因此,全体村民视这片树林为村寨保护神,一般在冬闲时集体祭祀树神。祭祀树神的地点,就在该树林前或树林中。除冬天全体村民集体祭拜外,也有以家庭为单位的祭拜。如孩子病了、家人身体不适、丢失财产等,都有人在此祭拜。家庭或家族祭祀所用牺牲,按其自家发生事情的大小而定,分别为雄性羊、猪、鸡等。集体祭祀所用牺牲则是宰杀的雄性羊或猪。集体祭祀时,由“贝木”或“道拜”或懂行的普通村民来担当此任,家庭祭祀由普通村民或祭祀人自己完成。时至今日,在白马族群居住区,尽管集体祭祀的次数几乎是寥寥无几,但以家庭、家族为单位的祭祀现象依然存在。
(三)“十二相”傩舞中的动物神灵
恩格斯说,一个氏族或部落,把生活于其中的特定自然条件和自然产物,都搬进了它的宗教里,“人在自己的发展中得到了其他实体的支持,但这些实体不是高级实体,不是天体,而是低级的实体,是动物”[1](P63)。
就白马人而言,他们也把很多动物搬进了他们的崇拜文化里。现今在白马人聚居的部分地区,每年一度的“十二相”傩面具舞的展演中动物崇拜得到了延续和传承。其中,甘肃文县薛堡寨跳“麻昼”傩舞的展演中,6个扮演者各自戴一具代表这些动物形象的面具分别模仿6个动物动作。据当地白马人说,这6个动物分别代表两个动物形象:狮(白马语称“生梗”)代表鼠、兔;牛(白马语称“捞梗”)代表牛、蛇;虎(白马语称“达梗”)代表虎、马;鸡(白马语称“谢梗”)代表鸡、羊;龙(白马语称“主梗”)代表龙、猴;猪(白马语称“帕梗”)代表猪、狗。薛堡寨跳“麻昼”时之所以一相代两相,据当地白马人称,十二个面具同时出场不吉祥。(六相面具见下图)

图1 文县薛堡寨“麻昼”傩舞中的动物形象面具
四川省平武县白马社区的“曹盖”傩舞中所使用的动物形象面具略不同于薛堡寨的“麻昼”面具,其使用的动物形象主要是狗、熊、鹰、猩猩和想象中的龙等。九寨沟县汤珠河白马人各部落“十二相”傩舞面具使用的动物形象在数量上多于薛堡寨和平武,其中动物形象龙、虎、熊、牛、豹、蛇、凤凰等表演时,间或加上大雁、孔雀、狮子、大象以代替鼠、兔等。这些动物在与人的共舞中就成了具体神灵的代表,具有了沟通神与人的特异功能。白马人正是在每年一度的人神共舞中完成了对动物神灵的顶礼膜拜。
二、白马人山、树和动物崇拜的原因
从古至今,神灵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能够满足信仰者的生存之需,尤其是精神需要。当然,信仰者所崇拜的对象,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来自于信仰者生存环境之中,即为人们所崇拜的神灵的具体形象均是自然存在的某一具体物的人格化或神圣化,这种自然物被神化或者人格化均是处于造神者之生存需要。因而,崇拜意识首先产生于人们生存的自然环境中。自然环境对于崇拜意识的产生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自然为人们的崇拜提供载体,即崇拜的对象,而且崇拜对象必须是能够满足造神者实际生存需要的某一自然物。
白马人聚居区山大沟深,气候严寒,自然灾害频繁,不利于农业生产,自古农业生产水平极为低下。如《龙安府志》记载:“郡连氐羌,境带灵山,其地四塞,山川重阻,峭壁云栈,联属百里,五关设险,六阁悬崖”,“地土俱系深山,悬崖绝壁,附葛攀藤,刀耕火种,历来并未认真纳粮赋”,“番民男妇务农为主,每年三月种大麦、青稞,七八月始收获,备作炒面与酒。五月种荞,九月始收获,霜迟则获,霜早则不成颗。一岁之供全赖乎荞,多荒少熟,不外出佣工,荒则采蕨根作面为食”。这是清代白马路“白马番”生存状况的真实反映。其实,现在文县铁楼乡白马聚居区仍能见到汉代的“二牛抬杠”式的耕作技术。平武县白马人聚居区农业生产水平也很低。据白马人学者曾维益说,平武县白马乡在20世纪50年代,玉米亩产100斤,民国年间土豆开始传到当地,人们才开始种植土豆。据1957年的统计,白马乡粮食产量平均每亩90斤[2](P86)。可见,总体上白马地区的经济形态至少在1956年民主改革之前是典型的生存经济。尽管最近几年,白马人聚居区经济形态有所变化,如政府倡导的旅游经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改变了传统的生存经济形态,但总体上这种生存经济形态依然占主导地位。如至今在白马人山寨,若遇久旱,当地白马人会去神山祈雨。届时全寨男人由头人指挥,备好干粮,敲锣打鼓,列队走到神山前。在巫师的主持下,人们虔诚地站立于神山前。紧锣密鼓,巫师背靠神山,面对村民站立着。大约过一个时辰,巫师就会不由自主地均匀地抖动起来,这时似乎山神已附体,他成了神的代言人。站着的村民们在山前整齐地呼喊“噢,查席!”(白马语)意即“请给雨”。待到巫师伸手向村民要“木卦”时,村民们意识到“神山”有话要告诉大家,于是不约而同地齐跪于神山的代言人——巫师前,其中有一威望较高的人尽快将木卦递给巫师。巫师口里喊到“呕嗨”将木卦打在地上。这时巫师只管打卦,村民中的一位老者主持要卦。当老者说要“阳卦”,巫师连续扔下三次均是阳卦时,打卦即终止。巫师告诉大家下雨的日期后,村民才回家。白马人祭山神求雨、还愿均是自西向东呼唤山神的名称。可见,在白马人眼中山不仅仅是保护神,还是能“兴云雨,产万物”的主宰者。白马人的祈雨不仅仅是应生存之需所做的无奈之举,也是农业生产技术低下的真实反映。
白马人聚居地区,一方面可用于农业生产的自然资源有限,导致了该地区农业生产长期发展水平极为低下,白马人生存艰难;但另一方面该地区森林茂密,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如这里仍生活着大熊猫、金丝猴、扭角羚等珍稀动物。这一动植物自然资源的优势,加上作为古代氐、羌民族系统遗存的白马人,自古就有狩猎的传统使得白马人从狩猎活动中或多或少弥补了农业生产的不足。白马人以动物作为生存资源的必要补充在1960年得到了很好诠释。据连玉鉴调查,在1960年春,平武各地普遍发生缺粮,人均每天只有四两粮,有大量水肿病人。但由于白马人有狩猎的传统,加上杀了一部分牛羊,饿死的人很少[3](P15)。又据载“猎手曾万六,在政府的支持下,仅去年(1952年)一年中,即消灭野兽130只左右②。猎获的动物主要有野猪、黑熊、黄羊、扭角羚等。兽肉人食,兽皮制衣服鞋子。此外,山区药材较为丰富,在每年五六月冰雪融化时,成年男女结伴而行,到老林深山、草地挖药材,如遇晴天,每天可挖30到50斤,所采药材主要有羌活、独活、当归、党参、大黄、赤芍、秦椒、贝母、康香等。药材成为白马人与外界交换生活必需品的主要物资。
从上述可知,白马人利用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作为对农产品不足的必要补充。这一必要补充的逻辑结果就加剧了白马人对山、树和动物生存资源的依赖。诚如费尔巴哈所言:“人的依赖感是宗教的基础,而这种依赖感的对象,亦即人所依靠,并且人也为自己感觉到依赖的那个东西,本来不是别的东西,就是自然。自然是宗教最原始的对象;这一点是一切宗教和一切民族的历史所充分证明的”[4](P1)。正是对山、树和动物等生存资源的依赖促使了白马人把作为其生存之源的山、树和动物幻化成神灵,并对其加以顶礼膜拜。而造神者膜拜神灵的基本目的依然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如白马人出于村寨兴盛富裕、安宁,不会发生灾害,不发生偷盗而集体祭祀树林神。平日谁家孩子病了,家人身体不适,丢失财产等,都有人用雄性羊、猪、鸡等牺牲来“贿赂”神树以求消灾辟邪。也有人为了出远门、求财、求平安、寻物、上学等事而许愿,事后还愿。也有遇到了“凶事”而许愿,过后逢凶化吉就还愿。一般是带香纸,杀鸡还愿。白马人学者曾维益在《白马藏族研究文集》中写道“……在部分白马人的大门靠神山一侧的上方部位,至今仍保存着悬挂野猪与老熊头的习俗。白马人说,在门上挂野猪与老熊的头,是为了避邪”[5](P100)。平武白马人平时也有把跳曹盖的傩面具挂在自家大门上方以驱鬼辟邪的习俗。可见,在白马人基于现实需要而与山、树和动物神灵的诸如此类的双重互动中,神灵不仅仅满足白马人的生存需要,还培育了白马人的宗教情感。如在5·12特大地震后,白马庙倒塌,白马人纷纷不约而同地感到悲伤与茫然,一位白马妇女说,“庙塌了,神就走了,心里觉得空空的,没了依靠”。很多白马人表示,白马庙倒塌之前觉得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倒塌之后觉得诸如冰雹、泥石流之类的自然灾害增多了,而且缺少安全感。他们将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不顺归结于庙的倒塌,神的庇佑缺失[6]。从上述材料中可以看出,作为山神的“白马老爷”不仅仅是当地白马人的保护神,更是白马人的精神家园。
如果说,生存经济加剧了白马人对于山、树和动植物自然资源的依赖,那么,作为这一经济结构的产物——山、树和动物崇拜,则是白马人对于自然神灵的情感依赖,正是这一双重依赖构成了白马人山、树和动物崇拜的逻辑起点。这也是白马人至今崇拜山、树和动物神灵的直接原因。
三、白马人山、树和动物崇拜的生态意蕴
在白马人创世神话中,有如下一则:天也有了,地也有了,动物、植物都有了,就是没有人住在其中。天老爷派来了“一寸人”。一寸人长得太小了,老鹰要叼他,乌鸦要啄他,土耗子要咬他,连小蚂蚁也要欺侮他。一寸人太软弱,庄稼也种不出来,后来慢慢就死绝了。天老爷又派来了“立目人”。立目人太懒惰,不会种庄稼,又不学,天天坐起吃喝。身边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立目人也渐渐饿死了。天老爷又派下来“八尺人”。八尺人身高力大,食量也大得吓人,种的庄稼,三年的收成还不够他一年吃。开始他还能捕野兽、禽鸟和采野果添着吃,后来这些都吃光了,八尺人没有充足的食物,知道自己只有死了,于是不断地哭,也逐渐灭亡了。天老爷没有办法,最后才派来了我们现在的“人”③。透过神话的表层,折射出了白马先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中庸主义”态度,即“万物中心主义”[7](P76-77)。白马先民“万物中心主义”的态度超越了传统伦理学中人是唯一纳入道德关怀的对象,“把爱的原则扩展到动物”,认为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没有高低贵贱的等级之分,人类应当给予周围所有生物的生命以道德关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白马人山、树和动物崇拜其实也是给予山、树和动物以道德关心。这种道德关怀,在笔者看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万物平等,人与万物和谐共生。万物平等是指自然万物都有生存的权利;人与自然万物不是对立关系,而是息息相通的依存关系[8](P170)。作为这一观念的逻辑延伸就是“人类活下去,其他生命体也要活下去”。而万物都活下去的路径选择就是和谐共生。白马人正是本着这种观念来处理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如白马人唱的《拉惹》,其歌词大意是:“广阔的天空千古长在,太阳、月亮和雷是天空的主人。宽阔的草地千古长在,花草和豺狼在那里居住,花草和豺狼是草地的主人。茂密的森林千古长在,金丝猴和虎豹在那里居住,金丝猴和虎豹是森林的主人。陡峭的黑岩千古长在,老鹰和岩羊在那里居住,老鹰和岩羊是黑岩的主人。清澈的海子千古长在,水獭在那里居住,水獭是海子的主人。富饶的坝子千古长在,人们在那里居住,人是坝子的主人”④。今天的九寨沟县草地乡和平武县白马乡,人们所跳的熊猫舞(“阿里嘎珠”)中就表现了大熊猫吃竹、喝水、爬树、嬉戏等生活场景。这种舞蹈表面是为了感念“大熊猫为媒”的功劳,但从其深层次意义来看,实际上,这既是动物真实生活状态的一种写照,也是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二,万物都应该受到人类的关怀和敬畏。万物有灵论者认为万物皆处于宇宙生命体的链条上,从珍惜人的生命出发,必然要渐渐走向珍惜万物;从敬畏生命出发,必然走向敬畏宇宙,敬畏万物。法国哲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看来,敬畏生命,意味着对一切生命,不仅指人的生命,还包括其他动物和植物的生命,都应该保持敬畏的态度。在白马人聚居区,这一敬畏生命观念的具体体现就是禁忌。白马人的不少习俗禁忌均从“趋吉避凶”的愿望出发处理着人与山、树和动物的关系。如他们严禁在神树林和“神山”中打猎,因为在他们看来,神林是神与鬼栖息之地,人们时时要向神树祈祷,感谢它对村寨和人畜的护佑,神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祭祀这片神林,村寨就会安宁,就不会发生灾害,村寨也因此会兴盛富裕。再如在捕猎方面,猎取动物也要适可而止,不能贪得无厌,围猎时不能斩尽杀绝,而且打猎要避开动物繁殖的季节。如每年农历四五月之后,白马人一般不上山打猎,他们认为春夏之交是动物的交配和成长季节,若这时猎杀,不利于动物的繁殖。白马人把熊猫叫“灯嘎”,即“白色的熊”,不猎取大熊猫,认为熊猫是吉祥物,是部落的神,谁打死谁就不吉利,不单家庭不安宁,全寨子也都不安宁,再者大熊猫不伤害人类,是和平的使者,爱情的象征,智慧的体现。因此,他们十分喜爱大熊猫,若大熊猫进到寨子来觅食,要给予热情款待。白马人也禁忌猎杀棕熊(马熊)(白马语称为:知貌,即棕色的熊),认为谁要是打死了棕熊,他的家畜就要病疫,或从山崖上滚死,或被豺狗吃光。诸如以上禁忌,体现了白马人对山、树和动物生存所给予的应有的人文关怀,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维护了生态的平衡和物种的多样性。敬畏生命和生命神圣的思想,使白马人在现实生活实践中,树立了人与其他生物平等的观念,懂得了其他生命也具有生存的权利,使人类尊重和珍爱包括自身生命在内的一切生命,以及使人类尽可能地摆脱以其他生命为代价保存自身生命的必然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物种的灭绝,优化了人类生存的空间,并为子孙后代留下他们应该拥有的资源。
尽管白马人的山、树和动物崇拜中从未明确提及“环境意识”这一概念,但在实践中却蕴含着珍贵的生态意识。以神灵的名义,在对诸神的祭祀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化着人们的环保意识。无论山、动物也好,植物也罢,在白马人眼中,都已不是单纯的生物,它们和人类一样具有繁衍生存的权力,同样是自然界的臣民,不能任意加以亵渎。尽管白马人的山、树和动物崇拜不是出于一种科学高度的意识,有的甚至带有虚幻色彩,但其所蕴含的生态思想客观上对当地生态环境的维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注 释:
① 白马族群指的是现居住在甘肃省文县和四川省平武、九寨沟县境内的游离于汉、藏和羌族群边缘的一个少数民族,大约有2万余人。关于白马族群的归属,解放初,官方称其为“白马藏族”。平武县白马人自称为“夺补甲育尼”或“夺簸甲育尼”,文县白马人自称“甲育尼”,“甲育尼”是“人”的意思,“夺补甲育尼”是“夺补河边居住的人”的意思。九寨沟县白马人都自称“peY”(贝),俗称“白马人”。
② 萧猷源.平武白马藏族[M].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平武县委员会,平武县王朗白马分情节领导小组内部资料,2001:175-176.
③ 白马人族属研究文集(辑刊之二)[C].平武县白马人族属研究会内部出版,1987:111.
④ 四川白马藏族民间文学资料集[G].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四川分会,四川大学中文系,平武县文化馆,1982.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 四川省民委民族识别调查组.“白马藏人”调查资料辑录[J].中国少数民族(人大复印报刊资料),1981,(6):86.
[3] 连玉鉴.现代化进程中白马藏族的社会变迁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历史丈化学院,2005:15.
[4] 〔德〕费尔巴哈.宗教的本质[M].王太庆,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 罗布江村,杨嘉铭.藏族面具文化的历史探源——兼述藏族面具活态遗存的基本要素[J].中国藏学,2006,(3):100.
[6] 杨胜利,高云鹏.甘肃省文县白马藏族灾后文化重建调查报 告[EB/OL].http://qkplan.blog.163.com/blog/static/11561895320099194024589/2009-10-01/2011-06-10.
[7] 王铭铭.初入“藏彝走廊”记[J].西北民族研究,2007,(4):76-77.
[8] 叶舒宪.神话的意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本科二类综合性院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改革探讨
- 高自尊与低自尊儿童父母教养方式结构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