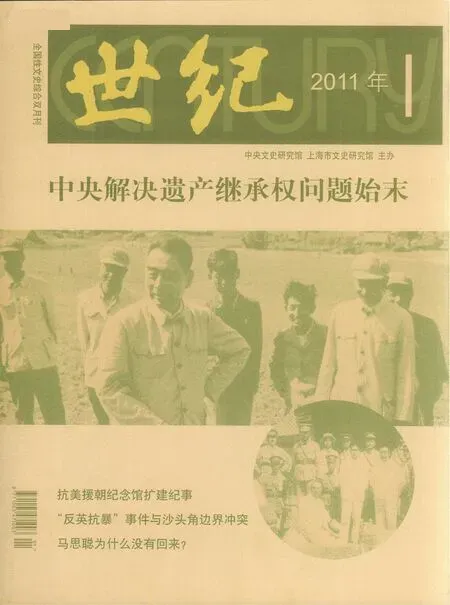相隔61年的两次台湾之行
丰一吟

丰一吟(右)在台湾“大家来谈丰子恺”座谈会上发言
2010年1月底,为了去台湾参加一小时“大家来谈丰子恺”的座谈会,我竟办了去台湾旅游8天的手续!这次座谈会,是由香港陈一心基金会召开的,无法由台湾发出邀请信。于是,除了参加旅游团并在其间离团一天去参加座谈会之外,似乎没有别的办法。既然有这么好的机会,那就办手续,去游8天吧!
台湾同胞的素质真不错
我们是所谓“高进高出”,也就是从上海飞往台湾的南端高雄市,在宝岛上兜了一圈,又回到高雄,从高雄飞回上海。这次旅游,台湾美景全收眼底。但给我印象更深的是宝岛上同胞的素质真不错!
我遇到了两件使我感动的事。有一回,不记得是为了什么原因,我们的团队必须在山里走相当距离的一段路,才能和我们的大巴车会合。在整个团队中,我和另一位男士是“八零后”的高龄,走路走不快。别的人都到达汇合点了,我们两人却由导游陪着落在后面了。时间不早,天已渐渐黑暗。
忽然,一辆白色的私家车从我们左边驶过,却在前面停下来了,而且开了门,我以为有人要下车。岂料车主在向我们打招呼,请我们二老上车,要带我们一程。(他们看到拿旗子的导游陪着我们,知道是掉队的)我受宠若惊。怀着感激的心情,和另一位老先生上了车。车主送到前面,看到了团队,就停下来。我们说了很多感谢的话。我心里感谢车主的,其实不是为了少走了这段路。慢慢地走,我们还是走得动的。我感激的是萍水相逢,车主居然毫不犹豫,对我们伸出援助之手。
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上海那几家台湾人办的“枣子树”(“早吃素”的谐音)素菜馆来。素菜馆的女主人对我说,“枣子树”录用员工的标准是“孝顺”。她说:“孝顺的人必然是好人。”这句话很有道理!
我们虽然和团队会合了,可这是三岔路口,我们竟走错了方向。导游一再和大巴司机手机联系,但山里除了茂林,找不到一个人可以问问。走到后来,在导游一再和司机联系下,终于发现我们是走错了路!说来也巧,从后面忽然驶来一辆暗红色的小货车。导游拦住他问路。司机回答说要退回到那三岔路口,从另外那条路往前走。导游告诉他队里有两个老人走不动,司机竟愿意载我们,调头走回头路专门送我们到大巴所在地。他把车里的货整理了一番,好容易腾出两个座位来让我们坐进去。然后调头经过那三岔路口右转弯,顺利地把我们送到了大巴所在处。我手里早就准备好一些台币要酬谢他,可他说什么也不肯收,调回头把车开走了。
我在台湾遇到的这两件事,至今一直念念不忘!
对了,还有一件事呢!我们到一处海边游玩。会游泳的队员就下海游泳。我和一块来台的女儿对此没有兴趣。我倒是想找一个“洗手间”。女儿陪着我往公路方向走。可两旁都没有WC的指示牌。我们来到一家喝咖啡的店前,进去想向女营业员打听哪里有厕所。她很客气地说:
“我们这里就有!”
我向她道谢后就进去了,出来时总觉得不好意思,就请她卖一杯咖啡给我们。她说:“好的。”就要动手制作。我一边取台币一边问她多少钱。“送给你喝,不要钱的!”“啊,那我不要,不敢当!谢谢你啦!”我一边说,一边和女儿连忙离开了。我们都感觉到:“台湾同胞真客气!”

我离队一天,除了参加讲座外,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朋友家坐坐。江朝阳先生是虔诚的佛教徒,得知我要来,请了慧观法师等好几个朋友来一起聚聚。饭后,我对江先生提出要求,希望他陪我去开明书店看看。我在到台湾之前就向他提出过。所以他已打听到了开明书店的地址。这时便驾车载我们过去。开明书店果然出现在我们眼前了!虽然这条马路已面目全非,但开明依旧还保留着61年前的模样。这一天店内无人,我们只能在外面看看。我拍了几张照,感慨万千!61年前的夏秋之交,爸爸曾带了我来到台湾。那时我才19岁,如今却已是白发苍苍的老妪!
61年前,在自己的土地上,要借助日语来通话
1948年,开明书店的负责人章雪村(锡琛)先生要去台湾看看开明书店的台湾分店,约爸爸同去。那年暑假,我正好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章先生是带家属同行的,所以爸爸就带了我一起去。我们两人于1948年9月8日离开杭州,记得那时爸爸的好友《浙赣路讯报》编辑部副主任舒国华先生用小汽车送我们去火车站的。那时,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妈妈几乎每天都要为生计费尽心机。家里人多事杂,不胜烦恼。爸爸倒有意去看看刚收复不久的宝岛台湾,是否宜于安家。当然还打算在台湾开个画展,以补贴天天涨价的油盐柴米的开支。我们在上海会合了章先生一家。
爸爸去台湾的缘由,就是上面所说的,想换个环境。可是到了台湾以后发现台湾没有他喜欢喝的绍兴酒一类的黄酒,只有米酒、红露酒,他喝不惯。酒的问题总是使爸爸伤脑筋。钱歌川先生来台湾时带来一坛绍酒,要请爸爸去喝,爸爸叫他送到开明书店来与众同乐。上海的弟子胡治均从老师的来信中得知他思念绍酒,马上到麦家圈去买了两坛上好绍酒“太雕”,托人带到台北开明书店。爸爸很高兴,烟酒是不分家的,爸爸马上在开明书店举行了一次“绍酒宴”,让江南来的朋友大过其瘾。大家一起吃,很快就没了。黄酒是爸爸的命根子,于是只得离开了台湾。这是后话。

台湾开明书店今貌

且说9月27日,我们和章家坐上了“太平轮”(就是后来沉没了的那艘轮船),离开了上海。在船上一宿,早晨发生了章老板(我们都这样称呼他)手表被窃的事。船上的工作人员因见旅客名册上有丰子恺的名字,对于查这案子特别起劲,终于查到了小偷——一个衣冠楚楚、相貌堂堂的青年知识分子!爸爸后来写下了《海上奇遇记》以记其事。
我们在基隆上岸,来到台北。章老板一家就在开明书店住下,我们被安排在附近的文化招待所,地址是中山北路一段大正町五条通七号。我这回重游宝岛时没时间再去探访这宿处,料想也已变了样了。当时宝岛收复才三年历史,因此这里的地名还保留着日本统治时的遗迹。不仅地名如此,当地人还会讲日本话呢。
有一回爸爸和我去餐馆吃饭,女招待讲台湾话(即闽南话)我们听不懂。爸爸和我吃菜都是很苛求的。爸爸能吃海鲜,但要求菜里别放猪油;我不吃海鲜,吃猪肉还要指定瘦的。这样复杂的内容,无法用手势来表达。这下完了!忽然爸爸灵机一动,试着对那女招待讲日文。爸爸一开口,她就应答如流。唉,想不到在自己的土地上,要借助日语来通话!
在台北,爸爸也有不少新朋旧友往来。1923年钱歌川从日本留学回来后,他在上海遇到任教于立达学园的在日本认识的黄涵秋先生,通过黄认识我爸爸。后来交往甚多。那时,钱歌川先生受台湾大学陆志鸿校长之聘,正在台大创办文学院,他和爸爸在台北常相往来。爸爸与学生萧而化一家,也在台湾重逢,互相回忆抗战时期在萍乡他们夫妇接待我们一家的情况。想不到会有抗战胜利后在台湾重逢的一天!
刘甫琴先生在这里任开明分店经理,招待很客气。我们平时都是在店里吃饭。爸爸和章老板一起喝酒,论古谈今,谈到高潮处,章老板就拍拍屁股哈哈大笑。如果换了现在,我一定会倾听他们的谈话并仔细记录。章老板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的谈话内容一定是极精彩的。可那时19岁的我,什么都不关心,甚至不喜欢听。有几次我不跟爸爸去开明吃晚饭,情愿自己在招待所里用电炉煮面食吃,有一回把保险丝烧断,整个招待所漆黑。他们惊讶怎么回事,忙着修复。我躲在房里装作没事一样。即使去开明吃饭,也总是闹着要早点回去,而他们的谈话方兴未艾,惹得章老板搔搔头皮连声说:
“一吟要先回去,葛东西……葛东西……”
“葛东西”是绍兴话里表示无可奈何的意思吧。有时候我就一个人先回去了。
10月13日晚上8点15分,爸爸应邀在台北电台作了一次以《中国艺术》为题的广播演讲。还在中山堂举办了一次画展。
可是,靠带来绍酒喝,决非长久之计。爸爸决定不到台湾来安家。于是,我们随章老板一家游玩了一番后,便离开了台湾。我们先游离台北较近的草山,下榻阳明山庄。后来启程到台中,坐小火车上阿里山。那火车是头尾各有一个龙头的,走在“之”字形的铁路上,轮换着用前后两个龙头拉动车厢上山。我们观赏了三千年神木,爸爸后来还画了一幅阿里山云海的画,题名《莫言千顷白云好,下有人间万斛愁》,是一幅富有宗教意义的画。
最有趣的就是住宿在山顶日本式的旅馆里。躺在“榻榻米”上通过落地玻璃窗俯观云海,犹如躺在一大堆雪白的棉花丛中。棉花中间伸出一株株树梢来,真好看。次日清晨,冒着严寒去看日出。
在阿里山上,我买了一个比眼镜盒短一点的手炉,里面不知装着什么,点燃后,用手握着它可以取暖。这东西竟然一直保存下来,后来捐给重建的缘缘堂陈列起来了。
离开了阿里山,我们来到日月潭,在山顶的湖泊中泛舟,访问当地的高山族公主。大公主不在家,我们就与二公主合影留念。下山后,经嘉义、新竹回到了台北。
在台湾盘桓了56天,我们于11月28日渡海回到了厦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