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经验的重量——往事随感三则
洪子诚
“自反式”思维
我1956年进北大中文系,因为政治运动不断,从57年下半年开始的三年中,许多课断断续续或被取消。到了60年的五年级(当时是五年制),才补上一些基础课。这样,在北大系统听课的时间可能不到一半。不过,有一些先生的课还是让人难忘。印象较深的有吴组缃先生讲明清小说(《红楼梦》、《聊斋》、《儒林外史》)。从他那里,见识了生活阅历、写作经验、艺术感觉等。还有就是常被提及的林庚先生讲唐诗。他讲李白,想象着李白的神采飞扬,自己也如想象中的李白那样神采飞扬,解读者与对象似已融为一体,主客体相互投射。尽管模仿吴、林两先生的后学者不少,却不是可以轻易得其神髓,因为着重点属于难以复制的个体生命,而他们也都有小说、诗歌丰富的创作经验。倒是朱德熙先生讲课的“方法”,是我后来经常复习的启示。
朱先生主业是现代汉语语法和古文字学。当年他研究现代汉语语法,运用的是索绪尔、布龙菲尔德的结构主义。1960年代他著名的论文是我没有能读懂的《说“的”》;由于无知,我上学时对语言课程没有多大兴趣,也就没有动过念头去听朱先生为高年级开设的语言课。结构主义那时在中国大陆不大为人所知,成为“显学”是80年代的事。但朱先生也讲写作,分析文章,他是当时汉语教研室副主任(王力先生是主任),分管写作教学。虽是“副业”,文章分析却引人入胜。记得他分析过的文章有《传家宝》(赵树理),《欧游杂记》(朱自清),《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羊舍一夕》(汪曾祺)。选择这些文章,应该和当时的政治、学术“气候”相关,换一个时间,也许他另有其他的选择。

我1961年毕业到1966年也在北大教写作课,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最主要的是两个方面,一是他对语言的敏感。从他那里,我发现了匠气式的繁琐与感叹式的含糊之外,存在着基于艺术感觉之上的清晰分析。在艺术鉴赏与作品分析上,确实存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况。朱先生努力的是将意会到的,通过语言分析加以传达。在这个问题上,“言传”也许不都是必须,更不都是“正确”,却落实了感觉所以由来的依据,创造了一种对于“含混”的穿透力。朱先生讲课更为重要的另一方面,是那种自觉的“自反式”思维。“自反”这个词那时候还没有被使用,是现在回忆的时候加上的。通过现象分析提出某种看法,并说服听讲者信服这个看法,这是所有授课者所要达到的目标。他当然也是沿着这一过程推进,不过和其他教授不同的是,他的着重点不在提出和论证结论。对于涉及的文章的篇章结构、词汇句式,会提出若干可能进行比较,从中发现较佳的处理。在作出判断之后,接着也常会回过头来质疑这一看法,或将这个判断的合理性限制在一定(比如某种文类,某种风格)的范围内。对于朱德熙先生的这个方式,听过他的课的孙绍振有这样的概括:他“并不要求我信仰,他的全部魅力就在于逼迫我们在已有的结构层次上进行探求,他并不把讲授当作一种真理的传授,而是当作结构层次的深化。”(孙绍振:《我的桥和我的墙——从北大出发的学术道路》)
“自反式”是一种思维、言说方法,也包含“世界观”的内涵。最主要是认识到对象的复杂性,也认识到认知个体存在的各种局限;真理的探求自然责无旁贷,也认识到这种探求的艰难。因而,这里也包含了思考上,对待知识上诚实的伦理持守。这种方法,在一个以宣讲“真理”作为唯一目标的时代,显然不合时宜。“文革”时期不必说,就是现在这种言说方式也较为少见。相比而言,我们有太多的“真理”拥有者和宣告着,太多的将自己排除在“反思”之外的先知先觉者。这样,就出现如耿占春说的那种局面:“知识的增加没有促成耐心而诚实的思考”,“立场的两极对立或站队”成为普遍的知识现象。也许,在“真理”的鲜明、坚定的宣告之外,作为补充,也需要一些“自反”的言说者,以改善思想界、文学界论述上过于板结、坚硬的现象。
消逝的风景
大概是1969年夏天,“军、工宣传队”在北大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已近尾声。一天,顺手拿起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早期作品《地粮》。这本书是1957年初我从王府井东安市场旧书铺购得的,盛澄华先生1930年代末的译文,1940年代文化生活社的版本。在《译序》中,盛澄华先生写道,“流浪,流浪,年轻的读者,我知道你已经开始感到精神上的饥饿,精神上的焦渴,精神上的疲累,你苦闷,你颓丧……时代需要你有一个更坚强的灵魂。如果你的消化力还不太疲弱,拿走吧!这儿是粮食,地上的粮食!”——这些文字写在1942年,盛先生当时“流浪”到陕西汉中的城固,那是战争艰苦的年月。(当时盛澄华任西北大学教授,抗战期间西北大学迁移到陕西汉中的城固。1950-1960年代,盛澄华在北大西语系任教授。1970年在江西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时,心脏病突发猝死。当时我也在“干校”,却不知道这件事。)在得到这本书的1950年代,我心头充溢的是幸福感、满足感,肤浅地自以为世界已经一目了然,所以,根本就没有想从它那里获取精神食粮的愿望。
到了1969年,也许有了一点精神疲累、精神焦渴了吧。这时我读到这样的一段:
我沿着昔日的路走去而我认识一切。
我把步子重印在自己的足迹上……。以前我曾在一条石凳上坐过。——正是这儿。——那时我坐在那儿看书。什么书?——唉,维基耳。(现通译为维吉尔,古罗马诗人)——而我听到飘来浣纱女捣衣的声音。——这一忽我还听到这声音。——那时空气非常静穆,——正像今天似的。
孩子们散学回来;我也记得。路上的行人过去,也正和昔日一样。那时正是落日光景;而眼前又恰是黄昏;而白日的歌声行将沉默下去……
没有别的。
——但这不够做一首诗……安蕊儿说。
——那就算了!我回答说。
“沿着昔日的路走去而我认识一切”,“眼前又恰是黄昏”……这些句子触动了我。为什么呢?心想可能是那时候对于“昔日”的寻找,常以认不出一切告终。我还能把步子重印在自己的足迹上吗?坐的还可能是当年的石凳?可能再重习落日静穆光景,听曾经的歌声的行将沉默吗?
那些日子,生活中经常遭遇的是与过去的切断。1956年初到北京,曾为复兴门到木樨地两旁高大挺拔的杨树惊叹,现在,为着修建地铁它们已经消失。北大“棉花地”操场被翻开种上蔬菜。一院到六院之间那个美丽园子的树木、草地已被砍伐、铲除。……这些好像都是一夜间发生的事情。一个早上,我从宿舍去中文系所在地的二院,出现在眼前的景象让我惊愕地停住脚步,白杨、榆树、刺梅、丁香都已狼藉逶迤散落,天空因突然空洞而变得慌乱。也是那些日子,一次遇到谢冕,他激动而忧伤地说起未名湖畔那株榆树被无端砍倒,仍躺在路旁:“一个礼拜了,我回家都绕着走,不敢从它身边经过。”我明白,我们谁也无力阻挡“风景”的消逝。
1980年代初,我读到牛汉先生的《悼念一棵枫树》,这首诗写于1973年,“文革”之后才发表。诗写到,秋天的一个早晨,湖边那棵高大的枫树被砍倒,这时,家家的门窗、屋瓦,每棵树,每根草,树上的鸟,都颤颤哆嗦起来,“整个村庄都飘忽着比秋雨还要阴冷的清香……”牛汉先生因美丽的毁灭,时间的切断产生的“阴冷”,我完全能够理解。
2008年9月,我在安徽屯溪书店购得刚出版的中译黑塞散文集,在等待旅行团集合的空隙,坐在屯溪街头公园里翻读。黑塞写到他的园圃里一株桃树的死亡。(《桃树》,见黑塞《田圃之乐》)在一个狂风大作的夜晚,桃树被折断,它所站的地面破了一个大洞,“我的小世界因而有了缺口,空虚、阴森、死亡和忧郁全都从这向内窥伺”。接着便有了这样的感叹:“连树木都有不测风云的命运,也会猝逝骤亡,也会一朝被人弃置,消失于无尽的黑暗中!”不过,牛汉枫树的死亡和这株桃树死亡的情境是否相同?黑塞说,桃树不是被空投的炸弹所爆裂,不是被人连根拔起远离故土,不曾因受到玷辱而痛苦求死……它“死得庄严而自然”。枫树呢?我并不知道它死亡的原因,是否受到玷辱,还是死得庄严而自然我无从知道。不过,这并没有关系。这些树木给予我们震撼的,绝对不限于它死亡的悲苦。也许,从它那曝晒于阳光之下的伤口上,可以辨识它一生的哀伤、病痛和兴旺的如实记载;但也许如黑塞说的,它的死又包含了“看透人类德性”而“大概看不起人类”的骄傲。
要补充说明的是,我1969年那样读《地粮》,绝对是扭曲了纪德的原意。《地粮》不是要读者沉湎于昔日,不是要人们流连旧迹,相反,期望的倒是走出“昔日”和书本。因此说“这不够做一首诗”;“你应该边走边看,但你不应该在任何地点停留下来。……让重要性在你自己的目光中,而非在所看到的事物上。”不过,当你生活在“断裂”接连不断,并且“断裂”总是成为关注点和中心话题的环境里,“风景”、足迹的加速消逝,难以留存、辨认,仍不时引人惊恐。也许,我们只有从这样的信念中求得解脱:
在人们心中和大自然里,都有不可分割的同一份神性在运作。一旦外在的世界毁灭了,我们所保有的这一份神性或许能够将它重新建立起来;因为山川与河流、林木与树叶、根干与花朵,所有这些大自然的创造物,全都已经预先在我们内心形成,从灵魂里源源而生。(黑塞:《外在世界的内心世界》)
历史经验的重量
1980年代在亲历者那里,总是记忆犹新。它或被怀念、赞叹,或被反省、质疑,成为许多人选择新起点的参照。
1983年前后,发生了一场有关人性、人道主义、异化的争论。争论“领头”的一方是周扬、王若水、王元化,另一方是胡乔木、黄森。随后,并发生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工作队”进驻北大时,周围富于历史感的人们,警觉到“反右”那样的运动好像又要开始,气氛压抑而紧张。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教研室是重点,教师纷纷被“工作队”约谈说明问题。那时我正给学生上当代文学史课,对于这个事件,在课堂上只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好像没有经历过文革。”“这个人”指的是从此爆得大名的哲学系教授黄森,他最先起来批判周扬有关人性、异化的论述。我觉得既然是讲“当代”文学,必须对这个事件表明我的态度。但我不是勇敢的人,就只说这样的一句话。没有想到的是,这句简单的话获得许多青年学生认同的感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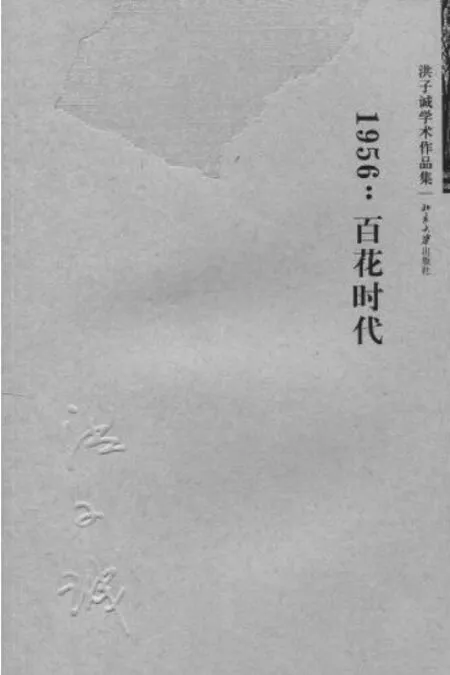

1990年代以后回顾这场争论,我多少意识到周扬他们的论述存在的问题,意识到胡乔木、黄森的指责并非都没有道理;至少是指出人性、异化论者一定程度离开特定历史条件,将人性、人道主义、主体等作本质化理解这一点。稍后,我读了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了解到这样性质的争论,在1960年代前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有过;中国发生的一幕,是另一情境下的“重演”。在《保卫马克思》里,阿尔都塞谈到二次大战之后这个“历史时间”,那时:
政治方面那就是大罢工、群众示威、斯德哥尔摩宣言和和平运动。那时,抵抗运动唤起的巨大希望濒于破灭,千百万人开始了长期而艰苦的斗争,力求使冷战不致恶化成为战争的灾难。在哲学方面,那就是全副武装的知识分子如同围猎野兽一样地到处追逐错误,我们的哲学家不研究任何哲学,并把一切哲学都当作政治;对于艺术、文学、哲学或科学,总之对于整个世界,我们统统用无情的阶级划分这把刀来个一刀切。用一句挖苦的话来概括,那时只是漫无边际地挥舞“要么是资产阶级科学,要么是无产阶级科学”这面大旗。(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
阿尔都塞称这个公式,是波格丹诺夫和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极左公式”,是一种“专横路线”。当阿尔都塞这样描绘斯大林式的“教条主义”,我完全能够理解。不过,当他也指认五六十年代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却格外引起我的注意。在他看来这一批判,是在继续这种“把一切哲学都当作政治”的方式,是“太热衷于在马克思青年时期著作的意识形态火焰里重新发现自已炽热的热情”。他认为,“马克思的著作本身就是科学,而过去,人们却要我们把科学当作一般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必须退却,“必须从复习基本知识开始”,“用一种超脱历史的观点去承认历史”。对于1960年代国际共运中的人道主义思潮,阿尔都塞认为,人道主义只是一个意识形态口号,而不是科学概念;马克思只是在还信奉费尔巴哈时才是人道主义者,而在“认识论断裂”后,已与人道主义决裂,人道主义不能科学地解释历史。
这些话,好像就是针对二十年后发生在中国的那场论争而说的。他的精湛见解表现在这样的论述,随着斯大林教条主义的结束,斯大林教条主义“并没有作为历史环节的简单反映而消失,它们依然作为我们的问题而存在着”,“人们从教条主义那里解放出来的东西,无论如何只能是业已存在的东西”。他指出,教条主义的结束虽然“使研究工作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但“同时也使有些人产生了一种狂热,仓促地把他们获得解放的感受和对自由的喜爱这类意识形态言论宣布为哲学。”(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也就是说,批判者与被批判者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共享了相同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当前我们接受的思想“遗产”的性质,看到“如同围猎野兽一样地到处追逐错误”,“对于整个世界,我们统统用无情的阶级划分这把刀来个一刀切”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
但是,我并不想收回“这个人好像没有经历过文革”这句话。同样,在认识周扬们的局限的同时,也不打算赞赏他们当年理论和现实关怀的勇气。当然也不认为周扬们的对立面是立足于不败之地的“政治正确”者。原因在于,这些“意识形态火焰”有它发生的历史、现实依据。在面对历史问题上,“超脱历史”与“承认历史”、“回到历史”并不能分离。在周扬他们的论述背后,伴随、蕴含着个人,特别是超越个人的生活感受、历史经验,有着难以被理论描述所包容的痛苦、欢乐、激情、期待。对“基本知识”的复习,并不能完全离开对一个时代,甚至几代人的感受,对他们积聚的激情的深刻了解。从这个角度说,“意识形态火焰”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要放置在受到质疑的位置上。
2009年11月,在人民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国际汉学大会上,我听到陶东风先生的发言。他谈到1993年刘禾的《一个现代性神话的由来:国民性话语质疑》这篇文章;它在国内思想界、现代文学界有很大影响,甚至已经当成经典被引述。陶东风说,这篇文章认为,外国传教士斯密斯的《支那人的气质》(又译为《中国人的气质》)一书,支配性地塑造了鲁迅的国民性思想;鲁迅的“国民性”这一“本质主义”的话语建构,是“翻译”了西方传教士的“国民性”理论,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来自西方的中国观。陶东风对此的质疑和提问是:“到底西方的汉学包括西方传教士的一些书对于中国作家、中国的文学有多大程度的影响,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国作家的自我认知和民族身份认同?……难道鲁迅等现代启蒙作家全部被西方传教士或者汉学家的殖民主义洗脑了?如果没有看过汉学家的著作,他们就不会批判和反思传统文化?反思批判传统文化的动力和根源到底来自何处?”
我赞同陶东风的质疑、提问,这是因为“国民性”问题,并非“伪命题”。这是“启蒙”的先行者深察历史的发现,这个“概念”中淤积着他们摸索探寻的血泪。在今天,这仍然是尖锐的现实问题,并不因“崛起”什么的而消失,甚且因信仰的崩塌而膨胀。近一二十年来,思想史、文学史研究的词源学、谱系学的兴起,推动、改变着学科的面貌和知识认知深度。但如果这样的“超脱历史”不能导向“承认”、“回到”历史,导致脱离中国特定情境,忽略中国作家、知识分子的生活感受和历史经验,忽略他们应对现实危机的那种激情和智慧,那也是令人忧虑的事情。
2010年11月,北京

